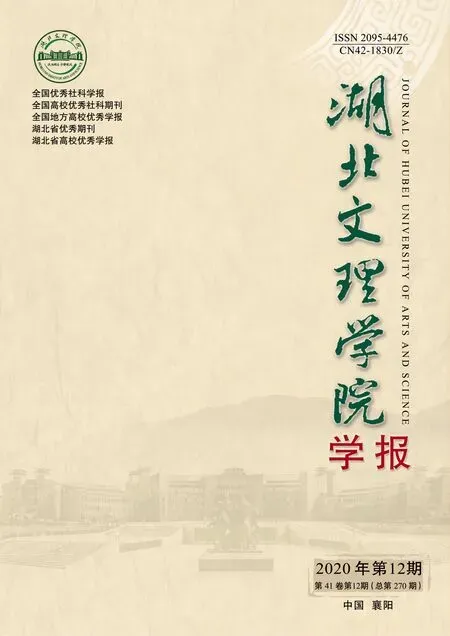跨学科领域绽放的一树繁花
——评楚林的“本草”散文
王海燕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按照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对于任何文本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读者既有的“前结构”与“期待视野”之上的,都会受到读者文化背景、思想观念、阅读兴趣等因素的影响。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1]。经典文本,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在与读者的视阈融合中生发的意义维度也更多元。《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先民们从祭祀、生产、战争到婚恋、渔猎、交际等活动的方方面面,堪称两千多年前先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如此博大丰饶的元经典,对于读者来说,呈现的自然也是见仁见智的多重面目。历史的兴衰更迭、男女的喜怒哀乐、活泼的草木虫鱼、优美的辞采乐章等要素随着读者的意识结构而各有侧重。对于出身中医世家、有着中医职业身份和职业眼光的楚林来说,《诗经》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一个草木摇曳、葳蕤生光的蓬勃世界。“读《诗经》就像走进了神农百草园,到处都是植物。采食以果腹,伐薪以生火,刈麻以成衣,煮草以为药,吟之以传情。古人用最原始的方法让植物的宽厚、仁慈、坚韧和爱,滴水穿石般地慢慢渗透进炎黄子孙的骨子里”(《灼艾贴——艾》)。[2]对于单一农业文明形态的先民来说,植物有着食用、衣用、器用、药用、祭祀、审美等多重价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诗经》植物所衍生出来的成语如桃之夭夭、敬恭桑梓、葑菲之采、投桃报李、采兰赠芍、摽梅之候、萱草忘忧、绵绵瓜瓞、甘心如荠等,足可见证《诗经》中的植物对中国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力。
以植物起兴,是《诗经》篇章结构的一大特点,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这些频频出场的桑麻黍稷,葛苇萧艾,兰芹藜棘,芣苢、卷耳等植物意象在普通读者的视野里不过承载着诗歌托物起兴的抒情功能,但它们对楚林展现出的却是双重功能:既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学符码,也是能够治病疗伤的神奇本草。神农尝百草而知药性,岐黄穷天地以定纲常,自上古时代起,先民们就在“天人合一”的认知框架中积累起了丰富的关于大自然和人本身的经验知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在汉代就有了属于它的特定称谓——本草。对于本草的认识也逐渐发展为中医药学这种专门的学问,从经验知识向现代编码知识靠拢,从而拉开了与大众的距离。难能可贵的是热爱写作的楚林跨越了文学与中医药学的现代鸿沟,以中医为背景,以本草为线索,以乡土记忆为宝库,融叙述、抒情、议论为一体,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表意世界。30篇散文以《诗经》中精挑细选的30种本草为线索,打捞起那些与本草有关的家族故事、伦理亲情、乡村记忆、成长历程,还有那些默默无闻却也用尽全力度过一生的芸芸众生。每一种本草唤起的都是满满的诗情与故事,让置身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读者借以重返到生机勃勃的自然宇宙之中,去细细感受自然的博大、土地的深厚、本草的普通与神奇,扩展着他们对大自然、对本草、对生命的认知与理解。
在乡间长大的孩子,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关于本草的记忆。笔者家中虽没有从医者,却也记得小时候母亲的不少单方:感冒了,就从菜园里拔来七根葱白,加上紫苏梗、生姜熬水;牙龈肿痛、嘴角起泡了,摘一把水竹叶,加石膏泡水;腮腺炎发作了用鱼腥草煮水;皮肤起了红疹子用艾草煎水。汤汤水水,疗效似乎也不错。具有浓厚经验特征的中医药学在乡村其实早已化作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经过楚林的点拨,才发现乡间随处可见的桃树、桑树、荷等本草,居然全身都是宝贝。“‘桃树治病五件宝,仁花叶胶与碧桃’。桃木辟邪,桃仁活血,桃花养颜,桃叶清热,桃胶通淋,仙桃补气,延年益寿。”(《嚷桃花——桃》)一钵桑椹治白发,一斤桑根治肺痨,一树桑叶赛人参,老外公会用一把桑柴火治“搭背”,神奇的是,树上还会不停地出现桑耳、桑寄生、桑螵蛸……这些奇奇怪怪的小生物。(《簸箕星下凡——桑》)荷一身九用:荷叶、荷梗、荷花、莲房、莲子、莲芯、莲须、莲藕、藕节,中药房的红木抽屉里,应有尽有。(《步步生莲——莲》)真正是“世间百草皆入药”!一种本草居然可以根据各部位的不同功能做成上十种中药,不得不让人惊叹中医药学对植物的认知所达到的无比精微的程度,虽然现代科学还没有完全认同其功效,但孰知这不是它超越科学的所在呢?
从野外自由摇曳生长的鲜活本草,到治病疗伤的成熟中药,程序之复杂颇像人作为个体从自然蒙昧状态蜕变、成长为社会文明组织一份子的过程,无不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与各种外力的考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酒炙黄连、醋喷香附、盐炒杜仲、姜汁厚朴、蜂蜜冬花、水飞朱砂……这是百草的另一种人生,磨棱去角,炼狱重生。”(《百草长春——远志》)生地熟地一字之差,却要经历九蒸九晒的炮制,“水蒸为阴,光晒为阳,阴阳和合,不断循环,历时月余”。如此,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阴阳互补、五行制化的大熔炉里相生相克,互相成就,其中的医理又何尝不是人生哲理!自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在懂得医理的基础上,于人生,楚林也表现出了更多的通达与更多的热爱。看她笔下和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一起做蜜丸、包香囊、做艾条的那些场面,何其繁冗琐细,又何其甜蜜温暖。“成千上万次的碾压,才能把药草变成细细的药面。压好的药面,嗅一下,全是沁鼻的香气,仿佛所有的精华都在纷纷溢出。树皮、草根、花朵、种子、阳光、雨露以及大自然的气息扑簌而来。”这岂止是作者用嗅觉对于本草气味的识别,这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相通!那些疗效非凡的苍耳膏、十子丸、五仁丸、苇茎汤、酸枣仁汤、蒺藜散、桑葚膏、木瓜酒、酸梅汤,每一种成品都是若干种本草经过复杂炮制程序之后融合在一起的甘甜,它们既来自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医者仁术、仁心、爱心、耐心的结晶。
“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作为一名中医人,如果说楚林让人艳羡的是她丰富的本草药理知识,那么令人敬重的则是她在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的悲悯情怀。只有热爱大地,热爱人们的人,才能清楚地看见人们和大地,也才能深刻地懂得人们和大地。与本草朝夕相处,看它们的来路去处,她懂得敬畏自然;为病人去疾祛邪,感他们的喜怒哀乐,她懂得敬畏生命。所以,在追溯自己的家族史时她更看重那一脉相承的“医者仁心”。从太爷爷、老外公,到父亲,到自己,虽然时代背景、阅历经验、身份性格各有不同,但他们都秉承着不矜名、不计利、挽回造化、立起沉疴的中医精神。深通医理、精通针灸绝活的太爷爷不仅把“大元药铺”做成了汉江边的标志性建筑,还把江边一条街的穷苦之人都教成了能用芦根、浮萍、竹叶、荇菜、通草等本草治病的先生。处事以仁义为本、行世有清澈之心的太爷爷,却无法从亘古未有的洪水灾难中拯救神仙眷侣般的妻子,他以悲剧告终的传奇人生留给人们的是关于人与自然未解之谜的追问。爱吹牛爱瞪眼的老外公是最具民间色彩的中医,他的治病绝活全在一棵桑树上,“春取桑枝,夏摘桑葚,秋打霜桑叶,冬炮桑根白皮”,相信桑是簸箕星下凡的老外公和很多农人一样保留着古老朴素的“万物有灵”哲学。出场最多、距离更近的是父亲,他是乡间的文化人,不仅精通从种药采药、炮制药材、到诊脉号病的每一个环节,也会写“厚朴待人,使君子长存远志;苁蓉处世,郁李仁敢不细辛”这样以本草明志的对联。尽管父亲话语不多,每一句却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深刻的人生哲理。他用和乡亲们同样粗糙的手为他们诊脉看病,“在月光下倾听每一个生命的声音”,感知他们身体上的寒热温凉,也读懂他们生命中的酸苦甘辛咸。所以,父亲不仅是家庭的柱石,孩子们的靠山,也是小学校长田秀才的知己,是倒卖膏药知错就改的“赵伯”的把兄弟,是乡亲们依赖信任的好中医。“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盯着父亲抓药。他不称重,他的手就是秤,是最准的戥子,是仙人的手掌。眨眼之间,一味味植物或动物药就在黄皮纸上排好了队,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只见父亲眯着眼睛朝空中轻轻地一招手,天瓦下悬挂着的素色棉线就应声而来。上下左右,绕过三两圈儿,一剂药就打包好了。掂一掂,鼓鼓囊囊,窸窸窣窣,像远行前的低语。我看呆了。”(《百草长春——远志》)这样娴熟、精准、利落的动作,非传统中医不可为也,也非懂医者不可摹也,它属于楚林中医世家的专利。
如果说家族中的男性传承的是中医之道的那一份担当、坚韧与阳刚,那么家族和家族以外的女性传递的则是一种更具普泛意义的悲悯、柔软与母性情怀,如此阴阳调和,才凝成了中医文化刚而不折、柔而不弱的中和之美。爱吃荇菜、名为水荷的太奶奶,寡居五十年亦和命运抗争五十年依然爱美爱嚷嚷的奶奶,“性子磨,耳根子软”,实为脾气好、心肠好,抚养了八个子女的母亲,这些饱含着深情的记录是楚林的散文中最柔软、最打动人心的部分。她们就像扎根大地深处的本草,默默地成就各自的死生,却不曾辜负一生的高贵与洁净。作为女性,作者更懂得女性身体和精神上的疼痛和不易:“一个女子从出生就注定要承受爱与不爱,承受月经、怀孕、生产、哺乳的痛苦,如一朵花儿,注定要经历发芽、打苞、绽放、结果和凋零。如果你曾温柔地注视过一株开花的益母草儿,就会理解一个女子生存的全部意义。”(《益母草》)因为懂得,所以悲悯。她用文字为一辈子不会说话的坡奶奶立传,为无儿无女却一生相互成全的瞎子舅爷和疤奶奶立传,她记得一生没有嫁人、会纺会织会染会绣的美人王阿婆,她记得走到生命尽头却迸足全部精神专心画荷的女病人,她记得坚持喝了三年益母草汤终于如愿怀上宝宝的乡下农妇……一股博大深沉的悲悯在字里行间流淌,也像清泉一样缓缓滋润着读者的心灵。以本草疗病,以文字疗心,读楚林的本草散文,读者获得的是身与心的双重疗愈。
中医讲究主辅佐使、四象平衡,深谙中医传统文化调和之道的楚林充分发挥了“散文”作为文体之母的优势,广采博收小说的叙述方法、诗歌的抒情表现艺术以及戏剧的场景再现艺术,在和合中生发出独具特色的话语方式与修辞特征。“古代的巫医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咒语诗歌,疗效的发生主要在于激发语言的法术力量;现代的文学治疗方式侧重于叙述性的故事,疗效来源于幻想的转移替代作用。”[3]叙述性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特别具有共情性质的关于童年、家园、乡土、成长的记忆,对于身心常处于分裂状态的现代人极具疗效。因为回忆性事件在散文中的比例较大,所以作者充分发挥了叙述在散文中的独特功能。“叙述在散文构成中的地位,是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结合议论、描写和说明的结构形态。”[4]本草的故事,与本草有关的人物故事,都离不开叙述。有的篇章直接就以本草为人物做传,如荇菜之于太爷爷太奶奶、酸枣仁之于母亲、桑之于老外公、竹之于坡奶奶、香蒲之于瞎子舅爷和疤奶奶、瓜蒌之于下放教授老胡、桑寄生之于白血病女孩……如果说以本草的特性象征传主的品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手法,那么能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按照主辅佐使配合得恰到好处,就是楚林的独门绝技了。
但是散文中的叙述不同于小说,小说的叙述语言偏重冷静与客观性,散文的叙述语言则具有浓厚的抒情倾向。而且,犹如细节之于小说的重要性,散文如果缺乏精致的描写作为构成单元,就不会有杰出的叙述表现。楚林的散文虽大多数依循时间性的组织,但她亦十分重视以空间性、共时性为特征的场景描写,且抒情色彩浓郁。如《嚷桃花》以“桃”为主线,巧妙撷取奶奶、父亲母亲、“我”三代人的生命轨迹中那些重要的片段:“我”的出嫁、父亲的春耕、奶奶的去世,以及桃花、桃子、桃树、桃仁各自的魅力,琳琅满目,美美与共,令人目不暇接。如此丰富的材料组织得有条不紊,魅力四射,精致的描写功不可没:新娘子的特写,春耕的特写,农人割麦吃桃的特写,无一不在唤醒着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感觉等多重感知系统。天空、大地、风,父亲、我、老水牛,不多的几个元素构成的那一幅带有原型意味的春耕图,强烈的空间即视感突破了物理时间的限制,似乎是从远古直指当下,刹那永恒!暮归时一幕印象式的描写更给人一种天地长存、岁月静好的诗意想象:“黄昏的阳光下,从山岗上依次走下来的是父亲、耕牛和我。辛苦和劳累让我们都低着头,像一幅剪影。精疲力竭的剪影。走到村口,我的眼神却突然亮了,疲惫一扫而光。桃花开了。屋后的那几株桃树,开出了满天粉色的花朵,单纯明媚的女儿红。一大团粉色的光,照在屋顶上,照着一屋子的温暖和喜悦。晚饭早已备好,母亲迎上来,父亲说:‘桃花开了。’母亲说:‘是啊。桃花开了。’”落日与桃花的光影辉映、山岗与大地的静默肃穆、家人明亮的眼神与熟悉的声音——这幅既恬淡又热烈、意境隽永的画面让所有读过的人无不沉浸在被幸福击中的甜蜜之中,这是从《诗经》、陶渊明、孟浩然一路而来的现代田园诗。凭借这些诗情洋溢的书写,楚林不仅跨越了医学与文学的学科限制、中医与作家的身份限制,实现了诗心与仁心的融合,而且也实现了本草散文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珠联璧合。
《诗》教的传统是温柔敦厚,是“思无邪”,得性情之正。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指出:“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是“中”。[5]这与中医的“中和”观念相一致,因为中国传统文学、医学都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长久濡染在中医文化中的楚林在写作中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其态度中庸平顺,其文字温雅亲切。尽管在《青蒿》《蓼》《蒺藜》等篇章中偶一露之的针砭之笔也颇锋利,但她主要做的是固本培元的功夫,存仁心、怀仁慈并扬仁术,发现美、创造美且分享美。在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不啻是一剂醒脑提神又补心补气的本草良方,为如何讲好中国的本草故事提供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