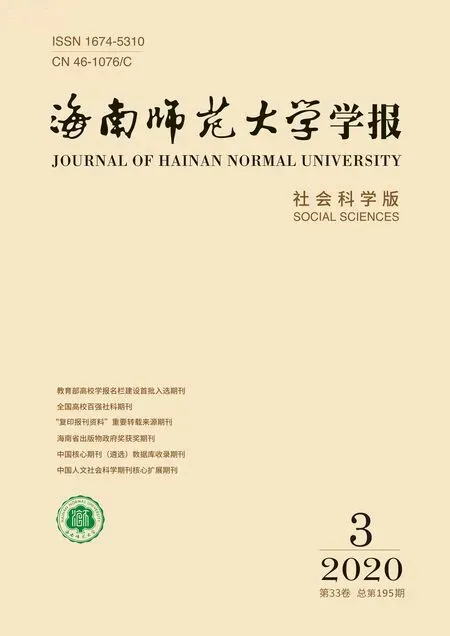家庭妇女解放的问题:从《新闺怨》到“十七年”电影
戎 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就与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休戚相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流是倡导妇女通过社会劳动获得解放,革命的实际工作对家庭妇女有很多研究和动员,对家庭妇女走向社会予以引导。但在民国时期的“进步电影”(1)根据电影史家李少白的概述:“‘进步电影’这一概念,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的四五十年代之交,是对三十年代(1931—1937)的左翼电影运动和四十年代(1945—1949)的进步电影运动中所产生的电影创作的一种概括,一个统称。这一概念,正如‘十七年电影’的概念一样,未必十分贴切,然而叫习惯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代替,于是也就约定俗称,沿而用之。”李少白《中国进步电影艺术的基本特征》,《影心探赜:电影历史及理论(增订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中,妇女解放固然是很重要的主题,家庭妇女却是不被关注的身份,“进步电影”的女主角多是已然“走出家庭”的城市女性,如城市中的小手工业者、小职员、妓女舞女、有志于社会改造和民族救亡的女学生,以及不被突出家庭妇女身份的农村劳动妇女。而有一些“小市民”女性虽然是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固定职业、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在经济上依靠丈夫的家庭妇女,但是电影并不凸显其家庭妇女身份和家庭妇女问题,而从性格上刻画其“小市民”的身份,展示其懦弱、保守的“小市民”性格,或者进一步发掘她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改造的可能,电影《丽人行》中的梁若英、《万家灯火》中的又兰就是这类“小市民”女性的代表。直到1948年史东山编导的《新闺怨》,深度聚焦家庭妇女问题,借此表达社会革命过渡时期家庭妇女的解放之道。但电影在1948年就引发进步文化界的不同声音,乃至受到批判。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新闺怨》再次受到批判。
在“十七年”期间,妇女解放被更加紧密而统一地纳入到社会革命之中。新中国初期的电影界依然不够重视家庭妇女问题,直到“大跃进”时期,为配合鼓励家庭妇女就业的政策,涌现了一批家庭妇女解放题材的电影。这批电影讲述“大跃进”时期家庭妇女积极参加社会劳动获得妇女解放,其家庭妇女解放叙事呈现出新面貌。然而将这种电影叙事放在大文学史中,对照现实中社会革命与家庭妇女解放的复杂状况,以及同时期电影之外的文学作品对此问题的表现,可以引发很多深思。
一、从史东山的《新闺怨》谈起
按照史东山在1948年《新闺怨》受到批评后解释拍摄动机的说法,这部电影剧本是他在昆仑影业公司的另外两个剧本《天官赐福》《希望在人间》,因思想内容和创作态度问题没有通过当时民国政府的电影审查而搁置的情况下,匆忙之际随手拿起他最熟悉的妇女题材又预计能顺利通过审查而写的。(2)史东山:《〈新闺怨〉的产生》,《剧影春秋》1948年第1期。这样的说法很可能淡化了史东山拍摄《新闺怨》的深厚蓄意。“进步电影”对付电影审查体制向来有许多办法,剧本没通过初审很正常,可以再改,或者索性打通审查官员,如《八千里路云和月》就是昆仑董事夏云瑚通过跟审查官员打牌输钱通过的,(3)夏瑞春:《夏云瑚与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的不了缘》,田本相,董健:《中国话剧研究》第12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总之有周旋的余地,要继续拍摄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史东山1947年起意拍摄《新闺怨》应该不是仓促的决定。他为编导这部社会问题剧搜集了关于家庭纠纷的丰富资料,其中包括1946年上海警察局对十个月来自杀事件的调查,调查显示800多宗自杀事件中,家庭纠纷占据最大比重,多达300多宗。(4)南:《〈新闺怨〉主题之珍贵资料:家庭纠纷自杀数字惊人》,《昆仑影讯》1948年第10期。而更深的动机还在于他一直都非常关心妇女解放,对家庭妇女问题特别敏感,此前编导的电影《女人》(1934)、《长恨歌》(1936)和抗战时期参与编剧并执导的话剧《重庆屋檐下》都包含着家庭妇女问题,《新闺怨》应是史东山有感于共产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时局下,着眼长远的未来,思考家庭妇女解放之道而作。然而,影片展示的家庭妇女困境和暗示的家庭妇女解放之道,恰与当时共产革命对群众包括家庭妇女的动员龃龉。
《新闺怨》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5—1948年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廖韵芝和何绿音自由恋爱结婚,何绿音婚后做了家庭妇女,与从事音乐事业的丈夫感情日渐疏远,可她心有不甘,嫌弃家庭妇女的身份,一心想出去找工作,最后找了一个从事不正当商业竞争的公司做文员的工作,把孩子交给没有经验和责任心的保姆照看,致使孩子染病身亡,再加上目睹丈夫与女同事的亲密举止,绿音受到双重打击,最后自杀身亡。史东山借电影传达其“妇女应该有条件有原则的跑出家庭去做事”的观念,绿音成为反面例子,绿音的大姐紫来对绿音的劝告:“如果去从事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有益的工作,叫家庭牺牲一下也值得,反之则不值得”,则代表史东山的声音。电影上映后受到“妇女界”有组织的批判。上海《现代妇女》组织的“妇女界《新闺怨》座谈”和《现代妇女》随后刊登的一系列评论文章普遍认为:一、影片没有强调经济问题,社会现实是很多家庭因经济拮据逼迫着女人非出去工作共同维家庭生活不可,而现实社会又给这些妇女就业以限制;二、经济独立对于妇女解放意义重大;三、妇女应该走出家庭,致力于社会改革。(5)史良等:《妇女界〈新闺怨〉座谈》,《现代妇女》1948年第6期。经济独立是晚清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妇运人士普遍认为妇女解放固然并非完全取决于经济独立与否,但经济独立确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同时,鼓励妇女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也与政治上的革命形势密不可分。国民党在北伐时期也倡导妇女走出家庭,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保障男性劳动力而裁减女性劳动力,出现“妇女回归家庭”的口号,这股风潮也对中国产生影响。民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展开的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也主张妇女以家庭为重,倡导新的贤妻良母。中国共产党则大力主张妇女从事社会劳动,这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和现实革命的需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证了私有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私有制使家务劳动成为私人的事务,女性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男性从事社会劳动并合法化地享有财产支配权,从而奠定了男性高于女性的地位。妇女解放的途径是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和公共事业,直到达到消除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妇女才能得到根本解放。(6)[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198页。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坚决和“妇女回归家庭”的舆论做斗争。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重点在于发动妇女参加生产。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统区,妇女运动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以配合军事斗争。“第二条战线”特别强调以“经济问题”来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统治。(7)周恩来在给党内的指示中强调,“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表扬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等人“引导群众转入经济斗争甚妥。”参见《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李勇,张仲田编:《统一战线大事记 解放战争卷》,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组织批评《新闺怨》的《现代妇女》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统战刊物(8)《现代妇女》杂志1943年在邓颖超的倡议下在重庆创刊,1946年迁至上海出版,主编是妇女运动领袖、妇女共产党员曹孟君,1948年秋赴解放区后交给共产党员胡锈枫主持,1949年3月杂志被民国政府查封。,抗战胜利后,《现代妇女》的编委几乎都是中共南方局支持领导下的中国妇女联谊会理事或成员,参加“妇女界《新闺怨》座谈会”的也几乎都是中国妇女联谊会成员,她们中许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员或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领导人(9)参加妇女界《新闺怨》座谈会的有丁慧涵、王静君、史良、左诵芬、朱立波、林君慧、宋元、胡兰溪、胡锈枫、胡子婴、徐镜平、徐学海、许广平、陈善祥、陈玉俊、曹孟君、高静宜、陆慧年、戚逸影、莘薤、彭慧、杨志诚、叶晚崑、刘海倪、卢琼英、钟复光、严玉华。参见《妇女界〈新闺怨〉座谈会》,《现代妇女》1948年第6期。史良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和民盟中央委员;曹孟君也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共产党员、民盟常委;许广平是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和常务理事;胡子婴是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和理事;胡锈枫和她丈夫李剑农、姐姐关露都是共产党“隐蔽战线”工作者。,她们所从事的妇女运动直接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的群众运动挂钩。《新闺怨》受到她们批判恰在于,电影在国统区动员群众方面没有突出经济因素。本来,突出阶级分析和经济因素是“进步电影”应具备的,史东山战后编导的另一部著名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就展示了一边是抗战演剧队员在抗战中出生入死,复员后却连基本的生计都难保障;另一边是贪官污吏大发国难财,战后搞“劫收”。《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后广受欢迎,社会影响巨大。但《新闺怨》却没有突出这两个因素,这并非完全出于通过电影审查的考虑,这部不合时宜的电影其实寄托着史东山对妇女解放和社会革命的深思。
1948年10月,史东山发表长文回应《新闺怨》受到的批评,重点解释了为何没有突出“经济因素”,表达他对社会革命“过渡时期”妇女解放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按照一些批评意见,写妇女的痛苦和强调当今社会经济混乱的影响,那么妇女问题的主题就会滑掉,或被冲淡或中途转移,“在现制度之下,无论社会经济情况好或坏,妇女问题都一样存在,所以我以为不必那么写。”他又援引苏联斯维托洛夫《新家庭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参加国家生活仍要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的观点,进一步表态:“我在《新闺怨》里写的是这社会革命底‘过渡时期’和‘过渡地段’的‘妇女问题’啊!在这过渡时期的过渡地段中,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得不顾到许多实际问题而有条件有原则的来处理的啊!”“‘妇女跑出家庭’是一句革命的口号。凡是革命一定要为革命的目的或手段喊出许多口号,但革命一定也有过程,口号亦不过是一个原则或提纲,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一成不变的机械地执行的,今天,在此时此地,我们要叫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妇女不顾一切地统统跑出家庭去是不可能亦不妥的事。”(10)史东山:《一个电影工作者的道谢与自白》,《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27日。史东山所谓 “过渡时期”和“现制度”其实并不仅就当时内战的进程和日渐颓圮的民国体制而言,他思考得更为长远,“壮有所用,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应该指向非常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时期,妇女解放之路该怎么走?他所主张社会过渡时期的妇女解放之道,暗含的正是“家庭”与“革命”的平衡法,警惕激进化的“走出家庭”可能损害家庭,反过来也可能损害革命。史东山此前的影剧作品《女人》《长恨歌》《重庆屋檐下》都有一种极端化的情节设置:家庭妇女受到“娜拉出走”的感召,嫌恶自身的家庭妇女身份,盲目出去找个工作,导致小孩因照看不周染病或致死。《新闺怨》和史东山对《新闺怨》的阐释,则更加清晰地显示他对妇女解放的看法确实与左翼文化阵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动员倡导的“走出家庭”有所龃龉。然而,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后持续推进的妇女解放历史和相关文艺作品的表现,再来反顾《新闺怨》探讨的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关系问题,可以见出史东山的隐忧意义深远。
1952年在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中,就《新闺怨》问题,史东山不再像1948年那样做辩解,而是做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承认剧本基本等于在宣传“妇女应该回到家庭”的资产阶级观点,这是“个人创作史上最大的污点、心中最深的创痛”。(11)史东山:《认真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133页。史东山此后再也没有创作这类妇女题材的社会问题剧。然而,现实是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取得进展的同时,家庭妇女问题也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倡导妇女从事社会劳动和国家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有限性之间构成矛盾,这致使许多渴望从事社会劳动的家庭妇女心理受挫。晚清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大力倡导妇女就业,加上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这方面宣传更加强化,家庭妇女就业诉求越来越大。1951年,一部讲述中国共产党解放妓女的电影《姊姊妹妹站起来》上映后,就有观众特别关心被解放的妇女今后的工作问题,向《大众电影》提出疑问说“对新时代的光明表现的很少。只是几个人被分配到张家口工作(大部分未分配工作)”。编导陈西禾解释,原来剧本的结局里有过交代,可惜后来嫌啰嗦删去了。原剧本让暂时没有被分配到工作的银花起来讲话,表示应该向已分配工作的姐妹学习,“咱们没有去的人也不能落后,早下工厂,努力生产,处处向他们看齐……(大家热烈鼓掌)。”(12)陈西禾等:《关于〈姊姊妹妹站起来〉影片中的几个问题》,《大众电影》1952年第7期。这样的解释意在抚慰现实中大量渴望参加工作而不得的家庭妇女。这其实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工作的一项内容,一边肯定家庭妇女就业的诉求,另一边劝导她们不能操之过急,耐心等待时机,并在理论上开始提出社会主义家庭妇女的价值,化解她们的困惑和不自信,在肯定家庭妇女努力参加社会劳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之外,也对家务劳动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予以肯定,批驳以个人经济独立与否来判定妇女解放与否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观念”。(13)1955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领导下的《新中国妇女》杂志(1956年改为《中国妇女》)发起“社会主义家庭妇女”的讨论,旨在树立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家庭妇女”观念和典型形象。讨论批驳以个人经济独立与否来判定妇女解放与否的“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观念”,阐明我国的家庭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是保证全家人积极参加社会劳动的必要条件;是培养新生一代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因此对建设社会主义有积极作用。”“只要家庭妇女确实有益的家务劳动,那么在她的家人的工薪中,就有她的劳动成果,而且她享有宪法上所给的各项权利。” 参见本社:《家庭妇女应该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原载《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0号),《新型的家庭妇女》,北京:中国妇女杂志社,1956年,第53-60页。同时,主流媒体宣传介绍苏联家庭妇女满怀自信从事家务劳动的状况。不过“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肯定声音比之社会劳动价值的高扬仍然是微弱的,这种肯定的声音出现在1955年左右,很大程度上意在抚慰暂时未能参加社会劳动的家庭妇女,等到“大跃进”急需大力发掘妇女劳动力,这种声音就被淹没;与此同时,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家务劳动价值认同的问题变得更为严峻,家庭妇女解放之路颇为曲折。然而,“十七年”文艺作品,尤其是“十七年”电影对此不够直面现实。
二、家庭妇女解放叙事的单一化
随着新中国各项法律法规的颁布,妇女开始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婚恋自由权利、受教育权利,两性平等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新中国电影有不少妇女解放题材,这些电影多讲述妇女取得婚恋自由,并成为建设国家的劳动能手,甚至挑战传统看来男性化的职业,比如操作重型机车,不过还没有出现专门聚焦家庭妇女题材的电影。1953年《大众电影》编辑部和北京妇女界座谈,妇女界领导和妇女代表都提出电影界对家庭妇女的宣传介绍工作做得很不够。(14)《要求在电影里看到中国妇女的明天——北京市妇女界座谈对人民电影事业的希望》,《大众电影》1953年第4期。可是妇女界的呼唤没有得到电影界的积极回应,直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启。从1958年末到1961年,人民公社运动相继在农村和城市广泛展开,人民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基层单位,更加高度实现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集体调度,公共食堂、托儿所、街道里弄生产小组、缝纫组、各种各样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服务站大量兴办起来。“彻底解放妇女”成为口号,家庭妇女被大规模动员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妇女就业急剧增长。全民所有制单位女职工由1957年的328.6万,增长到1960年的1,008.7万,(15)陈雁:《“大跃进”与195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职业发展——以上海宝兴里为中心的研究》,《1950年代的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此外还有遍地开花的街道办工业。到1959年,“据北京、天津、沈阳等43个大中城市统计,共创办了44,000多个民办工业单位,参加街办工业的共约140万人,其中妇女占绝大多数。”(16)章蕴:《进一步办好街道集体生活福利和服务事业,全面组织人民生活,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大跃进而奋斗: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1960年3月12日在全国职工生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国妇女》1960年第7期。1958—1962年,文艺界涌现了一批专门讲述家庭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的作品,其中电影有《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春催桃李》(1961) 《女理发师》(1962)《李双双》(1962)。
《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催桃李》《女理发师》《李双双》这四部电影对家庭妇女的解放叙事呈现出共性,即讲述追求进步的家庭妇女终于冲破家人和社会上对妇女就业的偏见,顺利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劳动。这些偏见认为妇女就该守在家庭相夫教子、妇女不能胜任社会劳动的工作。《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王彩凤参加里弄生产小组遭到婆婆刘大妈的反对,刘大妈在解放前吃尽苦头,解放后儿子进工厂当工人,她在家照看两个孙子,她对现状非常知足,要儿媳好好守住这个家,不同意儿媳参加里弄生产小组,在她的观念里,女人出门去工作就守不住这个家了。与刘大妈一样男权思想深重的还有蔡桂贞的丈夫郑宝卿,他平时依赖妻子,妻子像仆人一样伺候他,他坚决反对妻子参加里弄生产小组,还把偷偷去参加劳动的妻子关在门外,不让回家。当然,最后他们都受到教育,转变了思想。王彩凤、蔡桂珍不仅克服了家人的阻挠,也通过向老工人学习技术克服了生产玩具的技术难题,证明了家庭妇女也有能力做好生产工作。《李双双》中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女理发师》中华家芳的丈夫贾主任、《春催桃李》中的唐主任都是男权思想严重,阻挠家庭妇女就业,或不相信她们能够胜任工作,最终都被妇女的实际能力击败。
细看来,《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催桃李》《女理发师》《李双双》讲述家庭妇女解放过程中的困难都不涉及家务与工作这个妇女解放运动以来现实中始终存在的矛盾关系,这其实也是“十七年”电影中向来缺少表现的。“十七年”电影只有极少数侧面触及家务与工作的紧张关系,如儿童电影《哥哥和妹妹》(1956)讲述一对小学生兄妹的成长问题,启示父母应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不应因工作疏忽对孩子的教养。电影结尾处,妈妈暂时放下工作,陪孩子和婆婆一起欢乐地畅游动物园。1956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影片,应该与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的价值有关,也与“双百”方针时期对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味”一定程度的肯定有关。同样是儿童电影,到了1958年的《兰兰和东东》所折射的工作和家庭的逻辑就变了。兰兰和东东是一对还在上幼儿园的姐弟,他们的父母在北京工作,他们在上海上幼儿园,身边没有亲人照顾。电影讲述在北京工作的父母要把两个孩子接到北京团聚,但因为工作忙离不开,幼儿园老师便委托铁路乘务人员帮忙把俩孩子护送到北京,乘务人员尽心尽责,最后顺利把孩子送到北京,与父母团聚。电影传达出,在这个社会里忙于工作的双职工父母不用过于担心孩子,教育行业、服务行业人士都会尽到关爱孩子的职责,家务和工作的紧张关系是不存在的。《哥哥和妹妹》所表达的家庭与工作关系的理念也同样存在于“大跃进”时期其他关于家庭妇女解放题材的电影中。“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重在树立为民族国家的公家人,当个人小家与公家出现紧张关系时,前者服从后者不言而喻,“十七年”文艺并不缺少讲述个人感情、利益最终服从革命事业的故事,可是在讲述家庭妇女解放的故事中,却连凸显繁重的家务被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机构(如公共食堂、托儿所等)代替以后,家庭妇女顺利走向工作岗位的叙事也没有出现过——家务事对妇女羁绊的现象始终就没有正面出现。老舍的眼光非常敏锐,在《万紫千红总是春》座谈会上,他指出电影对婆媳之间、夫妇之间的矛盾讲得很清楚,可是“父母与儿童之间的矛盾还没写足。有的孩子在学校里很听话,爱劳动,讲卫生,可是回到家来便变了样子。如果影片能够把小华写得年岁再小一些,作为这类儿童的典型,便又可以解决另一矛盾,并且可以教育少年儿童。是的,事实上的确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少年帮助父母做些事,使家庭生活更为美满”。(17)老舍:《要言不烦、有戏可做》,《电影艺术》1960年第5期。老舍实际上在委婉地指出,电影简化了现实中父母尤其是家庭妇女养育幼年孩子需要耗费的极大精力,没有真实地处理家务与工作的矛盾关系,老舍评价这个题材本身“有戏可做”,却没有把戏做够。的确如此,电影即便设置了王彩凤有一对三四岁的儿子,也没有凸显她需要在育儿上耗费精力,她的婆婆刘大妈顽固地将孙子留在家里自己带,不放心送托儿所。电影叙事中的家庭妇女解放的唯一阻碍是男权思想,并将之等同于“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观念。刘大妈只顾自己的小家,认为女人就该守在自己家里。郑宝卿的自私形象更加夸张,自己不在家时都不许媳妇吃鱼。《女理发师》中的贾主任面对外人时对家庭妇女就业表示支持和赞赏,实际口是心非,根本不能接受妻子去做街道理发店的理发师,他的男权思想还加上严重的等级观念,轻视理发行业是“伺候人”的行业。《李双双》中的孙喜旺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他面对公家事上的乡愿、糊涂、不愿得罪人都是自私自利人格的体现。这些电影对推进社会两性平等有一定作用,但对家庭妇女解放过程中的难题过于单一化,遮蔽了现实中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限度和妇女就业的紧张关系,而且在根本上未触及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同问题。电影配合政治形势的一时需要高调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就业,等到“大跃进”停止,需要大量清退妇女劳动力使之重回归家庭时,反而更加剧妇女的精神苦闷和妇女工作的困难。
三、对家庭妇女问题的弱化
“十七年”电影对家庭妇女问题的弱化从根本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关。新中国需要大力发掘妇女劳动力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国家的政治教育和主流媒体宣传都旨在塑造从事社会劳动的妇女形象,对家庭领域和家庭妇女缺少关注,(18)有学者选取1949—1966年《人民日报》《中国妇女》《人民画报》为样本,考察“十七年”主流媒体所建构的家庭和家庭妇女形象,其统计数据颇能说明问题:对于《中国妇女》《人民画报》封面女性出场场域的统计显示,《中国妇女》94帧女性封面中,家居环境、工作环境、公共场所、其它分别占1%、70%、12%、17%,《人民画报》46帧女性封面中,这些场域分别占7%、57%、17%、17%。对《人民日报》国内妇女人物报道的职业统计,93篇报道中,家庭妇女、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分别占13%、22%、39%、12%、7%。韩敏:《新中国对家庭和家庭妇女的媒介建构研究》,《理论月刊》2016年第12期。一度肯定“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和家务劳动价值的声音仍然很微弱。人民公社运动时期尽管开办了大量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服务站,但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和实际展开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家务劳动与工作的难题未能有所减轻,而且这些服务站并不都免费,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据上海市的情况,家庭妇女的劳动报酬远不如正式职工,基本是他们的1/2 、1/3 ,甚至更少(19)张牛美:《走出家门:上海妇女从业研究(1958—1962)》,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15-116页。,“有的妇女将外出劳动所得的报酬悉数给孩子交了托儿所费用,有的家庭孩子较多,母亲外出劳动所得的报酬还不够支付托儿所费用”。(20)汤奈尔:《“解放”的困境:—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妇女和国家建设》,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9页。在精神层面上,在国家强势建构和宣传社会劳动妇女的光辉形象下,家庭妇女普遍自我认同感低,怀疑自己学习进步的能力,担心被“进步”的丈夫抛弃。“大跃进”之后的退工潮中,大量被动员到工作岗位上的妇女被清退,又面临返回家务劳动的局面。仅全民所有制单位女职工就从1960年的1,008.7万,降到1962年的673.8万。(21)陈雁:《“大跃进”与195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职业发展——以上海宝兴里为中心的研究》,《1950年代的中国》,第263页。妇女工作的档案材料显示,妇女对短时间内形势的急剧变化缺少心理准备,充满困惑和怨言。(22)详见《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里弄工作办公室关于富华染织厂与民申翻砂厂辞退里弄妇女的情况汇报》,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A20-2-32-74。转引自汤奈尔:《“解放”的困境: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妇女和国家建设》,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2页。一方面家务劳动价值未被充分认同,另一方面家庭妇女渴望参加工作而不得,这更加剧了她们的苦闷和不自信。
“十七年”文学也对家庭妇女问题予以弱化。总的来说,正面、侧面的表现都非常少,家务与工作的紧张关系几乎很少出现,不过仍有极少数作品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这一问题和家庭妇女的精神状况问题。陈桂珍的讽刺剧《家务事》(1956)就是反映家庭妇女解放问题的代表作。陈桂珍原先就是家庭妇女,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了哈尔滨铁路工作管理局的干部和工人俱乐部的图书管理员,并从事一些妇女工作。工作中,她发现男性干部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热情,但对家务事充满偏见。《家务事》讽刺了一位担任工会主席的男性干部对家务事不关心也看不起,爱嚷嚷“你看我们到处都喊建设社会主义,谁听说建设家庭事?”“妇女的事,老娘们的事”。他的妻子,一位家庭妇女,一边反抗丈夫的轻视,一边缺少自信,时时疑心丈夫有外遇。陈桂珍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男性干部对家务事和革命工作关系的认识不当,而非一般群众或知识分子男性的“男权思想”甚或“个人主义”,可见批判的深度。这部剧作发表以后反响两极化,许多观众认为写得好,“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也有少数工会干部认为“这是污蔑工人家属”。(23)陈桂珍:《谈谈我是怎样创作讽刺剧〈家务事〉的》,《剧本》1956年第5期。田汉编的《1949—1959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戏剧卷》特意收入这部剧作,认为它“生动地处理了工人阶级应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家庭,家属工作应该为工人生产劳动服务的主题”。(24)田汉:《1949—1959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戏剧卷序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第3页。这部剧作的出现也与当时一定程度肯定“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和“双百”方针下的文学氛围有关系。1960年陈桂珍创作的表现家庭妇女参加城市人民公社的电影剧本《社员之家》,展现的矛盾就不再是家务与工作的矛盾,而是先进的妇女工作者在带动家庭妇女参加城市人民公社中遇到懒惰自私的落后妇女的情况。这部剧本后来被改拍成电影《大家庭的主妇》(1960),不过电影没有公映。类似的例子还有著名女作家茹志鹃的家庭妇女题材小说和电影剧本对家庭妇女解放问题的不同表现。茹志鹃在“大跃进”期间也写了反映家庭妇女参加城市人民公社工作的系列小说,其中《如愿》《春暖时节》还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作。有学者指出,茹志鹃的这些小说在外在叙述动机和内在情感性叙述中存在“缝隙”, 即从茹志鹃创作的目的来说,是要表现妇女经由“社会化劳动”获得“人格独立”“性别主体”的主题的,但在情感的日常性结构上,事实上又构成了对社会化主题的某种抵制。《如愿》中家庭妇女何大妈过分热衷成为“国家的人”,乃至表现出滑稽感,她的“翻身感”并不仅仅在于劳动,还必须是“公共性劳动”,更重要的是还要具有“进工厂、吃食堂”的形式外观。《春暖时节》中静兰伤感于丈夫对自己感情变淡,回想起新中国成立以前,夫妻俩一起从事钓虾贩卖这样“私人性劳动”时感情非常好的时光,静兰后来参加里弄生产福利合作社的心理是“她觉得大家都参加,她也就应该参加”,在工作上“她觉得跟在家里做那些家务一样,并没有特别出劲”。(25)张鸿声:《“城市人民公社”与文学中的“女性独立”主题——以茹志鹃“大跃进”时代小说为例》,《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当然,小说最后,静兰在投身零件生产工作中责任心被唤起,而丈夫端详着工作中的妻子,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妻子。小说的这种“缝隙”折射出现实中有家庭妇女既对其自身身份不自信,也对社会劳动热情不高,还有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动机不纯。但是在茹志鹃参与编剧的电影《春催桃李》中,类似的“缝隙”就消失了,电影只表现家庭妇女出身的顾三娟在创办民办小学中遇到群众不信任、学生不好教的难题,然而都被她毫无悬念地克服了。家庭妇女解放题材的电影和文学的“差距”可见一斑,大概电影比文学更需要直接面向群众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因而对现实中家庭妇女解放问题的表现更为狭窄和弱化一些。
像《春暖花开》所展示的家庭妇女通过参加社会劳动来确立自信和挽回爱情,虽然很难看出茹志鹃叙事背后的姿态,却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从战乱到和平,人民的聚散离合、政权的新旧更替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爆发离婚潮,尤其城市的家庭妇女和进城的农村妇女面对丈夫是先进的工人阶级或干部,更有婚姻危机感。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的《新型的家庭妇女》中收录的一篇纪实报道《“他还能爱我吗?”》,反映了许多家庭妇女的精神状况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她们的引导。女作者的丈夫是鞍山钢铁厂干部,当丈夫把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的好消息告诉妻子时,妻子百感交集,既高兴又担心丈夫会越来越看不上她这个“土包子”;妻子农村出身,原先不识字,解放后随丈夫进城做了家庭妇女,这时她丈夫周围很多男性干部都在与乡下妻子离婚,也有人劝她丈夫离婚找个女干部;然而,后来妻子在丈夫的引导下追求进步,参加识字班,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加入职工家属居委会,参加社会活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我认同感获得大幅度提升,和丈夫的感情也亲密了。(26)徐芳:《“他还能爱我吗?”》(原载《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8号),《新型的家庭妇女》,第39-47页。主流意识形态旨在通过引导家庭妇女从事社会劳动来成为“国家的人”,并赢得思想先进的丈夫的爱情。
宣传家庭妇女通过参加社会劳动来成为“国家的人”并获得家庭幸福,和“十七年”电影宣传家庭妇女战胜男权思想对女性就业的阻碍正好是一种逻辑、一体两面,都没有真正认同家务劳动价值和女性价值。这是出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掘妇女劳动力的现实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后来世界上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已经涉及到家务劳动是否存在“异化”现象,也论证了家务劳动是不止于使用价值的生产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就业市场、法律法规、福利事业等领域中的两性平等。中国的妇女解放维系于民族国家的命运,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前进。如今在大力鼓励创新创业,深化推进职场上两性平等的同时,也应该推动家务劳动价值和家庭妇女身份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尊重。家务劳动的价值应不只局限于《婚姻法》规定的离婚补偿照顾中,而应该更加深入人心。如今的家庭妇女形形色色,她们有的因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负担保姆照看家庭的费用而退守家庭,她们不能再过多地承受社会对家务劳动价值的不公的压力,有的则是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都很优越而自信的女性,出于自身对家庭及育儿的理念主动选择成为家庭妇女,她们对社会和谐与下一代成长的意义都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