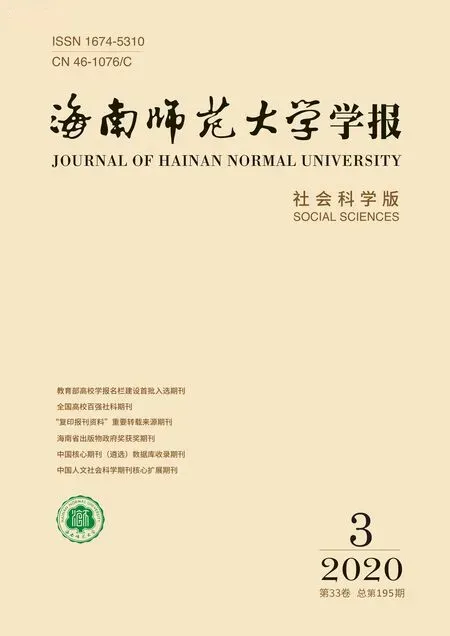红十字运动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郭进萍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江苏 苏州 215131;苏州大学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江苏 苏州 215325)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的时代思潮,由其衍生出来的“民族国家”(1)迄今为止,学界对民族国家一词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界定为由一个或多个民族基于共同的国家认同而建立的主权国家。参见于春洋:《外观与内核: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话语体系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题中之义。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所包含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具有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国民中间建构出统一的民族性,即在国家疆域之内的所有居民中培育出一种不惜为之抛洒热血、牺牲生命的忠诚情感,创造全体国民对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2)王建娥:《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内涵、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在此过程中,红十字运动以其独特的价值强化了国人民族心理和现代意识的塑造,培育了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从而推进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一、红十字会:作为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表征
(一)民族主义视域下的红十字会
清末,伴随西学的大规模输入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据学者考察,1895年后,“国家”和“民族”一词的使用次数激增。到1903年,“民族”和“国家”的出现次数相差无几,“意味着当时视物竞天择为公理的普遍观念对国家主权的肯定,这导致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中被动地产生的”,确切地说,“是现代性的产物”。(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在晚清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浪潮中,西方种族、民族等新知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族类意识产生化合反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催化作用下,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汲取中西文化交融的思想资源,通过使用“民族”“种族”“国民”“主权”和“民族主义”等新概念,最终确立了“现代民族观念和思想意识”。(5)黄兴涛:《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
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大行其道且愈演愈烈,这从《申报》上“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即可窥其一斑。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民族”一词在《申报》上的使用频率一路高涨,1911年243条,1925年502条,1936年1,507条,1939年则达到2,369条。(6)黄道炫:《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民族主义如燎原烈火一般燃遍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驱策无数国人为之努力和奋进。民族主义的威力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得到彰显,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轫和壮大即是民族主义驱动下的一个衍生品。
红十字运动无分国界,超越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提倡救护不分畛域,一视同仁,被时人视为衡量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戊戌时期,受甲午战争惨败和洋务运动破产的刺激,国人潜心反思,逐渐将目光放到西方的制度层面。这一时期,受甲午战争期间传教士创办红十字医院和日本赤十字社战地救护实践的刺激,国人要求仿行西法,创设红十字会的呼声不断高涨。1898—1899年间,以《申报》为代表的各类报刊多次刊文呼吁中国创立红十字会,参与国际竞争,壮大民族国家。
在有识之士看来,红十字会“为最文明之举动,亦为最紧要之事体”,“凡地球上之文明国无不入会者”,中国若不“附入此会”,“是自摈于文明国之外”。(7)《演说红十字会敬告全国》,《北京杂志》1904年第2期,第20-21页。可以说,19、20世纪为“文明”的世纪,“西方各国满怀信心地把他们到达的水准称作‘文明’,并将其当作认识世界的普遍尺度”。(8)[日]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页。中国欲通往近代世界,也必须了解和汇入这一“文明”体系。如果中国不创办红十字会与世界联盟,那么不仅无法跻身现代文明国家之列,反而会沦落到野蛮、落后国家之列,这不但为国民“之耻”“之危”,也是国家“之耻”“之危”。(9)王熙普:《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申报》1907年7月3日第20版。
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正是基于这样的动机:希冀向国际社会靠拢,进入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合作场域。(10)郭进萍:《〈申报〉与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起步》,《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这样的理念贯穿近代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始终。直至1937年,时人虔修道人在回答“何以各国的会员这样踊跃?”的问题时,依旧持此看法,称:“因为各国国家的文明和野蛮都以红十字会会员的多少为标准。简单说,国人对于慈善公益的观念愈深切,就是人类互助的优良表现绝少自私的劣根性。国人的优良表现愈多,国家愈强盛。我们要站在最高的国际地位,须大家来提倡红十字会的事业,希望全国同胞快快请来加入。”(11)虔修道人:《红十字会问答概要》,沈金涛校,《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年第19期,第9页。
(二)作为现代性表征的红十字会
除了民族主义,红十字会还是现代性的表征。在文化理念上,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为宗旨,尊重人道,救护赈济不分畛域,提倡责任和服务意识,与传统慈善理念截然不同。
尽管“人道名词,我国产生最早,义经四子等书,见诸记载”,但“排斥异己,黜落百家。其所见者小而人道卒未发明”(12)朱瑞五:《人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杂志》1914年第2号,第2页。。究其原因,这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深蒂固脱不开干系。托克维尔曾生动刻画了专制制度对人道主义的阻遏: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4-35页。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性的务实、功利、缺乏同情心及公德意识等也阻滞了人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人道的论说,但现实情境依然是“中国人民的性命就像是草中野鸡一样,就像是山野猕猴一样贫贱,即使是一天死几千几万人,又有谁知道呢?又有谁怜惜呢?”(14)梁启超:《新民说》,张健注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众所周知,红十字会的创建源于对战场伤病兵、俘虏的救护,而中国向无救护战俘的先例,反而以坑杀战俘为常。直至1874年,《字林西报》《申报》还撰文称“亚细亚诸国之从事于战阵也,以戮杀俘囚为常”。(15)《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申报》1874年9月7日第1版。因为向无救护战俘的先例,也就无所谓战争救护时持中立原则了。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红十字运动为中国输入了现代人道理念,并推进了中国战争救护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红十字会还拓宽了社会救助的视域,从国内延展到国外。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积极参与国际会议、开展国际交流和救助海外华人及恤邻活动即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
1905年,因海参威城中的华人遭俄军滋扰,“华民买卖街所有庐舍悉付一炬,受伤八百人”,尽管不知这800人“是否尽属华民抑连西人在内”(16)《十月十九日红十字会沈任施三观察致海参威商务局委员李兰舟》,《申报》1905年12月10日第10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仍积极派人前往救济。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地震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捐助银2万两汇寄灾区,从事抚恤(17)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1924年,第2页。;1914年救济日本鹿儿岛地震灾害,捐助2,000元(18)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12页。;1923年救济日本关东大地震,共用款17,217.64元(19)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编:《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第50页。。这些充分显示出红十字会社会救助活动的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即已然突破传统慈救事业的地域藩篱,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慈善走向人道,进而与国际接轨。
在筹款方式上,红十字会也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比如发行公益奖券,举办“义演”、“起会”等活动筹集经费。如绵竹分会采用发行“慈善卷”的办法筹措经费。“慈善卷”类似今天的奖卷摸奖形式,一般发行1,000号,每号发行3-4条,每条售价0.30元,共收1,000元上下,抽30%作经费(约300元),其余配成奖金分成十等奖。(20)黄德明:《民国时期绵竹红十字会始末》,绵竹县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绵竹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96年,第138页。这种方式民众喜闻乐见,反响热烈。又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为救济难民灾童起见,于12月8日“假座大上海戏院,聘请中外歌剧家,演唱义务剧”,“异常精彩”,票价分三元、二元、一元三种,售票所得,“悉以充救济难民之用”(21)《红十字国际委会定期演义务戏》,《申报》1937年12月4日第6版。。
总而言之,红十字会被用来表达、宣扬或传播人性和文明,被视为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表征。国人透过红十字会这面橱窗发现了中国所没有的救护组织和人道精神,进而孜孜追求。
二、红十字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路径
民国时期,通过种族竞争的思潮,关于民族和人种优生学的概念得到广泛传播。直到20世纪早期,不管是具体的个人或者特殊的论坛上,民族这个概念仍有着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触目所及、伸手所触、每个人的席间谈论,都可以看到“民族”这个词(22)[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更确切地说,遍及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这场红十字运动的背后驱动力。这场运动的推行概况及壮阔表现,为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路径。
在近代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积极灌注民族主义情感是红十字运动在推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勒庞曾说:“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昂立。”(2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70页。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历程中创造的最重要的两个术语是“博爱恤兵”和“人道”。“博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术语,反映的是中国近代革命话语体系下对红十字精神的诉求。“人道”则如上文所述,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这两个术语表达了红十字运动组织者的诉求,即渴望把红十字会与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联系到一起,而不是与传统慈善事业相关联。“博爱”和“人道”在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颇具号召力,它们在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贴上“博爱恤兵”和“人道”标签的红十字会在会务拓展中潜移默化地将“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灌注给受众,成为日常习见的,并且遍及整个中国。
红十字运动在实践中还积极拓展基层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成立后,各地分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萌发,成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主要基地。这些分会秉承“博爱恤兵”的宗旨,一面积极从事赈灾救济、救伤瘗亡的会务活动,一面积极传播人道精神和现代医疗卫生理念,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诉求相呼应,从而“在社会意识的层次上超越地方层面而与民族国家的宏观进程发生了直接勾连”,(24)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5页。推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诚如义赈“这种以地方认同为基础的行为完全可以达到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效果”(25)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483页。一般,以地方认同为基础的红十字分会组织也完全可以达到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效果。
红十字会被纳入官方管理体系最终确立了红十字运动民族性优先的原则。红十字运动的开展,使政府意识到红十字会在战争救护、灾害赈济及国际交往方面的重要价值,急欲“收入麾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监督慈善团体法》,将红十字会纳入慈善团体的范畴,加强监管。该法有意淡化红十字会的国际性,凸显红十字会的民族性,明令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团体一样受主管官署监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博弈中,最终国家权力日益扩张并成为主导。其后,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立案办法》等规章,进一步强化了对红十字事业的监管。
需要强调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的管理与系统调控不单是出于公众监督的考虑,还把红十字会看作建构“三民主义”国家的通盘计划之一部分。“社会民众团体之健全、发展,乃促使社会繁荣进步的主要因素,亦为巩固国家基础之重要力量”,基于此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极力统一社会体系、推动社会建设、进行战时社会改造,以充实国力,“支持抗战建国之遂行”。(26)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辑 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第1页。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下,红十字会最终被纳入官方管理体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助力。诚如资料显示: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最可纪念的地方,就是它真能照着“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的目标去执行它的任务。(27)汤蠡舟:《救护工作第八年》,《救护通讯》1944年第23期,第2页。
围绕抗战建国的使命,国人积极尝试建构民族主义的视觉认知,并将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比如,1941—1948年间举办的七届红十字周就试图把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理空间,创造一个民族化的视觉形象。红十字周打出的广告、宣传标语、展览品等,每一件物品都揭示了红十字会和抗战建国的关联。如“参加红会工作与参加前方工作同样重要!”“民众为国致力最切要的目标,便是致力红十字会事业!”及“中国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是中国人的荣誉!”(28)《中国红十字会周宣传标语》,池子华,傅亮等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9页。等宣传标语传递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民众不仅可以通过服兵役上前线,而且可以通过赞助红十字事业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抗战事业的支持。而“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29)[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第29页。。事实也的确如此,相当一部分人因参加红十字周而成为红十字会的会员抑或红十字事业的积极赞助者。他们通过加入红十字会的方式来证明民族主义意识。与此同时,他们的参与本身也进一步强化了红十字事业和抗战建国之间的关联度。这些行为至少可以视作有利于民族主义意识增长的标志。
除了强化民族主义外,推动传统向现代更生,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红十字会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沟通转换的桥梁角色。如推动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又如推动乡村医疗卫生的现代化进程。抗战时期,红十字会医疗队深入广大农村地区,为当地带去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并破除了一些封建迷信。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就是一个典范,据时人回忆,该医疗队在延安时经常为农民治病:
由于医疗点地处农村,我们还常为周围的农民治病。虽然边区是抗日根据地,但边远山区的农民文化落后,迷信愚昧,加上缺医少药,时常受巫医的欺骗。婴幼儿高烧惊厥,巫医说是“丢了魂”,要老百姓拿了扫帚、簸箕去“招魂”,妇女久婚不孕,巫医说“得罪了鬼神”,装神弄鬼地去“阴间”赎罪。针对这些情况,医疗队除对农民宣传卫生知识,教授一些治疗方法,还免费治好了一些病人。此后农民生病就找医生,再也不找巫医了。(30)侯道之,朱朝政,朱朝成:《光荣的使命——记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在延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5辑,1993年,第71-72页。
上述材料生动呈现了红十字医疗队的工作风貌。从中不难窥见,医疗队的工作有力破除了当地农民的迷信思想,推进了当地医疗卫生的现代进程。复员时期,红十字会秉承“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宗旨,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除了在城市集中举办各类服务外,红十字会还将触角和视域延伸到了乡村。诚如资料显示:红十字的医药服务在城市建立基础之后,“急切地需要推展乡村市镇的工作”,应该找寻“没人照顾的贫苦人群”。红十字的旗帜,“今后将在贫穷、疾病、灾害、痛苦的每一个角落里飘荡”(31)《红十字旗帜在乡村——武进分会前黄、厚余服务站鸟瞰》,《红十字月刊》1948年第29期,第27页。。围绕此指导思想,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乡村巡回医务队十二队,由各分会自行办理。如孝感县分会第三乡村巡回医务队、邕宁县分会第四乡村巡回医务队、青浦县分会第六乡村巡回医务队、砀山县分会第七乡村巡回医务队、江都县分会第八乡村巡回医务队、开封市分会第十乡村巡回医务队以及东双河支会乡村巡回医疗队等等。此外,南京鼓楼医院乡村卫生科还开展了防盲业务。武进分会自1947年2月始,先后设立了前黄镇、湟里镇、寨桥镇、厚余镇等9个服务站,在乡村服务方面颇有声色。如前黄镇服务站设有疗养室、待产室、调查室、手术室、门诊室等。自成立至1948年4月,共计诊治病人49,952人。保健方面,举办儿童健康比赛、妇女节叙会以及敬老会等。此外,该服务站还曾与当地热心的中医合办夏令施诊所,致力环境卫生工作;对贫苦的居民分发寒衣,补助贫苦儿童学费,利用农隙举办失学儿童夜校,举办妇女缝纫班、会员联谊会、筑路、开设书报阅览室、农民教谊室等,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很光荣的被大众注意”。(32)《红十字旗帜在乡村——武进分会前黄、厚余服务站鸟瞰》,《红十字月刊》1948年第29期,第27页。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人道精神和服务理念在乡村的传播,带动了偏远地区的现代化。
三、红十字运动参与者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
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乃是民族主义驱动的结果。基于此,或许可以说作为民族主义的产物,红十字运动自始至终灌注着民族主义的情感。在民族主义无孔不入的浸染下,红十字会被塑造为民族认同的凝缩象征。国人踊跃参与红十字运动,表达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而这种参与本身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认同感。
红十字运动的参与者首先是红十字运动的组织者。他们认识到红十字会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重要作用并孜孜宣讲。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空前的危机带来民族主义情感的空前高涨。红十字会救伤瘗亡的重要性也得到空前凸显,被赋予服务抗战建国的重要使命。红十字人对此作了充分阐释和解读。有高屋建瓴地指示红十字事业发展方向的,如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业应该是“平时有备”“战时有能”的事业,“要紧密配合抗战建国的工程,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33)潘小萼,汤蠡舟:《三十二年元旦告全体工作同仁书》,《会务通讯》1943年第14期,第3页。又如,红十字事业今后应与社会安全计划、世界和平运动以及国家建设工程相配合,在社会安全计划中承担广泛的社会救济工作,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扮演“国际卫生员”或是“国际服务员”的角色,在国家建设工程中成为“建国的卫生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助力”(34)汤蠡舟:《救护工作第八年》,《救护通讯》1944年第23期,第3页。;有从红十字会在战时保全人力的重要性角度立论的,如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神圣的组织”,是伤病军民的“救命堡垒”。(35)胡定安:《发挥人类应有的博爱精神》,《会务通讯》1943年第21、22期合刊,第31页。战时,人力是决胜的基础,在战场上救活一个伤兵,等于为军队保持了“一分战斗力量”,救出一个难民,则等于为国家增加“一分生产力量”(36)陆诒:《救苦救难的红十字会》,《会务通讯》1943年第21、22期合刊,第33-34页。;也有从红十字会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独特价值方面建言的,如红十字会秉建国旨意,“于辅助军医救伤之外,更筹余力,以助政府建设卫生行政上永远之规模”(37)袁松人:《战时救护工作之影响》,《救护通讯》1944年第22期,第1页。等。大体言之,红十字会救护工作在抗战方面的影响,最低的估计,“应当是辅助军医加强了战时卫生勤务”,从而“直接的加速了抗战的胜利”。至于建国方面的影响,则体现在辅助“健军养兵”和“公医公药”(38)汤蠡舟:《救护工作第八年》,《救护通讯》1944年第23期,第3页。事业方面,从而增强了国家抗战力量,并推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这些认知都凸显了红十字事业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间的内在关联性。围绕抗战建国的使命,红十字人呼吁国人积极支持和赞助红十字事业,“自我们红十字旗帜之下,造成一股强劲有力的风向,达成抗战建国的全功”。(39)《胡兼总队长于本年四月四日总队部举行国父纪念周讲词》,《会务通讯》1943年第17期,第4页。
广大的战时救护人员是红十字运动的中坚力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组建救护总队,“尽量吸收智识份子参加”。(40)《庞京周谈改革红会之计划》,《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年第26期,第53-54页。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踊跃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诚如史料披露:“记得上海四郊燃起抗战的烽火时,就有成千成百的青年男女,都自动投效到中国红十字会中去工作,在战地上冒险犯难,忠诚服务,这种可歌可泣的史绩,至今犹活现在我们的记忆中。”(41)陆诒:《救苦救难的红十字会》,《会务通讯》1943年第21、22期合刊,第33页。
据谭宗英回忆,自1938年起,红十字会救护队开始从社会上招收医护人员、学生及流亡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后编入各救护医疗队,随同抗日部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员。其时,她正在上海娜菲德路医院读书,“毕业时,碰上红十字会救护队在上海招生”,于是“不顾父母兄长反对,报名参加了,随同从上海招收的一百多名青年学生到长沙丝毛冲进行军训和业务学习。除了在教室里上课外,还到操坪上练习在危急情况下如何抢救保护伤员、自卫反击等项目”(42)谭宗英口述,邓立群整理:《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工作回忆》,长沙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125页。。1940年,张荪芬在北京习医毕业后即南下云南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也是受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的感召。据她称:“听曾到过后方的朋友说,看到有红十字会医疗队随军服务。于是我拿到毕业文凭的第三天,就独自离开了家乡,一心只想赶快去找中国红十字会,让自己也在抗战中贡献力量。”(43)张荪芬:《回忆抗战期间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情况》,泗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泗阳文史资料》第7辑,1990年,第24页。其后,她辗转到达贵阳图云观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与国际援华医疗队一起,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
在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医务界也积极响应中国红十字会号召,投身抗日救国救死扶伤的战斗行列中。据史料载:“上海市以及各地的医院病房里以及护校课室里之护士们,先后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44)王从炎:《中国红十字会小姐一页奋斗史》,《救护通讯》1944年第13期,不著页码。李应元作为其中的一员被编入第一医疗队赴徐州抢救重伤病员,他回忆道:为伤员治病,队员们“感到骄傲,无比快慰,并一致表示要学习他们抗日救国的崇高献身精神,为抗战胜利尽心尽力,奉献一切”。(45)李应元:《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疗队工作片段》,无锡市南长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南长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1995年,第106-107页。此外,还有“不少地方的医护人员自发组织起来上前线救护伤员”。如1937年9月,供职南京卫生署的原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王禹昌医师奔回母校,发起筹组医疗队,由他和王金泉(护士)、朱朝城(学生,后改名朱朝成)三人具体筹备。不久,又有齐鲁大学医学院医护人员7人参加,共10人组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津浦路医疗队。(46)侯道之,朱朝政,朱朝成:《光荣的使命——记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在延安》,蚌埠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5辑,第62页。其后,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接洽后被改编为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赴延安从事救护工作。
从军事或政治的角度来讲,“战时救护人员可以说是医药师,同时亦可以说是战斗兵。因为由于救伤护病的成功,减少了我们战阵死亡的数字,亦即加强了我们战场上作战的能力,直接他救护了伤病官兵,间接他打击了和平人类共同的敌人”。因此,可以说“战时救护事业,其目的是含有国家性民族性,甚至世界性”。(47)王洽民:《革命人生观与战时救护事业》,《会务通讯》1941年第2期,第3页。在这场“含有国家性民族性,甚至世界性”的红十字救护事业中,广大救护人员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诚如一位救护员的内心独白:“际此国家危难、民族大劫之秋,宁敢谓劳?宁敢谓苦?只求为国家、为团体、为本位工作,多尽点心力。”广大救护人员深刻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救护工作是“直接有利于抗战大局的”,因此“明知前方尚有许多困难”,但本着“谁叫我们做中国人?”(48)林竟成:《别了大溶江》,《救护通讯》1944年第26期,不著页码。的国民意识依然披荆斩棘、排除万难,为抗战建国贡献一己之力。
红十字运动的参与者还包括广大的支持者和捐助者。他们有时是主动自愿的,有时则是不知不觉被动卷入的。抗战时期,各个阶层在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下,对红十字事业呈现出空前的参与热情。如著名电影明星秦怡就曾不无感慨地说:“红十字会对我来说,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她回忆自己早年参加中华职业学校的红十字会的情形时,就提到是受民族主义的感召:
当我还只有十四岁时,我在学校参加了红十字会的队伍。那时非常简单,有比我高班的土木科的三位女同学及和我同班的一位,加上我共五人……我记不清是怎么和她们走到一起的,好像是她们贴出了布告,建议参加校红十字会,国难当头,每个中国人都有神圣的义务等等。我是一个“热水瓶”式的人物,外表安静,内心却非常容易激动,类似这样的号召,我一定会被吸引。我成了首先的呼应者,于是我们五个人就成为校红十字会的骨干。(49)秦怡述文,刘澍编著:《四季美人秦怡画传:海伦的诉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不少民众纷纷受民族意识的驱动而加入红十字会。如“荷枪战斗于沙场的将士们,他们非常踊跃地来加入为会员”(50)刘鸿生:《我的希望》,《会务通讯》1943年第21、22期合刊,第16页。。另从红十字周的征求成绩上也可窥见一斑。1941年和1942年举行的第一、二届红十字周分别征得各级会员16,907人、14,552人。自1943年1月到抗战胜利为止,红十字会征得各级会员42,069人。(51)朱子会:《中国红十字周史话》,《红十字月刊》1947年第20期,第10-13页。这些会员积极投身救伤瘗亡、卫生防疫等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不少国人以捐助红十字会的方式表达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1937年,上海邮政总局包裹收寄处人员王裕功将儿子弥月贺礼移购药包1,000包,交慰劳委员会运送作战将士备用。(52)《慰劳将士》,《申报》1937年10月20日第6版。扬子舞厅鉴于“忠勇将士浴血苦战,受伤后亟需救护”,将每日营业所得,抽出2%,交《申报》馆代转市救护委员会,充救护经费之用。(53)《扬子舞厅热心救护 亟望其他舞厅影院闻风响应》,《申报》1937年10月21日第6版。次年,上海海格路海格公寓职工,有感于难民苦况,解囊输助难民,“合捐国币三十元另五角”;另有社会人士“垂念难民苦况”,以寿仪悉数助赈。(54)《附录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记事》,《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年第38期,第31页。10月10日当天,上海各界市民有鉴于难民“给养堪虞”,自动节衣缩食,捐款送往国际红十字会、国际救济会等团体,以救济难民。(55)《国庆节市民节衣缩食捐款救济难胞》,《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年第41期,第15-16页。1942年,中华电影公司演映《博爱》一片,将门票收入所获的52,810元,悉充善举,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为指定分派慈善机关之一。(56)《中华电影公司拨款捐助善举》,《申报》1942年12月16日第5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尽管红十字运动参与者的动机多元而混杂,但民族主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因素。形形色色的参与行为本身巩固了某些概念的话语霸权,即红十字运动具有民族性,民族国家的公民必须支持和参与自己国家的红十字事业。由此,红十字运动的参与者不但表达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借由参与运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同感。
四、结语
在晚清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体系下,红十字会作为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表征进入公众视野。其后,这场运动以波澜壮阔的表现为推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路径。被卷入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也强化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红十字运动宣扬人道主义,超越国界、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和现代性色彩。而民族国家是有主权、地域意识的,还有传统意识。这两方面其实是有矛盾的。如何处理、转换这种关系,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中国红十字运动面临的一个难题。为此,在数十年的红十字运动实践中,参与者们紧扣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为红十字会创造了一个集体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调和红十字运动的国际性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地域意识方面,组织者不断宣讲红十字事业是文明国家的标志,是参与国际竞争的砝码。因此,要建构和壮大现代民族国家,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就必须举办红十字事业。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起就被置于国际竞争的全球视域下,在具备天然的国际性之余,被赋予了浓重的民族主义底色。其后,红十字会因其独特的社会救助价值,被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建构三民主义国家通盘计划之一部分而纳入官方管理体系。红十字会的国际性被淡化,民族性得以凸显。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红十字会被赋予服务抗战建国的重要使命。组织者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红十字会和抗战建国的关联性,宣称加入或赞助红十字会就是支持抗战建国的表现。为此,国人纷纷参与红十字运动,而这种参与本身又进一步强化了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
民族国家根植于本土传统。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必然要破除传统意识的阻力,推动传统意识向现代转换和更生。红十字运动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沟通桥梁的角色。如红十字会积极拓展基层组织,以博爱恤兵为宗旨,从事救护赈济活动,普及现代医疗卫生理念和人道服务精神,推动地方救助事业的近代转型,形塑现代国民意识。伴随红十字会业务活动的普遍开展和人道主义的热烈感召,国人踊跃投身红十字运动,突破了传统功德果报的行善范畴,体现了民众在社会参与、国民责任意识等方面的觉醒和努力。这些新气象进一步助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概言之,红十字运动以其独特的价值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并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而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红十字运动也确立了自身的定位,实现了本土化建设,并得以蓬勃发展。在这个层面,可以说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这对透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独特意义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