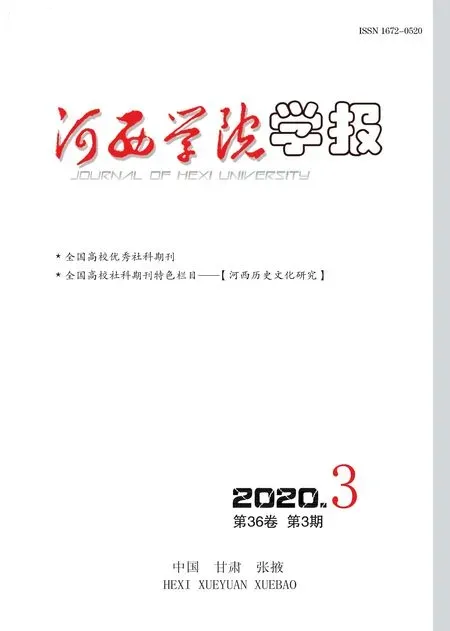朱熹《训蒙绝句》的语言特色
程建功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朱熹《训蒙绝句》作于宋隆兴三年(公元1164年)。明·朱培《文公大全集补遗》和清·朱启昆《朱子大全集补遗》辑录《训蒙绝句》均为94首,清·朱玉辑《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共收100首,清·郑端编入《朱子学归》的则为99首。因此,王利民考证认为《训蒙绝句》原来只有98首,《困心衡虑》和《困学》2首乃后人为凑整数而窜入。[1]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中束景南撰写的《训蒙绝句》“辑录说明”也认为原本为98首,今当从之。[2]1-2这98首绝句在语言上很有特色,今以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所收诗歌为据(束景南的“辑录说明”指出以朱玉本为底本)略作分析。
一、全部诗歌纯用七言绝句,易记易诵
根据朱熹《训蒙绝句》诗序“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2]5所记,原诗应当有五言绝句,但今本所见全部诗歌均为七言绝句,没有五言绝句,其中原因尚待考证。或许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忘记了诗序,或许作者感觉七绝更适宜表达训蒙内容,又或许作者更擅长七绝,总之现存《训蒙绝句》只有七绝而没有五绝。就诗歌形式来看,只有七言绝句一种,未免显得单调呆板,缺乏变化。如从内容上加以分析,七绝与五绝相比,诗歌容量要更大一些;尽管与律诗比,诗歌容量无疑要小多了,但绝句比律诗更易于记诵,对于训蒙当更为便利,这或许是朱熹选择七言绝句这一形式的一个原因。如《小学》:
洒扫庭堂职足供,步趋唯诺饰仪容。
是中有理今休问,教谨端详体立功。
该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与作者在《朱子语类》中的“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3]125的蒙学思想完全一致。再如《学》:
轲死如何道乏人,缘知学字未分明。
先除功利虚无习,尽把圣言身上行(一作“寻”)。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4]334故朱熹在《朱子语类》说:“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3]129此诗主旨意谓童蒙放散其心,追逐功利,不集于义,学所以不进也。孟子以后,鲜有知此理者。因此,朱熹要求童蒙效法圣人,收回放纵散漫之心,专心向学。
与《朱子语类》里的说理相比较,以上诗歌的表达显然更加生动形象,也更加易于记诵和易于童蒙接受。若将以上两诗改为五绝,表达这样的蒙学思想似乎也不难,但诗歌的字面内容,或许会因诗歌字数限制显得过于紧凑、局促,削弱或影响诗歌字面的形象性,反而不利于童蒙理解和接受。众所周知,不仅内容可以决定形式,接受对象同样也可改变和决定语言表达形式。如何才能更加符合童蒙的阅读口味,这是作为一代大教育家的朱熹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这或许也是他选用相对中和的七绝作为表达形式的主要原因吧!
二、诗歌标题简洁明了,题旨突出
通观《训蒙绝句》全篇,诗题字数以一言、二言和四言为主,间有三言、五言、六言等,极为简洁明快,且题旨明确,颇具特色。一字的如《天》《学》《心》《意》《性》《命》等,二字的如《唤醒》《体用》《鬼神》《任重》《博约》《克己》等,四字的如《人心道心》《鸢飞鱼跃》《安仁利仁》《斐然成章》《逝者如斯》等;杂言的有《太极图》《知天命》《乐亦在其中》《莫我知也乎》《就有道而正焉》《出门如见大宾》等。
标题是为内容服务的,从诗题内容看,作者紧紧围绕理学思想和童蒙教育展开,且题旨突出,均为训蒙所需的基本概念,令人一望而知。与诗序所述相一致,《训蒙绝句》诗题大多取自《四书》。这不仅因为《四书》是诗人朱熹精心编选的,而且在其教育体系中,《四书》更是重要的启蒙读物,为童蒙所熟知,故选用《四书》内容作为标题乃顺理成章。如《致知》(来自《大学》)、《戒慎恐惧》《谨独》(来自《中庸》)、《克己》《三省》(源于《论语》)、《刍豢悦口》《仰思》(源自《孟子》);还有一部分诗题直接以《四书》原句为题,如《中庸》(以篇名为题)、《就有道而正焉》(见《论语·学而》篇)《君子去仁》(见《论语·里仁》篇)、《动心忍性》(见《孟子·告子下》)《故者以利为本》(见《孟子·离娄下》)。仔细考察,我们发现《训蒙绝句》诗题与《论语》有关的最多,据笔者初步统计约有48篇,约占全诗的一半;其次为《孟子》,约有20篇,约占全诗的五分之一;与《中庸》直接相关的仅有3篇,与《大学》直接有关的只有1 篇。作者的倾向性极为鲜明,这显然与诗歌的接受对象直接相关。因读者为蒙童,不宜讲《大学》内容,而《中庸》内容较为抽象,同样不适于中小学生。《论语》为语录体,多为口语,内容相对来说较为浅显通俗,适合童蒙口味,故选用最多;孟子是朱熹推重的“亚圣”,多选用《孟子》内容作诗题也符合作者的教育倾向。
《训蒙绝句》另有部分题目与《四书》无关:如《天》(即诗中“乾”)《太极图》《先天图》等,与《易经》相关;再如《西铭》不仅借用张载原题,而且借用原铭文有关乾坤父母的概念(关于《训蒙绝句》的易学思想,笔者将另文论述);再如《心》《意》《命》《性》《道》《情》则以人性、天道等抽象概念为题;至于《小学》《学》《唤醒》等题目则显然是直接针对教育童蒙而作。
由上可见,诗人拟题的标准大致有三:一是从理学“性”“命”“情”“意”“天道”“人心”等最基本的问题入手,以便从根本上教育童蒙;二是充分考虑童蒙的接受程度,尽量选用童蒙最为熟悉又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四书》内容;三是主题要单一、醒目突出,易解易记。这样的选题可谓匠心独运,又可谓用心良苦。
三、语言简洁明快,寓教于理
《训蒙绝句》九十八首几乎全为说理诗,这既与宋代以哲理入诗的诗学传统紧密相关,更与诗人欲借此传播理学思想的主旨相关。由于诗歌形式的独特性,决定了《训蒙绝句》在表达上必须具有形象性;同时,因训蒙主题以及接受对象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诗歌表达上必须具有通俗性。正因如此,《训蒙绝句》中的所有诗歌绝非板起面孔的生硬说教,而是循循善诱、寓教于理,体现出了启蒙诗独有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由于诗歌创作是受《四书》启发完成的,且主要用于“训蒙”,故《训蒙绝句》里免不了出现理学与儒学的抽象概念,而作者依据自己对这些概念的深刻理解,运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将深奥复杂的道理阐发得浅显通透。这一方面得益于诗人长期从教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诗人深厚的学养和纯熟的语言表达功力,通常所谓的“深入浅出”正是《训蒙绝句》全诗的最好注脚。如《中庸》:
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平常不是庸。
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
该诗先将标题的“中庸”二字拆开解说,作者用诗歌语言明确指出“中”即无过、无不及之弊端的恰到好处。“过”与“不及”源于《论语·先进》篇,是孔子回答子贡对子夏与子张的比较问话的,认为“过犹不及”,即“过”与“不及”均非中道。《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5]1625郑玄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5]1625朱熹曾对中庸作过这样的解释:“言常,则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则是事之已然者。自后观之,则见此理之不可易。若庸,则日用常行者便是。”[3]1481朱熹在诗中将“庸”即日用常行的意思从反面作了通透的解说和强调。后又将“中庸”二字合在一起加以强调,认为“中”即在日用常行之中,二字不可等闲视之,须细细体味和把握,且指出其妙用无穷。这种先分后合、化难为易的说解不仅体现了诗人的思想深度,更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表达技巧,而这样通透的解说也更易于童蒙理解和接受。再如《道》:
如何率性名为道,随事如缘(一作“由”)大路行。
欲说道中条理具,又将理字别其名。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1624朱熹解释说:“‘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又说:“率性者,只是说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许多道理。”[3]1491“道”本是一个较为抽象复杂的概念,而诗人用随事顺大路而行作喻便将“道”的基本特性全部突出了出来。可以说,因应物性依循其理而行就叫“道”,所以“道”就如同行路一样。随后又进一步总结“道”中自有“理”在,故可用“理”作其别名。
诗人这样的表达既突出了诗歌形象生动的特点,又轻松自如地将抽象的事物解说得具体透彻。
四、夹用独特的口语表达,语言明白如话
《训蒙绝句》虽为诗歌,但语言并不像一般诗歌那样典雅、华丽,而是在说理之中夹杂一些习用的口语来表达,使诗歌内容显得清浅自然、通俗易懂。如:
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天》)
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中庸》)
常求四者无他法,依旧同归主敬中。(《戒谨恐惧》)
事到理明随理去,动常有静在其中。(《静》二)
事来心向理中行,事过将心去学文。(《博约》)
此心活动原无定,或出他乡入此乡。
猛省不知谁是主,只因操舍有存亡。(《莫知其乡》)
像这样通俗如口语的语句全诗中随处可见,但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口语与日常口语是有区别的。诗人所用的是教育口语,即师生之间探讨问题时所习用的口语。诗人之所以采用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固然与诗歌的阅读对象有关,更与诗人小学“教之以事”的蒙学思想紧密相关[6]。朱熹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又曰:“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3]124不仅如此,朱子还对小学之事作了具体细致的分类。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4]1既然小学是“教之以事”,口语又与教育教学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那么采用教育口语来表述清浅的事与理教童蒙依理去做也就是再好不过的语言选择了。诗人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谓形式与内容巧妙完美结合的典范。
五、善用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诗歌形象性
《训蒙绝句》为说理之作,所以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之外,最好的莫过于用比喻、比拟等修辞手法化深奥抽象的道理为生动具体的形象,或用设问、反问等修辞手段对事理加以强调,从而使童蒙更易于接受和增强印象,诗人正是这样做的。如:
静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旧者流。
流之东之源不息,始知聚散返而求。(《命》二)
《命》诗所谓“二五生人物”,“二”谓阴阳,“五”谓五行。意即人和物皆禀赋阴阳五行而生。在这里,诗人用源和流作比意在说明“返而求”之理。因为在诗人看来,所谓“源”即理,返求则“命即性也,性即理也”。这样的比喻形象生动、化难为易,对童蒙而言不仅易记易解,而且终生受用!
体用如何是一源?用犹枝叶体犹根。
当于发处原其本,体立于斯用乃存。(《体用》)
诗人将体、用关系拿树根与枝叶作比极为妥帖形象,且极易为童蒙所了解和接受。这样的比喻看似简单,实则显现了诗人深入浅出高超的艺术功力。
鬼神即物以为名,屈则无形伸有形。
一屈一伸端莫测,可窥二五运无停。(《鬼神》)
鬼神本无形,诗人用拟物的手法化无形为有形,并用阴阳五行之规律范围莫测之鬼神,比起将鬼神迷信化者不知要高明多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人用自然规律解说鬼神,对童蒙而言可谓善莫大焉!
神化谁知本自然,盍将此意返而观?
试当事上深加察,才着些私便不安。(《鸢飞鱼跃》二)
该诗针对“神化”问题,将设问与反问搭配在一起,前者自问自答,后者寓问于答,从两个角度巧妙地解答了何为“神化”的问题。“神化”非神秘,其源于自然,应当返回到本源去寻求答案。这样的表达可谓神来之笔,不禁令人叹服!
谁云贫贱人难处?只为重轻权倒持。
钓渭耕莘皆往辙,圣贤不法我何归?(《君子去仁》)
此诗首联采用设问,尾联采用反问,轻松自如地回答了“君子去仁”的问题,且与题旨相切合。这样的表达也属巧妙独特!
六、诗歌音韵和谐、如诵儿歌
朱熹作为宋代儒学宗师,不但学术思想为当世翘楚,诗歌修养也可谓炉火纯青。通观《训蒙绝句》全诗,均符合律绝平仄格式,押韵基本依据“平水韵”押平声韵。如:
性蔽其源学失真,异端投隙害弥深。
推原气禀由无极,只此一图传圣心。(《太极图》)
人因形异种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
直自源头明说下,尽将父母属乾坤。(《西铭》)
两诗平仄符合绝句体式,前诗真、深、心均押平声侵韵,后诗根、源、坤均押平声元韵。当然也有个别诗歌出现邻韵通押的情况。如《唤醒》(二):
二字亲闻十九冬,向来已愧缓无功。
从今何以验勤怠,不出此心生熟中。
其中“冬”为冬韵,“功”、“中”为东韵,属冬、东通押。为了表意之需要,音韵上作一些必要的变通实属正常。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分析平仄用韵规律,还可校订诗歌用语的正误。如前举《学》:
轲死如何道乏人,缘知学字未分明。
先除功利虚无习,尽把圣言身上寻(一作“行”)。
“尽把圣言身上寻”一句,朱培本、朱启昆本均作“行”。根据用韵规律,“明”“行”属庚韵,“寻”为侵韵,当以“行”为是。另外,从朱熹“教之以事”的蒙学理念来看,也以用“行”为妥。
从以上诗歌可看出,诗人在创作时充分考虑了诗歌的主要阅读对象,特别注意诗歌的音韵和谐;结合前述语言表达上的善用口语、用语浅显等特点,使诗歌读来朗朗上口、如诵儿歌、如话家常,且易记易诵,显示出诗人深厚的语言功底。当然也有个别诗歌为了说理和内容表达的需要,或牺牲了诗歌的音韵美,读来有些拗口;或出现重复字眼,影响了诗歌的形式美;但从训蒙角度而言,只要易于蒙童接受,形式上略有缺憾当属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