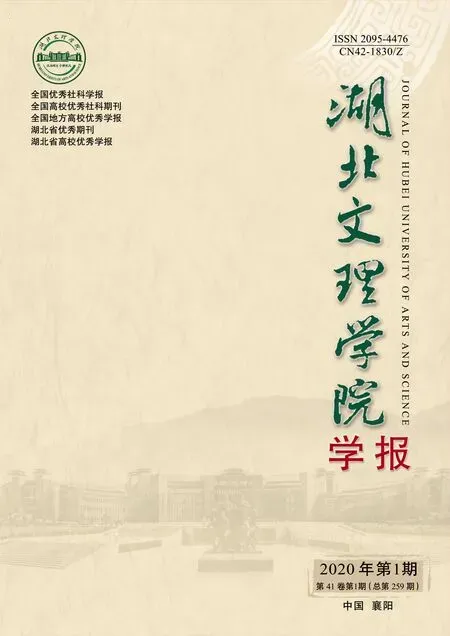胡适与桐城派之关系研究
丁永杰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桐城派起始于清朝康乾年间,因前驱者方苞、戴明世系安徽桐城籍而得名。但它绝非一个纯地域性的学术流派,其影响范围辐射广大,“绵延三百年,涉及一千多人,留下二千余部传世之作”[1]。桐城学人姚鼐曾说:“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里,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2]可见桐城派在晚清文坛上的显赫地位。但在1917年文学革命中,民初桐城派因固守古文传统,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学人重点抨击的对象之一。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即是系统批判桐城思想的滥觞。目前关于胡适与桐城派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论述二者关系的文章主要有朱洪《胡适论桐城派》、任雪山《胡适论桐城派》以及李晴《胡适与桐城派》。[3-5]朱洪和任雪山的文章大都论及某一段历史时期胡适对桐城派的态度,较少注意胡适对桐城派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李晴的《胡适与桐城派》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胡适和桐城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复杂关系。笔者以此为基础,欲通过更多的历史细节,来梳理胡适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桐城派的态度转变及其因由,意在重新审视文学革命与桐城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借此反思文学革命的历史得失。
一、胡适与桐城派的渊源
胡适所著文字中,几乎没有提到桐城派在自己学术道路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但在他实际成长和求学的经历中,桐城思想对他的熏陶则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追溯胡适与桐城派的渊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胡适受其家世影响,二是自己求学道路上对桐城思想的接触。
胡适的父亲胡传于1841年出生在安徽绩溪,自幼饱读诗文,24岁时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同治四年的秀才。后入龙门书院,师从清末大儒刘熙载,深受朱子理学和今文经学的影响。不幸的是,胡传在胡适三岁时就得病身亡,但他对胡适影响却无法替代。胡适曾回忆:“我父亲在临死前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6]卷1:41父亲走后,胡适在启蒙阶段念的第一本书即是胡传通读《四书》《五经》之后改编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事实上,“胡适终生都在念这部‘四字经’,他的为学做人实际上是在践行他父亲留下的这一理学精神灌注其中的‘伦理’,并将他生命的元气和活力对象化在这一徽州文化的特质上,他的毕生言行的实践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父亲留下的这一‘新儒学’伦理文化的认识和改造”[7]。胡适读的第二本书是胡传编的《原学》,此后又多读经书原著,且用朱子注本。胡适晚年旅美时曾说:“我想我那时是被宋儒陶醉了。我幼年期所读的《四书》《五经》,一直是朱熹注。我也觉得朱注比较近情入理。”[6]卷1:262沈卫威对此谈到,“朱子‘新儒学’的伦理观及哲学精神,影响胡适至深,铸成了他思想性格的最基本模式。”[7]39胡适读的第三本书是《律诗六抄》,虽然不记得是谁编写的,但胡适自己回忆,“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不敢坚持此说”[6]卷1:43。此外,胡适在绩溪老家读书时,还读过《论语》《大学》《书经》等书籍。桐城派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胡适阅读的这些书籍,内容多是桐城派所坚守的“道”,换句话说,胡适在求学道路上不自觉地受到了桐城思想的正面影响。
胡适1905年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对胡适影响很大。他曾回忆:“《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6]卷1:64胡适的名字也是来源于《天演论》中的“适者生存”。可见严复译作《天演论》对胡适的冲击很大,除了《天演论》,胡适还十分重视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不仅是胡适,《天演论》对鲁迅、周作人等“五四”同人都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晚年胡适谈到林纾时还说:“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8]胡适后来在文学革命中把严复和林纾都当做桐城派的“嫡派”,他发起文学革命无疑是亦在传统中反文言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从‘桐城’到‘五四’,是历史性的变革,同时又是历史性的传承。传统就是这样处在生动的、不断的自我扬弃的过程当中,它在为自己培育掘墓人的过程中走向消亡,同时又走向新生——历史在这里排演着富于喜剧色彩的人间正剧。”[9]不难看出,桐城学人及其思想对胡适等人启发颇大。但当新文化运动需要落实属于自己的那套言说方式时,胡适所谓的桐城思想的各种弊端就会在文学革命中无限被放大。
二、胡适对桐城派的历史批判
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代表的文章坚决反对传统古文,提倡白话,桐城派成为被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相较于文学革命初期的全盘否定,胡适此时对桐城派的批判态度已有所缓和,能够正视桐城派的历史功绩。到了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对桐城派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从胡适在这近20年间的3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桐城派的批判力度逐渐减弱。换句话说,随着历史的线性推移,胡适对文学革命的思考更加审慎。
(一)《文学改良刍议》——激进批判
胡适认为桐城派的最大弊端即“文以载道”。《文学改良刍议》对“载道”的桐城古文做出批判,“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之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6]卷2:8。为了声援胡适,陈独秀随后发表《文学革命论》,把唐宋八大家,明之前后七子以及方苞、姚鼐、刘大櫆称为“十八妖魔”。[6]卷2:16以非常激烈的言辞攻击桐城派。在《新青年》该期“通信”栏中,还发表了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信中骂桐城派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0]。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认为“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等都没有破坏的价值”[6]卷2:41。1920年11月,胡适《吴敬梓传》首句写到:“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6]卷2:534由上观之,从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到1918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再到1920年的《吴敬梓传》,在文学革命发生的前几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对桐城派持激烈批判态度,尚不具备自我反思意识,且在一定程度对桐城古文进行了“妖魔化”的攻击。
胡适、陈独秀1917年攻击桐城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北大文科内部的宗派斗争,而桐城派是胡、陈等人在北大文科派系斗争中的敌对对象。1902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初,其译书局总办、副总办分别是严复和林纾。此时姚永概和马其昶也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12年严复出任北大首任校长,可见桐城学人在北大文科的地位较高。此后章门弟子沈兼士、黄侃、钱玄同、周作人等悉数赴北大任教,对桐城学人在北大文科的地位形成了巨大冲击。杨亮功后来回忆:“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教授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及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马皆已离去。代之而起者为余杭派,如黄季刚(侃),朱希祖、马幼渔(裕藻)和沈尹默兼士兄弟诸先生皆系章太炎先生门弟子。”[11]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于1916年、1917年受聘于北大教授,二人携同钱玄同、周作人等借助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机会,竭力批判桐城思想,为自己在北大文科界的领导地位扫清障碍,继续宣传新文学思想。
(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有所觉悟
1923年2月,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谭嗣同、梁启超的议论文章;章炳麟、章士钊的述学、政论文章都归为桐城派门下。但难得的是,胡适在此初次对桐城派作出一些正面评价。“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6]185-186。胡适虽然依旧坚持白话新文学主张,但他首次肯定了桐城古文的价值,对桐城派“通顺清淡”的文章作法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
另外,胡适在该文中认为“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6]181。曾国藩确实为桐城派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曾国藩在总结“桐城前辈”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丰富了桐城古文的理论。姚鼐主张以义理、考据、文章三者为内容的学问,曾国藩在此三事中增加“经济”说,曾国藩认为“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12]。曾国藩主张作文的“经济”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桐城派文空疏之病,用清淡朴素的语言表现重大题材和深刻思想,即为后人称谓的“湘乡派文”。第二,曾国藩的“湘乡派”网罗了当时一大批人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师承体系,后来培养了严复、林纾这些对中国现代化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正如胡适所言:“文人如吴敏树,张裕钊,陈学受,方宗诚,吴汝纶……都在他的幕府之内。怪不得曾派的势力要影响中国几十年了。……吴汝纶思想稍新,他的影响也稍大,但他的贡献不在于他自己的文章,乃在他所造成的后进人才。严复、林纾都出于他的门下,他们的影响比他更大了。”[6]卷3:185曾国藩的幕府网罗了大批学术人才,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和发展学术血脉的文化场所,使得“湘乡派”得以发展壮大。后来通过严复、林纾等人通过介绍西洋文学和科学思想,对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等人产生重要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者,胡适此时已经注意到桐城派与文学革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
(三)《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理性审视
1935年仲秋,良友图书公司决定推出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赵家璧请胡适为其中《建设理论集》写导言,他遂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10节扩写成《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该文对桐城派作出了更为理性而客观的评价,且能够正视桐城古文的历史意义:“宋之欧阳修,明之归有光,钱谦益,清之方苞,姚鼐,都比唐之韩柳更通畅明白了……散文体做到了明白通顺的一条路,它的应用的能力当然要比那骈俪文合模仿殷盘周诰的假古文大多了。这也是一个转变时代的新需要。这是桐城古文得势的历史意义。”[6]卷1:97—98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等追求文章写作的“雅洁”和“雅正”,这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不作无病之呻吟”的实质内涵比较相似,而胡适也十分称赞桐城派“文章通顺”的优点。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还强调:“古文到了桐城一派,叙事记言多不许用典,比《聊斋》时代的古文干净多了。”[6]卷1:99这与他《文学改良刍议》“不用典故”也十分类似。虽然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胡适主张“不用典”是受桐城文法的影响,但某些桐城文法启发了胡适后来的创作也难以否认。所以具体到文章的作法,桐城古文和新文学也不能完全被割裂,二者实则是一种继承发展,亦或是互相借鉴的关系。
三、桐城派与文学革命关系之反思
纵观胡适对桐城派的历史批判以及态度转变的缘由,一方面在于文学革命胜利,桐城派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不断衰落,白话文运动通过国家层面得以落实。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领导者和胜利者,其对桐城派的态度有所缓和合乎情理;另一方面,时过境迁,胡适对这场文学革命不断进行总结,从而得出相对客观理性的看法。时至今日,再次重新审视桐城派和文学革命,二者非但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对桐城派“文以载道”的追求进行简单梳理。理学处于清朝官方主流学术地位,是桐城文论的思想来源。但到了清朝后期却面临尴尬境遇,儒家道统逐渐没落,“文以载道”已经不具备其实质内涵了。“他们在理论中自然地走向了对文章写作技巧的强调,从而比前人更为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长于论文而拙于论道,是桐城派诸作家的共同特点”[13]。桐城文人虽以“文以载道”作为自己的立身祈向,但在严苛残酷的社会高压下,这种诉求难以实现,所以他们更为关注文章的作法,使桐城派形成了以“义法说”为核心,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审美批评标准的散文方法。“文章风格清澄淡远,词采纯净幽美,并时或间以声调之铿锵与气势之雄伟磅礴,所以易为人们所接受。”[14]这是桐城文法的美学意蕴,也是该流派在文章作法方面的重要贡献。白话文的发展和成熟,特别是现代散文理论,均借鉴了传统古文的优点,所以必然不能割裂古文和白话文的关系。
另外,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运动,把桐城古文完全作为其对立面来看待,容易走向矫枉过正。早在1919年4月,桐城派文人林纾就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认为“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15]?林纾其实并没有多么痛恨白话文,他只是认为发展白话文不能彻底废除文言文。可见林纾早在1919年就有文言、白话不可割裂的意识。周作人于1922年发表《国语改造的意见》,认为“现在普通语虽然暂时可以勉强应用,但实际上言辞还是很感缺乏”[16]。而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之一即为“采纳古语”,主张白话文应该吸收古文的优点。1932年周作人又用“二桃杀三士”的例子来证明“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学的本身并没有明了的界限。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17]。纵观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可以看出:他只选取了汉朝、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几个朝代出现的白话文和白话诗,没有撷取其他朝代的“白话现象”,这种论述方式本身就缺乏连贯性和统一性,容易使人对古代白话文的理解产生偏差。有学者谈到:“白话文运动不但是在克服古文弊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还是古文运动的使命延续。”[18]这些都可以看出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是此消彼长、难以分割的。
最后,桐城派对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贡献不只在于学术层面,亦或是文法方面。它还对北京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吴汝纶提倡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引进日本的教育体制,其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一直影响着北京大学日后的发展。桐城派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北京大学,丰富了北京大学的历史,其后期的代表人物不仅为近代的书院教育作出了贡献,也为近代的大学教育付出了心血”[19]。另外,桐城文人虽然在文学革命中遭到陈独秀的惨骂,但当他们面对正义是非问题时却毫不含糊。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发传单时被便衣特工逮捕,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和姚叔节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1925年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还说起此事:“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20]这也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桐城文人的宽广胸怀。
桐城派是晚清一个固守传统而又能不断革新的文学流派,它在由古文到白话的过渡进程中起到了桥梁般的联接作用,是文学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无奈在疾风骤雨式的文学革命中遭到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激烈批判。20世纪30年代,胡适、周作人等对桐城派重新作出了一些新评价,无奈在新文化运动光环的笼罩下,学界长期对桐城派的态度并不客观。正如张器友指出:“尽管包括桐城派在内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渗透到了新文学当中,但理性思维的偏执性总是使一些人把‘反传统’一味地理想化、图腾化,以致在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成果的同时也遭受到了其中负面因素的惩罚。”[9]168作为历史后人,回头再看这桩“桐城案件”时,应该重新思考文学革命和桐城文学的关系。同时也应该借此反思文学革命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复杂暧昧关系。文学革命初期,“五四”学人在传统和现代的对峙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后者,但在思想观念的深层,依然无法与传统分割。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历次反传统的破坏与成长以后,必然会迎来新一轮对传统“断裂”的反思。不难发现,传统之中一些优秀、精华的东西不会轻易被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