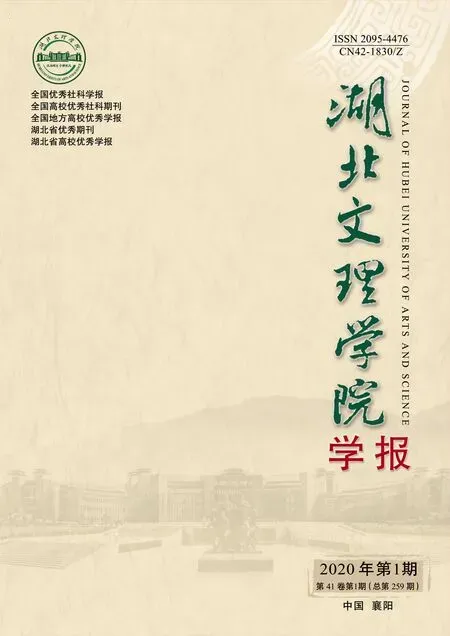作者、文本、读者的交互沟通
——浅析《小说鉴赏》的小说批评观
甘秋莉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国内主流学界通常侧重对布鲁克斯、沃伦作为“形式主义者”的诗歌理论的探讨而较少涉及到其小说批评实践。即便涉及到他们的小说批评,也会预先断定他们的小说批评与其诗歌理论一样,是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批评。而一旦学者们发现布鲁克斯、沃伦的小说批评不符合他们的预设时,便认为这是布鲁克斯、沃伦不得不打破自己禁区的无奈行为。对于布鲁克斯、沃伦的小说批评观,笔者有着自己的见解,与以上学者的阐释多有不同。通过对《小说鉴赏》的阐发,并结合其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指出:国内主流学界对布鲁克斯、沃伦的评价多有偏颇之处。
一、以“人”为核心的小说三要素
在《小说鉴赏》中,布鲁克斯、沃伦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范畴,即“连贯性”——“指小说所有组成要素之间应具有的那种重要关系。”[1]42并且认为连贯性是判断小说好坏的根本标准,由此形成他们的小说批评理论。小说三要素为情节、人物、主题,所谓连贯性就是小说的情节、人物、主题交织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相关性。是什么使得三者得以统一?这一问题在很多的论述中始终没有得到关注。如若不理清在小说三要素中一以贯之的核心,便容易造成对布鲁克斯、沃伦小说批评观的误读。
情节要素。在正式提出情节要素定义之前,布鲁克斯、沃伦先区分了动作与情节。在他们看来,动作是一系列按照时间线性顺序展示出来的事件,含有开始、中间、结尾三部分的构成,具有真实世界的时间连续性。而情节不可能严格按照动作发生的顺序形成,必须要对动作进行选取和安排。由此,在动作的选取上,并不是所有的动作都能够成为情节发生的部分,在顺序上情节与动作也发生了位移。在区别了动作与情节之后,布鲁克斯、沃伦给情节下了如下的定义:“情节无非就是对于动作富有意义地加以使用而已。”[1]43情节在这里被看作“动作的结构”,这种人为的构成表明人对事件如何加以处理的一种方法。对动作富有意义地加以使用必然牵涉到建构小说文本的作者因素,这里其实强调了作者的主观意志对小说构成的意义所在。作者的主观意志在情节安排的三个阶段(破题、开展、结尾)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各式各样的小说中,破题、开展、结尾的安排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在此,布鲁克斯、沃伦强调,在阅读小说时需领会作家的意图,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作者以何种方式安排故事情节,如此安排的意义何在。“所谓情节‘就是对于动作富有意义地加以使用’、情节就是‘动作的结构’等命题,从根本上确立了小说家作为艺术创作者的主体地位,肯定了小说情节是作家主观创造的创作论思想。”[2]60布鲁克斯、沃伦对于作者的关注在这里极其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人物性格要素。在讨论情节要素的时候,布鲁克斯、沃伦特别提到情节必须是行动中的人物,而且在分析以情节要素为主的小说文本时,他们始终关注人物行为是否合理、是否真实可信的问题,抛开人物单纯讨论情节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提出的就是人物性格问题。这是他们提出的小说三要素之一,并且是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内在地连接了情节和主题要素。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人物行为是否符合性格问题的极大关注与强调,这一点将会在下文的文本分析中加以论述。因为强调人物性格对小说的重要性,在面对一个小说文本时就必须要问“这是谁的故事?”谁做了什么事?是什么导致他(她)做出这样的行为?这是了解一部小说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布鲁克斯、沃伦一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可以有无性格的故事而不可有无情节的性格的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人物性格作为艺术审美中心的观点,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思想。
主题要素。“主题是某种观念某种意义,某种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诠释,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它是通过小说体现出来的某种人皆有之的人生经验。”[1]220布鲁克斯、沃伦关于主题的看法需要同认为小说是图解的看法区别开来。就图解而言,是一种释义,它假设存在着某种观念,继而通过描述事件来对之进行阐释,有一个客体对象存在有待于我们去解说。预设了一个他者的存在,小说要素存在的意义是为这个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服务的,这就造成了为所谓的普遍意义而机械地使小说人物朝着固定方向发展,进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布鲁克斯、沃伦不同意这种小说观。他们认为小说创造的世界有其自身存在的权利。小说是进行中的活生生的生活的一种演出,它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作者凭借自身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将自身的领悟融进文本,力图在文本中揭示出生活本身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读者作为一个生命主体,被卷入文本所揭示的人所共有的经验中,在此理解过程中形成自己对生活更为深刻的体悟,在与文本、作者的共同交流中,赋予自身以意义。
通过对小说三要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始终贯穿其中的核心是“人”——不论是情节要素中强调的作者,人物性格要素中的人物,还是主题要素中的作者与读者。对人的价值的强调与布鲁克斯、沃伦作为“逃亡者”成员和南方批评家的背景有极大的关系。以兰色姆为核心,集合了泰特、潘·沃伦、布鲁克斯,形成了所谓的南方批评家。他们都成长于南方重农主义的背景之中,因而反对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传统价值缺失和人的价值失落。由此,南方批评家致力于重建南方文化传统以对抗科学带来的人的失落。“南方集团的批评家们首先关注的就是现代都市化和商业文明及其对传统的冲击。……他们的目的仍在讨论一部艺术品的普遍价值,它的连贯性和成熟性——它的人文的和社会的价值。”[3]284这一观点也被其他论者意识到:“资本主义化的南方并不是战后南方的最佳社会状态,南方诸多传统的优秀制度和思想被科学的蛮横斩断,整个南方社会和思想文化需要某种温和的变革。”[4]南方批评家以恢复南方文化传统秩序为使命对抗资本主义,彰显出批评家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小说三要素中,“人”成了三者连贯统一的连结点。在情节要素中强调作者意图对文本结构的影响,在人物性格要素中强调文本人物的合理性,在主题要素中强调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把握。如此,以“人”为核心,小说三要素就内在地联系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的沟通。
二、“细读式”文本分析
布鲁克斯、沃伦《小说鉴赏》这本著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书的体例构成。该书分为概论、文选、讨论、问题四个部分。除了概论部分是以比较理论化的形式阐发他们的观点之外,其余三部分明显是基于具体的文本分析从而体现他们的小说批评观。其中体现了布鲁克斯、沃伦小说“细读式”批评。在他们的文本分析中,什么是他们一再反复提醒我们注意思考的问题?
在第一章《小说的意图与要素》的文本分析中,小说三要素被初步提出来并提出区别小说优劣的标准是情节、人物、主题三者是否交织成为一个整体,其中尤其提到“人物动机”。
第二章《情节》中,重复提到的问题是人物动机是否能令人信服。第三章《人物性格》中,人物行为、性格在这里再一次得到提醒,同时优秀的小说一如前面所言,各个要素始终贯穿文本之中具有内在统一性。第四章《主题》的文本分析,布鲁克斯、沃伦有较少的分析,在此不作论述。可以看出,布鲁克斯、沃伦在其“细读式”解读中始终关注小说三要素的连贯性,除此之外,一再被提到的问题如上所说是“人物动机是否能令人信服”。要求分析文本的内在逻辑性,文本是如何构成一个连贯整体的。涉及到逻辑推理能否成立的问题。如,因果联系能不能成立,一件事如何导致另一件事,这样的结构安排合不合理,前后是否协调一致,铺垫、背景的作用何在,有没有意义……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根本问题何在?
一方面,涉及到作者的维度。作者这样写能令人信服吗?作者的意图何在?在此,布鲁克斯和沃伦时刻提醒我们注意作者的意图,去关注文本是如何被作者以怎样的方式“制作”而成的。但是作者的意图并不需要从作者现身于文本中做出评论而得到体现。布鲁克斯、沃伦批评那些作者现身说法的小说创作,如认为作者故意在结尾处来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使得小说结局看起来显得富有深意,这是一种拙劣的手段。再如作者有时为了渲染气氛,使用“诗化”的语言过分虚饰景物,造成一种感伤情调,而这情调却不是故事本身能够呈现给读者的。作者的痕迹太过明显,没有让作品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发生。如此,高明的作者必定是让他自身的痕迹消失在文本之中,读者自然可以从文本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中揣摩出作者的意图。布鲁克斯、沃伦所关注的意图不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法所注重的作者个人的思想,而是“作者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5]489,至于作者在写作时的设想和他后来的回忆都无关紧要。他们承认研究作者生平经历及其思想具有价值,但是“对作者思想状况的研究会使批评家将注意力从作品本身转向对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心理的研究。”[5]489-490作品结构本身体现出来的作者意图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克斯、沃伦在海明威小说《杀人者》的分析中涉及到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看起来这一解读与他们所关注的作品中实现了的作者意图相矛盾,有论者据此认为“新批评方法是有局限性的。”[5]425因为,对《杀人者》的分析“下半部分,涉及到海明威主人公的类型,涉及到海明威的特殊风格与‘一个土崩瓦解、四分五裂的世界’的关系,我们就很难看到什么新批评的特殊方法了。”[5]424然而,从布鲁克斯、沃伦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先是从作品本身的结构和人物态度的分析中,得出了海明威小说中的世界是“支离破碎、无意义的世界”[1]246这一破碎的世界也存在于海明威其他的小说中。从海明威的整体小说中总结出的世界推出作者本人的敏感性,并将之归因于作者所属的世界。布鲁克斯、沃伦始终是先从文本出发分析得出结论,再从其他的维度探寻解读的可能性。并不是首先阐明作者的思想,进而拿一个文本作为作者思想的注解。在运用新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纳博科夫说道:“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看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关系。”[6]19有关论者认为在新批评理论中涉及到作者本人思想以及外在世界的做法是一种“折中主义理论立场”[7]18,这种论断其实已经预设了一种理论偏见,即新批评理论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批评。即便他们偶有涉及到作者和外部世界,也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但纵观布鲁克斯、沃伦的《小说鉴赏》,这种说法其实已经不攻自破。
另一方面,涉及到读者的维度。读者能不能够从文本中获取一种可以提供人生经验的意义启示,布鲁克斯、沃伦认为是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有关读者的理论体现在布鲁克斯、沃伦对《理发》一篇的分析当中,他们提出作者使用叙述者的角色,用意何在?分析之后他们认为,读者的态度与叙述者的角度产生了抵触。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读者参与”的能力。布鲁克斯、沃伦意在说明一个事实:当读者进入文本时,没有预设自己必然会认同叙述者的观点,而是秉持着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在文本之中和叙述者进行沟通协商,辨析叙述者的态度,进行反思,从而更深入地进入文本,达到有效的相互沟通。布鲁克斯、沃伦的批评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假设小说文本是一个统一的结构整体,然后对之进行全面的细读分析,最后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结论,以提供启示。这与乔纳森·卡勒提出的关于文学的程式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的程式即“超保护原则”“交流基于一个根本的程式,即参加者的相互配合。”[8]27
在前文的论述中已阐明了布鲁克斯、沃伦等南方批评家反抗资本主义,力图重建文化传统的努力。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他们反抗的方式是“细读”——一种科学化的客观分析。科学化的分析看起来似乎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而与他们的人文主义立场相矛盾,因而有论者将他们的理论归入与人本主义思潮相对立的科学主义思潮之中。[9]2笔者认同这样的划分,因为新批评理论在文本分析中确实呈现出科学化分析的特点,但因此总体划分而断然判定在他们的批评中缺失人文价值,显得过于片面。布鲁克斯、沃伦在《小说鉴赏》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们总结出的原则“目的在于使读者较为接近写得成功的小说的真谛——接近一种意识,知道小说与过得富有意义的生活的关系。”[1]6在上述的文本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时刻关注作者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意义,而读者是否能从文本中获取一种可取的人生态度。他们正是以科学化的细致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直观到文本具有的审美特性和人的价值,从而在使人的主体性失落的现代文明中重建一种秩序,寻找某种生存的意义。
许多批评家尤其是文化批评家和一存在主义为基础的批评家对新批评理论的科学化倾向进行强烈指责,前者认为新批评理论的客观阐释是一种“技术心态的扩展”[10]157,后者认为新批评理论将文本当作一个客观对象进行分析,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而人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已然丧失了意义和价值。但是,在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如兰色姆、瑞恰兹、布鲁克斯等人的理论中,对科学的排斥一直贯穿于他们的批评中。他们正是以自己的批评对抗科学带来的混乱秩序。“新批评为保卫人文学科明确地维护浪漫主义传统,以此作为对抗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手段。‘细读’法不是试图摹仿科学,而是试图驳斥它对文学的贬低,通过展示即使是在最简单的诗歌中都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意义,新批评家证明自己是‘冷静的自然主义者’。”[10]161胡珂在其学位论文中对此有较为深入地论述。[11]布鲁克斯、沃伦的细读批评也长期遭到国内学者的批评:“细读式批评(close reading),是新批评派创造的一种具体批评方法,这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方法。”[5]7该论断因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影响了后来学界对布鲁克斯、沃伦的定势评判。但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布鲁克斯、沃伦的批评观始终是以人为核心,具有强烈的重建文化秩序的历史使命感。由此看来,学界所谓新批评理论“极端形式主义”[9]124的论断存在极大的片面性。
作者建构文本,力图给我们揭示一种人生价值意义。意义体现在由人物性格形成的动机以后的行为当中。读者进入文本,在小说虚构的人物中试图寻找更好的观照自身经验的启示。然而当我们无法从作者提供的文本得到一种有效的逻辑连贯性,那是一种无效的沟通,小说的意义便不复存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的交互沟通在布鲁克斯、沃伦的“细读式”文本分析中彰显出来。
三、小说涉及的三个领域
布鲁克斯、沃伦最后从宏观的层面提出的小说涉及的三个领域:“我们的实际生活领域、作家的实际生活领域和作家为我们创造的那个生活领域。”[1]366这三个领域的提出,表明了布鲁克斯、沃伦在论述了小说三要素和进行了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后关于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的交互沟通的深层阐释。
在小说三要素中,作者的主观意志得到强调,如何使得动作“富有意义”地体现作者的主体地位;在具体的文本中,作者建构的文本必须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令人信服、具有意义。而所有创造层面想象的生活领域及其意义,无疑有其产生的基础。一部小说,只能植根于现实,植根于作家的实际生活之中。如何使得小说富有意义,便是作家将自己的经验诉诸文本的过程,是一种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想象过程,他力图寻求生活的意义,在探索之中逐渐窥探到生活的真谛,并将之传达出来以供读者分享。所有的意义只能通过文本合乎逻辑的建构体现出来,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作者用生命体验活生生的世界而带来的体悟。“每一篇作品都表现为作家在寻求生活意义时所做出的一种努力。”[1]366在选取的文本中,或者因为“童年时代的生活”,或者因为和实际生活联系着的“环境”,或者因为“某种偶然的回忆”[1]368构成了小说形成的因素,无一例外都来自作者的经验。在文本的时空当中,作者赋予人物以各种各样的性格和意义,即建构了自己的生存意义,而这所有的意义,只能来自作者最真实的人生体验的投射。由此,在富有意义的情节建构和人物塑造中,作者展现了人皆而有之的某个深刻的主题。
作者因追求某种意义而不遗余力地建构合乎逻辑的文本,这种努力跟我们在生活中意欲追求的意义具有同样的价值。读者在进入一部小说时,也是为了获取一定的意义,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去遭遇文本,与作者在文本中实现了的意图进行沟通。情节安排是否合理,人物性格能否令人信服,主题是否能引起共鸣,这一切都在于读者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对文本进行解读。当读者在想象中把文本的各个部分连接成一个整体,继而将之与自己的生活体验联系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共鸣,获取了某种人生的意义。在此种意义上便是成功地分享了作者建构的“幻象”“别人是否能分享这种幻象,这一点事实上也就决定了一篇小说的成败。”[1]367即意味着作家所创造的世界如果不能使得情节、人物在其中根据自身的逻辑连贯性而自行发展,没有表现出内在统一性从而揭示生活的意义,在读者那里不能唤起活生生的幻象,小说从根本上就是失败的。
由此可知,不论是从小说三要素中还是从具体的文本解读来看,作者、读者的维度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而以上所有的意义构成,都只能来自作者和读者的实际生活领域。这里,布鲁克斯、沃伦的小说观已经极为明确地表达出来,作者、文本、读者本来就是一个交互沟通的整体,并非我们惯常所认为的割裂文本与作者、读者的关系。至此,我们可以说,以往对布鲁克斯、沃伦的小说批评观的见解存在着极大的偏见与误解。这一误解如何产生,下文试图论述这一问题。
四、误解成因分析
《小说鉴赏》作为布鲁克斯、沃伦阐明其小说批评观的经典著作,为何长期以来不被国内学界重视并且遭受误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国内学界对新批评的整体评价带来的理论偏见,继而缺少对布鲁克斯、沃伦理论的全面梳理,忽略新批评理论内部的丰富多样性。
从前述来看,国内学界大多认为新批评理论主要是针对诗歌。诚然,新批评的理论批评侧重于诗歌,这种观点毋庸置疑。但是,秉持着这样的理论观点,他们侧重于对新批评诗歌理论的译介,而对新批评的小说批评理论少有涉及或者完全忽视。在对新批评理论的总体特征有所总结之后,在这样大的框架之下有所选择的作为,体现的是一种狭隘的理论视野。如此,第一手资料译介的缺失,使得国内学者偏重于研究布鲁克斯、沃伦的诗歌理论,其中主要集中在对布鲁克斯《精致的瓮》中关于诗歌张力、悖论的研究。《精致的瓮》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布鲁克斯作为一个形式论者的思想,但仅凭一部著作而将其等同于其他形式主义批评家却有失公允,忽略了他在其他批评实践中的丰富性或者不愿意承认他不一样的理论阐释。韦勒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焦点放在克林斯·布鲁克斯才华横溢而又眼光敏锐的细读举隅——在他两部最为著名的论著《现代诗与传统》(1939)和《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1947)中的范例俯拾即是——那就是在评判他的著作的总体性方面严重地有失公允。”[12]312并以极其丰富的材料说明了布鲁克斯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意识。相比国内对布鲁克斯其他著作研究的不足,国外许多学者却对布鲁克斯的全部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挖掘了布鲁克斯其他极具价值的思想,并对布鲁克斯作出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13]
当国内学者凭着对新批评理论整体特征的认知(极端的形式主义)去观照布鲁克斯、沃伦的批评理论时,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因为他们已经预设了布鲁克斯、沃伦是形式主义批评家,所以试图通过相关著作竭力证明他们确实是割裂了文本与社会历史、作者、读者的联系,而不管布鲁克斯、沃伦的理论批评是否存在其他的观照维度。有论者在没有对布鲁克斯、沃伦的文本进行相应的解读的前提之下,而仅凭布鲁克斯对几首诗歌的解读便断然声称布鲁克斯的理论“其片面性则在于割断了文学作品与外部事物的联系,这样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作品,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9]110这样未免太过于以偏概全。此外,这种理论预设也造成了国内学者面对当布鲁克斯、沃伦涉及文本之外维度的批评时,便自认为抓住了他们的局限性,继而对之进行指责。认为他们作为形式主义批评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打破他们的理论宣称,而动摇了他们自身的批评立足点。“一般来说,新批评派分析小说时,都不得不撕破新批评方法论的紧身衣。”[7]91所谓“混乱的折中主义”的评价其实暴露出了许多论者观念先行的偏见,而不顾布鲁克斯、沃伦的实际批评。当他们固守这样的观念而不去全面梳理布鲁克斯、沃伦的思想,恰恰表明了他们自身的狭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