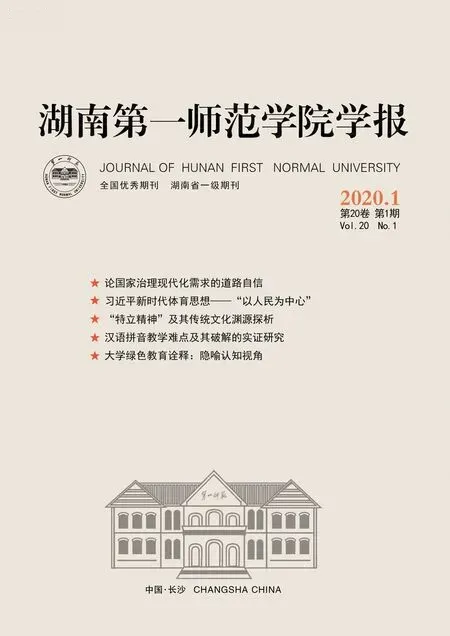试探析侦破徐渭心程及艺术成就的正确思路
张兆勇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不可不反思的误读
徐渭,字文长,别署田水月、天池生、天池山人。晚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人,正德十六年(1521)生。从中华艺术史可知,他是以独具的个性与丰富的创作立于人世的。
世人论及文长均从“奇”切入。在笔者看来,世人思路不外有两层涵义:一者,依其命运侦破奇由;二者,因其命运而震撼其不同凡响的人品及创作成就,由此结论徐渭是“狂人”。不难知道,此思路及结论在徐渭同时代就有。
例如陶望龄《徐文长传》:“文长负才,性不能谨饰节目,然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与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以成其为文长而已。”[1]1341
袁宏道《徐文长传》:“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荡曲蘗,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而幽峭,鬼语秋坟。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1]1342
袁宏道这里的称誉虽不无过誉之辞,但显然出于真情。在笔者看来,徐渭其实是一个平常的人,并不是精神上的奇者,最多是性格上的直汉、硬汉。此诚如陶望龄所云,有属于他自己的个性人格及施展模式而已。笔者以为徐渭作为一个平常人并无特别处在于:
(1)他亦如常人一样,坚持期待走科举入仕之途,换言之,他也是非常期望以科举荣身以换回名利的,只是科场却一直不顺。从文献可知,徐渭在嘉靖十九年(1540)获山阴县学诸生(秀才)资格后,一生曾连续八次落榜,直到四十一岁铩羽而归,不曾获举人身份。
(2)为了谋生,他还选择应聘,其《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云:“渭少嗜读书,志颇宏博,自有书契以来,务在通其概矣。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1]1106
(3)甚至于婚姻他选择入赘,据史料,徐渭出于无奈,二十岁入赘潘氏。刚满六年,潘氏死于生子,徐渭离开潘家回山阴已无家可归。
就是说徐渭并不否认于人生的各方面走世俗之路。徐渭以白衣秀才的身份受聘为总督幕僚,其才学受到浙江总督胡宗宪器重。虽在此多数受命作一些属于“无端代人哭”的应酬文字,但徐渭还是坚持在做。而对于此,据徐渭自己解释他也需要做的周详,他是这样理解和开展的:虽知所照浅俗,也同样相信反照清明。学人们往往结论以为出于义气是他入幕府的一个原因,也的确为了谋生他不避污秽,但无疑也体现着儒者“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气[2]78。徐渭自己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1]1341其实他的成就正是在这些俗务往来杂糅中筑成的。
他的诗今存有2700余首,多数是应时感物以抒怀之作,个中只在表达对自己家乡、对各地风土人情、对花鸟四季的真情实感,从选材到表达再平常不过,性情亦只是淡在于其中。
例如他解释自己的周围:
空中云气无边白,雨后山光一片青。坐石听泉何处好,乱峰深处有茅亭。[1]1320
解释自己于此中人的定位:
花居一纸不异春,人在人中岂异人。山中窗隙观四海,坐见毫端收一尘。[1]1318
他定位他自己真相:
我本澹宕人,忘忧非尔力。[1]1318
又,徐渭解释自己对周围的意义:
乾坤非人谁料理,无一不是秀才事。(卷二送章君之海宁教授七古)
他解释自己所依托的手段:
不过破纸败墨,与君争一日之能。
综上看来,徐渭虽落拓,但一生其实不以奇,而是将此行为与心态展开在清晰的自然生命延展与仕途曲折反思朗照中。在他看来世界无非如此,以此而有灵性。其云“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下段欲写之情。”[1]458
在本文里,说他是直汉、硬汉在于他虽毕生参加科举,但同时也指责科举之弊;虽在幕府谋职,但随时保持着自己的品性。可以说无论如何他首先是期望并切实走着平常人的平常生活之路;换言之,只是坚持在平常日用中自我保持着有相、有志,不被世俗湮灭,是其生活、生命而已。
今天谈徐渭,学人也经常以“狂”视之。虽则如此,但在笔者看来,其实这应是过于粗放地考论了其个性。即是说,学人还可以近距离聚焦其狂,发现他狂之中隐有更深刻的条理性。首先,徐渭的个性来自于他的读书涵养,即在于个性是他愿意且逐步以理性明确的。笔者的这个断语概言之是出于在他一生之中许多处他对自己的表白。据其资料似可下这样的结论:一方面,他本就有被别人激赏的才情聪明,此乃培植个性的根。另一方面,他终于以读书使聪明凝结成了个性,因此完全可结论徐渭的一生聪明灵异结葩于读书,而其个性则在于以此为底蕴而自成其是,自展其质。
换言之,他的个性既因其天性,又最终因读书而在许多方面得以培植与明确。表现为,以其读书,徐渭才越来越愿意承认自己在很多地方与世人不一样。例如他厌恶时下的模拟汉唐的思路,厌恶世上的矫情俗雅气息[1]906(《胡大参集序》),厌恶世上标举虚伪的不实之求,《赠余医师序》对“伪”进行无情的嘲弄[1]516。
鉴于此,似可结论,徐渭所逐渐明晰了的理性个性可特别表述为,他也时刻在努力找寻自己的应世之姿,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是对个性的刻意开发,对自我的独特理解。至于开发的内容,即以“真我”为归趣来表现对自我个性进行阐发与真知。
什么叫“真我”?他在《涉江赋》中云:
才有一物,无罣无碍,在小匪细,在大匪泥,来不知始,往不知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得亦无携,失亦不脱,在方寸间,周天地所。勿谓觉灵,是为真我。[1]36
不难看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我”意念不是徐渭最初推衍出来的。甚或,他是带着前人“真我”来应物施展其个性的,但徐渭绝不是照搬与抄袭,他有自己的创造性。在《涉江赋》中,徐渭的思维重心在于追问“真我”者其体安在?据他自己理解,此真我“体无不含,觉亦从出,觉固不离,觉亦不即。”它“立万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
徐渭的创造性还在于是他以对人格的勾勒和直呈来指证“真我”的落点,从而深入明确了自己的个性,深化具体了“真我”,以至于我们能看到包括他得心应手的操作性。从徐渭的各类题材的诗文资料可知,他有时以“真我”切入描述思考别人人格,有时直呈自己的人格追求。例如其《代督府祭王封翁文》云:“以绝世之英,抱无所不窥之学,出则为贤士大夫,处则为高人,古今可指数者,今子盖居其一。”[1]1139其《吕山人诗序》中对山人描述云“至任野性,傲睨一世。”[1]901——抱奇才,有深计,雄视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间。又其《送章君世植序》云其乡友沈先生青霞“凌厉崛奇,深造远览,横逸不可制缚。”[1]517
不难知道,无论聚焦于何处,徐渭以“人格”所呈出的“真我”都不是封闭的。虽从宏观上说它有稳固的儒家精神涵容,但从个性上说,它又是生命的、开放的、含融的。总之,经常是以明晰理性而不是单纯的“狂”;经常是以个性自呈,而不是放任偏激。其在《郦绩溪和诗序》中论述郦君和苏轼《和陶》云:“苏文忠公在惠州和渊明之作,今味其词,皆泛泛兮若鸥,悠悠兮若萍之适相遭,盖不求以胜人,而求以自适其趣……(郦君)取苏文忠公之诗而和之……其嬉游傲睨,而不屑于工拙,亦犹文忠公之于渊明矣。”[1]903由此可见,对于徐渭来说,个性虽在“真”的意义上一致,但对不同人、对同一人所应对不同事,其呈现又不同。“真我”也正好在此体现着它的明确性以及自我所酿造的深沉空间。换言之,无论是徐渭所谓个性人格还是真我旨趣,显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狂”字。虽然有时徐渭把此放到狂放的程度,例如,他一生极为欣赏沈青霞的“凌厉崛奇,深造远览,横逸不可制缚”[1]517以为是当代屈原[1]625;但有时把此放到极冷静程度,他曾为许多人做过墓志,特别是他在四十五岁时曾自为墓志,在此也完全可以感到他越过“狂”所更凝炼的理性[1]639。
另外,徐渭又经常在他的作品中,通过人格表达关乎“真我”的孤独。在此,虽然有关乎仕途不顺的绝望,但显然更多的则是他个性已走上了孤标的呈示。在笔者看来,此应是理性深入人生之巅,更不应是简单的狂处。
其《黄甲传胪》诗云:
兀然有物气粗豪,莫问年来珠有无。
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1]1314
不难看出徐渭在此的理性在于首先强调个性是由于养,是以“真我”发育的。而捕捉它应定位在“莫问”以前,从而体悟它以“兀然”独特所致的贴切。在徐渭看来,世人应之以“问”则陷入世俗。
其次,徐渭以为“真我”在以个性呈示时,本质上又以思想的独特而独处。尤其是对于此徐渭越来越深知需用心去体验,而对于研发徐渭深知同样需用心抓住。例如,他一生均在体证“知行合一”在其师身上呈现及特征,从中体悟“真我”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其《先师彭山先生小传》云:“(先生一世)著书凡十一种,悉破故出新,卒归于自得……其为政急大节,略小嫌,绝不知有世情,卒以此稍得訾,唯名士大贤独心慕之。”[1]628
再次,徐渭虽明白处于一种无奈,但他也像历史上的一些高人那样并不是不掂量自己的作为行踪,自己所独步的出处、得失、手口①等在人生平台上的分量。也正是在此他认可了自己是兀然有物的,坚信这虽形同“气粗豪”,但更在于是以明珠在握,而自信能“独传时胪”。
基于以上几点,今天来体会徐渭的此处,当然不能简单以“狂”论之,而勿宁更应承认在那样一个以模仿而矫情的时代,徐渭是独以真实而走着心灵正道的。这是因为,徐渭明白,在那样一个鱼龙混杂的氛围之中,珠玉浅弄,往往“真我”并不在于此,因此也就不能于此而获得。作为一个儒家士子应该明白只有抱定儒家担荷情怀,他的亮度也只有更深刻地穿越于此,才能获得真挚的人生效果。
如此说来,在徐渭这里,其个性铸成的标志不仅不是简单的“狂”,而是充满并不简单的人生理性。我们不难发现,越是到晚年,徐渭越是努力以笑来结缔自己的人生,显然这是一种以真挚结谛的人生。
其《头陀趺坐》诗云:
四大谁从著故吾?十年浪迹寄菰芦。
闲来写个头陀样,且读青莲笑矣乎。[1]1322
就此,徐渭曾自云:“人生难逢开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耳。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只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抑闻山中有草,四时常笑,世人学此。觉陆士龙之顾影大笑,犹是勉强做作,及不得这个和尚终日呵呵,才是天下第一笑品。”[1]1322徐渭这里应是一种深悲之乐,就此似亦可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面对自然时才能开怀;只有表现独特时才能释怀;只有找回无饰时,才是最真切的表达。
在笔者看来,徐渭的这种快乐,显然是针对流俗来说的。其云:“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不知近日学王、孟人,何故伎俩如此狭小, 在他面前说李、杜不得,何况此四家耶?殊可怪叹。菽粟虽常嗜,不信有却龙肝凤髓,都不理耶。”[1]461(《与季友》卷十七)如果说这种针对性使他从不同角度涵容了自己的品格,那么显然我们没有理由去对此做抽象的误读。
二、人生超越的全方位开启
如前所论,如果说,他的个性出于“真我”理想,那么纵观《徐渭集》会发现,他一生均因个性导致心目之中更伴有理想掩抑的困惑。
徐渭曾以赋一口气借牡丹、菊、梅、荷表达了真我之品格和以真我涉世的困惑,且看他笔下的梅花“孤禀矜竞,妙英隽发,肌理冰凝,干肤铁屈。留连野水之烟,淡荡寒山之月……侧披断碛,委朔风其将吹。”[1]41这就是说,徐渭个性虽出于“真我”,虽表现于理性、率性于平常日用,但不可否认它却是一种带有困惑的个性。笔者以为,徐渭的这一困惑归根结底乃在于表现为志与命的不相谋,虽然这是中华历史上许多志士的共同命运,徐渭的不同显然在于他的个性又激发了这种矛盾性,即志愈高而命愈薄。
首先,且来看一下由个性所支撑的志与命。徐渭的志高诚如其个性,然究其实却不仅是自然与生俱有的,而是接受王学思潮对自己思维进行提升的。换言之,其志是以逐渐接受王学而具体化的。这样一来,就显然超出了徐渭的个性真我。关于徐渭与王学一般来说可以搜集到以下思路及其资料:
从史料可知,徐渭接受王学较早,一生均接收王学。王阳明生于1472年,比徐渭大四十九岁,是徐渭同乡。徐渭出生之初,王阳明刚率兵平宁王朱宸濠之乱,任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时,王阳明的学术亦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3]1271。徐渭的几个师友均是王门弟子,如季本、王畿、钱德洪、唐顺之。王畿被后世视为王门左派的代表人物。徐渭作为弟子尤其表现出对其师季本的尊重,据他自己说“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1]1331(《畸谱》)。“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1]638(《自为墓志铭》)
其次,徐渭全面接受王学是为了对自我个性内涵进行充实、提升。对此他自己这样解道:“某始见先生时,未始学也,既稍从事于学而先生则以殁。”[1]617
再次,尤其是徐渭在将自己的个性涵养安排到开放的同时,又始终深怀忧患,时刻警防自己陷入世人的平庸,因此在个性充实的同时,又主张为人应保持夕惕若厉的状态下志趣才得以洗凝,从而使其理性思致、冷静。
笔者在此下这些个断语主要是依据他全面接受他的老师季本的理论,他在《读龙惕书》[1]677中曾阐述对季本之说的理解云:(1)理想只在于它是理想,即所谓的“以自然为宗,不能整齐划一,不能无弊”,因此先圣主张“惕”正是为了时时处处慎之于心,涤除伪自然。(2)奔向理想的过程是向往与功夫的统一。(3)致使功夫者虽取法不同,然就其根本在于“惊惕”,以“惊惕”的心态而主变化才能获得成功。而惊惕者,主宰惺惺之谓也,因动而见故曰惊化,能惊惕才能获得当变而化。
由上可结论,徐渭的理性在于始终依儒以立。如果说他的努力在于思致始终被推及到宏大的人生背景上来,那么,他的冷静在于能接受老师以“望到岸”以显自由;如果说愿以功夫致狂,那么他最终以龙惕的心态来使内涵更充实朗硬。
在他看来,初学与圣贤以“用力疾徐亦因而异然,因时知惕则一而已矣。此皆龙德之所为也。”如果说,徐渭将自己的真我安排为以个性而表现的坦露状态,那么他正是在此以对季本《龙惕书》创造性的理解才得以落实,而安排为告别仕途使志得到全方位施展则是其最终结果。徐渭在其后期接受别人对其张颠的称呼,盛赞王维最先出格的雪中芭蕉的构思,恰意味着他认可了张旭、王维的那种表面癫狂,内在理性;表面个性,内在理性持守的心灵状态。
综上所述,应当说正因为有这种龙惕心态,徐渭逐渐修葺起了他的志高。笔者以为,其实还不仅如此。因为其志高,徐渭还最终走上了“立言”的陡峭之途,由此他也进入了王学的行列。关于此可从下几点分析:
其一,据徐渭言,他中年以后曾以追寻以李贺为代表的中唐诗文来更进一步解构自己依然还有困惑的功名心。其在《与季友》书中感叹云:“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不知近日学王、孟人,何故伎俩如此狭小?在他面前说李、杜不得,何况此四家耶?”[1]461《四库总目》就此亦云:“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魔趣”亦未必就是反义词,在笔者看来,也可视为四库学者对其自我攀登思维陡峭以别样立儒的别样标识的肯定。
其二,徐渭曾依立言深入表达挖掘王学给予自己的启示。
徐渭的立言系统表现在七篇《中论》中,在此他以明确的思路,彰显了综合三家、融通王学所结成的理论框架。
(1)徐渭首先界定圣人,他以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一句话让原来的圣人、原来的格调、原来的正统,一以干爽现底,在此,个性纯情,真我高度一体。
(2)至于凡圣本质在于凡圣为一。
凡圣一致于何处?统一于一,在这个层面是一致的。
(3)以为人之情贵中时,其云:“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1]488
综上,不难看出,在徐渭的思路中,他并不想纠结于凡圣两极,而始终更愿意表明自己处在由凡入圣、超凡脱俗运作中。由此理解徐渭也许更真实,会发现他标举的“真我”也许更在于此。在徐渭看来,“中”的特征在于是“时中”,它是与时偕行的。徐渭以为“中”亦可反转为主体理解的,即不是简单地去抓住一个外在实体,而是抓住于此之中的自我体现,以为须“悉视其人也”[1]488。总之,如果说“真我”是他早已标明的个性路标,那么徐渭以《中论》立言表明他一直都在营造的思维空间,经过艰辛的努力,徐渭才终于搭建了“真我”框架。
三、苦难,超越欤?审美事料欤?
从资料可知,徐渭之命运一直为许多学人所广泛关注。世人所关切所聚焦者,笔者以为有以下两点:
其一,同情徐渭命运多舛。据史料载,其父鏓始以龙里卫戍领贵州乡荐知巨津川,后官至夔州府同知。他生母乃其父通房丫头。大约是其出生刚过百日,父不幸病故,十岁时其生母被嫡母(父续弦正妻)苗氏所放逐,又四年,嫡母病逝,徐渭最终依异母兄徐淮。徐渭虽自幼聪颖,八岁学作八股文,文思敏捷。但科场一直不顺,除嘉靖十九年(1540)二十岁获秀才资格外,一生历八次科举均不中。
徐渭以才学受浙江总督胡宗宪器重,以白衣秀才受聘为总督府幕僚,但在此多是受命一些“无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因被弹劾与严嵩一党有牵连而逮捕,徐渭不仅因此失去幕僚身份,而且恐遭牵连,以致绝望,终以杀其妻(张氏为胡宗宪介绍)入狱。徐渭除杀此张氏外,年轻时入赘潘氏家,潘氏却是因生子死于非难。徐渭的上述曲折命运为世人所同情,学人习惯于将对徐渭的理解放到此背景之上。
其二,聚焦探索徐渭越来越茫然的无奈。
学人强调,徐渭一生亦曾反复咀嚼自己的命运云:“四时惟听雨,无日不惊秋。”[1]1315对此必须承认,徐渭曾于晚年为自己撰写了自传《畸史》。其实,世所周知,他在四十五岁时即自著过《墓志铭》,全面总结自己,个中亦透彻着无奈。
徐渭在自己撰写的墓志中亦撰述过其师季氏的行状,并与自己做了比较:
(1)徐渭倾慕季氏有明确的应世目的并获得成功,以为这是他最值得称颂的原因,通过比较最痛惜自己虽认同季氏的应世方式,却终以失败而告终。
(2)徐渭特别敬佩季氏以整治性情为目的所露的情怀境界,他表示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理解与期望走向季氏之由。并于此深感自己深陷悖缪。
在笔者看来,徐渭借以反思的依据是相互深交的知己,他期待通过比较师友,彻底寻求环评自己。他称许季氏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的人生。不难看出,人到中年的他亦在不时环顾着他的坎坷人生,由此他并不只是感到人生的无奈。如果说,他曾刻画自己云:“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1]1325,那么他也更深刻地体悟到:“义利关头三岔路,乾坤窝里一家人。”[1]1059由此我们能感到徐渭思维的一个明确特征,即徐渭已逐步将他的曲折苦难变成审美的事料。
换言之,徐渭以这样方式应世,从奋斗人生的角度来说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失败或用失态、颓废衡量之,学人亦多有兴趣于总结其人生,从而挖掘出更深刻的人生滋味来。在笔者看来,他的价值在于终于能够以向死之生转而起死回生②,人生在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斑斓色彩。在本文看来,徐渭虽除中年做了墓志以外,在晚年又做《畸史》概述其生,而其人之一生却怎一个“畸”字了得?
首先,命运之艰,导致徐渭无法实现将士人的使命、人生的思考成功安排为出与处、朝与隐等饱含传统文化意蕴的诗意氛围之中来落实,这就使他和文化传统中从陶渊明以来的许多名人不一样③。他曾借咏竹云:“四时惟听雨,无日不惊秋。”[1]1315
其次,不难推测,蹇祚的人生旅程虽导致他将其人生体验思路安排在一个残酷的生死背景上执行,但同时又使他因此支起艺术魔趣之床。不难看出,徐渭的心灵之渊,一方面是志与命关系的错愕,另一方面是他因此不断整肃自己的个性。诚然,如果说志与命二者在其心灵所致乃严重的错忤,那么二者又以交相作用转化而导致了徐渭对艺术的独慧。
例如:
(1)深入花丛之中,徐渭独赏百花的无情有格。其《午时花》云:
花品将题感客怀,年来倍更困尘埃。
谁知草木无情物,不到时来也不开。[1]1284
又其《巨石杏花》云:
太湖五尺石头新,勾勒寒梢已逼真。
杏花虽是无情物,遮却腰间怕见人。[1]1320
(2)对于百花丛,徐渭尤其赏其结成的自然氛围。其《荷花》云:
茨菰叶碧蓼花白,菱子梢黄莲子青。
最是秋深此时节,西施照影立娉婷。[1]1306
其《牡丹》云:
醉余洒墨暮窗寒,竹下花枝艳洛阳。
共指萧娘骑凤去,翠裙拖处尾偏长。[1]1306
(3)尤其是,徐渭特赏自然百花的向时之奇。其《秋海棠》云:
海棠花本春园丽,开向秋时别种奇。
赖得画工加点缀,竟将颜色门垂丝。[1]1284
其《蔷薇芭蕉梅花》云:
芭蕉雪中尽,那得配梅花。
吾取青和白,霜毫染素麻。[1]1306
其《榴实》云:
秋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
深山绍行人,颗颗明珠走。[1]1303
其《岁寒三友图》云:
罗浮仙子喷香风,万壑惊涛舞玉龙。
君子同心坚岁晚,不随桃李逐春融。
(4)赏其枯膏结蒂。其《山茶》云:
叶须犀甲厚,花放鹤头舟。
岁暮饶冰雪,朱颜不改观。
其《芙蓉》云:
丛藜恶棘穿根切,大柳深江浸瘿眠。
其《菊花》云:
曾是将军莳菊余,尚遗秋雪一藤癯。
综上可说,其实“真我”亦好,个性亦好,自然景致亦好,徐渭最终均安排到艺术之中落脚,在艺术层面上交融。他同时代的人亦即从这里来对其人生价值进行回溯、评价、肯定的。
据陶望龄《徐文长传》“尝大酒会,文士毕集,胡公又谓之文语曰:‘能识是为谁乎,茅公读未半,’遽曰:‘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谓渭曰:‘茅公雅意师荆川,今北面与子矣’。”如果说其心灵世界乃向死之生,那么显然他在此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性。
徐渭曾有意与松竹梅兰构成五友斋,其云:“松竹梅兰,四君子落落孤标,谁可如侬朋友社。”[1]1062在此又高度体现着他的独慧。由此可结论,他身心的超越性在于其思路正是在自觉状态下密联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氛围。
再次,徐渭的此种特异个性,还在于能因此转化为艺术创造的笔力,成为审美价值的涵容品性,并由此成为审美的驱动力,从而徐渭对世界及心灵表达有超人的迅捷和独特的表现力,而我们显然能透过此找到他所以能达于艺术成就的切入口与征信。例如,他写诗反对模拟之风,旨在于别无选择。其《叶子肃诗序》云:“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与鸟之为人言矣。’”[1]519
又例如对诗的欣赏力图自成别趣与别致。其《与钟天毓》云:“读来诗细腻中有老刺,老刺中有娇丽,且复间出新诗,真可谓大作也。嚼之不已,更有余味。”其《选古今南北剧序》云:“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1]1297而达到的效果则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1]482”(《答许口北》)。不难看出,他的这些理论均具有明确理性,并通过各种不同艺术主张而发散,从而显得多姿多彩。例如,写曲主张人质朴,还原真我之境。其《西厢记序》:“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咰咰也。”[1]1089
写字博采宋元而成于天成。其《跋张东海草书千文卷后》云:“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凡此种种,上述这些均在于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于己而不由于人也。蔽莫蔽于不出于己而由于人也,尤莫蔽于罔于人而诡乎己之所出,凡事莫不出而独于书乎哉。”[1]1090他曾经将历史上许多书法大家放到一起加以评论,然后指出自己为什么要学索靖。其云:“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入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则超而倣篆,分间布白指实掌虚,以为入门。”[1]1054徐渭曾特别批评了赵孟頫的媚处[4]。而他自己作画聚焦花鸟等,是以特写、以大写意笔触夸饰意愿,其《墨丹图》云:“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主,虽有生意,绝不是此花真目的,盖余本要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贵,风若马牛,宜弗相似也。”[1]1310又《雨中兰》:“昔人多画晴兰,然风花雨叶亦见生动,白玉蝉云:‘画师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可得其之味矣。”
在此,所要特别说明的在于,徐渭的追求与行为并不是为了标名,或曰标名以画,而是由个性自成其质,他如此的才气与审美理念也在无意之中产生了。亦正因如此,就既和公安三袁不一样④,也显出与宋代以来倡导的文人画不一样[5],与以意为诗不一样。此虽可说是徐渭的创造性,但同时亦是他致命的薄弱点。我们正好亦可以从中侦破他与道学更深的不同。世人论文长之画的思路习惯于找寻他关于绘画的一些论述,例如:
(1)游戏遣兴
平生江澥心,游戏翰墨场。[1]1310
尽取破唐聊遣兴,翻引长涎湿到鞋。[1]1305
(2)刻意、天趣
只开无趣无和有,谁问人看似与不。[1]1307
(3)抹笔
此抹扫乃京邸笔,携来重观可发一笔。[1]1306
笔者以为,徐渭的创造性在于仅就这几点就与宋代既有的文人画不一样,在徐渭这里所能亲切感到的是“我非庄惠俦,亦能知尔乐。墨池水自深,天机任潜跃。”[1]1313其《山水》诗云:“木叶点秋风,虚亭映远空。波光流不定,山色有无中。”[1]1312笔者以为,宋代的文人画,意指宋代士人怀抱着一种明确的人文理想。或言之,宋代人文理想在绘画中有着极其明确的形成印迹,具有极有魅力的价值应对潜能,因而呈现着由理性营造起来的活泼的生命力。而与之相比,徐渭追求“始于学而终于天成(《跋张东海草书千字文卷后》)”标举“天机任潜跃(《游鱼》)”,显然更是以天成为旨趣,然虽讲“天机”、讲“真我”,却暴露出令人所不能有深刻迸发的空洞。
如果说文人画是指画从构思到运笔表现着道学的明确性,徐渭在此至少是淡化的,或说没有深入下来有意涵容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感,或者说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境地,因而就不同于宋代的文人画。
另外,笔者把徐渭搁置在文人画之外,还在于徐渭的花鸟经常只注意处于悬置而表其痛快淋漓,虽此也不可否认包含关于个性的隐喻,但儒者那种天人情怀显然要差点。从中国绘画史上可知我们通常所谓宋元文人画是流贯于道学,流韵于逸气的,无论怎样去看它们,都不能否认它们已经以自己的成功树立在徐渭之前。徐渭的绘画就算是有特征,但若要靠文人画价值观品评必须要以之与发生在前面的成功作比较。而本文以为徐渭非文人画是想结论他的画是宋元文人画的变异。对于他的这种认定并不是否定,笔者在此是想提醒,要理清它(他)更需理清关乎他文艺的种种现象及成果。
笔者在此想要得出的结论是徐渭的成就不在于模拟,不在于相仿,而在于自成,而所以有这样的结论则始终在于他追求以表达“真我”为旨趣,是以“真我”显露来切入的。而他的弱点也正好能从此见出,即是说虽有个性,但缺乏充实的内涵。
注释:
①在笔者看来,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一生往往纠结于得志与否,出世与入世问题矛盾,身心人格操纵与衣食情怀的困惑之中的,他们的思想也是即此的深发。
②向死之生与起死回生应该说可作为两种审美观:一个强调悲壮,一个强调悲情。
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受人尊敬的先贤其魅力即在于能将对人生宇宙的感知结合着出与处、朝与隐、得与失上来执行,因而有宏观宇宙意识。
④徐渭之后的公安派以举“性灵”标个性,究其实是形成与感性的空框架。徐渭虽亦有相似之处,但不标榜,更强调自然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