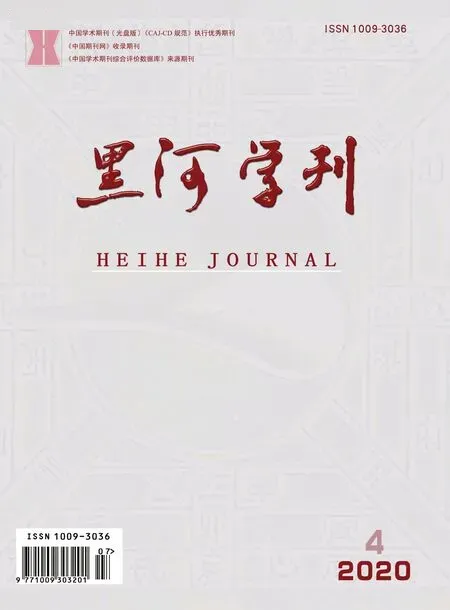浅谈存在主义视野下高职院校师生观的建构
徐代珍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湖南 益阳413000)
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强调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忽视主客体双方特别是客体的特殊性,从而在自然界、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自然与人、生活与个体、他人与自我的对立,反映在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作为实践的主客体被剥离开来,师生关系成了附属于教育和教学的产物或附属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师生关系被宣染着强烈的强迫、专制色彩,这一切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师生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才是对师生双方主体性的澄清?存在主义用存在本体论使哲学重返前柏拉图时代的始源本体论语境,高度宣扬存在的主体性和主体之关联性,警示人们体悟真理的本意,关注现实中的人存在的生命意义,对高等职业教育有很强的借鉴与启发作用。
一、对话与交流:存在主义教育观下的师生观
存在主义强调敞亮、绽放地生存,重视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交流。
(一)教师—引导者和监护者
存在主义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教育中强调学生的一切都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但这并不是否认教师的作用,而是要求教师在维护学生的主体性的同时也要维护教师自己的主体性。
首先,教师是帮助学生吸纳知识的引导者。教师不能屈服于教授或行政领导的要求,也不能屈服于外在压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是出于本心,引导学生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服务。在教法上,教师要体现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除了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外,还要灵活运用各种教材教法,使学生吸纳这些知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指教师不能只成为学生学习知识和构筑道德规则的灌输者;“有所为”指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把学生作为一个“此在”的人而不是物来看待,避免课堂教学中的拔苗助长和个人独白行为。“在充分讨论之后,教师向学生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观点,然后问学生是否接受这一观点”。[1]
其次,教师是学生学习知识过程中的监护者。教师在向学生提供知识和道德规则的过程中,对学生的创造性、能动性实施监护者的责任。人的本质是人选择的结果,教师也不例外。教师有选择“为什么教”的自由,也有选择“怎样教”的自由,在选择的过程中,教师要体现作为学生监护者的责任意识,“教师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教师身上转移到学生的自身,而教师本人则退居暗示的地位”,[2]所以教师不能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随意给学生贴上各种“标签”。同时,教师在自由选择的同时,还要有影响学生的意识和责任感。“意识到自己是一切事物中想要影响整个人的唯一实体,并从而产生责任感,即感到他负有给学生提示对现实应作抉择的责任。”[3]302教师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信奉的原则,以及自己之所以信奉这些原则的理由告诉学生,至于学生是否接受,教师不必强求。也就是说,教师对学生发挥的作用应该是“生产性”而不是“复制性”的。[4]
(二)学生—自由者和选择者
一方面,学生是独立的个体,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选择的严峻性,对此良心会详细地告诉自身,同样也不应由外界的判断来承担责任”,[5]64受教育者要主动地、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天赋的潜力,使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得到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学生要有意识地、当机立断地选择,并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做的是让学生认识到,每一次的选择都关乎自己今后的道路选择。学生要对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承担责任,因为“凡是不再能全副精神决定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并对这种决定负责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心灵空虚的人。而一个心灵空虚的人立刻就不成其为人了”。[3]312
(三)师生关系—“我与你”的对话或交流
教师和学生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主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哲学家马丁·布贝尔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当作主人与物品的关系,学生完全由教师摆布,师生之间形成了“我与它”的关系;另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存在主义者认为,要促进学生的自我生成,必须在“我—你”的关系基础上进行对话或交流。
1.“我—你”:存在主义教育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我与你”(I—You)关系的前提是相互信任。当教师充分信任学生时,学生就能充满激情地、积极地生活;也可以帮助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低的学生顿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教师只能以他的整个人,以他的全部自发性才足以对学生的整个人起着真实的影响。因为在培养品格时,你无需一个道德方面的天才,但你需要一个完全生气勃勃的人,而且能与自己的同伴坦率交谈的人。当他无意影响他们时,他的蓬勃的生气向他倾注着,极其有力而彻底地影响着他们”。[3]301可见,教师的人生态度和对学生的坦诚程度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师生之间因为世界观、人生观等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应增强,同时运用自己的洞察力、经验和爱使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发挥作用,化解矛盾和冲突。
2.对话或交流:存在主义最完美的教育形式。雅斯贝尔斯认为青年学生“已清楚地意识到要成为完整的人全在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并取决于日常生活的指向、生命的每一瞬间和来自灵魂的每一冲动。毋庸置疑,年轻人都希望受教育、能从师获益、能进行自我教育,并与人格平等的求知识获智慧的人进行富于爱心的交流。”[5]1-2这种“对话或交流”指向的不仅是沟通,而且是面向存在,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对话(或交流)是让人(生存)“不脱离更新、更深刻的生活基础的唯一办法”[6],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同样适用;“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5]12。
总之,“我与你”的“对话或交流”要求师生之间没有任何距离和隔阂,需要双方发自内心的真诚、理解、信任,需要热情和爱,保持“真我”。
二、走向关怀:存在主义教育师生观的终极要求
存在主义教育观照下的师生观引领着人们回归充满温情的教育世界,其终极目的是要让教育走向关怀,从对知识的关注转向对人的思考。
(一)关怀是人类的一种存在形式
关怀自古以来就是与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关怀既是人对他人生命所表现的同情态度,也是人在做任何事情时严肃的考虑。关怀是最深刻的渴望,关怀也是一瞬间的怜悯,关怀更是人世间所有的担心、忧患和苦痛。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关怀中,关怀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7]。关怀也是良心的根源,“良心是关怀的召唤”并且“把自己显现为关怀”[8]。
(二)“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是一种关怀关系的形成
师生之间“我与你”的对话是师生共同进行的交流活动,“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9]雅斯贝尔斯也指出,“在……(存在交往)中,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连,处于一种身心敞放、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因此,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5]2当教师和学生作为独特的精神整体、完整的人相互作用,最大程度地相互沟通和理解。
(三)“我—你”的关系是师生关怀关系的表现
关怀是人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根本,是人对其他生命表现出同情态度后的一种情感和行为的拓展和延伸,也是爱的重要表现形式,“爱本为每一个我对每一个你的义务”,[10]有爱就有关怀的存在,没有关怀也不会有真正的爱,关怀是孕育于爱之中的,体现了对所爱者的生命与成长的主动关切,这种关切是“我—你”关系的基础。“我—你”的师生关系是以尊重、责任、民主、对话为基础,以关怀为首要的、根本性的交往原则,是师生关怀关系的表现,预示着关怀的“在场”。
三、反思与借鉴:高职院校师生观的建构
受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高等职业教育正逐步实施“专业+项目+工作室”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再加上高职院校迎来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提升服务能力。教师与学生做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主体,必须通过自发性学习和行动研究来不断发展学生学的能力和教师教的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师生关系亟待改善,而存在主义“我—你”、对话或交流、教师和学生主体地位的强化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一)重塑教师形象,实现多种角色的统合
要进行高职院校师生关系的重建或改善,必须变课堂主体、知识权威为教学主体,而不是以有限的知识去说教看似无知的学生。教师应扮演引导者、指导者,与学生共同探究和反思。一方面,指引学生学生搜索更多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打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教学中不断反思。教师在角色统合的过程中,既是学习者又是教育者,帮助学生逐渐成为顿悟和构建新知识与新技能的新型人才。
(二)重视学生和教师“双主体”地位
重构师生关系不仅要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且要促进教师的发展。在学校教育场域中,学校要为教师提供足够的时间、空间,鼓励教师争当学校的主人,为教师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也要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示个人才能的舞台,例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立德树人是检验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
(三)加强对话交流,促进教师观与学生观的适配
“互联网+教育”视域下新型师生观关系的重要保障是教师观和学生观的匹配。慕课、微课、云课堂、翻转课堂、智慧树等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所接纳和应用,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就在于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及时的满足和反馈,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反应,帮助学生适应新的教育教学模式,构建教师和学生互教互学的关系,在思维品质培育、语言与思维的融合、认知与逻辑的统合等方面达到统一。
师生观是师生关系的重要内容,是高职院校建设“双高计划”,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新形势下,构建关怀型师生关系不仅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而且需要高职院校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协同共生,促进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