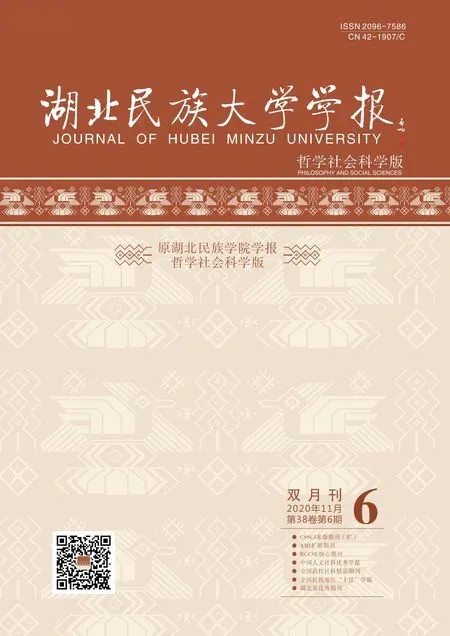朝鲜时代《燕行录》与清代满族女子的域外镜像
姚晓娟
一、引言
朝鲜半岛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与中国交流频繁,往来密切,特别是明清时期,高丽及其后的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每年都会定期派使者来华朝见,少则一年二次,多则一年六次,这些外交使节及随行人员将沿途见闻以日记、小说、杂录等形式记录下来,统称《燕行录》。《燕行录》内容丰富,数量庞杂,几乎涉及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是域外视角反观当时中国的宝贵文献,其中不乏一些鲜为人知的珍稀史料,可以弥补本土文献的缺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当时汉文化圈的中心,对周边的成员国产生了巨大辐射作用,朝鲜王朝与中国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对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变化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明清易代,面对神州陆沉的惨痛现实,饱受程朱理学“华夷观”和“事大至诚”意识影响的朝鲜王朝对异族建立的政权充满了无奈,甚至敌意。对满族这样一个在风云变幻之际与金戈铁马之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充满了好奇与不甘。因此,入清燕行使以十分细密的眼光审视着满族群体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满族女子则以精致的妆容、奇特的服饰、洒脱的个性、尊贵的地位引起了朝鲜使臣的格外关注,纷纷将其诉诸笔端,缜密又翔实,琐碎且不乏精细,以生动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满族女子的鲜活面貌。清代满族女性生活的历史印记,就犹如零珠碎玉一般镶嵌在浩瀚而庞杂的燕行文献中,排沙拣金,往往见宝,《燕行录》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清代满族女子生活的域外观察史。
二、民族特性与满族女子日常生活的域外剪影
《燕行录》内容繁复,书成众手且前后相袭的情况频现,燕行使对于满族女子的描述大多较为零散,缺乏统一性与整体性,常常呈现片段式的描写特征,梳理其中,将这些零散的印记勾连起来,不难发现朝鲜使臣的关注焦点,而这恰恰又是满族女子特有民族风貌的再现。
(一)“花”与满族女子的不解之缘
“满鬓插花”是朝鲜燕行使对满族女子的第一印象,花与满族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生活中养花,市肆中卖花,且头簪花、衣绣花、鞋带花。“满鬓插花”的习俗源自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花朵驱邪作用的虔诚信奉。满族民居庭院内井然有序,庭院中绿植繁茂、花草众多, 富贵大家甚至还有专门的花草舍。乾隆四十三年,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朴趾源记述在栅外寓居的满族鄂姓人家的庭院布局时写道:“北庭平广,葱畦蒜塍,端方正直。瓜棚匏架磊落,阴庭篱边紅白蜀葵及玉簪花盛开。簷外有石榴数盆及绣球一盆。万秋海棠二盆。”(1)朴趾源:《热河日记》,《燕行录全集》5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92、316、289、324页。道光二年出使中国的徐有素记载富贵大家不仅有祭祀之室、迎客之馆,“又有燕饮别堂,行淫密屋及酒房记室漏室,梅榭莲亭,禽兽圈、花草舍此等别屋无数”。(2)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48、152页。事实上,燕行途中的满族人家,放眼望去,庭院中皆是护阶绿竹、花草盈园等自然景观。庭院中的鲜花自然成为满族女子日常装扮的绝佳佩饰,如“以茉莉、兰馨、野蔷薇、蕙兰为主。鲜花具有多种象征意义……在祭祀中,族众戴花环。其他野花,如芍药花是驱除恶魔的吉祥物。声息花则用来敬神,寓含人类对神灵的虔诚。”(3)刘铮:《燕行与清代盛京——以〈燕行录〉为中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201页。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以及美的追求和宗教祭祀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庭院种植花草、女子满鬓插花早已成为满族独特的生活习惯。燕行使来华,发现途中“卖花者极多”,花草铺与酒肆、书店、毛皮铺子、药铺等一齐呈现了市井奢丽、车马骈阗的大都会气象,鲜花不仅可以用来插在鬓上作为装饰之用,还可以制成香粉、胭脂涂于脸上,因此“厚涂真粉,满鬓簪花”的满族女子便成为朝鲜使臣燕行途中的一道靓丽风景,满族“女子无论贵贱,长幼无不靓粧,服饰必欲华丽,虽白发老妪及行乞之女皆傅粉簪花,其俗然也,故所见绝不见貌丑者”,②嘉庆二十三年,出使中国的成祐曾写诗:“红是芙蓉白水仙,簪花色色斗婵娟,问尔村婆倭堕髻,缘何霜鬓学青年。”(4)成祐曾:《茗山燕诗录》,《燕行录全集》6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86页。由此可见,“鲜花满鬓,香粉傅面”使得满族女子在人群中格外亮眼,燕行使李海应认为相对于形态袅娜的汉女,“满女容姿举多娇艳,而亦丰厚硕大,间或有丈夫之像”,(5)李海应:《蓟山纪程》,《燕行录全集》66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72、574页。朴趾源则直接得出“满女多花容月态”的结论。
满族女子同男子一样喜欢着黑色长衫,燕行使来华,途中所遇满人第一印象便是衣着尚黑,乾隆五十八年李在学观察到满族男女喜穿黑衫的习俗,“村中诸人群集纷聒,俱服黑色长衣,莫辨男女”,(6)李在学:《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58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1页。为此作者还作诗打趣道:“银钗乱插又花枝,面皱头蓬尚粉脂。一样长衣浑黑色,似乌谁得辨雌雄。”(7)李在学:《癸丑燕行诗》,《燕行录全集》57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80页。显然,满族女子头上五颜六色的鲜亮花饰在黑衫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夺人眼球,甚至成为满是黑色簇拥的人群中,区分性别的重要标志。花枝招展的满族女子常令朝鲜使臣印象深刻,使臣李海应在《蓟山纪程》中记载:“女人被绮罗,涂粉簪花。”⑤洪大容亦指出,满族女性“总发为发髻,穹其中,而盘其端,可三四旋焉。周簪小笄以安之,遍插彩花,虽老寡妇不去也”。(8)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42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46、441页。事实上,满族女子的发饰根据年龄的差别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对此朝鲜使臣观察到“十数岁以上,惟留顶后数百茎,分三条为辫子,贵贱同然”;⑧“满洲女孩婚前多梳辫,额头留‘刘海儿’”。(9)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5页。出嫁后的女子头饰为“围髻”,(1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八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如朴趾源就曾遇到一位满族女性,依据其“髻发中分绾上”的发饰特征,确定其为待字闺中的少女。但无论年龄大小、发式如何、婚姻与否,满族女子“满鬓插花”的习俗都不会因为上述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朴趾源在通远堡见到一位年近五旬的满族主妇,“满鬓插花,金钏宝珰,略施朱粉”。①在塔铺遇到老妪,头插红白葵花,随正使在一鄂姓满族人家,发现主人母亲年近七旬,犹“满头插花,眉眼韶雅”,①甚至“颠发尽秃,光赭如匏,寸髻北指”的老妪,“犹满插花朵,两耳垂珰”。①曹雪芹作为包衣的后代,在《红楼梦》的创作中留存了诸多满族文化的印记,其中就有关于以鲜花制香粉、簪花等情节的描写,主人公贾宝玉就曾将茉莉花制成香粉赠予平儿使用,刘姥姥喜游大观园时,适逢下人将刚采摘的鲜花奉于年迈的贾母,伺候其簪花,王熙凤则故意将五颜六色的鲜花插于姥姥头上,引众人大笑不止。实际上,“头插乱花”的现象何止出现在小说里,据燕行使崔德中记载:“宁远以东多是胡女,而内外不分,露面出见,唐女则内外甚密,而胡女头插乱花,金玉饰头,着长衣缓缓而行。”(11)崔德中:《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二辑第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4页。可见满族妇女无论年龄大小,皆以插花为美,以簪花为俗。
满族女子善养花、常簪花,也爱绣花,满族衣饰、鞋靴,包括绣囊都十分讲究绣花纹样。事实上,着绣花纹样衣饰的传统由来已久,《金史》曾载:“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傍复为双襞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带色用红黄,前变垂至下齐。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此皆辽服也,金亦袭之。”(12)脱脱:《金史》43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5页。满族女子喜爱穿绣花纹饰的衣裙,连老妇亦不例外,如朴趾源在塔铺便遇到一位满族老妪,“衣一领鸦青桃花绣裙”。不唯如此,满族男子衣饰也着绣花纹样,如作者在栅门遇到的“胡商”,亦有身着“绣花绸衣”者。精致考究的绣花纹饰非常吸引朝鲜使臣的目光,燕行使在途中常常看到忙于刺绣的满族女子,如咸丰五年,以姜长焕为书状官的朝鲜使团行抵沈阳时,见“胡人凡大小事役,男子悉任其劳,凡织布、裁缝、舂米、炊饭等事,亦皆为之。女子则不过缝鞋底,或刺绣而已。”(13)姜长焕:《北辕录》,《燕行录全集》77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43页。不同于汉族女子全面操持家务的烦琐活计,刺绣女工则是满族女子日常居家生活最主要的任务,而在汉族男子看来本应为女子所做之事,如裁缝、舂米、做饭甚至织布等活动在满族百姓生活中,则由男子承担。正如洪昌汉《燕行日记》所载:“胡人之女,工针履底而已,无服之事,汲水炊饭之事皆男胡为之。”(14)洪昌汉:《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9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26页。精湛的刺绣工艺令一向崇尚简朴的朝鲜文人大开眼界,道光二年,出使中国的徐有素记载:“世间之物无不可绣者,其精丽犹胜于笔墨,人物之毛发、颜色,禽兽之毫羽文采与夫花果草木之文理色态,笔画之所不能尽处,以绣则无不臻其妙。”(15)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92、157页。同时,绣技的高超还体现在绣囊的制作和使用上,“绣囊,俗名荷包,或称凭口子。烟袋、烟包、槟榔、茶香之类装焉,斑布、洗巾、扇袋、粧刀、火镰具焉。”(16)金景善:《燕辕直指》,《燕行录全集》72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1页。使臣李田秀《入沈记》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囊制有二:其一制小,以红锦为之,而刺彩绣佩之袍带者也;其一制大,向外者以朱皮为之,加黑缘向内者以白皮为之。”(17)李田秀:《入沈记》,《燕行录全集》30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56页。李海应还将满族绣囊与其国做了对比,指出:“囊子大异于我国之制,然甚小而必以纹绣,又有烟竹囊、烟茶囊,而此则多用皮革,左右佩绶,可谓累累若若矣,谓荷包者此也。”(18)李海应:《蓟山纪程》,《燕行录全集》66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37页。事实上,佩戴绣囊是始自满族先民的一种风俗,满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佩戴绣囊。徐有素《燕行录》描述满族男子“衣之内外,遍佩荷包香囊,内储香,香气常逼人”。④朴趾源《热河日记》在栅外对所见满人有这样的描述:“群胡观光者,列立栅内,无不口含烟草,光头摇扇。或黑贡缎衣,或绣花绸衣,或生布生苧,或三升布,或野茧丝。袴亦如之。所佩缤纷,或绣囊三四,小佩刀,皆插双牙箸。烟袋如胡芦样,或绣刺花草禽鸟。又古人名句。”(19)朴趾源:《热河日记》,《燕行录全集》5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76、316页。不难看出,满族男女对绣有花纹饰样的衣服、绣囊等精美物件的喜爱。
和喜欢穿绣花衣衫一样,对绣有花草蜂蝶的鞋或靴,满族女子也是青睐有加,燕行途中,朝鲜使臣所遇到的绣花藤于靴鞋的满族女子比比皆是,雍正七年出使中国的金舜协记载:“其俗男子躬为女工,而女子则无织衽针线供馈之事,只作绣花女鞋及缕绯鞾底而已。盖其男女所着靴鞋等皆以黑缯为之,而罕用皮物,至于靴底则元不用皮,而以布罽缕绯造成,故家家女人惟造此物而已。”(20)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38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38、220页。作者燕行途中曾“夜宿于张俊云者家,见胡女服饰与男不相远,足着花鞋,身着长衣,其制下尖而无领,纽而有单枢焉。”⑨朴趾源《热河日记》描述满族女子:“满髻插花,金钏宝铛,略施朱粉;身着一领黑色长衣,遍锁银纽;足下穿一对靴子,绣得草花蜂蝶。盖满女不缠脚,不着弓鞋。”⑧满族女子喜欢穿高厚如屐的鞋子,这种鞋子既牢固又美观:“鞋之底以木为之,其法于木底之中部,即足之重心处,凿其两端,为马蹄形,故呼曰马蹄底,底之高者达二寸,普通均寸余。其式亦不一,而着地之处则皆如马蹄也。底至坚,往往鞋已敝,底犹可再用。”(21)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12页。花枝招展的满族女子配上花盆底的鞋子,走起路来自然是娉娉婷婷,摇曳多姿。
(二)“金银”与满族女子的喜好装饰
满族是个天生爱美的民族,对于金银饰物格外青睐,雅好文玩更是满洲贵族的习性。“穿金戴银”的民风习俗历史悠长,据《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2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页。《金史》载妇人“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此皆辽服也,金亦袭之。”(23)脱脱:《金史》43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5页。清朝建立后,满人不仅享有政治特权,经济上也受到额外的优待,事实上“从入关时起,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丁的差役、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在圈占京畿汉民土地分给旗人的同时,禁止旗民交产。(实际上只禁止民人购买旗地,对旗人购买民地却并不禁止)”(24)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据嘉庆二十三年出使中国的成祐曾记载:“满人生来十余岁属之旗下,皆有银料,故满人皆不贫。”(25)成祐曾:《茗山燕诗录》,《燕行录全集》6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99页。燕行使徐有素也了解到:“凡满人无论京乡皆入于仕籍、旗籍,各有恒产,故所至见满人其衣服外样皆非贫寠者。”(26)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29、158、157页。这项举措也为满族女子穿金戴银的需要提供了稳定的物质保障。
满族女子酷爱金银玉饰,“妇女则专用花饰,或生或彩,簪篦珠贝之属,满头缠插,老少同然。”(27)李在洽:《赴燕日记》,《燕行录全集》8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43页。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女人之髻,如我国(朝鲜)之围髻,插以金银珠玉为饰。”(28)李民寏:《建州闻见录》,《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八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金钏宝铛”的满族女子常令朝鲜使臣感慨不已,徐有素发现:满族“妇人所着花冠仿佛以珠翠金银遍饰之,一冠之资至千金云”。④满族女子的珠翠满头令金昌业“眼眩不可谛视”。(29)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3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6、64-65页。使臣崔德中的描述更加细致:“路逢一队胡女,则皆挂黑长衣,至踵而止。下着黑袴如男袴,纳唐鞋袜子,亦以青布造作。毋论老少,皆耳挂双珠珰,指着白铁环,而以黑帽罗裹头,或编发作环,如我国之制。不裹头者,或当脑妆以铅钿,状如圆镜,络以真珠,厚涂真粉。”(30)崔德中:《燕行录》,《燕行录全编》第二辑第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2-273页。由此可见,满族对金银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少、等级贵贱。贵者“穿金戴银”不仅是民俗与礼俗的标志,数量的多寡也是等级地位的象征。贫者就算老妪也仍是涂脂抹粉、珠玉满珰。满族女子不仅头饰金银,指环、手镯、耳饰也常常为金银珠玉所制,据燕行使徐有素记载:“所着指环名曰约指环,多水晶之属,侈者或金玉,而只单环,不用双环,或以银为长爪冒于指头指环,则男子或有着之者,女子两臂或贯青玉大环。”④至于耳饰,“则虽乞人亦皆悬之者,多或悬三四个,至于幼稚男子或有穿耳而悬者”,燕行使李在学对此俗非常好奇,“问之皆以为如此,则俗称长寿,故悬之云”,(31)李在学:《燕行记事》,《燕行录全集》5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2页。可见扎耳眼、穿耳环不仅是满族女子所秉承的旧有风俗,更寄寓了长寿健康的美好愿望,满族女子的“一耳三钳”更是引起了燕行使的格外注意,李在洽的《赴燕日记》中载:妇女“耳珠作数三孔,穿以珰环。”⑤李海应的《蓟山纪程》也载:女子“穿而悬珰,至三四环。”(32)李海应:《蓟山纪程》,《燕行录全集》66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73页。不仅饰品如此,就连纽扣有时也为金银珠玉所制,如李颐命就曾发现,“男女衣俱无袵,内外所着又无敛结之带,皆以小团珠无数纽缀”。(33)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燕行录全集》3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2页。金昌业在京城就曾注意到京旗提督之子的衣服无比奢华,其纽扣“内系青丝广组,其左右前后皆有镂金带眼,以前眼锁之”。⑦朴趾源在京城也遇到一位着衣“遍锁银纽”的满族妇人。
金银珠玉除了作为衣饰、头饰、耳饰外,还同象牙等珍品一道用来制成精巧的文玩,令满人尤其是贵族及富商大贾爱不释手,洪大容《湛轩燕记》记载满族“佩用多品,左右绣囊,俗名荷包,或称凭口子,烟袋、烟包、槟榔、茶香之类装焉;斑布、洗巾、扇袋、妆刀、火镰具焉。妆刀多用鱼皮牙骨,双筋抑于外,皇城人多以铁锁为索,不然行道必见盗剔也。其满洲多佩鼻烟壶,学生辈学为诗句者,又佩袖珍诗韵也。”(34)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42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43-444页。吸食鼻烟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习惯,进入中国后,曾在满族、蒙古族等草原民族间流传,后来鼻烟成为明清皇帝打赏王公贵族的礼物。作为鼻烟的盛器,鼻烟壶自然也成了权贵炫耀的玩物,更能显示主人的格调,水晶、玛瑙、玉器、象牙等各种贵重材质都被用来当容器,壶上加以绘画、书法、雕刻等。如朴趾源于栅门所遇见的“胡商”,则“无不口含烟草,光头揺扇……所佩缤纷,或绣囊三四,小佩刀,皆插双牙箸。烟袋如胡芦样,或绣刺花草禽鸟,又古人名句”。(35)朴趾源:《热河日记》,《燕行录全集》5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76页。不难看出,这些满族商人雅好精巧,品位不俗。
(三)“车马”与满族女子的奔走出行
生长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以游牧、打猎为生,习武骑射也被作为满族传统而流传,所以满族人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彪悍、英武、善于骑射。满族人认为万物有灵,在围猎、放牧和采集之前有祭奠神仙的传统,在满族看来是山神保佑了其围猎的安全,使他们获得很多猎物。一个满族男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寄予射鹄之志。“凡生男儿,则悬弓矢以门前志喜,六七岁时,即以木质弓箭练习射鹄……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配弓箭驰逐。少有暇日,则至率妻妾畋猎为事,盖其习俗然也。”(36)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校释》,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第44页。
骑射成为满族人代代相传的民族习俗殆非偶然,既是日常生活所需,也是维护政权所系,无论男女老幼,都以精湛的骑射技艺为荣,且早年女真人多以打猎为生,以猎物果腹。为方便骑射游猎,他们住毡庐,穿皮毛。这一方面是源于满族人世代依山林而居的地理环境因素,另一方面也与统治者推崇“国语骑射”的方针政策有关。清军在崛起和入关时,其军队主力即为骑兵,所以八旗兵必须具备精湛的骑术。崇德元年,皇太极就曾有“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的忧虑,并于三年后重申:“我国武功,首重习射”“切不可荒废,嗣后尔等当严加督率。”(37)《清实录》75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9页。雍正、乾隆两代皇帝曾多次下达谕旨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在皇帝的倡导和呼吁下,骑射之俗,蔚然成风。《入沈记》记载:“公主今方十一岁,亦能跨马而来”,(38)李田秀:《入沈记》,《燕行录全集》30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57、178页。“诸军聚会试射如前,问日日如此,则答如是云”,③崇武善射之风,可见一斑。
燕行使来中国常见满人有骑马者皆不用人牵马,大抵是骑术纯熟,风俗使然,且汉人不许乘马,故而燕行使常见胡人骑马者则不足为奇了,骑马不仅仅是满族的出行方式,更是其必备技能,甚至是其谋生之术。燕行使到达中国之后,遇见诸多表演骑射技艺的满族女子,骑术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如权拨《朝天录》记载蓟州“段家岭铺有二女,年才十五六,被彩衣骑大马,按辔徐行,行数步,跃马而来。于马上起舞,或以手攀马鬃,横载而驰,倒首于鞍上,两足向上,千变万殊,倏忽如神,观者如堵,争以钱购。”(39)权拨:《朝天录》,《燕行录全集》2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88页。
满族虽擅长骑马,然而以马驮载者绝少。稍有钱财者皆不乘马,可见日常道路出行则专仗车制,正如雍正二年来中国出使的金舜协所言“地宜使车,故毋论远近,凡有出入者必乘车焉,凡有运输者必用车焉。”(40)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38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32页。京城尤是如此,“北京市中,最多驾车必以马,否皆骡,骡力大故也。将车者持丈余鞭,坐车上,鞭不尽力者,众马齐力,车行如飞”,真可谓“车辙满路,纵横如织”。(41)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燕行录全集》3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4页。如道光二年出使中国的徐有素记载:“城内咫尺之地出必乘车,故京城街路上罕见步者,妇人则虽至贱流绝无步行者,又不见骑牛骑驴者,皆其所耻也。”(42)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2页。根据《燕行录》记载,太平车是最为常见的运送客人的车制,满族女子常常乘之,燕行途中,朝鲜使臣经常看到乘坐太平车的满族女子,燕行使李有骏记载:“每于路上见乘车者,辄有姿色车中坐者或至数三人,前揭门帘,全露身面,衣粧鲜华,各不谛视,颇有贞静之态,此皆朝士家妇女云。”(43)李有骏:《梦游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7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5页。嘉庆八年出使中国的李海应记载:“女子出入乘太平车,贵主命妇亦然,男子骑从之,往往露面朝外而坐,或深闭帘帷,而衣髻粧严皆从玻璃露现,盖汉女避人,清女不甚避人云。”(44)李海应:《蓟山纪程》,《燕行录全集》66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72页。道光二年出使中国的徐有素记载:满族“妇人之乘车出行,无不珠翠满身,香闻于远端,坐车上少不飞目邪视,惟逢我人或暂时开视之。”⑦同治五年出使中国的柳厚祚记载:“皇城之内,盛粧女子乘太平车不垂面帐,或追从,女子凭轼而行,此是朝士家妇人之类也云。”(45)柳厚祚:《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7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76页。由此可见,太平车设计精巧,实用美观,且因有窗、有盖,形似坐落在车轮上移动的房屋,因而也被称为“屋车”,满族女子乘之者非富即贵,即彰显了身份,又满足了乘者隔尘观光的需要。
三、“贵女”习俗与满族女子社会地位的域外考察
不同于汉女地位卑下,满族由于受到萨满教及母系社会的影响,女子地位往往较高,这令有着男尊女卑传统的朝鲜使臣非常惊奇,翔实记录了燕行途中满族女子优越地位的种种表现,如燕行使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录》载:“其俗大抵贵妇女而卑男子,虽遐乡下户之女华衣饰、静红粉、安坐闲游。汲水、炊饭之役皆男子为之。”(46)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50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68页。李有骏《梦游燕行录》载:“女子盛服明粧非游赏则罕出门外,所业不过缝靴底,而男子则大小事役悉任其劳,如舂米、汲水、织制等事,无所不为。”(47)李有骏:《梦游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7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35页。同治五年出使中国的柳厚祚记载:“织锦汲水炊饭等事皆男子为之,女子则抱幼儿横竹长游戏于门内而已。”(48)柳厚祚:《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7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74页。不同于汉女操持家计的奔忙,满族女子的生活显得闲适而肆意,甚至女工等活计都由男子代劳,因而引发了朝鲜使者“生于此土者,反是为女好矣”的感慨。于是男子织布往往成为朝鲜燕行使途中所遇的常见景观,如乾隆四十二年出使中国的李押记载:“今日殿中适见店主男子方织布,其机轴之制投梭之法与我国大概相同,而但以两匹互引机绳,用力颇省矣。问之曰:‘男耕女织,各有其任,今汝何为而织云?’尔则答谓此土女子虽或纺织亦不能工,故男子多为之者云。”(49)李押:《燕行记事》,《燕行录全集》52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67-368、44页。生活居家的满族女子日常所做不过炊饭、缝履底而已,除干活少,满族女子家庭生活的优越地位还体现在日常服饰上,据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载:“男子衣服,除富奢者外,悉用大布,虽北京亦然,女子衣服,贫寒者外,悉用绮罗,虽穷村亦然。女人无论老少,并收发作髻,裹以黑缯之属,额贴玉版,被绮罗,塗粉簪花,而其夫则衣服敝恶,面貌丑陋,乍见,皆认为奴。”(50)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燕行录全集》3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1页。燕行使李押记载:“男子富贵者外皆服大布,女子虽贫皆服缎衣,凡大小事皆责于男子,如汲水、舂米、洒扫、织锦等事,无不为之。坐贾行商,日不暇给而亦未沐洗,故尘垢满面,衣衫褴褛,作人兼极粗劣,其妇缎衣粉面头花耳珰,不治女红,倚门冶容,虽至贫且贱者不过炊饭、缝履底而已,视其夫不啻奴主,其女对我人亦羞称以家夫。”(51)李押:《燕行记事》,《燕行录全集》5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46页。由此可见,男女服饰材质的差别显示了满族男女地位的差异,不同于汉族女子以夫为尊的传统,满族女子常有视夫为奴,甚至轻贱其夫之事。
日常生活中,满族女子不仅可以和男子一样列坐而食,还可如男子一般骑马、吸烟,出入人前。吸烟是满族的传统习俗,同治五年出使中国的柳厚祚记载:“南草男女老少至于三四岁儿无不吃焉,虽处女佩南草小囊,囊中必插短竹矣。”嘉庆二十三年出使中国的成祐曾作诗言道“人人囊插一袋烟,时匄东方狼怕烟,童女老婆临大路,湘江斑竹尺余长。”(52)成祐曾:《茗山燕诗录》,《燕行录全集》6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88、186页。燕行使李海应甚至发现在满族人丧礼上“女子虽服素者,必傅粉塗朱,或老妇两眼垂泪,而口含烟竹”,(53)李海应:《蓟山纪程》,《燕行录全集》66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75页。令他哑然失笑。因为家庭地位高,故而满族女子日常生活所受禁忌相对较少,个性大胆而爽朗,燕行使李押记载:“汉女则避外人,而胡女则不知避,虽诸王卿相之妻皆乘车以行,遇我国人必驻车褰帷而见之,胡女日冷则或着其夫之红帽子以御寒,汉女则终不着。”④女子出行不仅不避生人,反主动与生人搭讪,甚至与男子杂坐吸烟,接膝交手。燕行使成祐曾载:“每使行所过,妇女萃观,虽老婆贫女头必插花,面必傅粉,语笑自若,或有乞烟茶丸药者,有自囱户而窥者,乘车之女亦从琉璃而见其面矣。”⑦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亦记载:“行数里遇胡人,所骑马善步。昌晔换马,余又与昌晔换骑。走极快,先至三里堡,坐店房待行次至,以马还昌晔。路遇胡女八九人步行,元建问何往,一女答曰为观高丽人,盖戏之也。元建曰好生不安,群女皆笑。”(54)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32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99页。开朗大方、毫无扭捏造作之态的满族女子反倒令朝鲜使臣感到局促不安,为此嘉庆六年出使中国的柳得恭作《满女》诗云:“大靸宽衫雌满洲,野花红压玉搔头。儿啼稳放腰车里,对客求药了不羞。”(55)柳得恭:《辽野车中杂詠》,《燕行录全集》60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3-44页。这里的“腰车”即是摇车,是满族女子常用的育婴工具,对此朝鲜使臣李宜显详细记载道“孩儿之不能坐立者,例盛以大篮,篮底铺以襁褓,而垂索悬挂于梁间,如鞦韆戏状,左右摇飏,俾令儿快爽止啼,放二便则出而洗涤,更以他襁而盛之,终日摇之不已。”(56)李宜显:《庚子杂识》,《燕行录全集》3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3页。摇车操作简单便宜,即缓解了满族女子日常抱子的辛劳,又因为摇晃而易使婴儿入睡,从而使满族女子有更宽裕的时间从事刺绣缝鞋的工作,这令朝鲜使臣称赞不已,如李田秀《入沈记》载摇车之制:“儿啼则纳于此而推之,使即止啼,久则辄睡,故乳子者依旧作日用事,不如我国之汩于调护,无暇及他矣。”(57)李田秀:《入沈记》,《燕行录全集》30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66-367页。可见,满族女子既不必为繁重的家庭活计所扰,亦不必为辛劳育子所累,日常生活的悠然自在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汉女以温婉含蓄为美,那么满女的动人之处则往往体现在不遮不掩、干脆利落之时。然而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朝鲜使臣认为女子应以贞静为美,而满族女子大方爽朗的个性常常令使臣们侧目甚至厌弃,如使臣金昌业见满族女子不避生人,认为此举“盖去禽兽无远矣”。(58)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3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5页。
同汉女相比,满族女子既不必受缠足之苦,亦可免堕入风尘之忧,缠足与否似乎成为朝鲜使臣区分满汉女子的重要标尺。《入沈记》朝鲜使臣诗云“不及弓鞋在,犹分汉女来”。(59)李田秀:《入沈记》,《燕行录全集》30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77页。不唯如此,朝鲜使臣还对汉女缠足的由来非常感兴趣,如李有骏《梦游燕行录》载:“汉女缠足着尖头短靴,行步摇摇,如不自立,满女不缠而着高靴,按南唐李窅娘俘入宋宫,宫人争效其小脚尖尖,勒帛紧缠遂成风俗,故元时以小脚弯鞋为自标异,鞑女嗤以为诲淫则免矣。”(60)李有骏:《梦游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7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4-35页。徐有素记载:“汉女必缠足,盖自始生之初已缠其足,足不能长。虽体大之女,其足则仅如十余岁儿,惟其紧缠,故其足自曲,而袜鞋亦随而曲如弓样。唐人所谓弓鞋者,岂此之谓欤?其曲处支小球于鞋底,使之践履不窘,然行步似不便,甚者杖然后仅行。其足虽父母昆弟间不许开视,惟成婚生子后暂视其夫云。满女则不缠足,此无乃汉人旧俗耶?或云此法自三代时已有。妲己本狐精也,虽化人不能变其足,恐露其本形缠裹之,时人以为宫样效之。”(61)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9页。朴来谦记载与汉臣的对话:“陈书示曰:‘中华风俗自潘妃步莲以后,竞相纤步,妇女皆缠足、弓鞋,习以成俗。东国亦有此俗乎?’余书示曰:‘东国则不然,曾闻明时网巾出后,人称头厄,烟茶出后,人称口厄矣,今见中华妇女,可谓足厄也。’因相与呵呵大噱。”(62)朴来谦:《沈槎日记》,《燕行录全集》6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86页。无论缠足是起于“南唐李窅娘之说”,还是“妲己说”,抑或是“潘妃说”,都表现了朝鲜使臣对女子缠足行为的格外关注,字里行间也充满了对汉族女子的同情。据朝鲜使臣观察,满族女子不仅无须缠足,而且若满女与汉族男子通婚,则“其女不得缠足,属于旗下,欲其久而成俗”。(63)李海应:《蓟山纪程》,《燕行录全集》66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71-572页。满族女子的天足令汉族女子羡慕不已,随着清末有识之士对汉女缠足恶习的批判,汉族女子也开始自觉抵制缠足行为,如风行一时的《劝行放足歌》便是鼓励妇女放足的重要步骤,“照得女子缠脚,最为中华恶俗,幼女甫离提抱,即与紧紧缚束。身体因之羸弱,筋骨竟至断缩;血气既未充盈,疾病随之暗伏。轻者时呼痛苦,重者直成废笃;举动极为不便,行走犹形踯躅;懿旨屡屡诫谕,士民尚不觉悟;人孰不爱儿女?微疾亦甚忧郁。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狃于世俗,意谓为此不美,且将为人怨讟。不知德言容工,女诫所最称述;娶妻惟求淑女,岂可视同玩物?”(64)转引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39-640页。
至于娼妓一事,汉女则多迫于生计使然,而满族女子则可免此患也。朝鲜燕行使在途中常常遇到汉女为娼妓者,且深以为耻,为此常有感于满汉女子地位和命运的不同,如朝鲜使臣李有骏在京城时发现衣着华丽的满族女子常常是朝士家的命妇,举止端庄,颇有贞静之态;而琉璃厂附近则多有娼妓,号曰“养汉的”,足见时人对其轻蔑的态度,“倚门娇笑少无耻”是燕行使对这些女子的直观印象,他还记载:“我人若独往则必锁门留之一宿,之后尽取其货包以去,往往空手垂橐而归,故不敢辄往云。”(65)李有骏:《梦游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7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5-36页。可见朝鲜使臣认为沦落于娼妓的汉族女子不但地位卑贱,其行强盗之举更为人所不齿。相对于李有骏的时时警惕、厌恶排斥,朝鲜使臣李押的记载则显得更加心平气静:“汉女虽艳,目皆直视,是以见者每以胡女为胜。尝见皇明稗记以为燕山妇女虽曰秾丽,十三辄嫁,三十而憔悴。译辈亦云汉女无非诲淫,故皆有眼疾,岂或然耶?又闻明时燕山娼妓皆以子为名,若香子、花子类甚多,无寒暑必系锦裙,而北京中娼家设东西教坊以仿金陵十六楼之制,实犹唐宜春院遗意,皇明则其盛如此,而康熙时京城娼妓绝禁,凡天下清女之为妓者则论以一律,惟汉女则无禁,故历路三河蓟州之间或有养汉妓而萧凋特甚。闻江南板桥诸院亦皆鞫为茂草,无复旧日佳丽云。盖考南京之板桥,唐之宜春院其制极盛,号称风流薮泽,未知果如何也。”(66)李押:《燕行记事》,《燕行录全集》5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46页。作者遥想明朝时期,京城多娼妓而江南地区尤盛,清朝建立后,满族女子作为政权胜利果实的分享者,地位尊贵,而沦为娼家的汉族女子,其地位却在满族女子的对比下显得更加刺目。
四、民族融合与满族女子历史变迁的域外印记
满族女子的形象特征、个性习俗、精神风貌是其在民族生活氛围中逐渐形成的,是了解满族民族传统与文化基因的重要密码。然而在与汉族长期杂居交融的过程中,满族特有的民族传统、礼仪习俗、生活习惯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满族女子的民族性特征也因为汉族的影响而逐渐消失,尽管清初的几任皇帝在保持民族传统、延续民族习性等方面做了巨大努力,如重视骑射与满语、优待旗人、首崇满洲等,然而面对人口众多且礼仪文化积淀深厚的汉民族,这些举措还是无法阻止满族汉化的脚步,这大概也是满洲贵族立国之初所未曾预见的结果。
首先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淡化了满族的旧有习俗,诞生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先祖肃慎、靺鞨、女真都以性勇、劲悍、善射而见长,在长期的狩猎及战争中练就了精湛的骑射技艺,如《满洲源流考》:“自肃慎氏楛矢石砮,著于周初,征于孔子,厥后夫余、挹娄、靺鞨、女真诸部,国名虽殊,而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莫能或先焉。良由禀质厚,而习俗醇,骑射之外,他无所慕,故阅数千百年,异史同辞。”(67)阿桂:《满洲源流考》,孙文良、陆玉华点校,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第342页。由此可见,满族先祖一直处于游牧生活的状态,生活资料的获取多源自狩猎,因此女子精湛的骑射技艺丝毫不亚于男子,为了方便骑射,女子多穿靴,着黑衣,衣袖多为狭袖。清朝建立后,稳定的农耕生活逐渐取代了游牧的生活方式,乘车取代骑马成为满族妇女最主要的出行方式,于是靴子逐渐为鞋子所取代,而《燕行录》中关于满族女子穿靴的记录并不多见,可见生活环境与方式的改变使得着靴的满族女子逐渐淡出了朝鲜燕行使的视野。
不同于汉族女子的穿红戴绿,满族男女,无论奢俭,则皆穿黑衣。究其原因,燕行使徐文重认为:“概以尘埃常满,故皆用黑色云矣。”(68)徐文重:《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24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00页。满族先祖一向崇尚俭朴,穿梭于密林间,靠狩猎获取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黑色是很好的隐蔽色而且又耐脏,可以避免因反复濯浣而导致衣服受损,这是满族喜欢着黑衣的一个主要原因。入主中原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满族女子的衣衫颜色也逐渐鲜亮起来,据《啸亭杂录》记载:“(男女燕服)色料初尚天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绛色,人争效之矣,谓之‘福色’。今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亵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绿袍之义。纯皇帝恶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无知者矣。近日优伶辈皆用青色倭锻、漳绒等缘衣边间,如古深衣然,以为美饰。奴隶辈皆以红白鹿革为背子,士大夫尚无服者,皆一时所尚之不同也。”(69)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55、16页。衣衫颜色的丰富显示了物质生活丰裕带来的精神审美品味之变化。与此同时,满族妇女的衣袖也由狭袖渐渐变为宽袖,狭袖与宽袍大袖的传统汉族服制大相径庭,也正是燕行使对满族服饰最直观的印象。朝鲜使臣来到中国,看到的景象往往是“自天子达于庶人其所着表衣皆夹袖也,阔袖大袍则绝无其制焉。”(70)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5页。然而随着游猎生活的结束,满族女子的衣袖尺度也日渐宽阔,甚至与汉女无异。衣衫颜色的丰富,衣袖尺度的阔大绝不仅仅标志着满族女子服制形式从实用性到审美性的简单转变,更从侧面暗示着生活环境改变下民族特征的日渐淡化与满汉一体化时代的悄然到来。对此清代诗人得舆在其风俗组诗《草珠一串》中写道:“名门少妇美如花,独坐香车爱亮纱。双袖阔来过一尺,非旗非汉是谁家?”
骑射习俗之于满族女子的改变可由靴、衣而观之,而对于男子来说,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却更为深远。虽然统治者一直强调弓矢为八旗旧俗,神武乃万世之家风,然而入关后,旗人大多聚居都市,市井闲适与安逸的生活使得他们骑射技艺渐疏,正如《啸亭杂录》所载:“本朝初入关时,一时王公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居之既久,渐染汉习,多以骄逸自安,罔有学勚弓马者。”③政治环境的安定,经济上的优厚待遇使得旗人奢靡之风渐长,骑射技艺早已不复往日纯熟之态,朝鲜使臣洪大容记载了东安门内数百旗人参加的射箭比赛:“射者虚胸实腹,高提后肘,俱有其式。又皆整容审发,极其才力,终未见一箭中的。不惟不中,其歪横或出十步之外”,这令作者不禁感慨“胡人长在骑射,而疏迂如此,未可知也。”(71)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4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38页。骑射本是满族先祖的看家本领,是流传在民族骨子里的遗传基因,然而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曾经帮助满族先祖攻无不克、立定江山的骑射技艺逐渐沦落为清末看家护院的空把式。故而生于咸丰七年的满族学者震钧说:“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已谓其去古渐远。及今而日惜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72)震钧:《天咫偶闻》10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8页。
其次是满汉通婚的举措推进了汉化的进程。《清圣祖实录》载顺治帝言:“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造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满汉通婚是顺治帝推行满汉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起初实施起来并不顺利,据燕行使李在学记载:“汉人耻于与清人结婚,而贫穷者不得不为之,然犹以为羞。”(73)李在学:《燕行纪事》,《燕行录全集》5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91页。由此可见,民族情绪是阻挠满汉通婚的最大障碍,然而随着汉化的加剧以及汉人对满汉通婚功利价值的考量,这种现象逐渐发生了改变,据道光二年出使中国的徐有素记载:“满人之入中国已近二百年……期欲与汉人结婚在前,则汉人颇不肯之。近世则反欲之,盖冀其有助于仕路及生计也。”(74)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30页。满汉通婚加速了满族女子的汉化步伐,满汉女子生活习俗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旗人家的汉人仆妇,服饰多从满俗”,(75)和邦额:《夜谈随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而在燕行使看来,“缠足”也失去了区分满汉女子的作用,“清初满洲女子有胆量,能干,性格泼辣,很少会有人东施效颦裹小脚。但世事随迁,随着汉化影响,竟也有旗女不顾缠足苦痛,甘冒受罚的危险,取仿汉人裹起小脚来。”(76)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39、654页。究其根由,或是为了满足汉族丈夫的特殊喜好,抑或是为了迎合受汉人影响的满族男子的审美趣味。相较于满女的“缠足”,汉女的“放足”行为亦愈演愈烈,福格《听雨丛谈》卷七记载:“八旗女子,例不缠足。京城内城民女,不缠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⑤一“缠”一“放”之间充分体现了满族文化的包容性与汉族文化的辐射性,故燕行使金昌业也说:“满汉混俗,杂用其制也。”(77)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33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29页。
再次,受儒学及传统礼教的影响,满族女子的天性逐渐被禁锢,地位不复从前。出于对汉文化的倾慕和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清朝建立后,皇帝尊崇儒学,慕效华制,吸纳汉人学子为官,如李有骏《梦游燕行录》记载:“大小官制,满汉参半,而满人独占权要。”(78)李有骏:《梦游燕行录》,《燕行录全集》77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4页。虽然“京堂俱一满一汉,印归满官。”(79)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9页。但耳濡目染之下,汉族官员一言一行、习惯喜好等都对满族官员产生不小影响。顺治、康熙都是慕效华制、崇尚儒学的有力推动者,前者对孔子之后人礼待有加,表现对孔圣人的追思,后者则将儒学经典用满文刊印,以教导旗人子弟“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如此,宗室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满洲旧制的现象屡见不鲜。清初的满族学者,被称为大儒的阿什坦曾呼吁:“严旗人男女之别”,这显然受到了汉人传统礼教的影响,并试图将礼教实施扩展于整个旗人社会。曾几何时,崇武少文、疏于礼制是朝鲜燕行使对满族族群的集体想象,甚至将背离儒学伦理的满族习俗视为与禽兽无异的野蛮之举。于是朝堂上交头接耳的满族官员,庙堂上杂乱无章的礼仪制度,剃发左祍的满族男子,抛头露面的满族女性,男女相见的“抱腰”之礼常常成为燕行使诟病的对象。随着儒家伦理思想的渐入,朝鲜燕行使则改变了对满族的固有印象,康熙五十九年,出使中国的李宜显感叹清代朝服“虽非华制,其贵贱品级,亦章章不紊矣。”(80)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燕行录全集》35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50页。但是与慕效华制而得来的礼制完备相比,满族女子的大胆泼辣、无拘无束的天性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禁锢与冲击,尤其是朝士家的贵族妇女,抛头露面、肆意攀谈仅仅成为残存于过去自由生活中的美好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太平车上的隔窗观望的典雅端庄。汉族女子的含蓄矜持正在慢慢地浸染着满族女子。入关前,满族接面抱腰的礼节并没有男女的限制,它仅仅表示见面时的亲热与尊敬,“在后金及清朝的史籍当中,可以发现妇女行跪拜礼的记载逐渐替代了行抱见礼的记载,而在经过康熙、乾隆时代修撰的官书实录中,早期抱见礼的记录基本上被修改和隐讳掉了。这个变化多少反映出清代的满族统治者逐渐接受封建礼教观念,认为妇女行抱见礼,不大符合男尊女卑或‘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规范。”(81)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男尊女卑思想也给满族女子的优越地位带来不小的震动,为此嘉庆二十三年出使中国的成祐曾写道:“曾闻燕俗女人则但缝袜底,不事女红,沿路所见或有爨薪而炙肉者,或簸米于驴磨之旁,或担水,或担粪,则传闻者多非实也。”(82)成祐曾:《茗山燕诗录》,《燕行录全集》6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91页。在作者的固有观念里,闲适与安逸才是满族女子的生活状态,毕竟早于他出使的前辈们的日记里大多是这样记载的,然而实地考察后的客观事实却并非如此,足见满族女子地位之转变并非朝夕之间,而是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过程中,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除此之外,长期禁锢汉族妇女的贞洁观也以其强大的征服力向满族女子铺天盖地地袭来,乾隆时期“从《钦定八旗通志》所载八旗节妇烈女人数来看,已经超过顺、康、乾三朝的总和,有九千五百名之多,而前三朝总计不过两千余人。”(83)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49页。可见,礼仪的规范、身体的劳作毕竟只是对满族女子日常行为的约束,而汉人的贞洁观才是对满族女子精神上的极大残害。
五、燕行使的多重身份与满族女子域外镜像的建构
“我们都知道,制作一个异国‘形象’时,作家并未复制现实。他筛选出一定数目的特点,这是些作家认为适用于‘他’要进行的异国描述的成分。”(84)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燕行录》对满族女子杂冗繁多的描述和记载表现了朝鲜士大夫对满族族群的高度关注,然而条分缕析的历史还原却掺杂了众多情感元素,丙子之乱的不堪记忆,“以夷变夏”的惨烈现实是朝鲜士大夫内心久久不能平复的伤痛,“胡皇”“胡俗”“胡女”这些称呼的背后是对满族族群整体的排斥与鄙夷,而对其不厌其烦地描写正体现了朝鲜士大夫的好奇与不甘。对满族群体的集体想象是残暴无礼甚至是妖魔化的,似乎一切与中华文明相契合的衣冠制度、礼仪文明均与这个民族没有关联,这种预设的思维定式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了燕行使的情绪与判断,甚至在实地考察后刻意地去对号入座,于是同被冠之“民俗蠢强,专尚弓马”的满族男子一样,满族女子的“奇装异行”也同样受到朝鲜燕行使的质疑与批评,在他们看来:女子本该以贞静贤淑含蓄为美,然而满族女子却插花戴柳、抛头露面、随意与男子攀谈,甚至大胆好奇地去观察燕行使的举动;女子本该侍夫为尊,以针织女红、相夫教子为己任,然而满族女子却安坐闲游,舂米、汲水、织制等事皆由男子代劳。就如同燕行使经常用汉族文士的噤若寒蝉来比较满族男子的骄横无礼,汉族女子的卑微也常用来衬托满族女子的优越。于是,便有了明末清初江南才女季文兰题壁诗蜚声于朝鲜文坛的特殊现象,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汉族女子因为被旗兵掳掠北上的悲惨境遇,唤起了许多燕行使的痛苦记忆,朝鲜使者申晸、金锡胄、金昌业、朴趾源、李宜显等人都在其燕行日记中记载了对季文兰题壁诗的深切感受。“季文兰情结”唤起了朝鲜燕行使的黍离之悲,在这种情绪的感染和驱使下,拒绝满汉合婚的事件常常被写进《燕行录》中,如乾隆十四年出使的燕行使俞彦述记载:“立国之初则满汉不相婚嫁,岁久之后渐与相通。今则婚嫁无所择而汉人犹以为羞,每对我人则讳其通婚。年前有一南京人来居北京而家甚贫,生女而不裹足,盖欲以满人为婚也。其兄自南京来,闻其将与满人通婚,切责其弟,至于失义不和而去云,以此见之则其羞与满人婚嫁可知。而俗习渐染,贫富不同,满人之家汉女甚多,诚可怜也。”(85)俞彦述:《燕京杂识》,《燕行录全集》39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93页。不难看出,燕行使在意并关注满汉婚姻的背后,往往是对固有文化传统的捍卫和对皇明王朝的追思,饱含对神州陆沉的慨叹,《燕行录》满族女子群像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朝鲜燕行使不甘屈辱的抵触情绪。
由于燕行使角色的多重性,导致其对满族女子的评价也呈现出多面性特征。抵触情绪影响下的使臣身份使他们始终用挑剔苛刻的眼光审视满族女子的服饰外貌、生活习俗、个性特征,而知识分子细腻的人文关怀又使他们对汉族女子的卑微地位寄寓无限同情,对满族女子闲适悠游的生活羡慕不已,引发“生于此土者,反是为女好矣”的无限感慨,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使其对花枝招展的满族女子赞赏有加。由此,燕行使笔下的满族女子往往是主观情绪描摹与客观具体陈述综合作用的结果,看似矛盾的描述实则真实、全面地呈现了清代满族女子的社会生活。它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多重角色影响下的朝鲜燕行使对描述对象的多棱透视,展现了满族女子从族群特质突显到个性气质模糊,甚至消失的全过程。满族女子的域外镜像也正是在燕行使复杂的情感、冷峻的观察、集体的想象与客观的陈述中逐渐构建起来的,因此相较于冷峻的文献记载,有温度、有情绪、有变化的文学描述则更接近历史的全貌。
六、结语
作为满族族群重要组成部分的满族女子,是满族文化呈现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以往学术界关于满族女性文化的研究基本上依靠本土材料,包括历史典籍及满文档案,而对于域外文献则关注较少。朝鲜作为我们的邻国,与中国有着同源的文化环境,朝鲜王朝对中国的变化反应最直接,感触最灵敏,印象也最深刻。正如张伯伟所言:“就异域之眼对中国的观察而言,其时间最久、方面最广、透视最细、价值最高的,首先应该算是我们的邻国,也就是在中国的周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汉文化圈地区。”(86)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7-8页。清朝建立后,朝鲜使臣常常在燕行途中格外关注新政权的建立者——满族的一言一行,对迥然有别于汉女的满族女子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常常将细致入微的观察融入《燕行录》的记载中,其内容包罗万象,从衣食住行到风俗礼制,从个性情感到社会地位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燕行录》时间跨度长,作者身份驳杂,决定了燕行使笔下的满族女子群像必定充满了动态的变化元素。它随民族融合的进程而变,随燕行使的心理而变,随中朝关系而变。集体想象的偏失与个体亲历的真实共同打造了燕行使眼中的满女形象。《燕行录》满族女子域外镜像的构建不仅还原了作为民族特征标志性存在的历史印迹,还见证了民族融合背景下满女特征逐渐消失的历史进程,凸显出汉文化的强大辐射性与满族文化的包容性。因此以域外文献《燕行录》为材料,挖掘整理其中关于清代满族女性生活的描写及评述,丰富、还原并重现清代满族女性社会生活的全貌与历史“记忆”,为满族文化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