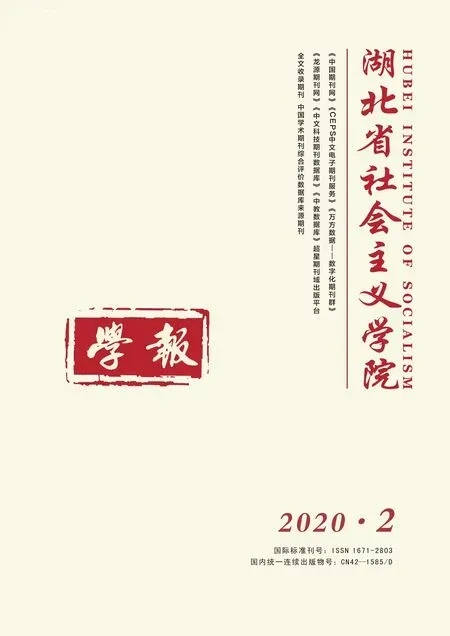试论佛教中国化
方 永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纵观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佛教为了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一、佛教通过商人由商路传入中国
诞生于天竺的佛教,从四个不同的方向传入中国:一是经西域的丝绸之路,从西北内陆传入关中和中原;二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从华南沿海传入东南进而进入中原;三是向北翻越喜马拉雅山传入西藏;四是向东北翻越横断山脉传入云南。这四条线路,都是著名的商路。也就是说,佛教是沿着这四条商路传入中国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四条路线,基本上是与四条商路重合的。经济的因素,是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最基本的考虑。文化的考虑,是处在第二位的。在考察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时候,不应当像一般的佛教徒那样,把佛教的悲天悯人精神当成第一位的因素。经过商路来到中国的那些商人,首先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即便涉及到精神文化,也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不是他们所到的那些地方的民众的文化需要。解救中国人的精神苦难,绝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根本宗旨,尽管这是后来中国的佛教徒信奉佛教的一个重要理由。
佛教虽然是经商路传入中国,但是,它们首先不是要为传入地的中国人提供宗教服务,而是为在传入地(中国)经商的外来商人提供宗教服务。在中国的佛教活动,一开始主要是外来商人的宗教生活。
经济是人类一切现实活动的根本,一切思想意识的活动都以经济为其根本的基础。宗教作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佛教传到中国,最初是在民间活动的,而且,其活动的主体是从事商贸活动的外来商人。当然,佛教要给这些外来商人提供宗教活动,需要僧人相伴。但是,在向中国地域传播佛教方面,开路人不一定是这些僧人,而是外来商人以及由这些商人扮演的使者。这些外来商人和使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用以保证这些经济利益的政治利益,向沿路的官吏打点礼物,以推销和收购商品,获得安全以及相应的安全保证。
外来和尚为外来商人提供宗教服务,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了。这样的情况,在各个宗教的向外传播史上是常见的。基督宗教是这样,犹太教是这样,伊斯兰教也是这样。这说明了什么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这是非常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总是要为它所依附的生产关系服务。当一种宗教所依附的经济关系主要在自己的诞生地和已经有了相当时间的流传地时,它对这种生产关系的服务通常是与它对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的服务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当一种宗教所依附的经济关系溢出于诞生地和长期的流传地而进入其他地域时,它对这种生产关系的服务也就是它与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的服务分开了。这样,就出现了宗教与政权相对分离的状况。但是,宗教为其所依附的生产关系服务的实质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它所依附的生产关系溢出到了为其他政权所控制的地域,而它与那里的政权还没有建立起依附的关系,处在两个地域的政权所形成的纽带之中。商业的往来以及进行这种商业活动的商人,就是存在于两个地域的政权之间的纽带。
佛教,在其主要是外来商人的宗教时,它是一种纯粹的外来宗教。但是,由于处在中国,它在为外来商人服务时,出于经济的考虑,也会对与这些外来商人打交道的那些本土商人产生一些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会反馈回去,对佛教本身产生影响。最初信奉佛教的传入地本土人,是与外来商人做生意的本土商人。当然,在官方的记载中,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官方记载的最早的本土信徒,是士人或者贵人。
二、佛教通过结交权贵在中国培育基本信仰土壤
外来商人和伴随他们的为数不多的僧人,以及与这些外来商人做生意的本土商人,为了经济利益和安全,为了更好地做生意,就得寻求所在地域和所过地方当局的保护,为此,他们会尽力地结交传入路线和传入地的官吏和权贵,尽力与他们处理好关系。而且,在这种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商人,而是当局中的当权者,也就是权贵。所以,结交权贵,是古今中外商人的不二法门。“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东晋时道安和尚的这句名言,道出了那些宣称佛教徒不阿权贵的高僧大德们内心的无奈。
汉传佛教的信徒经常说,佛教是皇帝请来的。这话在佛教的传播中确实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之前,佛教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中土。汉明帝遣使求法,不过是佛教得到汉王朝正式承认的标志。这表明,佛教的声音不仅已经上达帝听,而且皇帝也开始对佛教动心了。这是作为佛教徒的外来商人和本土商人最初结交权贵所希望达到的最高目标。有了皇帝的这一请,佛教在中土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虽然士人还不能普遍接纳佛教,但有皇帝的撑腰,佛教合法立足就不再成为一个大问题。
结交权贵,礼物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些礼物,大体可分为三类:方物、术法、经咒。当然,首先是方物。它们是难得之货,属于一般所说的金银财宝,但却最能吸引人的眼与心。其次是术法。它们是这些官吏和权贵们在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所追求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两样东西最为特别,一是用来延年益寿和对付各种灾难的医药方术之类的东西,二是用来呼风唤雨和预测命运的东西。前者关乎身体,后者关乎气象,这两样东西对于人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把这两样东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介,是占卜。占卜的核心,是把握人心,关键是预测人们当前和未来存在的大问题。在佛教中,紧接着占卜而来的,就是经咒。经咒的核心作用是禳解,以种种法力和功德,替人解忧排难、祈福纳福。
当然,这类东西在中国本土文明中也存在。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本土的东西在本土人士的眼中总是没有外来的新奇。于是,这些外来的商人和伴随的僧人便投其所好,献上这些新奇的东西。实在拿不出外来新奇的东西时,便把所在地域的那类东西加以包装,当作珍宝献上。
在佛教史上,我们看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传入地的官吏和权贵也是重视方物和法术,基本上不重视经咒,因为前者可直接利用,而后者却不能直接利用,须经相当的供养之后,才能被拿来利用,用时长而耗费多。但是,僧人对经咒却是十分重视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外来的僧人用献上前两样东西来获得官吏和权贵对经咒的尊重。有了这种尊重,外来僧人便可以在为外来商人提供宗教生活的同时,慢慢地寻找佛教植入中国的契机。
其实,在方物、术法和经咒这三者之中,官吏和权贵们看重的是前两样,外来的僧人心知肚明,第三样是门面性的东西,用来表明自己的信仰身份,并且希望得到接受者的重视。但是,往往用来装门面的东西,其实才是文化的实质。实际上,佛教文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既不是它传来的方物,也不是它传授的术法,而是它用来撑门面的经咒。当佛教的经咒为某个地方或某个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接受时,佛教的基本信仰土壤也便形成了。这样,在佛教的修行人士和一般信众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和利用的文化关系:修行人士负责提供和解释经咒,一般信众提供供养获得经咒并得到经咒所涵有的法力和功德的护佑。这种文化关系,是佛教经济真正的核心和基础。在这种基本的文化关系形成之后,经咒的核心地位确立,方物和法术便让位,佛教的本色就此显露了出来。这正是佛教所追求的理想关系:权贵们肃立在经咒边,或跪伏在经咒下,或心口耳不离经咒。有了权贵作榜样,一般民众也便跟风而起。
三、佛教以术法吸引作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方式方法
为外来的商人和与他们做生意的本土商人服务的佛教僧人,用来结交权贵的三样东西中,最被权贵重视的是方物以及与之相连的财宝,但最吸引权贵们注意力的是术法。
这些术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娱乐类,具有较强的技艺性,而且多数都有相应的器具和技法;二是实用类,特别是一个特殊的食品、药品和饰品的制作与应用;三是巫术类,如占卜、呼风唤雨等。
术法吸引,是宗教传播非常重要的方法。后来的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也采取了这类方法。不过,天主教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时,科学技术在术法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徐光启就是为利玛窦的渊博知识所吸引而受洗入教的。但是,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前,科学技术没有那么发达,但也不是没有科学技术,佛教传入中国时,显然也带来了古代天竺的一些科学技术,它们主要被包含在一般所称的术法之中,它们在佛教中被称为五明。正是术法中那些十分有用的东西,也就是五明,在相当程度上吸引了权贵,又通过有眼光的权贵而传递到一般士人,乃至这些权贵和士人治下的民众。
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经过两百多年,到了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这绝不是偶然的。人们在分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时,通常提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苦难深重。在这深重的苦难中,战乱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给人更深刻体验的是与这些战乱相随的众多的疾病。佛教自天竺传来的医方明,在给中土大地上受苦受难的民众医治疾病上,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有许多人就是在佛教僧人和信徒施药救治后皈依的。
在佛教史上,还经常有佛教僧人与道教的道士斗法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斗法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巫术类。当然,在佛教方面的写作中,斗法的胜利者多是佛教一方,许多地方的当政者和大户人家就是在这样的胜利中成为佛教的支持者。而且,佛教史中著名的佛图澄,就是依靠其高明的术法,而使许多权贵皈依佛门。
不过,佛教的僧人,在斗法中所使用的术法,不全是从天竺而来的,有一些是从中国本来已经存在的巫术中借用而来的。即便是来自天竺的巫术,为了顺应中国人的习惯,也做了相应的改造。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佛教中国化的内涵。
其实,不仅在巫术类的术法上有这两种情况,在娱乐类和实用类的术法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其中最典型的是音乐、绘画、文学和医药。总之,正是在术法的强大吸引下,一向重视实用和学习的本土中国人,有不少人开始喜欢上了佛教,开始成为佛教的鼎力支持者、信仰者和传播者。
四、佛教通过经典译释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及传播
佛教经典的翻译,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在进行着。可以说,佛教传播到那里,就开始把佛教经典翻译成当地的文字。就汉传佛教而言,在佛教传播到汉地之前,佛教经典就已经翻译成途经之地的多种语言。佛教最初传入汉地时,僧人所使用的语言就已经不是佛教诞生地的语言。不只语言如此,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也如是。初入汉地,僧人和经典上的语言,不是梵语,而是西域的语言。至于到底是哪种语言,已经没有切实的证据了,只能笼统地说是胡语。
汉地佛教,最早的佛教经典翻译,是在洛阳。译经活动虽然得到官方资助,但主要是私人活动,起初主要由外来僧人主持。由本土僧人主持佛教经典汉译,东晋的道安和尚可能是第一人。当然,历史上主持佛教经典汉译最为著名的人物,就是唐朝的玄奘和尚。
佛教经典翻译,在佛教传播中意义深远,它为传入地的信仰者和可能的信仰者提供了了解佛教的一个最基本的途径。同时,它也锻炼和培养了僧才。在隋朝以前,中国汉传佛教的主要人物,都与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分不开。正是因为翻译出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才有对佛教义理的深入探讨和弘扬,由论师而宗师,开出中国佛教的各个宗门和教门。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尤其是在早期,许多时候是以无本记的形式出场的,这种无本记由两个环节构成:一是“传言”或“度语”,由外来僧人诵出经文,另一人将这诵出的经文口译成汉语;二是“笔受”,由一人或数人将口译记录下来,再加以整理或润饰。这样造成不少麻烦,导致中国僧人西行取经求法,玄奘就是一个典型。
在汉传佛教的经典中,有不少经典是在西域被造出来的,甚至还有中国人在中国自造的。对于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找到梵文原本了。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现存的梵文佛经中,有一些是从中文转译回去的,其原先是否有梵文的原本,已经无可考证了。不能否认,有一些佛教的经论,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后来译成了梵文。可见,佛教经典的翻译,也存在着双向的现象。面对佛教经典,我们无需妄自菲薄。这种情况,在藏传佛教里也存在。至于在中国的南传佛教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就不好妄下断语了。
佛教经典在译为传入地的语言时,使用了传入地的一些固有的术语,并且还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术语,这在中国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中都可以看到。而且,在解释佛教的义理时,也采纳了不少传入地的神话、历史事件和习俗观念,将它们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佛系神话,乃至新的佛系文学形式。中国汉地历史中的变文,就是佛教观念以宗教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但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佛教经典翻译成传入地的语言并用传入地的文化来解释,这种做法,在宗教学术史上,统称为格义。但是,格义只是这种做法的起步,而不是其全部。在两种文化融合成功之后,格义这种比较生硬的办法,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严格地说,格义之后有了创新。这种创新,其核心就是相互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合一,除了通常的政治形势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起实质作用的因素是相互诠释。这种相互诠释,在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之相并行的,是佛教中对道教经典和儒家经典的诠释以及宋代开始的新道教的形成,特别是全真教的崛起。
五、佛教通过观念改造进行调适以减少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
在传播过程中,佛教经典与传入地的文化产生碰撞。为了应对这些碰撞,佛教本身有意做了一些适应性的改造。这种情况,在佛教传入中国时也发生了。比如,在汉地佛教中,为了应对儒家文化,佛教徒不但特别突出报恩思想以契合孝道观念,还特意把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现世报,而在来世报中特别强调报在子孙;为了应对道教,佛教徒不但特别强调脱胎换骨和成就金刚不坏之身,还特意制造出《十王经》之类的经典,与道教抢夺对死后灵魂的控制和超度;为了应对帝王思想,佛教徒特别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有力论证。
对中国原有的本土文化来说,佛教是异质文化。但经过这些观念改造,佛教竟然神奇地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融合而形成了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
在佛教中,观念创新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格义,二是造经,三是造论。格义是早期的主要方式,造经是中期的主要方式,造论是后期的主要方式。在中国,早期大抵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方式主要是格义。中期大抵在公元五世纪到八世纪,中国人已经对传来的佛教有诸多不满意,开始把自己大量的东西塞进去,甚至像西域的僧人那样,假托佛陀言说,开始自己造经。后来干脆不用佛陀的身份,自言即经,《坛经》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九世纪之后,由于伊斯兰教势力扩张和中原长期被压制,佛教在发源地式微,中国佛教被剪断了脐带,真正开始了其自立之路,造论成了最根本的创新方式,出现了论师即宗师这一普遍的现象。
六、佛教通过诸教合一与中国本土宗教相融合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与中国固有的宗教的冲突碰撞过程中,产生了令人奇妙的融合现象,这就是诸教合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三教合一。
佛教初入汉地,面对的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以及与儒家文化同根而生的、以民间文化形式存在的原始道教。在传入的佛教和变动中的儒家的共同冲击下,原始道教吸收佛教和儒家的成分,建立起宗派式的道教,与商人传来和官方请来的佛教作斗争。这样,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现象,其中,儒教居于主导地位,而佛教和道教为辅助。因此,在此后的三教合一中,不论采取主动的是其中的哪一种教,儒教总是居于中轴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佛教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无论它是主动还是被动,它从来都没有能够取代儒教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在汉传佛教的历史中,特别明显。
即便是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中,也存在三教合一的现象。佛教除了与藏地本土的宗教苯教融通使用之外,也要遵守中央政府定下的规则制度,服从儒教的权威。虽然中央政府可能把某个藏传佛教的领袖或大师封为国师,但中央政府的首脑是儒教的最大代表。
在中国的南传佛教中,实际上也存在三教合一,只不过合一中除了儒教和佛教之外的第三种宗教,是传入地的本土宗教,就像在藏地是苯教而不是汉地的道教一样。
当然,在进入由欧洲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在中国,佛教除了与儒教和其他的本土宗教打交道之外,还要与地位日趋重要的其他外来宗教打交道,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因此,在近代,佛教在中国,还出现过与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相融合的现象,佛陀与老子、孔子、耶稣、穆罕默德并座,五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