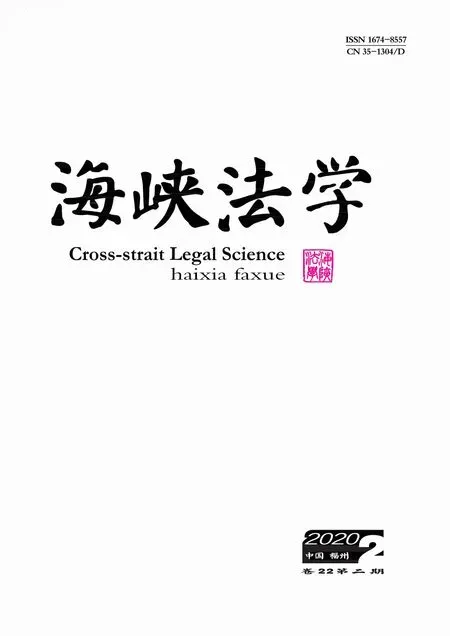论网络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
——以“偷换二维码案”为视角
吴情树,许钟灵
随着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流与商务交易为模式的资金流的高效结合,当今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掺杂有诈骗手段和窃取手段的复杂侵财类案件,使得原本泾渭分明的两种罪名的界分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有必要以诸如“偷换二维码案”这种非典型、有争议性的个案为坐标系,以构成两罪的关键要素为支撑来厘清两罪的界限问题。在此意义上,研究“偷换二维码案”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研究价值,而且有助于发挥刑法理论对刑事司法实务的普遍指导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偷换二维码案”中定性的困境
案情:被告人邹某多次将多个商场、菜市场店铺、摊位的商家微信收款二维码调换为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从而获取顾客通过扫描二维码支付给上述商家的钱款。经调查,邹某利用此方式共获取人民币6983.03元。①本案来源于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1 刑初1070 号刑事判决书。
针对上述“偷换二维码案”,石狮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而石狮市人民法院则改为盗窃罪。法院的判决理由是:首先,在商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邹某将商家的微信收款二维码替换为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从而获取顾客支付给商家的钱款,秘密调换二维码是其获取财物的关键,该行为符合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其次,商家向顾客交付货物后,商家的财产权利已然处于确定、可控状态,而邹某行为的本质就是把商家的收款箱变成自己的收款箱,间接占有商家的财产;最后,商家或顾客没有任何联络,没有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也没有人“受骗”。顾客基于商家的指令扫码付款,是完全符合当时交易规则的行为,其结果由商家承担,不存在顾客受邹某欺骗的情形,也不能认定商家主观上受骗。
针对上述“偷换二维码案”,检察院和法院的观点截然不同,①笔者为了了解全国各地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判决,以“(偷)换二维码、(微信)二维码、覆盖(调换)”为关键词,通过无讼网站进行搜索,共搜索到29 份判决书(2017-2019),这些法院均以盗窃罪判处,刑罚在几个月到一年左右,并处罚金几千元不等。但只有石狮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认定为盗窃罪有进行充分的说理,其他判决书仅仅是简单地引用刑法条文,没有展开论述判处盗窃罪,而不判处诈骗罪的理由。一方认为构成诈骗罪,而另一方则认为构成盗窃罪,这种观点的不同源于对偷换二维码行为性质理解的不同,也源于检察官和法官对二维码这种新型网络支付方式运行原理的不熟悉和不了解。因此,要分析“偷换二维码案”的行为性质,进而区分网络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必须从“二维码支付”的技术原理出发,结合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二维码支付”的技术原理及相关侵财犯罪的类型
由于专业上的差异,普通用户在使用二维码进行支付的时候,大多对二维码支付背后的技术原理不甚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直接影响了扫码支付交易的安全,进一步导致“二维码支付”领域的侵财犯罪案件频发。“二维码支付”侵财犯罪类型包括木马病毒的植入、恶意网站链接的诱导、信息劫持以及本文所讨论的“偷换二维码”。
(一)“二维码支付”的技术原理
二维码是一项集信息编码、信息自动识别、图形处理与数据加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子标签技术,是当下信息采集与传递的重要媒介。在设计上,二维码由若干黑白相间的方块按一定的规律组合成矩阵,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0”“1”比特流的概念,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通过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终端图形识别软件扫描二维码,并进行相应的解码程序后可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②黎四奇:《二维码扫码支付法律问题解构》,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3 期,第111 页。
二维码支付的模式有主读式和被读式两种,本文所举案例就是主读式。在主读式的二维码支付流程中,用户需要用支付客户端App扫描二维码,支付客户端App对支付二维码进行识读,用户确认支付金额等信息后,支付指令会被传输到第三方支付机构或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中,支付系统接受、处理支付请求,支付成功后,后台系统还需要再次与商户后台系统及智能移动终端进行信息交换,最后反馈支付结果到支付客户端App。③参见袁菲:《二维码支付技术安全性分析框架》,载《金融科技时代》2014年第10 期,第65 页。顾客以扫码确认的方式授权委托支付机构,将其对支付机构享有的债权转移给了商家。
(二)“二维码支付”侵财犯罪的类型
一是木马病毒的植入。植入者将木马病毒指令编译进入目标二维码,用户扫描携带木马的二维码后,用户的移动终端系统就会被悄然地植入木马病毒。借此,植入者可以篡改或窃取用户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账户的密码,获取用户交易记录,银行卡信息,造成用户财产的巨大损失;二是“钓鱼性质”网站链接的诱导。侵入者将植入了木马病毒的网站链接伪造成二维码,用户扫描二维码后直接进入其预先植入木马的网站,将信息输入后网站就能知悉该用户的个人关键金融信息,进一步盗取钱财。三是信息劫持。攻击者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恶意拦截商家、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买家之间的交易信息,恶意地修改用户支付的订单信息,从而给买卖双方带来交易风险。四是偷换二维码的行为。由于二维码的外观特性,用户仅凭肉眼难以有效识别二维码是否由持有人实际所有,由此“偷梁换柱”方式给不法之徒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提供了可乘之机。①参见周秀娟:《二维码支付的法律风险及监管对策研究》,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10 期,第4 页。
三、网络支付方式下“偷换二维码案”的刑法理论解说
关于“偷换二维码案”的定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体分为“诈骗说”和“盗窃说”两种观点。诈骗罪的观点细分为“一般诈骗说”“双向诈骗说”“传统三角诈骗说”“新型三角诈骗说”。持盗窃罪一说的学者则分为“盗窃财产派”和“盗窃财产利益派”。
(一)“偷换二维码案”的学说梳理
1.“一般诈骗说”中的“顾客被骗说”认为本案完全符合一般诈骗罪的构造。②一般诈骗罪的构造:行为人偷换二维码欺骗顾客——顾客对二维码的归属存在认识错误——顾客基于认识错误扫码——行为人取得财产——顾客遭受财产损失。简言之,该学说认为受骗人为顾客。行为人同时侵犯了顾客对于财产的占有以及对真实交易状况的知情权。本质上看,导致顾客陷入错误认识而扫码支付的原因是行为人向其隐瞒了商家真实的二维码。而且,欺骗行为的内容涵盖了“是否处分、向谁处分、处分多少”这三个要素。因此,本案中的欺骗行为,应理解为“欺骗顾客向行为人支付”,而并不能只简单理解为“欺骗顾客支付”。但是,本文难以赞成“一般诈骗说”中“顾客被骗说”的观点。
“一般诈骗说”的核心特征是受骗人和被害人必须是同一人。从民法责任承担的视角来审视这一案件,顾客是基于对商家的信任扫码付款,并无民事过错,无需承担退货或者赔款的责任。而且顾客扫码付款后获得了对价的商品,并没有损失,并不是被害人。同时,由于商家疏于仔细甄别自己店里二维码的真假,因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商家才是被害人。由此可见,受骗人和被害人并非同一人。
二维码是一种按照肉眼无法识别的编制规律在平面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几何图形,付款人只是通过移动终端识读条码并完成支付,对于条码背后完整的支付流程不甚了解。但是二维码中除了黑白格子,往往还包含了二维码账户的头像、昵称等一般人就能够显著识别的信息,故顾客不用特地识别也能够识读是否属于商家的二维码,顾客存在被骗的可能。
“一般诈骗说”中的“商家被骗说”认为网络支付方式简化了“顾客——商家——商家的二维码账户”这一支付流程的环节,商家基于受行为人欺诈而产生的错误认识指示顾客扫描被调换的二维码付款,顾客扫码付款完全是基于商家授权委托的处分行为,简言之,本案受骗人为商家。顾客对于其扫描的二维码是否为商家真实的二维码并无法律上的确认义务,也无被骗的可能。③参见姚景俊、范自强:《二维码支付领域新型犯罪行为之定性——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与界定》,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8年第19 期,第75 页。诚然,根据“一般诈骗说”中“商家被骗说”的分析进路,商家才有义务确认二维码的真实归属性,但实则不然。
“双向诈骗说”指出,行为人偷换二维码这一行为同时欺骗了商家和顾客,使得顾客错误地认为二维码就是商家的二维码,相应的,商家则错误地认为顾客已经支付了自己应得的货款。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作用下,双方皆错误处分了财产,顾客基于该认识错误扫码付款,商家基于该认识错误将商品交付给顾客。商家和顾客皆遭受损失,顾客遭受钱款损失,商家遭受商品的损失。④参见李永红:《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坐收顾客支付款,实务答案居然是……》,https://mp.weixin.qq.com/s/0rfT9OOPlEnDYH87eDu tUw.,下载日期:2018年11月20日。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不无疑问。
一是运用“双向诈骗”的思维来认定本案的行为,会导致对法益的理解存在偏差。我国台湾地区已故学者林山田认为:“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条款,均有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法益也就成为刑法解释之重要工具。”⑤林山田著:《刑法特论(上册)》,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 版,第6 页。概言之,对刑法条文所保护的法益理解不同,对某种犯罪行为的定性也会有所差异。如果按照此观点,本案中商家和顾客均已经产生了错误认识,并且都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错误处分了财产,那么就应该得出结论: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两个需要单独评价的法益。然而这一理由和其推导出的结论存在抵牾。实际上行为人只有偷换二维码这一个行为,并无针对商家的商品进行诈骗,因此,只侵害了本属于商家的债权这一个法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顾客已顺利达成获得商品的交易目的且商家无权以不当得利或其他理由请求顾客返还商品或再次支付商品对价。据此,难以认定顾客的法益受到了侵害。
二是定性为“双向诈骗”可能会导致分别定罪。根据“诈骗素材具有同一性”的要求,被害人失去的“财物”与行为人得到的“财物”具有同一性。根据该说,顾客支付的钱款、商家给付的商品均是“被害人失去的财物”。但是,行为人对商品既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实际上也没有取得商品。故,不宜将商品评价为本案财产犯罪的对象。如果认可“双向诈骗说”,就可能导致对行为人的两个行为分别论罪,这无疑是“双向诈骗说”的病灶。①张庆立:《偷换二维码取财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2 期,第131 页。
根据“传统三角诈骗说”的构造,②“传统三角诈骗”的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或维持错误认识——受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被害人的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在“偷换二维码案”中,顾客是具有处分商家财产权限的人,是受骗人;商家的财产被顾客处分,商家是受害人。毋庸置疑,这一观点虽然弥补了前两种观点的部分缺陷,似乎也能够全面评价案件事实,然而有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没有解决。
其一,顾客没有处分商家财产的权限。笔者认为被骗人的处分权限来源于:被害人授权、法律规定、交易习惯等。在“偷换二维码案”中,对于商家应得的债权,顾客没有法律或事实上的处分权限。顾客在取得商品后是债务人,作为债务人只有向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付款的义务。③参见邓兆源:《偷换支付二维码行为定性辨析——以邹晓敏案为例》,南昌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 页。
其二,诈骗素材不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意指行为人得到的财产和被害人损失的财产是同一的。“传统三角诈骗说”认为,行为人欺骗顾客,顾客基于错误认识将商家的财产处分给行为人,行为人得到了商家的财产,商家因此遭受了损失。但仅泛泛而谈商家遭受了损失,没有进一步论述商家所遭受的损失具体指的是什么,是否与行为人处分的财产具有“表里关系”或者“对应关系”。
其三,倘若认为顾客处分了商家的财产,笔者将进一步追问此处的“财产”内容。首先,顾客事实上并没有处分商家的商品,商品的处分主体仍是商家而非顾客;其次,顾客并没有将商家的货款请求权处分转给其他任何人。
与传统的三角诈骗显著不同的是,“新型三角诈骗说”④“新型三角诈骗说”提出三角诈骗的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或维持错误认识——受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中受骗人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不可否认,“新型三角诈骗说”的理论研究看起来合情合理、言之有据,实践判例风靡云蒸,但深入考察这一逻辑可以发现,“新型三角诈骗说”的论证和结论难以自洽。有学者另辟蹊径地提出“素材的同一性也可以理解为受骗人处分的财产与被告人取得的财产具有同一性。顾客作为受骗人处分的是自己对银行享有的债权,行为人得到的也是对银行享有的债权。”
首先,“新型三角诈骗说”对于“诈骗素材具有同一性”的理解似乎显得牵强附会。⑤张明楷教授认为,在“新型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处分的是自己对银行享有的债权,行为人得到的也是对银行享有的债权。笔 者认为,“新型三角诈骗说”所指的没有明确指出“行为人得到的也是对银行享有的债权”指的是谁对银行享有的债权,债权是否与被害人损失的债权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诈骗素材的同一性”指的是被告人得到的财产即为被害人损失的财产。然而“新型三角诈骗说”关于“诈骗素材同一性”的创新理论只是绕过正面回答,以预设结论的合理性为目标而根据偷换二维码的案情设置的论证过程。这不符合客观逻辑——使他人受到财产损失的原因只能是处分人处分了他人的财产,而非自己的财产。
其次,在“新型三角诈骗说”的架构下难以理解为什么顾客处分了自己的债权,却使他人受到了财产损失。笔者尝试以民刑交叉的视角,引入清偿制度的民法效果分析“新型三角诈骗说”。依据民法原理,当顾客未扫码付款时,顾客拥有债权;当顾客扫码付款时发生清偿效力,顾客与商家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清偿效果的发生使得顾客的债权一旦转移到行为人的账户,就成为了法律上应属于商家的钱款。因此顾客处分的本人债权和商家损失的钱款在形式上看似有区别,实质上却是一致的。
2.“盗窃财产说”认同“偷换二维码案”符合盗窃罪的基本构造,因为行为人违背被害人的意愿,破坏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并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应该被定性为盗窃罪。换言之,对盗窃罪而言,权利人对其财产的支配状态必须是被动地遭受行为人的破坏,故而属于典型的“他人损害”型犯罪。①参见王钢:《盗窃与诈骗的区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第27 号指导案例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4 期,第30 页。由于被害人对行为人获取商家财物的整个过程是完全不知情的,在本质上属于秘密窃取。无论是在一般观念上,还是在法律属性上,至少在顾客扫码支付的时,钱款属于商家,行为人的行为“成功”破除了商家对钱款的占有并建立起新的控制支配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偷换二维码与在超市的钱柜下面挖个洞让钱掉落到洞下行为没有本质差别。②参见李永红:《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坐收顾客支付款,实务答案居然是……》,https://mp.weixin.qq.com/s/0rfT9OOPlEnDYH87eDu tUw.,下载日期:2018年11月20日。从法院的判决理由可以看出,法院主张的是“盗窃财产说”。笔者大致赞成将“偷换二维码案”定性为盗窃罪的结论,但其具体内容还值得商榷。诚然,顾客取得的商品价格等值于其支付的钱款,但是不能认为行为人盗窃的是钱款(财物),因为商户从未占有过钱款。
一者,“盗窃财产说”违反了行为与行为对象同时存在的原则。根据行为与行为对象同时存在的原则,盗窃财产的前提是被害人对被盗窃财产已经所有。“盗窃财产说”认为顾客扫码支付时,钱款属于商家所有和占有是不言自明的结论,可笔者的观点却完全相反。从一般的交易习惯来看,商家向顾客交付商品后,就可以占有作为商品对价的钱款,可网络支付方式下商家和顾客是通过电子支付平台完成债权债务的移转,商家自始至终没有现实地占有或所有过顾客支付的钱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顾客将商家的钱款转移为自己占有的理论实为无稽之谈。
二者,把“偷换二维码案”的情节类比“行为人在商家的钱柜下挖洞进而窃财”明显不妥。挖洞窃取钱财的案件之所以构成盗窃罪,是因为商家将收的钱款放入钱柜即占有了这笔钱款,而行为人在钱柜下挖洞使钱款掉入自己口袋,当然是违反商家的意志,把商家已经占有的这笔钱款转移为自己占有。但这两个案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不管是社会一般观念还是客观事实上,“偷换二维码案”中的钱款都只是在收款途中,行为人截取的只是在途收款,商家自始至终并未占有这些款项,因此两案不能类比适用。
四、网络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界分的标准及其适用
互联网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网络支付技术飞速使用范围日益扩大,传统侵财犯罪行为随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信息网络衍化为财产犯罪的手段无形中加大了此类案件的定罪难度。在此大应景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异同之争愈演愈烈,网络支付方式下财产案件的定性标准也愈发模糊。即使是在互联网与经济深度结合的背景下,催生出的利用二维码等新型便捷支付媒介进行债权转移的财产犯罪也不例外。就盗窃罪而言,违背被害人意志窃取财物是其构成要件,偷拿、暗取是典型的手段特征,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缺乏信息沟通、交流。与此相对,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被害人在行为人的欺骗之下陷入错误认识,进而行使对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支配或控制的变更权,导致财产损失。行为人主动欺骗和被害人自我参与的信息交互是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素。
(一)诈骗罪与盗窃罪的辨析——以处分行为为视角
处分行为是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分水岭:行为人基于被害人的处分行为而取得财物,即“自损行为”成立诈骗罪;反之,缺乏被害人处分行为的“自损行为”则只能成立盗窃罪。在诈骗罪的检验过程中,处分行为的客观面和主观面属于并列的两个层面,而且从客观面到主观面来认定,有利于克服司法实践中单纯的主观归罪或者“客观不足,主观来补”的现象。客观要素决定了主观认识的内容,只有在肯定了处分行为的客观面之后,才需要检验处分行为的主观面。
1.处分行为的客观面
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和民法上的处分行为不同。民法上的处分权能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可以导致所有权的变更、转移与消灭,而且通常情况下具有引起法律关系变更的意思;诈骗罪中的行为并非刑法予以处罚的犯罪行为,而是作为诈骗罪中连接被骗者错误认识与遭受损失的链条,而且不一定有引起法律关系变更的意思。因此,刑法上的处分除了涵盖民法上的处分行为,还应适当外延,包括单纯的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
“所有权转移说”认为在处分行为的认定上,诈骗罪处分行为转移的是财物的所有权。坚持此观点的德国学者Backmann认为,只有当被害人自己将相应财物排除出自身所有权的范围并使之成为他人所有的财产时,才能认定被害人是自我损害地进行了财产处分。①Vgl.Backmann, Die Abgrenzung des Betrugs von Diebstahl und Unterschlagung,1974,S.65ff.转引自王钢:《盗窃与诈骗的区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第27 号指导案例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4 期,第32 页。笔者认为,“所有权转移说”的“阿克琉斯之踵”是将民法上的处分行为等同于刑法上的处分行为,这样使得大量以借用为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错误地定性为侵占罪或者盗窃罪。
“持有转移说”认为,被害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基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陷入错误,进而客观上使财物实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将财物转移给行为人持有的程度,最终导致财产损失就足以认定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这里的财产转移包括物权行为和如同像债权或准物权行为;也包括被害人出于瑕疵意思将财物转移给行为人的占有;甚至,持有的时间的长短在所不问。②参见蒋铃:《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 期,第53 页。笔者认为,若以“持有转移说”来认定处分行为,盗窃罪中的部分案件将会被纳入诈骗罪的范畴。
笔者认同“占有转移说”。此处的“占有”指的是对占有之物有着事实上的控制权能。该说认为,只要被害人有将财物转移给行为人占有的意思就可认定为处分行为,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所转移的是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控制、支配地位。正如日本学者团藤重光所言:“……因为取得只要产生了转移所有权的外形就够了。”③[日]团藤重光著:《刑法纲要各论》,东京创文社1979年版,第616 页。转引自张明楷著:《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 页。我国张明楷教授也在其论著中提出:“受骗者的处分行为,只要是使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就够了……。”④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3 页。笔者进一步认为,这种占有的转移允许出现时间、地域的间隔,允许直接或间接转移占有。因此被骗人对财产或财产性利益失去控制的行为不需要与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存在紧密的时间联系,也不必要求被骗人必须以直接交付的方式转移占有。
2.处分行为的主观面
接踵而来的是,诈骗罪是否存在处分意识?对于这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三种学说,分别是“处分意识必要说”“处分意识不要说”以及“区别说”。“处分意识必要说”认为,主客观方面都应当具备,受骗人客观上要有处分财产的行为,主观上具备处分财产的意识。“处分意识必要说”受到日本以及我国许多刑法学者的青睐,在日本最高裁判所和我国司法实践中占据着有力的地位。“处分意识必要说”又细分为“严格的处分意识必要说”和“缓和的处分意识必要说”。前者认为,处分者不但要有转移财产的认识与意思,而且对于处分财产的种类、数量、价值等也要有认识。“缓和的处分意识必要说”则只要求受骗者对财产的外形有转移的认识与意思,而对其他处分内容的误认无足轻重。“处分意识不要说”认为,处分行为并不需要与处分意识同时存在,只要被骗人主观上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客观上转移财产占有。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处分行为、交付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必要。”①[日]平野龙一著:《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 页。转引自张明楷著:《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 页。“区别说”认为,在诈骗财物的场合,必须是有意识的处分行为;而在诈骗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可以是无意识的处分行为。德国、日本之所以认为在诈骗财产性利益时可以无处分意识,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的刑法中,盗窃罪的对象仅包括有体物,而诈骗罪的对象包括有体物和财产性利益。按照“处分意识必要说”的观点,在无处分意识时诈骗财产性利益,既不构成盗窃罪,也不构成诈骗罪,只能认定为无罪,由此就会形成处罚漏洞,甚至给行为人指明了犯罪的方向。但我国不能采纳“区别说”关于诈骗财产性利益应适用“处分意识不要说”的观点,因为我国盗窃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
对处分意识的内容理解不同是关于处分意识的各种学说之实质分歧所在。笔者认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应该包括三个内容:首先,处分人需意识到自己占有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意识到将自己占有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转移给他人占有,意识到将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转移给了对方。其次,从宽限定处分意识的内容,只要求处分人意识到财产的占有状态发生了改变即可。最后,从客观主义的刑法基本立场出发,客观处分行为决定了主观意识的内容是认识到将财物转移给了“对方”,至于财物接受者的身份特征则无关宏旨。
(二)诈骗罪与盗窃罪的辨析——以秘密窃取为视角
“窃取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②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51 页。,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形之下侵入被害人的财产领域,破除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并建立新的占有。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本质特征,因此,本文对秘密窃取行为的认定,实质上涉及盗窃罪与诈骗罪的辨析。盗窃罪的侵害行为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或愿望完全违背,不会出现被害人与行为人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更不会由此而产生被害人基于错误信息的决定权而做出决定。
(三)“偷换二维码案”构成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
“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应当是两个彼此封闭的市场,法学理论界不应当只是将产品在本市场内自产自销,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间的贸易沟通应当是法学研究良性循环的必经之道。”③刘艳红:《求学问道莫忘初心,出罪入罪谨记法定》,https://mp.weixin.qq.com/s/YxfV0PuAFUnOzq_irLOeqQ,下载日期:2018年12月5日。因此,笔者就这几种学说的不同解释,导出理论分析,再回到实际案件的审视中,穿梭于理论和实务,弥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之间的鸿沟。“偷换二维码案”是成立诈骗罪还是成立盗窃罪的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谁是被害人以及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核心区分要素的问题。诈骗罪的核心特征是处分行为,但是,“偷换二维码案”中缺乏成立诈骗罪所必需的财产处分行为、处分意识,从犯罪构成来看更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综上所述,“偷换二维码案”宜定性为盗窃罪。
1.“偷换二维码案”中缺乏成立诈骗罪所必需的财产处分行为
显然,在“偷换二维码案”中,无论是顾客还是商家,都没有财产处分的行为。顾客扫码是为了与商家进行商品交易,结清款项后获得商品;商家指示顾客付款是为了取得商品对价的正常商业交往行为。笔者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在“偷换二维码案”中,虽然顾客和商家客观上有处分财产的行为,但是主观上都没有意识到将自己占有的财产转移给行为人占有,因此不成立诈骗罪。
2.“偷换二维码案”更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
网络支付方式下财产犯罪的定性不能脱离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构成要件构建犯罪论体系基础的机能。基于以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的法理释明,对于“偷换二维码案”本文坚持“盗窃财产利益说”,宜以盗窃罪定性。
首先,盗窃是违反占有人的意愿而秘密转移财物的占有的行为。本案中商家对于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被调换,顾客对于扫码后所支付的价款将落入的是行为人的账户的情况毫不知情,这符合盗窃罪之最大的特征——秘密窃取。
其次,网络支付方式下的财产犯罪案件,行为人主观上的“秘密性”体现在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利用网络空间的非接触性、非现场性刻意逃避追踪等。“偷换二维码案”中无论是商家还是顾客,对于财产将落入行为人账户的行为都完全没有任何感知,更加谈不上主观上自愿向行为人交付财产,因此,行为人取得他人财物是秘密窃取的。
最后,对于“偷换二维码案”,行为人盗窃的是商家交付货物后应取得顾客的债权(财产性利益)。从网络支付行业的规范上来判断①《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支付业务管理办法》(2015)第10 条:“支付账户所记录的资金余额不同于客户本人的商业银行货币存款,其实质为客户向支付机构购买的、所有权归属于客户并由支付机构保管的预付价值,不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该预付价值对应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归属于客户,但以支付机构的名义存放在商业银行,可由支付机构向其开户银行发起支付指令进行调拨。”,应当认为顾客完成扫码行为后,债权的占有从顾客转移给商家,而行为人的偷换商家二维码的行为又进一步侵犯了商家的占有。我国台湾学者储剑鸿认为,“交付方法……使被害人将物经由第三人之手交付行为人之间接交付亦属之。”②褚剑鸿著:《刑法分则释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35 页。因此,笔者认为,盗窃罪的对象包括无体的债权性利益,利用偷换二维码的方式,将商家的财产性利益经由第三方交付平台间接交付给自己亦为交付。
五、结语
互联网就像财产犯罪的“隐身衣”,在很多情况下,网络支付方式下的财产犯罪行为只是为了实施其他犯罪的“预备行为”。当互联网与经济发生深度融合后,网络支付方式下的财产犯罪不仅会对个人财产造成侵犯,其所引发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势必会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但万变不离其宗,网络财产犯罪的本质仍属于财产犯罪,并未突破传统财产罪名的定性,正确定性网络财产犯罪仍然可以在既有的刑法规则框架下分析网络犯罪行为,以是否侵害个人、国家财产,是否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为裁量标准,兼顾网络财产犯罪区别于传统财产犯罪的特性,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运用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思路。③参见陈丽、韩文江、王潇:《互联网金融行为的罪与非罪》,载《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4 期,第11 页。德国学者罗克辛说过“法律科学必须成为并且保持其作为一种真正的体系性科学……”。④[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 页。虽然刑法学界中关于网络支付方式下财产犯罪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但本文认为,网络支付方式下的财产犯罪翻新的仅仅是犯罪的手段,如何认定这种新型的网络财产犯罪,仍然必须回到每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并在相应构成要件的指引之下,准确地归纳和概括案件事实,才能对各种各样的网络财产犯罪作出准确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