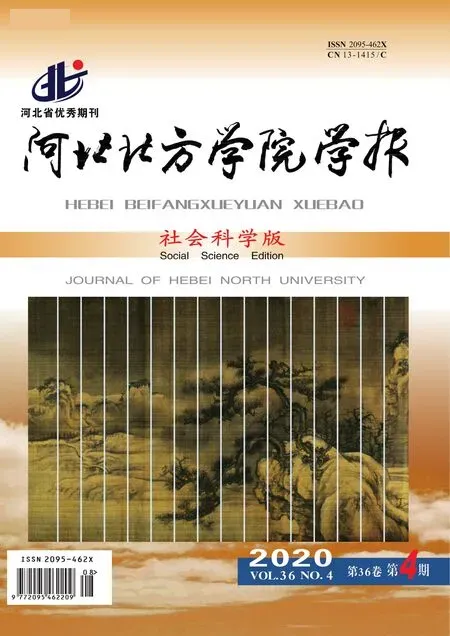湛若水与王阳明“格物”思想比较
赵 絮 颖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目前,针对湛若水与王阳明“格物”思想的差异,大多数学者认为湛若水的“格物”思想是理学与心学调和的结果,而这又可细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湛若水一方面肯定天理即本心,而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王阳明以本心省察意念,而是主张将本心推致于包括意念在内的万事万物中。如陈来指出:“湛若水认为……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去体认道德意识……湛甘泉的格物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陆王代表的心学的一种调和。在理的问题上,他以天理为心之中正之体,是心学的立场。在物的问题上,他用大心说把朱子格物的范围肯定了下来,与王阳明以物为意念不同。”[1]223第二种:在湛若水看来,天理涵盖万物,故而天理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所共有。因此,“格物”不仅是反躬内省,也包括向外寻求天理。正如童中平所言:“天理是形上本体,没有内外之分……‘随处体认天理’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积极成果,因而兼有程朱理学派‘格物穷理’的外求和陆王心学派体悟本心的内省两个方面的内容。”[2]方国根也持此观点:“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和兼融了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对‘格物’的理解,具有调和的学术倾向。湛若水一方面……将‘天理’解释为吾心中正之本体;另一方面又……要求在事物上体察天理。”[3]但笔者认为,湛若水与王阳明对于“格物”的理解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一方面,王阳明的“格物”并非只是端正个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对于道德践履的矫正;另一方面,湛若水与王阳明一样主张将本心天理运用于万事万物而使之各得其理,并无求理于外的弊病。
一、湛若水对于王阳明“格物”思想的误解
在《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中,湛若水集中阐述了他对王阳明“格物”思想的4点质疑,首先来看前两点:
“自古圣贤之学,皆以天理为头脑,以知行为工夫,兄之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之发,则下文诚意之意,即念头之发也,正心之正,即格也,于文义不亦重复矣乎?其不可一也。又于上文知止能得为无承,于古本下节以修身说格致为无取,其不可二也。”[4]265
湛若水认为,王阳明的“格物”仅是端正意念,故而“格物”与“诚意”“正心”在文义上重复。但王阳明所理解的“物”并非仅是“念头”所能概括的:“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5]7“意之所在便是物”并非是说“物”只是意念,“事亲”“事君”“仁民爱物”与“视听言动”很明显不是纯粹的意念,而是见诸于外的行为,但由于意念贯穿始终,故而此类行为物亦可称为“意之所在”。当然,王阳明也同样注重对于意念自身的端正:“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5]28要想扩充善念,遏制恶念显然更为重要,因为行为的产生需要意念的引导。有些行为虽然表面上是善的,但却并非出自于善念,故而对于意念的端正尤为关键。但端正意念仍然是为了使道德行为能够真正地如理合道。因此,用“正念头”并不能够准确地概括王阳明的“格物”思想,意念以及其所引发的道德行为均在“格物”的范围之内。正如何静所言:“他所讲的物一类是指意念中物……还有一类是指意识指导下的行为物,所谓格物也就是在具体事为上为善去恶,这不是湛甘泉的‘正念头’能够涵盖的。”[6]
关于“格物”与“诚意”“正心”的关系,王阳明首先肯定“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7]的修养次第,作为身之主宰的心须先端正,个人修养方能进行;而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意念,所以正心就要落实在诚意上;只有使良知主宰意念才能有诚意,只有切实的道德践履才能使人良知醒悟,最终得以意诚、心正和身修。因此,格致诚正修均有各自的侧重点,并非是同义反复。但王阳明也强调:“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5]1117“盖其功夫条理虽有先后次序之可言,而其体之惟一,实无先后次序之可分。”[5]1119即虽然工夫各有侧重,但实际上任何一种工夫的完成必然意味着所有工夫的同时完成。因此从该角度而言,王阳明的“格物”与“正心”和“诚意”为同一事也无不可,但这并不意味着3者仅是语义上的重复,而是在肯定各自独特性基础上的一体工夫。此外,“止”作为名词即至善的本心,“知止”就是对本心的深切体认,格物就是在道德实践中不断祛除私欲和扩充良知,使得良知得以朗现,此即“知止”之义。格物是具体的下手工夫,其目的就在于修身。因此,说王阳明的“格物”与“知止”无承接性,是有失公允的。
“兄之格物云正念头也,则念头之正否,亦未可据……夷、惠、伊尹、孟子亦以为圣矣,而流于隘与不恭,而异于孔子者,以其无讲学之功,无始终条理之实,无智巧之妙也。则吾兄之训,徒正念头,其不可者三也。”[4]265
“论学之最始者,则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若如兄之说,徒正念头,则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学之不讲’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问学’者何耶?所讲所学,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4]265
在前两点中,湛若水批判王阳明的“格物”与其他条目之间存在问题。而在后两点中,湛若水则着力于批判王阳明的“格物”乃空守念头而无实际讲学之功,意念之善恶难以分辨,而且很可能流于狭隘不恭而不自知。因此,湛若水主张:“学问思辨笃行诸训,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发其良知良能者耳。”[4]270即人虽先天具有良知,但如无学问思辨之功,个体则无法唤醒自己的良知甚至可能将邪念当作良知。但王阳明实际上是肯定学问思辨的工夫的:“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5]252王阳明认为在此思辨过程中,人的良知受到启发而觉醒,从而统率人的气质,使得人的道德践履都能循理而行。但学问思辨只是辅助工夫,个体能否革除私欲并恢复良知本来面貌关键还在于良知的自我觉醒,外在的引导只能够帮助但不能代替良知的自觉自省。
因此,王阳明的“格物”不仅是端正念头,更在于对个体道德实践的统御。王阳明赞同以“道问学”的方式来警醒良知,但道德实践的关键仍在于本心自身的醒悟。
二、王阳明对于湛若水“格物”思想的误解
王阳明对于湛若水“格物”思想的认识也存在问题。“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先生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5]112王阳明认为湛若水的“格物”与朱熹的“格物”一样有向外求理的弊病。湛若水的“格物”即“随处体认天理”之义:“仆之所以训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体认天理也。”[4]269“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应酬随时随处皆随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4]252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来解释“格物”,而王阳明认为“随处体认天理”同样是向天地万物寻求天理:“随处体认天理……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5]250
实际上,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思想是否真如王阳明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客观世界中认识天理呢?首先来看湛若水与其学生的几段对话:
“卫问:‘……学者能常常体察乎此,依着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处,存养扩充将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随处体认天理也……’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于大学《小人闲居》章测难,备言此意。’”[8]900
“潘稽勋讲:‘天理须在体认上求见,舍体认,何由见得天理也?’卫对曰:‘然。……体认是反躬而复也,天地之心即我之心。生生不已,更无一毫私意参杂其间,此便是无我,便见与天地万物共是一体,何等广大高明!’……先生曰:‘此节所问所答皆是。’”[8]895
“舜臣问:‘随处体认吾心身天理真知,……遇父子,则此生生天理为亲;遇君臣,则此生生天理为义;遇师弟,则此生生天理为敬;遇兄弟,则此生生天理为序……根本于中而发见于外,名虽有异而只是一个生生理气,随感随应,散殊见分焉耳,而实非有二也……’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随处体认以下至实非有二也,皆是。’”[8]889
通过湛若水的反馈,人们便可知“随处体认天理”就是“存养扩充”“反躬而复”和“根本于中而发见于外”之义。湛若水自己也表示:“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一耳,寂则廓然大公,感则物来顺应。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离于吾心中正之本体。”[4]269由此可知,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并无很大的差异。一方面,个体要将天理本心推致于万物,使万物皆能被赋予意义,此即“根本于中而发见于外”和“存养扩充”;而另一方面,个体在本心向外推致的过程中,私欲得以革除一分,本心得以恢复一分且终将全体朗现,此即“反躬而复”。因此,“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一样都具有“向外推致”与“向内回复”的双重内涵。正如牟宗三所讲:“‘致’字亦含有‘复’字义。但‘复’必须在‘致’中复。复是复其本有,有后返的意思,但后返之复必须在向前推致中见,是积极地动态地复,不只是消极地静态地复。”[9]因此,王阳明同样也误解了湛若水的“格物”思想,他以为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朱熹的“格物穷理”一样都主张向外穷理集义。同样,黄宗羲评价湛若水“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为旧说所拘也”[8]876,也是有失偏颇的。
在湛若水看来,之所以王阳明的“格物”即“正念头”以及王阳明认为“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因为彼此对于“心”的看法不同:“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4]264他认为,王阳明的“心”是“指腔子里而为言”,而自己所说的“心”乃“体万物而不遗”。关于“指腔子里而为言”,陈来认为,湛若水是想说王阳明所理解的“心”是个体的经验意识:“他认为王阳明说的心是个体的意识,而他自己说的心则是贯通万物的实体。”[1]221但笔者认为,“指腔子里而为言”并非是说阳明的“心”是经验意识,而是说王阳明的“心”只省察经验意识。“腔子”是个体意识,“指腔子而为言”是说本心仅省察意识。故而湛若水称其“小之为心”:“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4]1193以内为本心并无问题,但本心如果仅省察意念,而不作用于天地万物便是“小心”,只有自一念之微到事为之著都能遵循本心,方为内外浑融的“大心”。湛若水正是基于此才认为王阳明的“格物”只是“正念头”。同样,他以为王阳明也正是基于此才认为“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也就是说,从“正念头”的角度来看,将本心推致于天地万物便难免不被视为求之于外。“先生以为心体万物而不遗,阳明但指腔子里以为心,故有是内非外之诮。然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8]876湛若水将“腔子”理解为意识,而黄宗羲将“腔子”理解为本心,万事万物皆以此本心为超越根据。因此,黄宗羲认为王阳明的“心”并不是“小心”,而是包罗一切的“大心”。此观点是相对公正的。
三、对于“主一”与“勿忘勿助”的理解
王阳明和湛若水除了在学问主旨上产生分歧之外,对于具体的修养工夫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于“主一”与“勿忘勿助”的理解上。
关于“主一”,王阳明与学生有过这样的讨论:“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5]14“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空着。”[5]42他认为主一就是主天理,要时刻心存天理,不使心逐于物欲。但湛若水并不这么认为:“主一个天理,阳明常有此言。殊不知无适之谓一,若心主一个天理在内,即是物,即非一矣。惟无一物,乃是无适,乃是主一。这时节,天理自见前矣。”[8]907“然主一,便是无一物,若主中主天理,则又多了中与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则中与天理自在其中矣。”[8]882在他看来,主一不是主天理,而是无一物可主,如果主一是主天理,就会导致人心有挂碍。两人的看法似乎是对立的,但两者是在不同层面讲“主一”。王阳明是就天理之存有而言“主一个天理”,天理是个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唯有专主于天理才能使道德实践有理可循。
湛若水并非立足反对本心即天理这一层面反对王阳明的“主一个天理”,他同样肯定人人皆有本心天理。他是就天理之妙运而言“无一物可主”,即强调天理发用时的自然无滞之义。“无适”常与“无莫”连用,表示没有厚薄之差异。如果人心中时时刻刻记挂着一个天理,本心与天地万物相感应时便有所闭塞,心态就无法中正。唯有自虚其心,毫无挂碍,才能够物来顺应,不失其则。因此,不主一物方能真正主于天理。王阳明也曾表述此义:“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把道理一一说的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5]24王阳明用“执一”表示作用层面上的把持之义,可以看出,他同样赞成天理在运用上的自然无执。可见两者对于“主一”的理解并不冲突,且相互补充,如此才能将天理的内涵与妙用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
除此之外,两者对于“勿忘勿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王阳明认为:“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落实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5]102相对于“勿忘勿助”,王阳明更注重“必有事焉”的功夫,即道德践履。他肯定“勿忘勿助”起到令人省察警觉的作用,但他认为切实践履才是根本,踏实地去从事实践便不会出现“忘”与“助”的弊病,一味强调“勿忘勿助”容易导致人无法着手去做事。而湛若水就比较注重“勿忘勿助”:“求方圆者必于规矩,舍规矩则无方圆。舍勿忘、勿助,则无所有事,而天理灭矣。”[8]902湛若水认为“勿忘勿助”是规矩和准绳,没有“勿忘勿助”的省察,让人遇事时希望止于至善就如同舍规矩而求方圆。王阳明注重实际践履,湛若水强调规矩准绳,但这并不意味着王阳明否定“勿忘勿助”的提点;同样,这也并不意味着湛若水否定“必有事焉”的践履。二人只是侧重点不同,但都并非是坚持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湛若水与王阳明的“格物”思想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思想并非是程朱思想和陆王思想调和的结果,湛若水并非主张从事物上认识天理,而是同王阳明一样,主张将本心之天理作用于万事万物上,从而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此外,在具体的修养工夫中,王阳明的“主一个天理”与湛若水的“无一物可主”并不矛盾,前者立足于存有层面而言天理之实存,后者立足于作用层面而言天理之妙运。同样,王阳明侧重于“必有事焉”,注重实际的践履,湛若水侧重于“勿忘勿助”,强调践履中的规矩。但是对于两人来讲,“必有事焉”与“勿忘勿助”均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