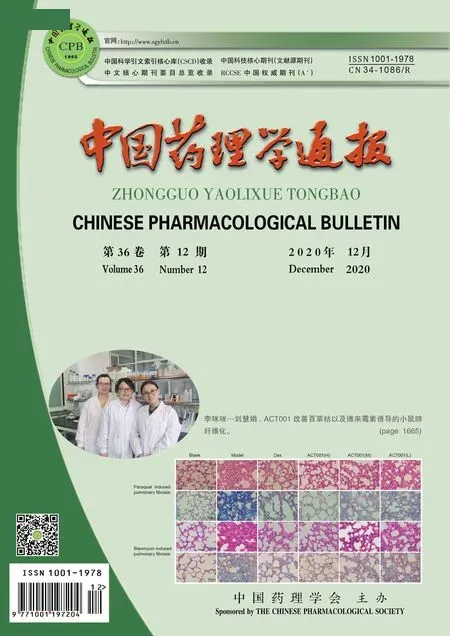μ受体在吗啡成瘾及免疫抑制等疾病中的作用和机制
卢志鹏,白 洁
(昆明理工大学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鸦片原体产自罂粟,19世纪初,德国药学家Sertürner首次从罂粟植物中分离出止痛成份—吗啡。吗啡可溶于水,在脂质中的溶解度较低。吗啡除了具有强烈的镇痛、镇静作用外,还具有调节周围神经系统的肌肉痉挛和组胺释放的作用。迄今为止,吗啡仍是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阿片类镇痛药物。然而吗啡的不良反应(便秘、皮肤瘙痒、呼吸抑制、哮喘发作等)极大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是吗啡导致的耐受和成瘾。吗啡主要通过μ受体(mu-opioid receptor, MOR)发挥药理作用。
1 MOR
MOR为疏水性蛋白质,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超家族(G-protein-coupled receptors,GPCRs),有7个跨膜α-螺旋,3个胞内环及3个胞外环,氨基N端位于胞外,其中第Ⅰ、Ⅱ胞外环上的半胱氨酸残基能够形成二硫键,胞内的羧基C端与Gi/o蛋白偶联,结晶化的MOR具有截短的N端和C端[1]。阿片受体种类较多,且分布广泛,中枢神经系统中表达的阿片类受体有:MOR、κ受体(κ-opioid receptor,KOR)、δ受体(δ-opioid receptor,DOR)、σ受体、孤啡肽受体(nociceptin-opioid receptor,NOP)。除NOP外,每种阿片受体都有不同亚型。根据MOR双向结合特性,将MOR分为μ1和μ2两个亚型。μ1受体激动产生镇痛作用,μ2受体激动主要与吗啡的不良反应有关。
2 MOR的镇痛作用及分子机制
吗啡是一种纯阿片类激动剂,对MOR具有高亲和力,对KOR和DOR的亲和力较小。敲除MOR基因的小鼠,吗啡的镇痛作用消失。
内源性(内啡肽)或外源性(吗啡)配体与MOR的结合导致Gi/o蛋白活化。配体与受体结合后,GTP与G蛋白α亚基结合从而导致MOR活化,GTP 取代GDP结合G蛋白α亚基,二聚体βγ与α亚基解离。α-GTP复合物和二聚体βγ分别参与细胞内信号转导,抑制细胞中腺苷酸环化酶以及蛋白激酶 A(protein kinase A,PKA)的活性,导致环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的产生减少。α-GTP还激活磷脂酶C(phospholipase C,PLC)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途径,PLC将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酯(phosphatidylinositol 4;5-bisphosphate,PIP2)水解为肌醇1,4,5-三磷酸酯(inositol triphosphate,IP3)和二酰基甘油(diacyl glycerol,DG),IP3增加内质网中Ga2+的释放,从而激活Ga2+依赖性信号传导。此外,βγ二聚体激活G蛋白门控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G protein gated inwardly rectifying K+channels,GIRK),引起细胞超极化,导致神经元兴奋性降低。βγ二聚体还可直接阻断Ga2+通道(P/Q型,N型和L型通道),并降低细胞中的Ga2+浓度,从而抑制其他神经递质的传递[2]。
G蛋白解偶联过程是由激动剂依赖的细胞内丝氨酸(Ser)和苏氨酸(Thr)残基磷酸化介导的,MOR的C末端含有11个磷酸化的S/T残基,吗啡所致S375的磷酸化,对β-抑制蛋白(β-arrestin)募集至关重要。特异性磷酸化残基与吗啡不同药理效应密切相关:MOR的特异性S/T残基被丙氨酸(alanine,Ala)取代,磷酸化位点被阻止,S375磷酸化去除,吗啡的镇痛效果增强,而耐受性不变[3]。β-arrestin除了介导受体内吞外,还介导G蛋白非依赖途径中的受体信号。偏向激动剂Oliceridine(研发代码TRV130),选择性激动MOR,该药在不招募β-arrestin的情况下激活Gi/o信号。在临床研究中,TRV130比吗啡能够更快地达到镇痛峰值,镇痛强度是吗啡的5倍,而且很容易被纳洛酮逆转,在同等镇痛剂量下,其便秘和呼吸抑制作用比吗啡少[4]。
偏向激动剂PZM21(compound(S,S)-21),是MOR拮抗剂,具有高亲和力和完全激活Gi/o的功效,但对β-arrestin的募集作用很弱。在小鼠实验中,它产生完全的镇痛效果,便秘副作用更小,也没有明显的呼吸抑制作用[5]。还有研究发现PZM21的类似物也具有MOR高效性和选择性[6]。在包括阿片类药物自给药的大鼠实验研究中,显示TRV130和PZM21这两种药物可导致类似于传统MOR激动剂的成瘾性。
NOP的激动剂具有调节MOR激动剂药理效应的作用,免疫共沉淀和免疫荧光实验显示MOR与NOP可形成二聚体。在灵长类动物中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平衡NOP和MOR活性的双功能激动剂,可以有效地缓解疼痛和治疗吗啡成瘾[7]。
DOR拮抗剂可以阻断慢性给予吗啡所产生的镇痛耐受和依赖,DOR 敲除小鼠对慢性吗啡治疗的耐受性降低。在细胞和脑组织中,已经证实有MOR/DOR二聚体的形成,MOR/DOR二聚体与MOR单体相比具有不同的药理特性,前者对阿片肽的亲和力高于后者。MOR/DOR二聚体的破坏,阻止了吗啡慢性耐受性的形成,且目前已开发MOR激动剂/DOR拮抗剂的配体[8]。纳洛酮是MOR较强的抑制剂,可以结合70%的MOR,用于吗啡过量处理[9]。
MOR在中脑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的非多巴胺能神经元中也有表达,在非多巴胺能神经元中,MOR的激活会招募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而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NMDAR)的激活会招募PKA来解离MOR和NMDA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镇痛效应[10]。
3 MOR在吗啡耐受中的研究
吗啡耐受是指长期使用吗啡导致在固定药物剂量时,镇痛效力逐渐减弱的现象。耐受表现为需要不断增加药物剂量,以达到与之前相同的镇痛效果,止疼作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并伴有恶心、呕吐、嗜睡等不良反应[11]。不同给药途径、不同剂量以及不同给药时间(间歇或持续)都可以产生吗啡耐受。
吗啡产生耐受效应与MOR有关,MOR与G蛋白偶联后激活兴奋性Gs蛋白,引起cAMP浓度增加,对抗了吗啡的镇痛作用。长期吗啡给药,激活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kinase,GRK),诱导MOR胞内C端磷酸化,导致受体脱敏-内吞-复敏等,从而形成吗啡耐受。临床研究发现,缓解疼痛药物的耐受与MOR的单个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有关[12]。
此外,氧化还原系统与吗啡耐受有关,在吗啡给药后,c-Jun N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被激活,从而磷酸化过氧化物还原酶6(peroxiredoxin 6,PRDX6),磷酸化的PRDX6被募集到MOR复合物中,PRDX6通过激活NADPH氧化酶,产生活性氧,从而减少Gαi的棕榈酰化。选择性抑制PRDX6可阻止Gαi去棕榈酰化,阻断MOR失活导致的镇痛耐受[13]。
4 MOR在吗啡成瘾中的作用及机制
吗啡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病,反复的药物暴露引起逐渐适应,是大脑奖赏途径的失控和异常的学习过程。主要表现为用药失控、强迫性用药、持续用药和觅药行为等。吗啡成瘾使得大脑对压力和负面情绪更加敏感,导致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14]。
吗啡成瘾的易感性与MOR的OPRM1基因的多态性有关。在人OPRM1 A118G(小鼠中的A112G)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小鼠中,吗啡调节的VTA多巴胺能神经元投射到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内侧壳的抑制性和兴奋性投射被阻断,吗啡的成瘾性则被抑制[15]。
吗啡诱导的自噬有助于小鼠的条件性位置偏爱(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CPP)形成,MOR参与吗啡介导的自噬调控。因此,调节MOR-自噬途径,可能是治疗吗啡成瘾的重要靶标[16]。吗啡激活MOR的信号途径,产生触摸奖赏效应[17]。作用于MOR的麻醉药物曲马多可导致奖赏效应,这也与MOR的激活有关[18]。
MOR信号途径是治疗吗啡耐受及成瘾的新的药理学靶点[19]。例如鼻内纳洛酮给药可以迅速结合MOR,从而抑制与MOR相关的成瘾行为,如赌博成瘾和乙醇成瘾[20]。
5 MOR在免疫抑制中的作用及机制
随着对阿片类药物的研究,发现阿片类药物对免疫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关注,MOR除了在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表达外,在免疫细胞中也有表达。
阿片类药物成瘾者和长期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患者感染率增加,尤其是肺炎感染。研究发现吗啡具有免疫抑制作用,MOR拮抗剂或MOR基因缺失可阻断免疫抑制作用。例如在吗啡治疗肠炎沙门氏菌感染的野生型小鼠中,肠道淋巴组织、血液和腹膜液中细菌含量高,血浆中促炎细胞因子的水平升高,而用吗啡治疗的MOR基因敲除小鼠中,任何器官均未检测到沙门氏菌,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没有升高[21]。趋化因子是外周和中枢性疼痛途径中免疫和炎症反应的重要调节剂,靶向MOR-趋化因子受体5异聚体,可抑制炎性和神经性疼痛[22]。吗啡作用于活化的小胶质细胞,可增强核因子κB的活性,通过MOR-PKCε-Akt-ERK 1/2信号传导途径,增加一氧化氮、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白介素1β (interleukin1β,IL-1β)和IL-6的释放,从而诱导小胶质细胞的促炎作用[23]。
6 MOR在肿瘤转移中的作用及机制
MOR在癌症组织上表达增高,在MOR基因敲除小鼠中,肺癌细胞成瘤性被抑制。MOR通过非受体酪氨酸激酶(non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rc)/相关接头蛋白1(associated binding protein 1,Gab-1/GRB 2)/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肌醇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PI3CA)/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 3)/Akt1途径促进癌细胞增殖和迁移。 MOR的抑制(siRNA,shRNA或MOR拮抗剂)阻止生长因子诱导的Src/Gab-1/PI3K/Akt/STAT3信号通路的激活,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24-26]。
7 MOR在认知障碍和抑郁症中的作用和机制
靶向MOR的药物,通过前额叶、基底节等脑区调节奖赏效应,影响决策和认知功能。蓝斑(locus coeruleus,LC)-去甲肾上腺素觉醒系统,通过前额叶调节认知过程。在应激过程中,应激相关的神经肽、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和作用于MOR的脑啡肽,通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受体1(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 receptor,CRFR1)调节LC活性。CRFR1和MOR的激活分别对LC神经元具有兴奋性和抑制性作用,雄性大鼠LC中MOR表达水平较高,因此,阿片类药物对不同性别的认知影响具有差异性[27]。有研究发现:MOR在海马区的表达也存在性别差异,可能与认知障碍和抑郁症在不同性别发病率有关。
研究发现MOR在海马区星形胶质细胞表达,它的激活引起膜超极化并抑制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突触传递,从而导致CA1锥体神经元和齿状回颗粒细胞的抑制。因此,GABA能中间神经元的MOR在海马区MOR信号传导中起重要的作用,而星形胶质细胞MOR的激活会导致谷氨酸释放,从而增强海马区Schaffer侧支-CA1(SC-CA1)突触处的谷氨酸能突触传递,有助于MOR介导的海马区突触传递增强和阿片样物质介导的情景记忆。海马区MOR信号参与神经发生、癫痫发作和应激诱导的认知记忆障碍过程,星形胶质细胞MOR在这些疾病中的病理生理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28]。
人类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与应激反应和适应应激功能障碍有关,而内源性MOR与应激和情绪调节有关,MOR拮抗剂增强恐惧和焦虑感,因此,MOR在MDD发病中起重要的作用[29]。MDD患者前额叶皮质、丘脑、腹侧基底神经节、杏仁核和周围杏仁核皮质的MOR活性降低,缓解疼痛药物以及安慰剂可通过诱导MOR信号途径,从而止痛、抵抗抑郁以减轻焦虑症状,因此,MOR 可能成为MDD治疗的靶点[30]。
8 总结
吗啡耐受及成瘾是吗啡药物受限的主要原因,MOR在吗啡耐受及成瘾中起重要作用,进一步弄清MOR的药理作用机制,将为减少镇痛类药物的耐受及成瘾提供新的策略。此外,MOR可能成为免疫抑制和肿瘤转移以及精神疾患等疾病治疗的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