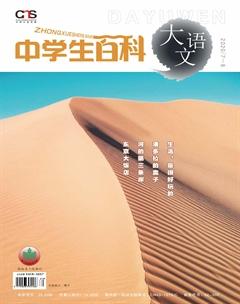末日长河里的冬泳
林林
当我们用尽全力生活在此时此刻之际,总是会忽视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溜走了,怎么都抓不住。而当我们回过头,翻开某些小说或是影视作品,那些时代的记忆再次席卷,原来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时代。当我翻开班宇的小说集《冬泳》的时候,我好像能看到陈旧的大型工厂,陈旧的大型机械设备,长满铁锈直入青天的烟囱,头顶喷火昼夜运转的锅炉,沙尘暴季节漫天飘舞的亮晶晶的铁粉,以及傍晚像海浪一样从工厂涌向居民区的人们,涌出的各种声音混杂如沉闷的鼓声,在脑海中一直敲打,就像是电影里的场景,掐下这一个片段循环播放着。
我在看河,从塔吉克斯坦流过来的那条河,水势平顺,藏着隐秘的韻律,梯形夕阳洒在上面,释放出白日里的最后一丝善意与温柔,夜晚就要来了,乌云和龙就要来了。我想的是,沿着河溯流而上直至尽头,在帕米尔高原被冰山回望凝视过的,会是什么样的人;一步一步迈入河中,让刺骨的水依次没过脚踝、大腿、双臂、脖颈乃至发梢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被溢出的洪水卷到半空之中,枕着浮冰、滚木,或者干脆骑在铁板上,从此告别一切过往的,会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很长时间,仍旧没有答案。天空呼啸,夜晚降落并碎裂在水里,周围空空荡荡。我知道有人在明亮的远处等我,怀着灾难或者恩慈,但我回答不出,便意味着无法离开。而在黑暗里,河水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充满诗意的描写,宁静中又包含温柔。从这篇《梯形夕阳》开始,班宇用准确、克制、优美之笔将画卷铺展开来,描绘着一群游走在昔日的身影:印厂工人、吊车司机、生疏的赌徒与失业者……他们生活被动,面临威胁、窘迫,惯于沉默,像一道峰或一道风,遥远而孤绝地存在着。
这些人物都扎根于一个共同的背景——工人村。
“85后”班宇出生于沈阳,从小就在沈阳铁西工人村长大,父母是变压器厂的双职工。他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工人村的衰落。而工人村,对于沈阳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时代的标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一直大力发展工业,铁西区更是被称作“中国制造业之都”。20世纪50年代,沈阳市投入1200万元,建设143栋建筑群,沈阳冶炼厂、沈阳电缆厂等44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在铁西区设立了家属宿舍——占地73万平方米的“工人村”——供工人及其家属居住。那个年代,住进工人村,就像今天住进了别墅。50年代全国流行过一句谚语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的就是当时沈阳的“工人村”。到了90年代末,沈阳工业企业陷入发展低谷,大量工厂停产、半停产,大量工人下岗回家“休假”。班宇目睹了成片的工厂消失,再看着商业住宅和商业中心拔地而起,年轻人纷纷逃离,整个城市都放慢了发展的步伐,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显得落寞。
而《冬泳》这本书中包含《盘锦豹子》《肃杀》《冬泳》等七篇短篇小说,它们都记录着那个年代的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就像漫长的冬天,清冷萧肃,而每个人脸上只留下漠然的神情,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灰蒙蒙的寒冷的冬天。
乌云很近,抬手可及,李承杰背对着山峰,目不转晴地看着两侧逆行的风景,班立新只注意着那片乌云,柔韧而漫散,他从来没有这么近接触过任何一朵云彩,他想,闪电会不会也在其中,然后他就看见了闪电,天上的一道光,在他眼前聚集、分解、消逝,伴随着巨响,他闭上眼睛,但闪电的模样仍停留在那里,长久不散。
有些人来了,有些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至于我,我总在这里,总在星星照耀之下。他不仅对一切大事不关心,对任何细小的事也不关心。与其说他在沉思,毋宁说他在幻想。因为沉思的人有一个目标,幻想的人却没有。他流浪,漫游,休息。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不过是高速运转的机械上的一颗螺丝,机器的运作声轰鸣作响,淹没了人们的声音。一个人对于时代只不过是一粒尘埃,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凝望时代的时候,才知道这是我们存在过的痕迹。
他本来以为自己并不在乎,但在不经意间,却发现自己的所有行动却变得很小心。
他不再喝酒,也不打牌,别人喝酒时,他出门抽烟,低着头走过狭长的通道,车间举架极高,左右两侧各铺着一条运输轨道,他跳到轨道里,踩着上面的锈迹前行,他比车床要低,比线圈和配电箱要低,比经过的人群也要低,一直走到尽头,才撑着铁门的底角跳上去,那时他的双腿仍十分有力。
而当我们面对生活这出悲喜剧时,面对那些冗长而琐碎的日常,我们无法探清眼前的道路,也找不到明灯,只能选择直面,又或者我们不曾拥有选项,只能转过身去沉默地生活着。但即便如此,个体所散发出的热量终将传递到那寒冬,融化冰面,点亮黑暗。如冬泳一般一头扎进寒冷的湖水中,冻得僵硬的身体慢慢舒展开,慢慢游动,再探出水面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