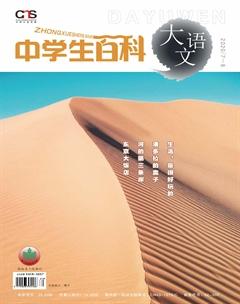鲁迅的十首新诗

一
诗人鲁迅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是他的二十几首散文诗,后来集印为一册《野草》;其次是他的一批旧体诗,其中的名句如“我以我血荐轩辕”“城头变幻大王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脍炙人口,传播尤广;他早先也曾写过几首新诗,知名度不高,现在读者也很少,简直几乎要被忘却了。其五四时代的新诗篇目如下:
《梦》(《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
《爱之神》(同上)
《桃花》(同上)
《他们的花园》(《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人与时》(同上)
《他》(《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
一共六首,都在《新青年》上,皆署名唐俟,是分三回发表的:第一回三首,第二回二首,第三回就《他》这一首。按这样的形势画一个统计图,直线下降,趋向于零。果然,鲁迅后来便不再写新诗;而于1919年8、9月间在《国民公报》发表了七段散文诗,总题为《自言自语》,看样子还要再写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戛然而止了,几年以后才重新开始。鲁迅有时会潜伏一段时间,酝酿进行新的工作(参见顾农《鲁迅的十年潜伏》,《上海滩》2013年第4期)。这种潜伏也可能细化到某一更小的领域。
颇堪注意的是,鲁迅停止新诗写作之日,也正是他开始动手来创作散文诗之时。这样一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转换,似乎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新诗这种文学样式不适合他自己,甚至也可以推测,他认为新诗不适合中国。
后来到三十年代,杨霁云首先把鲁迅的新诗搜集起来,编入《集外集》(五首,缺最后一首);为此鲁迅在该集的序言中回顾自己当年的情形道:……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到鲁迅晚年,他在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据说曾说过这样几句很极端的话: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这份谈话记录未经鲁迅本人审阅,而且有迹象表明,其中渗透了斯诺本人的某些见解;但斯诺也不大可能完全无中生有——鲁迅在闲谈时用极而言之的调子批评中国新诗,是完全可能的。
在1925年发表的《诗歌之敌》(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一文中鲁迅为年轻人的爱情诗辩护,意在抨击坚守旧道德的保守派,但他又写道:“说文学革命之后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可见他对新诗的现状及其前途很不乐观。
鲁迅的新诗大抵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威的,他完全摆脱了旧体诗的腔调,用非常散文化的文句,表达对新思想新生活的追求。
第一首《梦》,说中国人有许多梦想,往往后梦赶走前梦,诗人呼唤“你来你来!明白的梦”。这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
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他们的花园》一首则大谈应当大力向外国学习及其困难:从“他们的花园”摘来一朵白得像雪的百合花,却很快就有苍蝇来拉些矢在上面,令人气得无话可说,可是——说不出话,想起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还是要学外国,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诗歌这样写,很近于比兴体的杂文,乃是时代精神的号角,路径与小说《狂人日记》殊途同归。
他们的花园
小娃子,卷螺发,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
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 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这一批新诗中水平最高的大约是最后一首《他》:
一
“知了”不要叫了,
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头记着。
太阳去了,“知了”住了,——还没有见他,
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
二
秋风起了,
快吹开那家窗幕。
开了窗幕,会望见他的双靥。
窗幕开了,—— 一望全是粉墙,
白吹下許多枯叶。
三
大雪下了,扫出路寻他;
这路连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寻他,——阿!回来还是我家。
这诗的写法很像是魏晋之际大诗人阮籍的《咏怀》。“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忽忽朝日,行行将何之?不见季秋草,摧折在今时。”(《咏怀》其八十)鲁迅诗里的“他”,无非就是阮籍笔下的“佳人”,代表一种难以追寻的理想。鲁迅甚至说,追着追着,竟发现她已经死去,埋在山上(古代的墓上多种松柏)。这就比阮籍要更痛苦了。五四群众运动高潮到来之前,鲁迅有一种深沉的悲观,这一点他在《呐喊·自序》里也曾明确地说起过。
思想过于超前,形式也大为超前,这样的新诗就写不下去了。
鲁迅虽然不再写新诗,但仍然很热心帮胡适选他本人的诗作,又替周作人修改《小河》;鲁迅的诗人气质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他已经决心“洗手不作”,而一心运用那些更适合于他的文学样式,继续呐喊奋斗。
二
鲁迅写过旧体诗,有绝句和律诗;也写过新诗,五四前夜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六首,后来到三十年代初叶又有歌谣体的新诗四首——可是这四首一向被视为他的旧体诗,还有进而论定为“古风”的。否认歌谣体诗是新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错误,其意若曰:只有无节调不押韵的才是新诗——这个观念相当顽固而且可怕。
这四首歌谣体新诗是1931年底发表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童谣》以及1932年初的《“言辞争执”歌》,因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只能刊登于当年的地下报刊。《好东西歌》唱道:
南边整天开大会,北边忽地起风烟。
北人逃难北人嚷,请愿打电闹连天。
还有你骂我来我骂你,说得自己蜜样甜。
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
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
失了土地捐過钱,喊声骂声也寂然。
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
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
声明误解释前嫌,
大家都是好东西,
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讽刺国民党党国要人的内讧和勾结,令人想起眼前的事实,“牙齿痛”“上温泉”二句尤有比较明确的所指。这样骂上门去的歌谣是无从公开发表的。
这几首诗,内容具有尖锐的政治针对性,艺术上则充满了改进新诗写法的探索性。五四前后兴起的中国新诗数量不少,脱离群众,读者无多,影响远远不如白话文的小说和散文。大家比较熟悉而且能够记住的,还是旧体诗,特别是唐诗。
新文学在诗歌领域里的革命迄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鲁迅一向认为,新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1935年9月20日致蔡斐君)曾经有若干诗人在形式上作过种种努力,很成功的不算多。读者太少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鲁迅特别强调新诗应该能唱。1934年11月11日他在答复窦隐夫的信中写道:“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诗的改革就是要在这些地方作出努力。鲁迅继续写道:“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可以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
“实在不会做”是鲁迅的谦辞,他分明做过有节调而且押韵的新诗,《好东西歌》等四首就是例证;只可惜他不过偶一为之,没有作出持续的努力。即使是伟人也只能做属于他的那一份事业,可以只手包打天下的只有神仙。
附:鲁迅作于五四时期的另外三首新诗
爱之神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桃花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注:杨妃红,《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人与时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作者简介
顾农,1944 年 4 月生于江苏泰州,1966 年 6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8 年夏天开始教书,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建安文学史》《魏晋文章新探》《文选与文心》《花间派词传》《听箫楼五记》等,又曾编过《大学语文》教材和一部散文选《扬州的风景》。此外在《文学遗产》 《燕京学报》《文史知识》《书品》《鲁迅研究月刊》《散文》等处发表过论文和散文多篇。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专辑”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