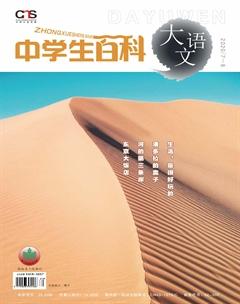霍乱之乱(节选)

1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悶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迹象。走暴不是预兆,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的走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1
晚饭异常地丰盛。还是由食堂送到我们站里来的。荤菜有红烧肉、糖醋带鱼,蔬菜有冬瓜、豆角,豆制品有家常豆腐、干子炒榨菜,汤有丝瓜鸡蛋汤。二号病疫区处理现场指挥部的领导同志都来了,与我们一同在大会议室吃饭,以汤代酒为我们壮行。
六点整,总指挥长挥动了一下小红旗,说了一声:出发。总指挥长是副市长,大家总也没有记住他的姓氏。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感觉到副市长和蔼可亲,一声“出发”也吼得很有气势。一个副市长亲临现场,无论如何都能够说明我们事业的重要性和伟大性。大家看上去自我感觉都比较膨胀,个个笑逐颜开,跃跃欲试,不由自主地就把巴掌都拍红了。
真正的出发时间是六点四十分,因为所有专业性的准备工作都必须经过闻达的检查,然后由他根据封锁疫区的程序调配车辆。到处都有人在叫“闻主任”,闻达“哎哎”地答应着,匆匆跑到前面又匆匆折身跑到后面,痛心疾首指手画脚地批评化验室粪样盒带少了,药房的药品品种太单一,万一还发现有其他疾病患者呢?你不给予治疗吗?闻达扯着嗓子叫道:“要知道,我们是去封锁,封锁,封锁!里面的任何人是不能够出来的。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治疗,防疫,吃,喝,拉,撒,等等,等等。”
消杀科的装备不合格。我们流行病室只带五只储槽是肯定不够的。闻达臭骂赵武装说:“你吃了八年的稀饭吗?臭塘乙村有九十九户人家,四百四十五口人,是计划生育的大漏洞。计划生育不归我们管,但我们不能不给没有户口的人接种疫苗!你告诉我?五只储槽够吗?”
赵武装只得严肃地回答:“不够。”
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和秦静拿储槽。”
我拉着秦静跑到供应室,请窗口的护士们都让开,对漂亮的小谢说:“我们可以再拿五只大储槽吗?”
秦静说:“能够尽量快一些吗?”
我和秦静既客气又优雅,装出有几分怕她的样子。小谢气得翻着白眼,用力地把储槽一只一只地顿在领料台上。我们抱起储槽,目不斜视地一直走出走廊才愉快地笑起来。
我们都穿上了进入疫区的正规防疫服装,除了自己贴身的衣服之外,一层白大褂,又一层后面开口的白大衣,没有想到这种白大衣是加厚的棉布,穿在身上跟盔甲一般。再把工作帽一戴,口罩一戴,飞行员的眼镜一戴,齐膝的长筒胶靴—穿,里头就开始哗哗地出汗。武汉的夏天,三十五至三十九摄氏度的气温。没有干活人就差不多要热昏了。大家高兴地抱怨说:“平时我们什么都要不到,这次上面一重视,夏天都恨不得给你发棉袄。既然这么地把我们当人,再热我们也得全穿上。”
我们一个个全副武装地从防疫站出来,体态臃肿,伸着胳膊,像太空里的宇航员一样,笨拙缓慢地爬上汽车。
马路上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后排的人站在自行车上。保卫科的人不时地逮住一个冲过来的愣头青,把他们往人群里掀,他们挣扎着叫喊:“疼死我了!”人们相互打听着:“这是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情?”有一些年纪大的人自以为德高望重,径直走到了防疫车跟前,问我们:“小大夫同志,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我们的帮助吗?”
我说:“需要。我们请您回到自己家里去。”
我的俏皮话在这一次的行动中获得了一个展示的机会,全站的人都开始认识到我的诙谐有趣。
六点四十分,闻达跳上了第一辆指挥车。我们浩浩荡荡的车队终于出发了。我们朝西行进,晚霞满天,太阳正在西下,红彤彤地映照着我们的车窗,给我们一种迎着朝阳向前进的错觉。不过错觉也同样鼓舞人心。
在十字路口,我们遇上了红灯,第一辆指挥车拉响了警报器,呼啸而过。后面的救护车和防疫车装备的是急救警报,与公安的警报声音不一样,但是也跟着呜呜叫了起来。所有的红灯对我们都没有了作用,我们一一地呼啸而过。我把脸紧紧贴在车窗上,看着一马路的车辆统统在给我们让道,我的眼睛潮湿了。参加防疫工作以来,我也曾屡次地外出访视病人,去其他城市,去农村,去工厂,去矿山追踪传染源。我们总是坐长途汽车,和农民以及他们的鸡和猪挤在一起。我们穿着解放鞋,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走大半天。天长日久,所以产生了关于我们的一段民谣:远看是一个要饭的,近看是一个烧炭的,一问是一个防疫站的。现在谁会以为我们是一个要饭的或者是一个烧炭的呢?这么一抚昔追今,泪水涌了上来。听见我吸鼻子的动静,赵武装说:“你这人哪,完全是狗肉上不了正席。”我说 :“我是狗肉又怎么样?”
他们嘲笑我,可他们也一直把脸贴在车窗上。
只用了我们昨天夜里三分之一的时间,臭塘乙村就已经遥遥在望了。
12
臭塘乙村原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村落,城市的地图上没有这个居民点,农村也根本不认为它是农村。它位于工厂与农村最边缘最荒凉的接壤地带。这一地带原本是农村的荒湖浅滩,是工厂的废料废渣堆。一段高高的水利土堤将它在城市的眼皮底下隐蔽了起来。这里居住的全都是工厂的半边户。丈夫是工人,老婆是农村妇女。丈夫本来是工厂里的老单身,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把老婆接到了城里,并居住了下来。臭塘乙村的房子清一色是工人自己动手盖的工棚。看上去简陋,实际上非常结实,使用的全是钢筋的大梁。村子里没有什么树木,一排排低矮的房子显得特别枯燥,铁皮的屋顶在阳光下闪烁着灼热的白光。村子的四周是荒滩和臭水塘,零星的荷叶已经孤零零地枯死。水面上浮着肮脏的泡沫拖鞋和家禽的内脏。此刻正是晚饭时间,大多数的屋顶都冒着炊烟。臭水塘边有妇女在洗菜,光屁股的小孩子与鸡鸭猫狗在外面玩耍。
一种在提法上已经被消灭的烈性传染病,就是发生在这么一个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这是我们昨晚冒着大雨寻找到的地方。昨晚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今天清楚地看见了所谓的臭塘乙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赵武装、我、秦静,我们搭着手檐,远远地望着臭塘乙村。我说:“这一次我深切地发现了自己的幼稚,我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秦静说:“我吃惊的是这些人在怎样生活。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组织。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们,假如肖志平不去看病,假如洪大夫他们没有送粪样作培养,假如我们没有发现他们,那么眼前的这个村庄就有可能被霍乱整个地吞没。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赵武装说:“看着你们在成熟,作为一个老大夫,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秦静说:“赵大夫!这么严峻这么荒诞的现实,一点都不能让你感到沉痛吗?”
赵武装偷偷地向我吐了吐舌头,旋即沉痛地说:“沉痛。怎么不沉痛呢?我是一个男人嘛,男儿有泪不轻弹。”
秦静没有说话,遥望着臭塘乙村,独自地向前走去。我捅了捅赵武装,示意他跟上去。原来我以为我非常了解秦静,现在看来我并不非常了解她。我突然觉得她在哪一点上有一点儿像闻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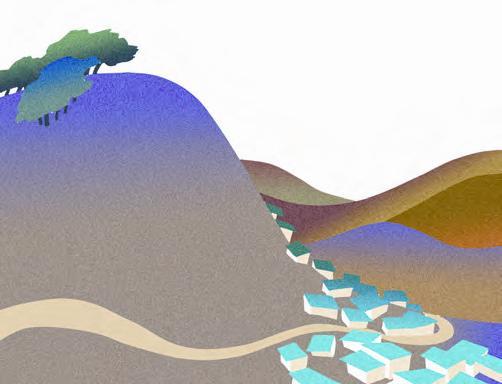
我们的几支队伍会合在土堤下面。除了我们防疫大军之外,还有街道办事处组织的提供柴米油盐的队伍,有派出所和民兵联防队的一支队伍,有半边户们所在的工厂组织的一支队伍,另外还有一支新闻队伍。他们离大家远一点,有长发花衬衣的摄影师、摄像师,有秀气的姑娘,他们都戴了太阳镜和各种太阳帽。他们不由闻达指挥,由市委宣传部亲自领导。其他几支队伍的头头都被带到了闻达面前向他报到,以便封锁行动能够步调统一。封锁还没有开始,有人就找闻达告状来了。有一些民兵已经把街道办事处的汽水和面包吃了许多,但是这不是为工作人员提供的,是受命提供给臭塘乙村的居民的。街道办事处的头头拽着闻达去找民兵的头头,闻达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可是民兵的头头并不买账,说:“这么热的天气,那我们喝什么?”
闻达不习惯人家的顶嘴,说 :“喝什么?我喝了什么?”
民兵们七嘴八舌地说:“你是谁?说话怎么这水平?我们管你喝不喝!”
趙武装率领我和秦静冲了过去,赵武装说:“你们说话要注意一点,这是闻达主任,是二号病专家,现场的一切都要听他的指挥。”
民兵们拿指头指点赵武装的鼻子,说:“哪里冒出来的小白脸,滚一边去!”
我和秦静也拿出指头指他们的鼻子,我们说:“你们干什么?活像土匪。我们不要你们的协助,你们哪里好玩哪里玩去!”
民兵们气极,大伙子的人挺着胸脯围了上来。
闻达在一边又是跺脚又是用力地拍着巴掌,大声吼叫道:“反了!简直反了!”
解围的人围了上来,有人劝阻民兵,有人劝阻我们,有人高声说:“同志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俗话说的是:同船过渡,五百年修。我们大家碰到一起是很不容易的呀!不要这样嘛。”
闻达在现场乱窜,到处找总指挥长,他逢人就说 :“我不干了!由你们来!”闻达把张书记、祈站长吓得跟在他后面连连作揖,说 :“老闻,老闻,咱们可使不得知识分子的小性子啊!让他们吃,让他们喝,最后不是有总指挥在吗?”
闻达哪里听得见张书记和祈站长的话,跑得飞快,满世界叫总指挥——总指挥——副市长终于被闻达找到了。副市长说:“闻老师,您别急,慢慢说。”
闻达说:“我都急死了,还慢慢说。马上就到封锁的时间了。”闻达看看表,气急败坏地纠正说:“封锁时间已经过了!”
副市长说:“是的,过了十分钟。我知道,我正在协调各方面的配合。一般大的行动晚几分钟算不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嘛。您有什么事情呢?”
不知是副市长泰然自若的态度还是副市长的话使闻达一下子又清醒了。他盯着地面看了一会儿,粗粗地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说:“没有什么事情了。我要开始了。您能不能管理好汽水饮料什么的。”
张书记责备地说:“老闻!”
副市长宽容大度地哈哈一笑,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一阵动乱过去,行动正式开始。派出所、民兵联防和工厂戴红袖标的老工人兵分两路向臭塘乙村包抄过去。他们到处乱喝别人的汽水固然不对,但是他们的包抄行动让我们眼界大开,不得不服气。他们的行动如猛虎下山,迅捷又准确,蹚泥过水,毫不含糊。包围一开始,臭塘乙村就砸了锅。许多人没头没脑就往外冲,被民兵像逮贼一样一个一个地按住了。
臭塘乙村工人们的厂长带着闻达率先接近臭塘乙村。厂长在电喇叭里喊话说:“大家都听好了,不要惊慌,这是医生,来给我们治病的。”
闻达接过电喇叭说:“乡亲们,工人弟兄们,我是闻达,是防疫站的流行病医生。你们这里在流行一种肠道传染病,我们要求大家从现在起一律不要外出,都待在自己家里,等候我们医生的检查和治疗。”
厂长与闻达走在进村的泥泞小路上。他们不停地轮流喊话。包围圈基本形成,消杀科的人马出动,都背着军绿色的喷雾器,戴着飞行员眼镜,全副防疫服装,沿着包围圈散开,准备由外向内进行卷帘式的消毒。
村里的女人尖叫起来,拉着孩子到处躲藏。男人们拿起了木棒、铁锤、扳手、起子等工具,在村口堵住了厂长和闻达,一把缴获了闻达手里的电喇叭。男人们把闻达的胳膊扭到了背后,凶狠地说:“你少来这一套,以为披一件白大褂就蒙哄得了我们吗?老子是工人阶级,什么没有见识过,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公安局的!”
闻达说:“我不是公安局的。我这么瘦,哪里有本钱当公安。我是医生,来给你们治病的。”
工人们说:“你以为我们是傻瓜,我们生病了会自己去医院的。实话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包围我们村子?后面这一圈围上来的人是不是要使用化学武器?”
闻达说:“不是不是,是来给你们消毒的。”
工人们怒火万丈,说 :“我们没有毒,你们来消毒做什么?是的,我们的家属没有户口,我们是躲在这里多生了几个孩子,我们擅自住在这里是不合法的,但是,青天白日,共产党的天下,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能偷偷地杀人灭口,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闻达急得不住口地解释,并且说市长都来了。工人们说:“说公安部长来了我们都不奇怪。”闻达又大叫厂长,要他解释,可是厂长哭丧着脸说:“现在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到底发生什么病,也没有人对我解释清楚啊!”
闻达说:“你这个同志,一点觉悟也没有!为什么要对你解释清楚是什么病呢?”
工人们不再与闻达啰唆,他们给闻达限定了十秒钟,把电喇叭给他,要他让包围村子的人员全部撤退,否则,他们就砍掉闻达的一根手指。
副市长在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他说:“太不像话了,太愚昧了。我得亲自过去。”
副市长周围的人急忙拦住了他,大家说哪里能够让您去呢?这里的全盘指挥一刻都离不开总指挥长啊。再等等看,只要聞达不是太书生气,有一点群众工作经验,这一点小矛盾是不难解决的。
村口这里已经数到了十秒,闻达说:“等等,别急着动武,你们看我这个办法行不行?”在这关键时刻,闻达急中生智把老何叫了过去,让他把消毒液喷在自己的身上。老何没有办法,只好把闻达喷得精湿。闻达在消毒液的淋浴下作出安全的、开心的样子给工人看,工人们突然笑了起来,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13
大部队呼隆隆地开进了村庄。
首先像共产主义到来了一样,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几个单位为各家各户提供了七日之内的柴米油盐,这是臭塘乙村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喜出望外,感激涕零,拉住闻达的手说:“让您受委屈了。您怎么不早说你给我们送吃的来了呢?”
秦静说:“你们还是工人阶级,说这种话真让我们替你们脸红。有吃的就是好?”
—些工人还的确是很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闻达说:“讲得好!”闻达说完之后并没有想到是秦静。秦静整个人全都包裹在防护服里头,站在闻达身边的就是一个笨拙的白人。闻达说:“你是谁?”
秦静说:“秦静。”
闻达说:“是你?你敢说这么尖锐的话?”
秦静说:“这有什么,刚才您一个人进村都不怕,我还不敢说一句坚持真理的话吗?”
闻达说:“好!说得好!你比你的同学有出息多了,别看平时她嘴巴厉害,但用得不是地方。从现在起,你要多负担一些工作,我顾不过来的地方,你要挺身而出,好吗?”
秦静说:“好的。谢谢闻主任。”
我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赵武装也站在不远的地方。我们流行病室所有大夫都在不远的地方。所有人都清楚地听见了闻达和秦静的对话。赵武装赶紧过来对我说:“是你吧?对不起,我替秦静道个歉。”
我捏着嗓子笑了一声,让赵武装以为他认错了人。赵武装果然以为自己认错了人,又挨个地摸索过去,问:“是你吗?是你吗?”
我溜到秦静背后,拍了她一掌,说:“现在你的确非常能干了,还会挑动干部斗群众了。”
秦静说:“别胡闹。你知道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工作太有意义了,我觉得我突然找到了自己得心应手的工作。”
我说:“你不再喜欢病毒了?”
秦静说:“不喜欢了。”
我说:“三分钟的热度。一时间的冲动。新打的茅厕三天香。看着吧,我不会比你差的。”
秦静说:“那就往后瞧吧。”
我说:“赵武装比你懂得人情世故,可怜他到处找我道歉去了。”
秦静说:“庸俗。”
我说:“就是,赵武装一个中专毕业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秦静说:“讨厌。”
夜又降临,想起昨天以前的一切,恍如隔世。我们成功地封锁了疫点。全村老少一个没有跑掉。正在病中的五个病人被我们检查了出来,当即就塞进救护车送回了医院。根据现场繁忙而混乱的情况,秦静提出了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将我们流行病室的医生打散,每人带领一个由检查、采样、注射、发药、消毒各专业组成的小分队。每个小分队进一户人家,就可以有层次有条理地完成整个疫情处理过程。闻达马上采纳了秦静的建议并且到处赞扬她,害得赵武装又一次地到处找我道歉。我当然又成功地躲开了他。谁要他道歉?再说,表扬秦静并不意味着批评我。赵武装懂事也太懂过分了—些。我讨厌这样的男人。
随着小分队的成立,现场的混乱局面大为改观。秦静率领的小分队工作效率最高。只见他们紧紧簇拥在秦静的身边,利落地进这家出那家。秦静高亢而果断的吆喝声命令声不时地划破臭塘乙村嘈杂的燠热的夜空。她这种嗓音里透出的是那种高学历高资深医生的威严和魄力。臭塘乙村调皮的孩子和难缠的妇女遇上秦静就老实了。
相比之下,我就没有秦静能干。我的口罩一再地被妇女们扯掉,她们也不是故意,她们有的人要么是怕打针,要么是拉不出大便不肯配合采样,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满村子地去追赶拉扯她们,她们跟我就像打架一样。当我的口罩在拉拉扯扯中不幸被弄掉之后,妇女就与我嬉皮笑脸起来,说:“是一个小医生呀,我有四川泡菜吃不吃?我没有病,就不要给我打针了吧。”我怎么发脾气,她们都不怕,说我是一个观音像,天生一颗糯米心,怎么也是软的。我都被她们气得流眼泪了。她们严重地挫伤了我欲与秦静争高低的信心。我只能对秦静服气。也许我才不适合做流行病医生吧?在臭塘乙村这个荒诞的村庄里,我首次注意到了我人生严肃的重大的职业问题。
工作到半夜,我累极了。汗水多次地湿透了我的防疫服,腋下窝、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已经散发出汗馊味,自己都觉得十分难闻。我找到一处无人的墙角,脱下了防护服和白大褂,只穿着短裤和背心迎风站着。我没有约束自己的毅力,我只知道自己快要热死了。如果闻达此刻发现了我,他肯定暴跳如雷,会立刻将我逐出封锁区,不再容许我进入封锁区工作。刺鼻的消毒液垄断了臭塘乙村的空气,我大胆地不顾后果地站在这熟悉的空气里,用敷料擦着汗水,望着臭塘乙村的幢幢人影,我的心再也回不到往日的平静状态中,我再一次地考虑这个问题:也许我不适合做流行病医生。
封锁区隔离了总共十四天。在最后一例带菌者连续三次粪检阴性之后,我们才鸣锣收兵。肖志平以及五名患者都健康地出院了。臭塘乙村没有一个人出现闪失。倒是我们防疫站的医生几乎都累病了。老的是高血压、心脏病、胆囊炎什么的旧病复发,年轻的是重感冒、无名低热、中暑休克什么的。我中暑休克了两次。秦静重感冒,赵武装也是重感冒。我计算了一下,这十四天,我们的睡眠平均每天只有两个半小时。
从封锁区撤回来的那一天,臭塘乙村的村民恋恋不舍地将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他们一定要我们的人马都停下来,听听他们的心里话。闻达让我们都停了下来,尤其让我们年轻人都走到前面来,受受感动和教育。
他们说:“说一句心里的话,我们最感激你们的是:你们让市长,让公安局长,让街道办事处,让工厂的领导们都注意到了臭塘乙村,重视起了臭塘乙村。我们从此有人管了。计划生育发现了我们的孩子,要罚我们的款,这个我们不怪你们,到哪儿生多了都一样罚款。其实我们哪里有什么病?拉一点肚子,算什么病?谁个夏天不拉几次肚子。肖志平是为了开病休条才去看病的,没有想到引来了你们。从来没有医生像你们这么好,我们一点小毛病,你们都主动地费了這么大的心。实在是辛苦你们了。”
闻达的脸色逐渐地难看起来。他对村民们挥了挥手,说:“算了,不用多说了,没完没了地干什么?”
我们无奈地笑笑,上车走了。臭塘乙村的人们觉得我们在小题大做。他们感谢我们的小题大做。他们最终也不知道他们患的是霍乱。
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行动严格保密。
这样,事后便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辉煌。别说臭塘乙村村民对我们的误解了,就连在疫情中出现过的领导也再没有来到我们防疫站。没有张灯结彩的表彰和大大的奖状。新闻媒体没有一点动静。赵武装的有关论文当然也就不可能寄到世界卫生组织去了。时间过去了一段,疫情期间购买的许多设备发生了财产归属纠纷。比如防疫车,站里认为应该归站里而不应该归流行病室;储槽应该归医院供应室而不是防疫站;大量的消毒剂应该由防疫站支付经费而卫生局当时是垫付;等等。就连医院食堂都天天找上门来,一是结账,二是搜寻他们丢失的餐具。我和秦静当然没有受表彰和涨工资,因为上面认为我们是在做分内的事情。工资就是那么容易涨的?这样一来,群众对领导大有埋怨之辞,张书记对祈站长大有埋怨之辞,祈站长对闻达大有埋怨之辞。大会小会谈的都是我们站在霍乱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有人议论说闻达太狂妄了一点;有人说闻达这个人好大喜功,贪大求洋。
总之,我们站除了增添了一些是非之外,突然地,一切都恢复了从前的平静和单调,就跟没有轰轰烈烈地处理过霍乱疫情一样。
但是,我是回不到从前了。秦静也回不到从前了。赵武装自然也回不到从前了。闻达却回到了从前,他的脸又垮了下来,目光躲闪,一副神游身外的样子,他与谁都搭不上腔,且走路又是拖泥带水了,鞋底总是吱吱地摩擦地面,两只不同的皮鞋又穿在了他的脚上。每天下班之后,闻达依然在小套间里写一个小时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他的妻子仍然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做家务而待在办公室的。要说闻达有什么没有回到从前,那就是他的皱纹和白发。他的皱纹更深了,两鬓也全白了。
14
后来,第二年的夏天,我到底还是放弃了流行病医生这一职业,又去投考了其他的专业,我将彻底转行。仅是去供应室换储槽这一件小事情,我都厌恶至极。我也不再有兴趣注意秦静与赵武装的关系了。我与他们太熟悉了,没有新鲜感。
赵武装是在六年之后离开防疫站的。他通过艰苦的带职学习,获得了医疗系的大本文凭,终于转到了临床,在医院做内科医生。赵武装顿时就变得比较牛气了,头发很亮,皮肤很光滑,手指很白皙。
秦静一直在防疫站流行病室,闻达也一直在防疫站流行病室。有一段时间,闻达有望提升防疫站站长,据说还是因为他的性格问题没有成功。
秦静与赵武装的关系不了了之。
其实后来不久就出版了新的流行病学教材,新教材还是比较地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我在新华书店翻着看了看,怅然一笑,便把它放回了书架。
闻达与秦静合作的关于那场霍乱的论文终于得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上进行宣读,这是近年的事情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的消息。报纸上说是秦静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某某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并且她的宣读赢得了广大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我为秦静感到了由衷的高兴。十几年执着的追求到底有了一个明显的结果,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不知道她自己作何感想?
那么闻达呢?他该有六十多岁了吧?他早该退休了。他退休了怎么办?最后他找到自己为什么总穿一双两只不同的皮鞋的理由了吗?
说真的,我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勇气为了消灭什么而遭遇什么,为了不可知的结果而长久地等待,为了保存内心而放弃外壳。
但是,在十几年之后,我懂了有一些事情是值得你去这么做的。当然是你热爱的事情。因此,闲暇的时候,发生霍乱的那一天经常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在回忆中为自己寻找生活的道理,有许多的道理总是在后来回头的时候找到的。往前走的路总是无可凭借,一如断了铁索的上山的小路。
(节选,有删减)
赏析
《霍乱之乱》是一篇与瘟疫相关的文章,来自大家熟悉的作家池莉。虽然现在是专职作家,但池莉本人曾在年轻时担任流行病医生,为《霍乱之乱》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由此可见人生阅历对写作的影响非凡。若是没有相关的经历或详尽的调查研究,专职作家恐怕很难写出经得住推敲的特殊职业角色。只有亲身经历才能带来普通人难以捕捉或想象出的细节和感受。赶上如今的特殊时期,重温池莉的旧文或许能让我们从医生的角度重新理解疫情暴发和他们工作的难处。
《霍乱之乱》与本期读到的其他几篇作品相比,更像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饱满的人物、戏剧化的冲突,池莉并不过多留恋于展示人物的内心,而是让人物替他们自己发声,她尽职尽责地讲好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或许与大家所期盼的略有不同。
可能只有经历过疫情的工作人员才能写出“大家看上去……个个笑逐颜开,跃跃欲试”这样的句子,也只有心系百姓的医务人员才能考虑到超生的可能性,并坚持带上超额的疫苗为所有居民接种,而当地居民的种种考量、与群众沟通的困难,更是难以琢磨。霍乱暴发在计生、争夺资源等大事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毕竟只是有几个人拉肚子。而这一段经历给文中各个人物带来的影响更是难以预计。
总是伏案工作的科室主任对流行病研究抱有莫大的热情,平日伏案工作的他在霍乱暴发中爆发出非同一般的领导力。平常自视甚高的秦静反而从一场战役中听到了内心真正的召唤。而跃跃欲试的“我”最终认定自己不适合这行,彻底离开了流行病学。面对生活剧烈的变化,人们时常感到被裹挟其中,无法用旁观者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分析。而事实上,一场流行病不仅改变了患者,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也改变了医者的生活。生病与治愈的过程、许许多多人力物力的投入、日后对危机的复盘,能传递给后代的信息复杂且多层。不轻视历史教训是我们最起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