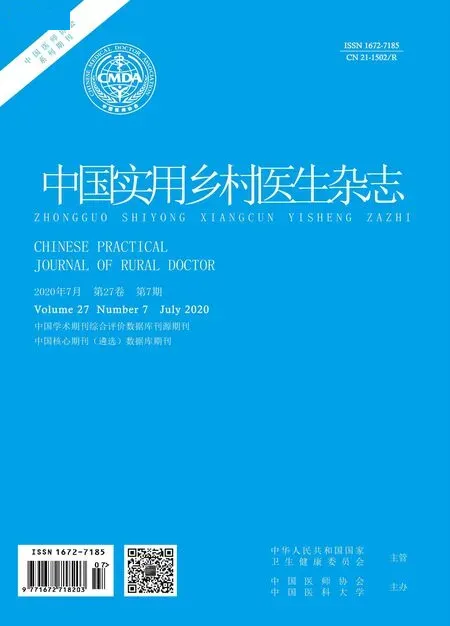艰难梭菌性腹泻与药物相关危险因素研究综述
韩伟娜
作者单位:110021 沈阳,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儿科
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 CD)于1935年首次被描述,这种细菌在健康新生儿粪便标本中发现,直到1978年才首次与疾病相关。艰难梭菌是引起一系列抗生素相关性结肠炎(AAC)的主要因素之一,范围从轻度腹泻到中毒性巨结肠[1]。由于广谱抗生素的普遍使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此类慢性病的折磨。
艰难梭菌相关疾病(CDAD)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在北美和欧洲正在增加。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CDAD患者的患病率、病死率、总归因死亡率和结肠癌切除率明显增加[2]。
虽然艰难梭菌感染病例在中国日益引起关注,但是却很少报告关于艰难梭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了对艰难梭菌性腹泻有更好的认识,本文从艰难梭菌性腹泻的发生机制和药物引起的艰难梭菌性腹泻相关危险因素进行综述。
1 艰难梭菌性腹泻发病机制
艰难梭菌的致病性中最重要的两个毒素是毒素A和毒素B,两种毒素的TcdA和TcdB基因均被编码,并与两个调节基因(TcdC和TcdR)相关联。TcdE对高毒力菌株(027型)分泌TcdA、TcdB是必要的[3]。毒素A通过释放白三烯,前列腺素2(PGE2)和肿瘤坏死因子α以及中性粒细胞迁移而产生严要的炎症反应[4]。毒素B通过狭窄连接的改变,流向上皮细胞的基底外侧。两种毒素的作用都导致严重的上皮损伤,伴有细胞水肿和大量的腔分泌物(分泌性腹泻)[5]。毒素在内体中被内吞并激活,然后使Rho蛋白糖基化,改变肌动蛋白连接,产生细胞毒性作用并改变肠屏障[6]。肌动蛋白解聚和细胞坏死,触发炎症级联反应,破坏细胞间紧密连接,使肠道黏膜通透性增加,导致组织损伤、腹泻以及伪膜性结肠炎[7]。
Warny M等[8]认为NAP1/027型是一种艰难梭菌的流行菌株,与严重疾病相关疫情有关。在N A P1/027中,毒素浓度在稳定期早期达到峰值,表明大部分毒素产生在对数阶段。发现NAP1/027产生的毒素A是对照菌株的16倍,毒素B是对照菌株的23倍。如果体外毒素A和毒素B的比例在结肠腔中相似,则NAP1/027的毒力菌株可能主要源于毒素B的产生而增加。毒素A(TcdA)与毒素B(TcdB)的蛋白结构和宿主六磷酸肌醇(IP6)介导的激活机制相似,但毒素B诱导细胞凋亡的毒性至少为毒素A的100倍[9]。
包括NAPI/027型在内的约17%~23%的CD产毒株可分泌CD二元毒素(CDT)[10]。核糖体027型流行病菌株的出现,其表现通常更为严重,与定植相比感染率增加,复发率更高,败血症、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更高。腹泻患儿中该菌株的分离率为10%~19%[11]。
2 艰难梭菌腹泻危险因素
最常与艰难梭菌感染(CDI)相关的抗菌药是克林霉素、青霉素和头孢菌素[12]。也许是由于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的增加,这类药物的使用最近被认为是CDI的一个危险因素。
2.1 克林霉素 克林霉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被广泛使用,是治疗厌氧菌感染的首选药物。然而,在1977年,一种克林霉素耐药、产毒艰难梭菌菌株被鉴定为仓鼠克林霉素相关性结肠炎的病因[13]。首批涉及克林霉素耐药艰难梭菌性腹泻暴发于1989年,随后在1990年代初暴发了3次更严重的情况。这些研究证实了克林霉素增加了CDI的风险。Johnson S等研究证实了在美国不同地区的四家医院爆发的大规模腹泻都是由一种对克林霉素高度耐药的艰难梭菌株引起的,并且克林霉素的使用是一个特定的风险因素,其中只有15%的非流行菌株对克林霉素有高水平的耐药性。结果表明,接触克林霉素后艰难梭菌相关性腹泻发生的相对较高可能性不仅是对驻留菌群的影响,也可能与机体的易感性有关。这种疾病的风险随着克林霉素的使用和克林霉素耐药艰难梭菌菌株的存在而增加[14]。
2.2 头孢菌素 第一代头孢菌素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批准在北美使用,并迅速获得处方认可。头孢菌素暴露很快成为CDI暴发的一个强有力的风险因素。艰难梭菌对大多数头孢菌素完全耐药[15]。使用第二代和第三代头孢菌素,如头孢呋辛、头孢他啶、头孢噻肟和头孢曲松,与CDI的特别高风险相关。Riley TV等[16]研究发现,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家医院通过禁止使用第三代头孢,导致在1999—2000年三代头孢使用量减少,CDAD发生率降低了50%,并使用时间序列干预分析法分析了第三代头孢使用政策对CDAD发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控制外源因素后,干预后的CDAD发生率在统计学上有显著下降。因此,抗生素处方做法的变化会影响CDAD的发生率,并可能影响抗生素耐药性病原体。
2.3 氟喹诺酮类药物 与头孢菌素类似,氟喹诺酮类药物因其良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活性光谱而成为治疗住院和门诊患者的常用抗菌药。自引入环丙沙星以来,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应用变得广泛[17],此类药物还有加替沙星、吉米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和氧氟沙星等。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使用与CDI的暴发有关,报告的OR值和相对风险范围为2.0~12.7[18-19]。Loo等[20]报告了由氟喹诺酮耐药艰难梭菌(即BI/NAP1)的主要菌株引起的CDI发病率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对较高,在超过1 700名接受评估的患者中,随机选择15%进行病例对照研究,以确定发生CDI的危险因素。自2001年以来,BI/NAP1菌株在北美至少8次暴发中以不同的频率被分离出来,这些暴发中的分离株对所有测试的氟喹诺酮类药物都具有完全的耐药性[21]。氟喹诺酮类药物的暴露被描述为CDI的独立危险因素[22]。在一些研究中,艰难梭菌中氟喹诺酮耐药性的获得与DNA促旋酶活性位点的突变有关[23-25]。
2.4 组胺2阻滞剂(H2RAs) Tleyjeh IM等[26]在严格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中观察到H2RAs和CDI之间的关联。在接受抗生素治疗的住院患者中,CDI与H2RAs相关的绝对风险最高,另一方面,证实了H2RAs在普通人群中作为非处方药使用不会明显增加CDI的发生风险。胃酸抑制的程度可能在增加感染风险中起重要作用。Kwok等[27]从15项研究中比较了CDI与胃酸抑制的风险,这些研究报告了独立于参与者样本的质子泵抑制剂(PPI)和H2RAs估计值,发现两者都会增加风险,与H2RAs相比,PPI具有更高的感染风险。H2RAs也可能通过减少细胞增殖,抑制炎症介导的一氧化氮浓度,通过影响结肠愈合和改变细胞因子产生来影响肠道免疫系统[28-29]。此外,维持结肠内源性细菌平衡可以防止肠道感染,胃酸减少已被证明可以改变较低的肠道菌群[30-31]。结肠细菌的改变可能增加CDI的发生风险[32]。
2.5 质子泵抑制剂 PPI和H2RAs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有效药物。因此,它们可能与上消化道内菌群改变有关,并导致诸如吸收不良、肠感染和胃肠道外感染等并发症[33]。Dial等[34]在两项不同的研究中发现,PPI的使用与艰难梭菌感染的风险增加独立相关。Turco R等[35]研究证实,PPI治疗是CDAD的相关危险因素,其风险比为4.8。PPI治疗是成年人和儿童CDAD的重要危险因素。尽管抗分泌药物在预防和治疗上消化道症状方面有明显的好处,但医疗保健提供者应考虑抗艰难梭菌感染的风险。Nylund CM等[36]研究发现PPI和H2RA都与儿童和青少年CDI和CDI复发的风险增加有关,证实了CDI在儿科年龄组中的增加趋势。特别是在CDI风险增加的患者中,应慎重使用胃酸抑制药物。
3 小结
本文对艰难梭菌的发病机制以及抗生素、PPI和组胺H2RAs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尽管抗菌药物对治疗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破坏了肠道内微生物平衡,可能引起感染复发。因此,在临床中治疗腹泻病应该注意处方药的平衡与剂量,避免药物带来的风险。益生菌、盲肠造口术进行冲洗或结肠切除术治疗艰难梭菌腹泻是当前和未来的研究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入,艰难梭菌腹泻病的危险因素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