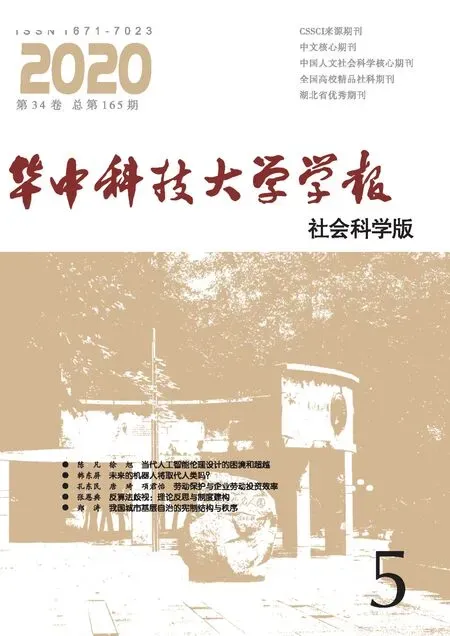论新技术环境下作品独创性的判断
——以“选择空间法”为视角
□袁锋
一、问题的提出
独创性也称为原创性,作为著作权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界定了作品的保护范围,没有独创性便无法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作品独创性概念的理解与适用却一直存在争议,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较为权威、统一的定论。因独创性问题的复杂性、模糊性以及不确定性,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如同哥德巴赫猜想般难解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1]。其主要理由或许在于:一方面,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文艺、科学领域的无形智力成果,不具备有形的、稳定的物质形态,理论界只能通过抽象的思辨或逻辑推理来认知它,同时还需要借助一些文学、美学、艺术等领域的理论来理解它;另一方面,作品类型的动态性发展与独创性标准的一体化程式之间的矛盾。理论界和实务界总是寻求一种稳定的、一体化程式的标准来判断作品的独创性,但文艺创作的方式和表达形式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伴随着各类新技术的发展,作品创作方式更加多样化,著作权法中的作品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从最初的小说、戏剧、绘画到电影、计算机软件,等等,每一种新型作品的出现都会对著作权法带来新的挑战,传统的独创性标准经常处于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状态。同时新型作品的出现迫使著作权法作出新的改变,尤其是要不断检验、调整作品的独创性标准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这进一步加剧了独创性判断的难度[2]。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现行立法并未对作品独创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对独创性内涵予以明晰,司法实践中关于独创性判断的盲目性和空洞化问题由来已久[3]。同时置身于当前媒体融合时代,各类媒介技术的空前发展和商业模式的日新月异,使得作品创作和传播方式愈加多样化,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表达方式也更加丰富,纷至沓来的是愈加复杂的版权利益纠纷。近几年来著作权法领域中几类新技术疑难问题的爆发,推动了国内学者和法官对作品独创性问题的争论浪潮,例如“体育赛事直播侵权案”“中国音乐喷泉第一案”“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争议案”,以及“黑洞照片版权争议事件”等。上述几类新型疑难案件和事件均涉及作品独创性的理解和适用,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作品独创性问题并未达成一致共识,这进一步扩展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在独创性问题的具体判断上具有主观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①例如,有学者通过对我国著作权相关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当前大多数法官对于独创性的判断仅是出于直觉,主观性过强,并未科学地适用独创性标准。参见刘丽娟.如何认识作品独创性[J].科技与法律,2006(4):71-78.。因而在新技术环境下,对作品独创性的理解和适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立足于作品独创性的理论基础,结合国内外的相关司法实践,总结归纳作品独创性的界定标准,并将其适用于新型疑难案件的分析,希冀为相关司法实践提供有益指引。
二、对传统作品独创性判断方法的反思
作品的独创性理念是司法实践的产物,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作品独创性判断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作品独创性判断标准的认定存在不少歧义,而要科学地界定作品的独创性,就必须对相关歧义予以辨析,这是本文论证的逻辑前提。根据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各种观点,判断传统著作权独创性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根据创作所需的成本来判断独创性。这一标准的最初雏形是英国的“额头流汗原则”,这是独创性判断最早的方法,也是英美法系之前的主流判断标准。该标准强调作品的经济利用,作者只要在创作过程中付出了劳动、资本等创作成本就具有受版权保护的正当性。在审判实践当中,不少法院虽然逐渐不再依靠“搜集信息的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大量劳动和成本”来认定作品的创造性,但依然根据创作过程所需的“劳动和技巧”来认定创造性。只要在创作作品过程中体现了作者的“劳动和技巧”,即使是少量的也足以构成作品的独创性②例如,在“Henkel KgaA v.Holdfast案”等系列案件中,新西兰法院依然认为,技巧和劳动的程度依然是判断独创性的必要标准。See Henkel KgaA v.Holdfast[2006]NZSC 102, [2007]1 NZLR 577 ,37;Karum Grp.LLC v.Fisher& Paykel Fin.Servs.Ltd.[2014]NZCA 389, 87; Univ.of Waikato v.Benchmarking Servs.Ltd.[2004]NZCA 90, (2004)8 NZBLC 101,561,27.。其二,根据“个性标准”来判断作品的独创性。大陆法系国家在判断作品独创性时,往往强调作者创作作品的事实,强调作品是作者的精神连接和智慧产物,因而要求作品应当体现作者的人格和精神,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独创性判断的“主观主义标准”[4]。作品要构成独创性必须为“作者自己的智力创造物”(author’s own intellectual creation),体现作者的个性③Infopaq International A/S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Case C-5/08[2009]I-06569.,作品的独创性必须体现“作者的痕迹”(personal touch)④Painer v Standard VerlagsGmbH(C-145/10)[2012]E.C.D.R.6.SAS Institute Inc v World Programming Ltd(C-406/10)[2013]Bus.L.R.941.。其三,根据“客观形式标准”来判断独创性。一些学者为应对和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定性问题,主张对作品独创性的判断采取“客观形式标准”,即通过作品的外观差异来判断作品的独创性[5][6][7]。为了实现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保护,“客观形式标准”对传统作品理论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调整:第一,“客观形式标准”将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从人的创造力扩张到机器的创造力[8],人工智能生成物因此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第二,“客观形式标准”将现有的作品判断标准客观化,只要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形式上与传统作品相同就可以获得保护[9]。例如,Shlomit Yanisky-Ravid等学者认为,作品的独创性判断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无关,版权法应适用“形式—客观”标准来认定独创性,即综合考量作品的颜色、外观、文字等整体外形,进而将人工智能创作的智力成果也纳入作品的范畴之内[10]。其四,根据“新颖性标准”来判断独创性。主张通过作品的外观差异来判断作品的独创性,而且这种差异必须达到新颖、独一无二的程度。例如,欧盟学者JAL Sterling认为,著作权法独创性标准应该向专利法的“新颖性标准”看齐,独创性的判断上应达到“独一无二”(unique)[11]的程度。美国学者William W.Fisher和Joseph Scott Mille等认为,当前司法实践对独创性的判断和界定过于模糊、抽象和不可操作性,增加了法官主观判断的任意性。为减少主观标准的偏见,应设立一种“客观的”“形式的”标准,据此,他们主张借鉴专利法中的“新颖性标准”,即申请注册的创作物的整体外观(overall impression)必须不同于之前公开发表的作品。当然为确保这一标准的实施,一方面,著作权法必须像专利法那样建立一套公示、查询的制度,同时也要建立完备的作品信息数据库;另一方面,作者在申请作品注册时,必须提交相应的证明其独创性的证据和说明[10][12][13]。
上述方法虽然都曾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各自都存在一些理论和实践的障碍和问题。首先,就根据创作所需的成本来判断独创性而言,其主要依据的是洛克的劳动理论。这一判断方法的优势在于:简单快捷,并且门槛较低,有利于对创作过程中融入了作者劳动、技巧和资本的所有文艺创作物进行保护。其问题在于:版权法对作品设定独创性要件正是意味着并非所有劳动都能产生权利,只有当劳动产生的结果满足某种标准时,劳动者才能取得权利。这种标准需要一定的异质性,而劳动概念显然不符合这一异质性[14]7-9。正如Gervais教授所言,“独创性意味着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显然远超技巧和劳动,而是充满着人类智力创造的事物”[15]。在“Computer Assocs诉Altai案”中,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更是明确指出:在判断作品独创性时,并非付出了劳动成果就一定享有版权。事实上,在制作过程中大量的、技巧性的劳动并不必然保证其成果的可版权性,只有付出了“创造性”劳动而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成果才能享有版权[16]。
其次,就“个性标准”而言,“个性标准”的确立是“浪漫作者主义”①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派指出,(浪漫派作家)强调表现人的主观情感,崇尚想象,试图剖析人的种种精神现象。此种哲学观点影响了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成为法国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参见李琛.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财产一体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4(2):68-78.的美学和哲学观被法律所选择,成为著作权合理性的基础[17]。一方面其对独创性的要求设立了一个较高的门槛,并非所有付出劳动、技巧和资本的文艺创作物都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只有体现作者个性特征、反映作者人格价值的文艺创作物才是作品;另一方面,“个性标准”也有利于解释体现作者个性、人格的独创性作品为何会有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人身权利。然而“个性标准”的问题在于:某对象是否反映了人格,只能是一种解读,“这种诠释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绝非逻辑的必然”[17]。如果说早期的作品类型是个体手工创作模式的产物,小说、戏剧、画作等确实可能体现个体创作者的意志和个性,然而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发展,各种蕴含复杂、碎片化信息的作品不断出现,例如计算机软件、大型数据库等功能性作品的出现,这些作品很难说具有多强的个性和人格特征,而是以追求功能性、合理性为目的的。此外电影作品、职务和委托作品等基于投资形成的作品,则并非完全体现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和人格特征[14]11。正如中山信弘所言,在作品类型繁多的今天,“个性标准”能否套用于所有的作品类型,不无疑问[18]49-50。另外,“个性标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较为空洞,很难提供较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独创性判断方法[19]。
再次,就“客观形式标准”而言,“客观形式标准”试图根据创作物整体外观的“可差异性”以及审美价值来认定作品的独创性。“客观形式标准”的优势在于:它认识到了作品的本质在于独创性的表达,因而作品独创性的判断应关注于最终成果的“表达”上,而非“个性”或劳动过程的判断,而且它还可以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定性问题。其弊端在于:一方面,作品的创作必须是基于人的意志之下产生的美感,有无“人的意志”作用是作品独创性判断的前提条件[20]。将人工智能作为著作权的主体会导致以激励人类知识创新为核心的著作权制度在理论上难以自洽。另一方面,法官并非专业的文艺专家,每个案件都要求法官根据外观的“可差异性”以及审美价值来认定作品独创性,难度较大,无法轻易实现。早在1903年,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就在“Bleistein案”中对法官给过警告:“由那些只接受过法律训练的人来对一件美术作品价值进行最终评判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超出了最狭窄和明显的界限”②Bleistein v.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188 U.S.239,251(1903).。此外,仅根据整体外观来判断作品的独创性还容易导致对一些外观上具有作品形式、但实质上缺乏智力创造性的成果给以保护,例如音乐喷泉和“黑洞照片”等(本文将在下文予以详细论述)。
最后,就“新颖性标准”而言,其本质是根据作品外观差异的“新颖性”程度来判断独创性,将发明创造的“新颖性标准”强制性移植到著作权法中,但《专利法》中的“新颖性标准”具有前所未有性和强烈的排他性,这是因为《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利用自然法则、客观存在的技术方案,发明成果是客观存在的,发明与发明家本身之联结较弱。而对于文艺创作而言则明显不同,作品创作往往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他人作品的启发,因而许多作品的创作是在模仿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人类文化的延续性也要求作品创作应当在先人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因而对作品独创性的判断,如果要求追求“新颖性”,限制一切模仿和继承,那么这不但违背文艺创作规律,而且也会阻碍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根据这一“新颖性标准”,如果仅从表达形式上进行新颖性审查,可能会导致一些虽形式上有所差异、但本质内容一致的情形;如果不但对作品形式而且也对其内容进行审查,那么上述学者所构建的“新颖性标准”就必然要求审查者进行相应的主观判断,那么,这一“新颖性标准”也并非绝对的“客观”和“形式”。同时上述学者也没有提出进一步审查的判断方法和规则,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也没有解决独创性判断的模糊性和抽象性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上述论者所倡导构建的“新颖性标准”仅是一种初步的理想化设想,而为了适用这一标准还必须构建类似于专利的公示、审查机制,并且需要配备更多专业的人力、物力资源,增加大量的制度成本。
三、作品独创性判断的新路径——“选择空间法”的基本内涵
关于著作权法独创性的讨论是著作权法一个永恒的主题,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独创性的界定标准存在诸多争议与批判。传统独创性的判断方法在应对和解决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实践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然而由于其各自的弊端和问题,逐渐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著作权法体系[18]52。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表达方式逐渐多样化,各类新型案例和争议事件也层出不穷,如“体育赛事直播侵权案”“中国音乐喷泉第一案”“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争议案”,以及“黑洞照片版权争议事件”等。传统独创性判断方法无法对这些新型案件和事件提供合理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建立一个无需从“作者体现个性”等主观要素入手,但足以涵盖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和现代功能性作品的统一的独创性理论[18]52。事实上,在著作权法理论和实践领域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方法,它散见和隐含于一些学者的论述以及法官的司法判决中,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总结和归纳,将其概括为“选择空间法”。在复杂的技术和利益现实面前,“选择空间法”所具有的内涵和活力有助于弥补传统方法的缺陷,有效地解决各类新技术问题,同时有助于构建更加合理和完善的作品独创性判断的方法体系。
“选择空间法”的核心在于:作品的独创性可以客观地从特定类别作品的表达空间进行界定。因而这一方法的关注对象既非“作者个性”,也非形成作品过程中所花费的任何劳动和资金,而是落在“选择空间”的判断上。有学者指出,“选择空间”这一概念可能最初源自德国。德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2项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仅指人格的、精神的创作”,即作品必须体现作者的“个性”,并以此作为作品概念的核心性质。而在判断独创性时,德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往往注重“创作余地”(Gestaltungsspielraum),即根据创作当时有无自由的选择空间做判断。此判断方式为德国部分学者采纳,认为“个性,以具有让创作者人格特征发挥的选择空间为前提”[21]。换言之,任何作品的创作都存在表达范围的宽度,它常常受限于创作作品的方法、题材、受众、合同的关系、作者和作品关系等,而表达范围的宽度会限制作者的选择空间,影响其个性发挥的余地[22]。正如美国法官在“Mattel,Inc.v.MGA Entertainment案”所举的例子,有许多方法拍摄以外星人入侵地球为题材的电影,这时作品的表达范围就很广,选择空间也很大,但如果要求你在白色画布上创作红色弹力球无法创作出太多差异性的表达,此时的表达范围便很窄(a narrow range of expression),可选择的空间也有限①Mattel, Inc.v.MGA Entertainment, Inc., 705 F.3d 1108(9th Cir.2013).。因为著作权法保护人类的智力活动,相关创作行为必须体现其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如果创作物表达范围足够充足,作者必须运用充分的智力活动,从广泛的表达空间中选择特定表达,以此即为赋予著作权保护的基础。如果没有智力活动运作的场合,自无保护的必要。举例来说,撰写10万字左右的恋爱小说,不同的人将创作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恋爱小说,选择空间极大,需要运用智力活动来对特定表达进行选择,故应赋予其著作权。在选择空间小的情形中,由于缺乏智力活动的创作,故应否定其创造性。例如,记录一年的最高或最低气温,不过是根据一些常规的技术规范和机械作业,基本上不存在智力活动选择的空间[23]199。简言之,选择空间大者,则肯定其创造性;选择空间小或是只有一个选项时,则应否定其创造性[21]。在运用这一方法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诉称创作物的创作仅仅是按照简单的步骤或既定的规则、公式或结构机械地完成一种工作,任何相关公众在掌握相应的技能或知识之后按照既定的规则或步骤操作所产生的结果,只要不出现失误,都是相同的,这说明创作可选择的空间极为有限,由此产生的创作物自然无法具有独创性[24]。例如,将五线谱改为简谱,在这一创作过程中虽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音乐知识,但由于五线谱与简谱之间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任何相关公众根据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去创作,在操作无误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最终成果都是相同的。因此,这种按照既定规则进行机械创作所形成的产物无法满足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只产生音乐作品的复制件[25]。又或是以全白的画布为条件,在全白画布作画,虽然有广大的选择空间,但倘若只是忠实地根据既存作品进行创作,按照既定的形式和规则进行创作,对此应该否定其独创性,这便是精确临摹所形成的成果无法构成作品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原因所在[23]202。
其次,某一创作物即便存在广泛的“选择空间”,但如果创作者的选择在相关公众看来是普通或显而易见的表达,那么该创作物也无法满足独创性要件。正如德国著名的著作权专家雷炳德指出:“创作必须更多地属于在自己的作品领域比人们期待的普通的智力劳动带来更多的活动”;“那些运用普通人的能力就能做到的东西,那些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成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是新的,也不能受到保护”[26]。举例来说,以1000字内为条件撰写新年贺卡,形式上选择空间极大,但如果创作者最后只写了“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指教”或类似的普通、显而易见的表达形式,这只不过是模仿既存表达、并无智力活动的运用,应否定其创造性。对这样的创作物如果进行保护,不但不能起到激励创作的作用,反而会制造更多、过滥的垄断,束缚和妨碍人们进行更有益的创作活动[23]202。例如,日本法院在“箱根富士屋ホテル案”中作出的判例中明确指出,表达某一内容时,即使有其他表达之可能,也不能因此将该表达理解为具有创造性。因此“选择空间”虽是肯定独创性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在判断独创性时,除了需有充足“选择空间”外,被选择的“表达”还必须展现其智力创造性,不能是显而易见的个性化表达①参见知财高判平成22年7月14日判决书。。
最后,由于作品类型和性质的限制,不同作品类型留给创作者的选择空间并不相同,因而不同作品领域的独创性判断标准也有所差异。具体作品的表达范围和选择空间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便是著名的“小铜板理论”(klenie muenze)②由于德国著作权法对客体保护的要求必须达到严格的“创作高度”,德国1895年“Inkasso-Programm案”中,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也要求达到严格的创作高度,此案遭到德国学界广泛的批判。之后,德国受到欧盟有关计算机软件准则的影响,在1993年修正1965年《著作权及邻接权保护权法》时增列第69条之第1款规定:“计算机软件是著作权人的独特智慧创作成果而表现个性之著作者,那么该计算机软件受保护。尤其保护能力之确定,不适用于其他准则,特别不适用品质或美学的准则……”此后,德国著作权法依著作权客体不同,有时不要求特别的“创作高度”,而依“小铜币理论”(klenie muenze)只要求适度的创作水准,如计算机软件、商品说明书、表格、目录等。蔡明诚.论著作权之原创性与创作性要件[J].台大法学论丛,26(1).。例如,对于小说和绘画等传统作品类型而言,由于存在无限的表达手段、表达方法,如果他人独自创作,几乎不可能与既存作品采取完全相同的表达,因此可以说传统作品类型通常具有较为充足的“选择空间”,其构成独创性的可能性较大。而对于设计图、计算机软件等功能性作品而言,由于其创作选择的空间较小,只要创作体现一定的、并非太过狭窄的选择空间,便应承认其独创性。当然,如果因功能性作品受限于表达手段或表达手法,可能不得不利用特定表达,又或者为追求功能性或效率性,可能只有同一或类似的表达,在此情形应否定“选择空间”的存在,否定其独创性[24]。我国司法实践也坚持“小铜板理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政策曾明确指出,“著作权司法保护既要维护独创性基本标准的统一性,坚持获得著作权保护首先要以具备最低限度的独创高度为条件,又要根据各类不同作品的特点……灵活把握独创高度,合理确定保护强度。”③奚晓明:《准确把握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研讨班上的演讲,2012年2月8日。
“选择空间法”有助于客观地判断作品的独创性,因而逐渐获得司法实践的青睐,并成为日本司法实践中的通说[27]。事实上,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国内外一些司法判例虽没有直接使用这一术语,但其所运用的原理与之基本一致,这充分说明其普遍的实践价值。例如,美国第五巡回法院在“天然气地图案”中认定,原告创作的加利福尼亚某居民区的天然气地下管道图非常真实、准确地反映了该地区天然管道的分布情况,任何相关公众在操作无误的情况下最终绘制的地图均不会与之产生本质区别,最终判决原告创作物不具有独创性[28]。欧盟法院在“Painer案”中也认为,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它留给创作者自由的、创造性的选择空间(free and creative choice)④Case C-145/10 Eva-Maria Painer v Standard Verlags GmbH et al.[2011]ECDR 6.21,89.。法国法院在其本土领域的经典案例“Pachot案”中,将独创性解读为一种智力投入和选择,同时指出如果某种智力成果是强制逻辑或自动生成的,那么它将因不具备独创性而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①Cass.civ.I,March,R.I.D.A.1999,no.181.。再如,在“不动产交易流程案”中,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如果表达方式和空间有限,相关公众在相同情况之时能作出相同之表达,应认为不具有独创性,因其难能展现作者主观上精神、智慧、文化、创意之表现②参见智慧财产法院97年度民著诉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我国一些法院在审理古籍点校类案件中也曾运用“选择空间法”。古籍点校类案件的核心在于:古籍点校者根据其对古籍含义的理解而对古籍进行点校,由此所形成的文本是否构成作品?我国法院曾明确指出,古籍点校的目的在于复原古籍原意,每个点校者根据自己对古籍含义的理解,在极为有限的点校表达方式中进行选择,但始终会忠于点校者自己所理解的古籍原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新的表达,点校成果也就不具有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不构成作品③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
四、“选择空间法”的具体适用
正如前文所言,“体育赛事直播侵权案”“中国音乐喷泉第一案”“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争议案”,以及“黑洞照片版权争议事件”等新型案例和事件不但对传统著作权制度带来一定的冲击和诘问,而且也在理论和实务界引发广泛的争议和讨论。笔者以为对于深陷技术“藩篱”的著作权制度而言,“选择空间”理论可以解决这些新型疑难问题。在前面的研究中,本文已经对“选择空间”理论进行了一定阐释和论述,然而判断方法是否妥当,也须由其具体适用予以评估。因而下文将试图利用“选择空间”理论对上述几类疑难问题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检验这一方法的解释力。
(一)“体育赛事直播侵权案”
随着体育赛事直播技术和产业的迅猛发展,体育赛事直播侵权纠纷接踵而至。“体育赛事直播侵权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具备独创性。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至今没有形成一致共识。一些观点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形成,是编导通过对不同拍摄设备、不同镜头的选择和编排所产生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和编排会产生不同的画面效果,这反映了最终画面的独创性④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民事判决书。。在最近备受争议的“央视国际诉聚力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涉案足球赛事节目通过机位的设置,镜头的捕捉、切换和衔接,慢动作的回放,故事的塑造等,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在其意志支配下对连续画面的选择、编辑和处理,彰显了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人格因素,属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且符合固定性要求,可以作为《著作权法》规定的类电影作品加以保护”⑤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15民初88829号民事判决书。。此外,由于体育赛事直播属于蕴含着巨大投资和经济价值的智力成果,因而相关的产业界强烈呼吁将体育赛事节目归入作品进行保护。
笔者认为利用“选择空间法”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对于体育赛事直播而言,由于其本质功能在于满足观众的需求,使观众更好地欣赏比赛,因而观众在特定时刻对于出现何种角度的画面通常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⑥例如,在篮球比赛中,当队员进攻时,观众所预期的是以这个进攻球员进攻为核心的画面,而当篮球得分之后,观众预期的是篮球进球的慢动作回放。。其次,体育赛事直播的拍摄设备、位置安排和方向定位都存在着固定的技术规范,在比赛中,拍摄设备应该出现在哪个位置和方向都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对于相关设备的位置方向、设置、镜头转换虽然需要相关拍摄技巧和方法,但这些拍摄技巧和方法都是相关领域的常规性安排。因此,观众的需求和心理预期性以及常规性技术规范限制了体育赛事直播的选择空间,任何相关领域中具备拍摄资质的拍摄者根据观众需求、心理预期以及常规性技术规范所拍摄的最终画面其效果差距不会太大,由此形成的画面显然不具备作品的独创性[29]。在“Murphy案”中,欧盟法院便明确指出,足球比赛受制于比赛规则、技术规范等限制,不具备足够的自由创造空间(leaving no room for creative freedom)⑦See Murphy v Media Protection Services Ltd ,C-429/08,[2012]34 EIPR 203.。在“凤凰网赛事转播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也指出,“在符合观众需求后的可个性化选择的空间内,同等水准摄影师所具有的拍摄技巧同样对于其个性化选择起到限制作用。可见,上述客观因素极大地限制了直播团队在素材拍摄上的个性化选择空间。”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民事判决书。
(二)“中国音乐喷泉第一案”
近年来依托计算机技术和音乐喷泉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音乐喷泉产业得以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愈加复杂的版权难题,其中尤以“中国音乐喷泉第一案”最为典型。在本案中,原告设计并开发了极具艺术美感的音乐喷泉,能够根据不同的背景音乐产生不同形态的喷射效果,之后,被告设计并开发了喷射效果与之相似的音乐喷泉,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侵权,将其诉至法院。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音乐喷泉的喷射效果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如果是,又属于何种类型的作品?本案历经二审,但一审和二审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判决。一审法院认为,音乐喷泉的整体喷射效果具有独创性,但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现行规定的作品类型,最终适用了“其他作品”这一兜底条款对其进行保护。二审法院却认为音乐喷泉的整体喷射效果具有独创性,可以构成“新型美术作品”类型②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40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同样引发了理论界广泛讨论与争议,对一审和二审法院判决的赞成与反对之声各执一词[30][31]。上述观点的分歧反映了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独创性理论以及音乐喷泉法律定性上的歧义,而前文所述的“选择空间法”有助于明晰这一问题。
按照“客观形式标准”,音乐喷泉的整体喷射效果确实具有艺术美感,进而给人以视觉和听觉的沉浸式体验,但音乐喷泉独创性的判断应结合其创作过程与机理进行分析。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的形成本质上是“预编控制模式”的产物,这一音乐喷泉最终效果的实现主要包括如下步骤:提取音乐文件、高低音域的选择、在水型模块库中对水型进行选择、各种灯光、水泵的开闭以及最终代码的编写③其具体运作流程如下:首先,设计师利用音乐喷泉的计算机程序对预定要演奏的乐曲提取波型文件;然后在这一波型文件之上对其进行编码,利用该程序对波型文件进行分段,并利用其水型编辑模块在不同段上人工编制各种水型动作、各种灯光、水泵的开启和关闭,最终完成喷泉喷射的设计,并由编程人员将上述构思设计转换为符合实施性的程序命令;最后,借助喷泉硬件和软件设备将预先编织好的模型在现实当中予以呈现,形成最终的喷射效果。参见袁锋.论音乐喷泉的著作权法定性——兼评我国“音乐喷泉著作权第一案”[J].电子知识产权,2019(7):11-20.。在这一过程当中,提取音乐、音域以及水型的选择、灯光与水泵的开闭都具有一定的技术规范和常规安排,留给创作者选择的空间是有限的,任何具备普通音乐常识和熟悉一定技术操作的公众依据固定的方式或规则都可以完成这一操作,并且由此所形成的最终呈现效果都是一样的,没有本质区别,因而其本质上无法满足作品创作所需的选择空间,无法构成著作权法意义的作品。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争议案”与“黑洞照片版权争议事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定性成为理论界的争议焦点,在司法界也出现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侵权诉讼。例如,2019年4月26日,我国出现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案——“菲林律所”诉“百度网讯”案,而同年的12月24日出现的另一起人工智能案件——“腾讯公司诉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下称“腾讯案”)。在这两个判决中,法院根据不同的独创性判断标准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在“菲林律所”诉“百度网讯”案中,法院依据创作主体的人格属性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无法构成作品④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而在“腾讯案”中,法院依据“客观形式标准”认定,腾讯公司利用涉案软件生成的涉案文章为文字作品而受著作权法保护⑤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民事判决书。。
另一个与之相类似的问题是备受争议的“黑洞照片版权争议事件”。2019年4月10日,事件视界望远镜(event horizon telescope)项目向全球宣布,其利用八个射电望远镜(阵)拍摄到了全球第一张“黑洞照片”。次日上午,视觉中国将该黑洞照片上传到至官方网站中,同时对外宣称“黑洞照片”的版权归其所有。之后“黑洞照片”版权问题引起国家版权局的关注,并将其纳入“剑网2019年”专项行动,一时间,“黑洞照片”是否构成作品、构成何类作品及其版权归属为何等问题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争议。例如,有学者认为,黑洞图片作为作者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32];也有学者认为,“黑洞照片”就其本身而言,其外观形式属于摄影作品的范畴,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33]。
这两类问题的共同点在于:根据“客观形式标准”,人工智能生成物和“黑洞照片”在外观上都满足相关作品领域的形式要件。由于学界当前对作品创作主体是否为人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在讨论上述问题时,如果暂且排除创作主体因素,上述创作物是否构成作品呢?当前理论界似乎无法对此提出较为合理和妥当的解释,而笔者以为运用前文所述的“选择空间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两类争议。
就“人工智能生成物版权争议案”而言,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表现形式上虽具有美感和价值,但对其法律定性依然要结合其创作过程与机理进行分析。虽然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发展,但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尚不具备深层次的人类思维,仿造人类大脑的神经元进行思考的深层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然十分渺茫,当前广泛适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然主要以符号性知识表达为主[34]。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运作机理在于:首先,由计算机程序设计者或使用者预先在人工智能系统中进行数据输入和算法设计,而后人工智能系统以海量数据为基础进行深度学习,通过提取和分析数据找出最优策略,最后根据该最优策略产生最佳结果,生成具体内容。计算机程序设计者或使用者事前无法知悉人工智能会生成何种最优策略,也无法知道根据该最优策略将生成出何种具体内容,但计算机程序设计者或使用者操作同一人工智能系统、利用相同的数据和同一算法分析,得出的最优策略和最终生成物基本上是一致的。事实上,不同的人工智能系统对相同的数据所得出的最优策略和最终生成物也具有高度重复性[35]。换言之,任何具备技术知识的人操作人工智能系统,利用固定算法和模板所生成的最终内容是唯一的或有限的,因而这一有限的选择空间决定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无法满足构成作品所需要的独创性要求,无法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就“黑洞照片版权争议事件”而言,“黑洞照片”的创作与日常照片的拍摄完全不一样,日常照片的拍摄尽管是借助照相机这一机械设备进行拍摄,但拍摄过程为拍摄者留下了充分的选择空间:一方面,针对同一拍摄对象,不同摄影师可以通过对明暗、距离、角度和光线等因素进行个性化的调整和选择,使得照片整体影像的呈现具有不同的效果;另一方面,摄影师可以通过对拍摄对象进行独创性的安排,如要求被拍者摆出特定姿势或表情等,使得影像在内容上具有独特的表现力。此外,拍摄出的照片还要使用各种软、硬件工具进行一系列后期处理,使其产生特殊的影像效果。因此,只要拍摄影像的内容和效果能够体现拍摄者充分的选择空间,就可以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摄影作品[36]。然而“黑洞照片”的拍摄则显著不同,“黑洞照片”的拍摄由全球现有的八个射电望远镜(阵)通过收集黑洞附近的各种相关的信息,然后传回到超级计算机之中,通过一定的算法综合分析、处理、推算,并最终“拍摄”出“黑洞照片”。因此,“黑洞照片”就其本质而言是特定算法推算的产物,任何具备相应技术知识的人按照特定公式和操作都能“计算”出这张“黑洞照片”。换言之,拍摄者对于最终“黑洞照片”的形成没有可供选择的空间,只能获得唯一的结果,因而“黑洞照片”无法构成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五、结语
作品独创性作为著作权法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著作权体系的重要术语之一。正如学者所言,只有独创性才是著作权法作品质的规定,独创性是作品的灵魂[37]。然而独创性概念是如此的捉摸不定,致使理论界引发经年不息的边界之争,同时也给司法审判实践带来盲目性和任意性判断的问题,成为当前著作权立法和司法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本文对传统著作权的独创性判断方法进行了辨析和反思,在明晰传统著作权独创性判断方法的诸种弊端后,建议引入“选择空间”理论作为独创性判断的新路径,以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本文对这一方法的基本内涵和具体适用进行了详细阐释,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并求教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