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诗人决心做美食,他为每道菜写了一首诗
李锐嘉
一位主业是美食家的诗人想要做场中国猪文化文献展。循着线索去,我们在他东四十条的餐厅见面了。
其人二毛,“莽汉派”诗人,成名于上个世纪80年代,穿着一件绅士风衣,眼睛大而有神,聊诗歌的时候斯文,聊美食的时候江湖。
“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烹饪是唯一的通道”
二毛讲起美食滔滔不绝,不仅有古今美食文献和现代物理学原理作依据,还带着诗歌的画面感,“天然气的火尖锐而猛,柴火猛而柔,火域宽广。柴火烧出来的肉是润糯的,炒回锅肉、烧红烧肉最好吃。”
回锅肉是他对美食的启蒙,也在心中埋下了痴迷猪文化的种子。二毛家的回锅肉有秘诀——把锅烧红,将猪皮贴上去烙,之后在温水中浸泡,再用刀刮至金黄,炒制的过程中,依次加入料酒、白酒、米酒,为回锅肉增添一层深远的甜和广阔的香。
后来,母亲在他二十多岁时过世,这份记忆里的甜传承到了二毛的灶臺。

二毛和他的菜谱。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二毛居住的家乡酉阳成为现代诗的重要阵地,涌进了全国各地的诗人。经济条件刚起色,大家暂时还没钱下馆子,好客的二毛就往家里招呼诗人朋友。那个年代,大家吃的都是应季食物,西红柿是西红柿的味道,黄瓜是黄瓜的味道,回忆起来也尤其有滋味。
餐桌上少不了二毛悉心准备的下酒菜,其中一道特讲究,只有大晴天能吃到——先用当地土豆切片,开水焯完后放在大太阳下晒干,再用油锅炸到焦脆,蘸椒盐配酒,满口飘香。二毛给它取了个浪漫的名字,叫“太阳的味道”。
无数个夜晚,诗和远方在美食美酒的香气中氤氲。 “对美食的依恋和想象,成就了我的诗歌,但是反过来我在诗歌中的想象也渗透到了烹饪里。”
实际上,美食和诗歌的交织在二毛童年时便产生。二毛的母亲只念过几年小学,但能把很多歇后语说得头头是道。做家务的闲暇里,她喜欢给二毛出谜语,“比如红口袋,绿口袋,有人怕,有人爱,打一吃的,答对了今天就煮给你吃。”馋嘴的二毛就使劲想啊想,最后猜出来是辣椒,便吃到了妈妈做的虎皮尖椒。在这种想象力游戏中,二毛心里的诗意也随之萌芽。
90年代,二毛一边试水餐饮文化,一边开始以美食入诗歌。尽管从孔子开始就有文人讨论美食的文化传统,但现代诗中以美食寓情的二毛算得上最先锋的一位。
当他研究重庆菜和成都菜的区别,便用两地的人文气质形容菜色,写下“成都菜平原丘陵,风和日丽,重庆菜高山流水,月黑风高”,思考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他说“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烹饪是唯一的通道”,就像一盘家传回锅肉,肉下锅了,香气就能带他到童年时妈妈的灶台边。
渐渐地,他的美食诗在文艺圈流传开来,他用文字下厨,用诗意佐味,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于是,干脆出了一本《二毛美食诗选》,在其中他用诗句讨论一只螃蟹的做法,也谈论锅气飘散出的日常哲思。
美食也是艺术,别人采风他采菜
湖南和重庆交界的一个小镇子,二毛拎着烟酒敲开一户人家。
“我是从北京来的,想在你们这学做菜,能不能看你们炒菜,和你们一起吃顿饭?”二毛托朋友打听到这家的婆婆和儿媳很会做菜,想要上门学习。
对方热情地把他请进去,于是二毛就像个实习厨师一样,跟着那家人买菜、择菜、做菜。那趟,他收获了两个属于这家人的独家菜方——碎豆腐炒榨菜皮和盐菜扣肉炒鸡蛋。
不忙的时节,他会在川渝黔滇等原始生态地区到处转悠,向民间烹饪高手求教,再改良融合到自己的餐厅天下盐的菜式中。画家和作家创作前要采风,二毛笑说他这种行为就叫采菜吧。
二毛相信真正的美食已经下沉到了四五线城市,抛去八大菜系的框架和网红餐厅的套路,他要在民间找到野生的美味。就像他写作的“莽汉诗”式的粗犷直给,他喜欢带着泥土味的食材和不按常理出牌的神来之笔。
菜市场是他找灵感的另一个好去处。看到土猪肉的时候是最兴奋的,老家的土猪肉颜色、纹路和皮脂含量都刚刚好,如果拿食指轻轻在肉上一蹭粘手,说明那块肉是新鲜无水分的土猪肉,炒起来会又嫩又弹,或只是煮熟成白肉蘸调料也是一等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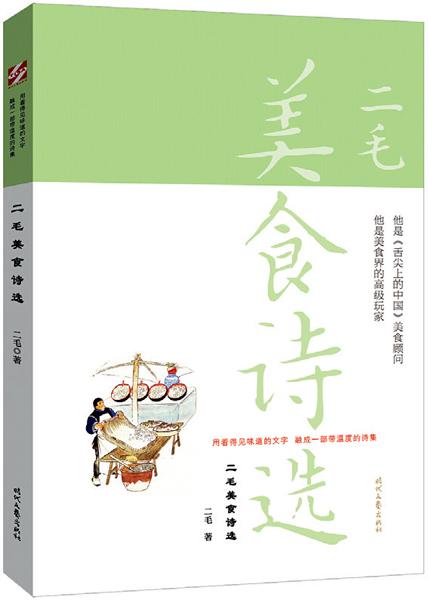
不管去哪个城市,二毛都要去那里的菜市场寻一些北京没有的菜回来,从西双版纳特有的、由野猪驯化成的冬瓜猪到贵州的各种野菜,有一次他甚至带回了两只活土鸡,典型的诗人做派。云游回来,呼上三五诗友,做一桌小菜,谈诗谈美食,仿佛又回到80年代的浪漫,著名诗人北岛、芒克、万夏、李亚伟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菜谱中的诗意
当诗人决心做美食,用功的方式都带着点墨香。
不仅走街串巷地收集民间美食,二毛还回头往老菜谱中探寻味道的美学。 “天下美食那么多,谁都没办法全吃完,但要研究的广阔透彻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多看菜谱。像下棋一样,打谱。”
挎一个陈旧的牛仔包,从成都杜甫草堂的旧书摊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三十多年间他收来了明清、民国和近代的数千册菜谱。这些菜谱在他手中被解构、重塑,最后都成了回馈食客味蕾的养分。
在一本上个世纪70年代的菜谱中,他发现陕西有道叫鸡面的名菜,深得武则天欢心。这道菜的做法颇为奇特,要取刚刚放血的鸡身上那块胸脯肉,捶打至泥状,接着擀成面条状,丢进沸汤煮,起锅后淋上高汤汁。
“民间传说,武则天和丈夫李治太喜欢吃这道菜了,所以把墓地也选在了做这道菜最正宗的咸阳。”二毛乐用神秘的语气分享这则秘闻,说罢,一扬手,“我也照着谱子做了,没有那么好吃,哎呀!古代人和现代人口味不一样!”
作为京城一位高级美食玩家,二毛对川菜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看来辣仅仅是川菜文化中的一种口味,只不过这十年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高油麻辣的水煮鱼、毛血旺等川菜迎合了人们解压的需求,逐渐演变成了川菜文化的主力军。
他的观点在收藏老菜谱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北京饭店名菜谱》记录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店里的经典菜色,二毛发现整本书143道川菜中仅有几道菜是香辣口味,其他川味名菜都是像开水白菜、雪花鸡淖、竹荪肝膏汤这样以鲜味为主打。
“我从收藏的菜谱中无比惊讶地感受到中国美食的博大精深,这在近代菜中看不出来。”在钻研菜谱的过程中,经常有这样超乎日常经验的惊叹时刻。在文本中,他与美食的对话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谁又能说不是一种诗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