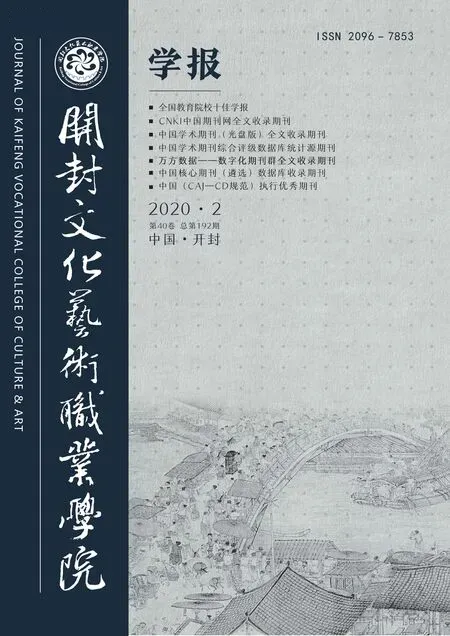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理法
佘爱丽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何为情理法
法国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得曾提出 “情理为法律之生命”,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中表现得很明显。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不区分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故在审判过程中常常需要去解释法,一方面遵循制定法,另一方面结合社会现实在符合情理与法理的基础上进行判案,情理法对国家治理和人民安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旧时的中国法律而言,情理的作用显而易见。自西周的“周公制礼”至两晋的“准五服以治罪”,从“春秋决狱”至“十恶不赦”,无不体现着情理与法律的结合。反向看,中国古代社会情理法的运用实践有着深厚的法理文化基础,其对构建更加完善的现代社会主义法治改革有重要借鉴作用。由此,我们有必要对以“情理法”为核心的古代法律系统进行更深层次、更全面的研究。情理原本应分开讲解,但出于论述方便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情理法亦是受特殊国情的影响,如吸纳儒家讲求伦理和三纲五常,然后结合形成以纲常名教为特征的“礼法”,这里的礼法再次与天理融合,最终成为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与统一体[1]。
(一)天理
天理即指自然的法则。《庄子·天运》有言:“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韩非子·大体》也提出:“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以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这里的天理即天道,有的人谓天可主持公道,儒家将其视为本然之性,程朱理学将其延伸指天理之性,为仁、义、礼、智的相加整体,也就是封建纲常伦理。正如《礼记·乐记》所言:“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处,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惑人无穷… …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二)国法
《周礼·秋官·朝士》:“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书·皋陶谟》:“天叙有典,赖我五典五哉;天命有德,五章五服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这均表达了人间的法律制度出自天命、天意。“法”字在西周写作“灋”,与其他汉字一样,是一个意象丰富的象形文字。由此可知:首先法是一种判断是非曲直、惩治邪恶的行为规范;其次法是一种活动,发生纠纷后由廌公平裁判,并由圣兽行使处罚的惩罚活动;最后是法律的产生、实施离不开廌这一圣兽。
(三)人情
“法不外乎于人情”为中国古代的常识。人情,人者;情者,是谓人和人联系时的本能感知;人情结合,才称为人情;人世社会中人情即世情,此又比人情更近一步[2]。故《史记·太史公自序》道:“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
二、情理法何为
(一)从刑事立法角度进行分析
1.孝子不可刑
君子不得侮辱先圣虞舜,其是二十四孝之首者。舜儿时极为不幸,父亲瞽叟为盲人,母亲去世较早。父亲续娶后继母生子取名“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里,父心怀歹意,继母表里不一,弟顽皮不顺,他们相勾结想将舜置于死地。然而,舜一如既往地对双亲非常孝顺,体贴弟弟。当时,法制已存在,但舜用孝抵国法,刑事立法上未禁止该行为发生,且百姓也认同此行为的有效性,还个个争相效仿。再有施剑翘生于千年后,她手刃杀父仇人,杀人行为的确违反刑法。但是,该女子始于孝而杀人,其志是值得敬佩的,因此,违法行孝情有可原,虽违背国法为父雪耻,仍可视为具备高尚道德的人。儒家认为,高尚之人不应用刑罚处置,即常言道“君子无刑” “礼以待君子,刑以威小人”,刑罚是用来对付卑鄙下流之人的,此说法也颇有儒家伦常之特色,“孝道”非孝必高于法,正确来说是法应当容情[3]。
2.无讼,自可断法
传统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贵和持中、贵和尚中”是旧时中国法律的文化特色。孔子(儒家思想的开路人)也为“无讼论”之奠定人,他曾经提出君主的执政目标是“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往人们无视诉讼,觉得诉讼为道德败坏的表征。儒家从正面倡导无讼的优点,重点宣扬“讼害”言论,“讼,终凶”,故诉讼不是吉利的,应即时停止,善于诉讼的人必凶。又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邓析事件,是中国最早轻视诉讼证据的案件,主角邓析后被称为小人,后死于君主之手。可见,在古代中国审理案件时多追求“无讼、贱讼”[4]。
3.从礼刑关系看三者联系
西周时礼刑关系紧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应和,一起形成较为完备的西周奴隶法制体系。西周的刑与礼是对应的一对概念,刑常称刑法、刑罚。礼为积极规范,从正面肯定地规范民众,即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刑则是对所有悖礼之行为施行处罚,凡礼制禁止的也是刑罚不能容忍的,二者互相证成,即 “出礼入于刑”。礼刑关系是礼先于法实施,得到民众支持和遵从,梳理情理法三者的关系对现代社会是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法理情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再者,规范体制是民众公共整体利益的表现,是较高层次之“情”,正确理解三者统一辩证之关系,坚持情理法有序,才可以保证社会长期、稳定、和谐发展。
(二)从刑事司法角度分析
情理法有机结合,为传统的法文化奠定了重情理的基调。故当情理与法理发生矛盾时,古代人通常都会酌情处理。诚然,我们说司法对情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容的,但是对严重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罪犯,司法必然是予以严惩不贷的。
1.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说把儒家思想引向法律,汉代的董仲舒是运用此方式的杰出人物。具体而言,引经决狱是将法律加以伦理化,欲将礼和法混为一体,使之作为定罪之依据。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求执法的人在审判案件时不光要依照法律,还要谨慎掌握司法之伦理精神,谨记民心之所向。现如今,董仲舒著名的《春秋决狱》已不现于世,后沈家本、程树德对其进行查询考证,发现引经决狱其实是允许“为尊者讳”相关的法律精神[5],此种案件只要不涉及严重负面影响的叛谋反逆案件,均不予归属刑事犯罪案件。
2.违礼是大罪行
传统古代社会,“三纲五常”为天理精髓,“不忠不孝”则为大罪不赦。自董仲舒引经决狱,致使原本仅是道德伦常的规范成为强行性的法律制度。若违反礼制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以往的案例中还有甚者被处以极刑,即当众斩头抛尸[6]。《后汉书·王尊传》中有一例,王尊担任县令时有一老妇告状说养子不孝顺,还妄想与她发生关系。王尊证明该事属实后,将老妇的养子抓到并处以极刑。被告人违反礼度,破坏人情伦常就是此种处罚下场。同为打架斗殴,处罚的程度又各有不同,不相识的两人打架,受四十鞭刑;若兄弟姐妹间相互斗殴,将被关押至少两年,殴打祖父祖母则会被斩首。可见,对打架斗殴之人的刑处会依据亲属关系的亲疏程度及上下尊卑等级来判定,这就是古代法文化中的情理。此构成古代中国独有的判处规则,故不守法者为轻,不遵循礼制者必重。
3.纲常伦理为主,司法真实为辅
中国特别重视三纲五常,尊卑有别。封建社会也正是依靠纲常伦理加以维系的。此构成方式决定了社会必须根据法律来维系秩序,在司法审判中要兼顾情理和伦理。大多数情况下,在某种利益的司法判决中是以纲常伦理为主导、事实司法为辅助的。例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曾讲述吴冠贤当县令时一对年轻人鸣冤,男子道女子是其童养媳,其双亲去世后女子反悔。女子则说己实为男子亲妹妹,男子欲娶她作妻有违伦常。经过知县查证,两人的父母均为无家可归的乞丐,现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按照当地的民俗,一个家庭可以平常养一个女孩作为童养媳,和未来的丈夫以兄妹相称。所以,有人献计在不知俩人谁的话可信的情况下按兄妹论断,到时即便有错也不过毁掉一桩婚姻,比断然违反纲常好得多。知县通过再三思考,采纳该建议。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法文化确实是以纲常伦理为重、以事实司法为辅助的。换句话说,在案情不清晰、不明了的状况下,应先考虑纲常伦理,司法是居于其后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社会,人情是基础,从中抽象出天理(即自然法思想),而以自然法思想为准来制定的便是国法,三者之间是并不矛盾的。但若统治者忽略人情,对天理把握不准确,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国法当然也是不恰当的。具体来说,即当统治者被统治利益所控制,被统治者的利益肯定会做出让步,这样统治者就会以一己之私导致天理与国法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