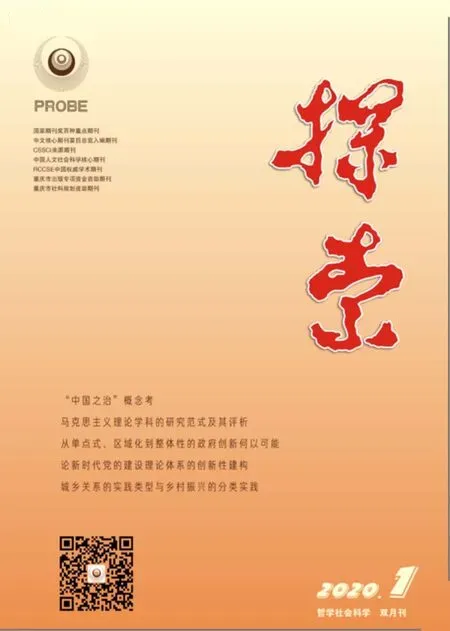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王 刚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党在新时代应该“坚持和巩固”与“完善和发展”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国家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依据和结果,国家治理是国家制度的实践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之制”)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效能,即“中国之治”。那么,“中国之制”从哪里来,它具有哪些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如何推进“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又将如何应对世界之变?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认清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1 历史脉络:从中国实践到“中国之制”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1]3。这一论断说明,“中国之制”并不是“舶来品”和“飞来峰”,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内蕴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1.1 “中国之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历史记载着文化,文化负载着历史,历史也就由一代代人的文化史型构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由此,历史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文化逻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演变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文化。这些丰富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植的文化沃土。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基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宗,四海为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经历了历史的发展与考验,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时代化的阐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观念、“一带一路”倡议等。
中国历史上逐步形成的郡县制度、土地制度、法律制度、货币制度、军事制度、监察制度等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在近现代直到当代的国家制度设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有许多制度还或显或隐地保留有传统政治制度的印记,如郡县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等。当然,我们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治理文化的母版,而是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接续实行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制度的一些历史优势转化为现实实践上的治理效能。传统中国“大一统”思想不仅仅意味着领土统一,而且还是对国家制度的有效构建。秦朝以降,“要在中央”、国家统一、郡县制等成为古代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思想的要素。“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大一统理念开始形成,大一统国家治理也随之成为历代王朝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的思想和制度,在新时代主要有两种体现:其一,面对广阔的国土与众多的民族和人口,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树立党中央权威,从而实现全国上下一盘棋,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其二,面对区域内有不同的地方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得益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思想传承,中国共产党在对港、澳、台的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显著成效成为“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之一,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2 “中国之制”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世界社会主义产生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实践、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发展历程。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制度的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他们在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如在改变旧制度的方法上,马克思确信“全部国家制度总是这样变化的: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2]72。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否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革命与和平过渡之后“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3]685。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3]684。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
马克思曾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35这启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对待,而应视其为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分析了各方面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转变。这是列宁当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地运用于中国制度变革具体实践中的做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继承、创新和完善。在邓小平看来,私有化是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5]111。为此,邓小平认为,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进程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目标确立为“以人民为中心”来解决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使“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6]5,从而在人类减贫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毋庸置疑,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对于实现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旨归。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独特实践场域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7]。
1.3 “中国之制”来源于中国的具体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担负着探索有效的国家制度的历史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临时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婚姻法令,实行了一系列与当时根据地相适应的制度,对苏维埃制度进行了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探索实行了“三三制”政权,这种政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也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与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权,它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同时,还针对当时抗日根据地民众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在选举上实行“豆选”法,深受根据地人民欢迎和好评。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各项制度都进行了探索,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报告制度、解放区的选举制度、土地改革制度等相继建立和完善起来,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创立新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共同纲领》与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与政体,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发展太慢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既有先进的生产力,又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运思逻辑,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在随后展开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完善,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8]
2 现实推进: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
中国实践形成“中国之制”,而“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则支撑了“中国之治”,即通过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把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回答新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之治”问题。这正如《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2这说明,“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即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依据,“中国之治”的一切活动都要以此展开;而“中国之治”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2.1 “中国之制”取得历史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党的领导制度上,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制度;在文化制度上,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文化制度;在民生保障制度上,形成了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在社会制度上,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生态文明上,形成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军事制度上,形成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上,形成了“一国两制”制度;等等。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组成,三者之间主辅有序、主次互补、相辅相成。其中,根本制度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根本方向,“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9]175;基本制度是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如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重要制度则从属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体现在国家治理各个领域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根本制度主要包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文化制度,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根本军事制度,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有: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制度则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文化发展制度、文化权益保障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一国两制”制度、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等。这些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
2.2 “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制”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奇迹的背后蕴含着“中国之制”的密码,《决定》把这些制度密码概括为13个显著优势,其中,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最为突出。
一是领导优势,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6]20这一论断的提出,是由党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运动不同于其他任何运动,它“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42。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1。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11]47。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论、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坚定的初心和使命,而且也具有为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的政治本领。因此,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2]22。一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切成就都将无从谈起。
二是力量优势,即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人民并不是无所作为、逆来顺受,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不断创造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295。由此,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13]4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无论是根本制度,还是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都要求必须坚持和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主要体现在于,在根本政治制度层面,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在基本政治制度层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有利于提升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凝聚广泛共识;在重要政治制度层面,有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凝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力量,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12。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力量由此得到充分彰显。
三是速度优势,即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优势和力量优势决定了速度优势,这里的“速度”,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方面。众所周知,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非常低的,这诚如毛泽东在1954年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4]329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生产力也由此实现了充分的解放和发展,在汽车、航天、军工、钢铁、船舶、高铁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1952年我国仅有679亿元,而到了2018年则达到900 309亿元,仅仅60多年的时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175倍,目前稳居全球第2位。从1979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9.4%,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为2.9%左右[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连续41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工业化,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优势。
四是目标优势,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同时也是一个鲜明的使命型政党,它有着十分清晰和远大的目标和使命。而远大的目标和使命往往会铸就政党高尚的政治品格,使其不断地朝着远大目标进发。从196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这一目标不懈奋斗。在这一过程中,其具体目标和制度安排也有过调整,但这些调整主要是对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进行调适,如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目标本身则往往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实现深化和提升,这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远大目标上的历史接力。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张蓝图可以绘到底,从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个主要显著优势,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实际上这四个优势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其分别对应的是领导主体、依靠力量、发展过程和远大理想,它们共同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完整程式。可以说,正是得益于“中国之制”的这些显著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7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2,作为这两大“奇迹”背后的制度和国家治理密码,“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既有独特性又有引领性,为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有力支撑。“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16]10这表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必将为“中国之治”提供更多的制度支撑。
3 时代要求:以“中国之治”应对世界之变
中国实践形成了“中国之制”,“中国之制”支撑了“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1]4这说明,“中国之治”也需要有效应对新时代国内外“大变局”背景下的各种风险与挑战。
3.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对“中国之治”的时代要求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7]298。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也并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6]15,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接力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正发生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一是处在“现代化冲关期”。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奋斗。无论是“洋务梦”“维新梦”“民主宪政梦”,还是“新文化梦”,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从2020年到2050年,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即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冲关期”。
二是处于快速发展与矛盾积累交织期。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站到了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最高点。不仅如此,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四个伟大”的全力实践以及新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的目标规划进一步明晰。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人民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渴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历经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深切的渴望。”[18]32由此,既有良好的国内形势,又有民族发展观念上的强烈自觉,已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但是,我们也处于矛盾的积累期。当前我们既有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问题,也有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升级问题,还有工业化后期的结构转型问题,工业化进程中历时性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矛盾和问题共时性地出现,这导致了目前我们处于矛盾的积累期。
三是处于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并行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保持了40多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虽然目前比较困难,但我们还需要继续保持下去。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家比较落后,我们更强调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了,新时代我们要把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面对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又必须使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中高速增长。因此,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并存并行,这对“中国之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要进一步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努力,必须既要紧紧抓住难得的时代机遇,同时又要谨慎处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挑战和矛盾,从而实现“中国之治”。这是因为,没有“中国之治”,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诚如邓小平所说:“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5]284为此,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强化系统思维,正确处理好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的内在关系问题,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3.2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之治”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并不仅仅意味着时代的更迭变化,更重要的是强调国际社会的结构性“逆转式”变化。这种结构性的“逆转式”变化,对“中国之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这里的“东”主要指新兴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的对比。其中,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体量最大、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无疑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和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其所肩负的国际责任也越来越大,国际社会期待聆听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因为“中国的故事不仅能激励中国人,更能激励世界人民”[19]120。由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发展走向正在影响和引领着世界的发展走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制度成果,努力凝练和创新制度的话语表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制度性公共产品,真正承担起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二是“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发。所谓“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实际上是指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事件,它们会极大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西方频发的这些不确定事件,使当今世界陷入极大的不稳定、不确定中。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习近平强调,在中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进程中,都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仅着力提高防范、应对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本领和能力,而且“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0]。同时,还要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果,使其显著优势持续不断地发挥,从而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形象。
三是民粹主义回潮。以民粹主义思潮为代表的美欧等国家明显转向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特朗普提出“购美国货、雇美国人”,在美墨边境修“隔离墙”;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等一大批右翼政党在欧洲强势崛起,甚至有些民粹主义思潮已经上升为个别国家的政策,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方面。这启示我们,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不仅要注重物质领域的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和批判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如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防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产生较大冲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在《决定》中,党中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23,这无疑有助于为实现“中国之治”提供根本的思想文化保障。
四是“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欧等主要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减弱,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并逐渐升级为一些国家的政策。特别是美国,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认为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吃了亏”,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则占了全球化的便宜,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倾向,使世界陷入“逆全球化”威胁中,从而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可预料的艰难。
习近平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中国不仅不会因为“逆全球化”思潮而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有所动摇,相反还会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这既“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21]11的重要举措。对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杜宁凯认为:“中国的开放正是在充分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中国愿意承担起几乎是领导全球的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19]149-150因此,在当前的大变局中,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家关系都在经历空前的大变动和大调整,面对这样的时代机遇与时代挑战,中国应有所作为,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世界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面前,中国共产党应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而以“中国之治”引领和推动“全球之治”。
4 结语
中国实践形成了“中国之制”,“中国之制”支撑了“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应对世界之变,最终将推动“全球治理”,由此形成了一个依次递进的逻辑链。而作为这个逻辑链条的中间环节,“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无疑起到了连接内与外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实际上,这两者不仅是一种命题,更是一种方法,是对中国向何处去和世界向何处去的有效回应。从这个意义而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旨在提升和强化“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效能的《决定》,显然是一个具有纲领性质的文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