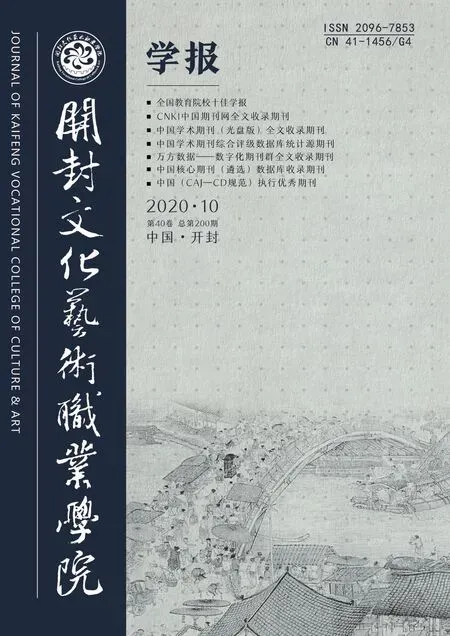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上帝救助孩子》中的创伤隐喻
蒙倩静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文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研究背景
《上帝救助孩子》是托尼·莫里森的第11 部小说,发表于2015 年,具有鲜明的现代元素。小说主要讲述的是21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孩子们遭受各种伤害的故事。小说描绘的种族主义、虐童、儿童暴力等主题,在当今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引发了人类对儿童生存状态的更为深刻的思考。正如1993 年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所述,托尼·莫里森的作品 “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 而著称,其文本往往具有多层含义。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是托尼·莫里森揭示小说主题、表达人物情感的载体,本文将系统分析小说中的多种隐喻构建,从隐喻的角度解读和阐释《上帝救助孩子》中人物的经历和情感。
二、创伤书写和隐喻艺术手法
“创伤转向” 热潮开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并在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引发广泛关注[1]。凯西·克鲁斯(Cathy Caruth)、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创伤理论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2]。其中,由朱迪思·赫尔曼所著的《创伤与复原》最具影响力。朱迪思·赫尔曼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创伤治疗的主要过程[3]156。国内关于该话题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守仁、吴心云的《走出童年创伤的阴影,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安宁:读莫里森新作〈上帝救助孩子〉》,他们强调“言说”对创伤恢复的重要性[4]。创伤会给个体带来身体和情感上的巨大伤害,但创伤同样是对个体重塑的过程,是对新个体的重新建构。托尼·莫里森编织了一个童年创伤故事网。如何修复童年创伤,继续前进和爱,是托尼·莫里森在小说里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而,《上帝救助孩子》是关于童年虐待和创伤的故事,也是关于疗治和成长的过程。
隐喻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而且是文本建构者思考事物、认识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作家往往借隐喻的方式抒发对客观事物的内在感知,从而达到与世界对话的目的。“在‘创伤叙事中的诗意的、文学性的隐喻不仅可以表达难以形容的和难以表征的创伤,而且可以用来描述创伤记忆、创伤经历和治愈过程’。”[5]《上帝救助孩子》在揭示人物创伤的经历和情感及探索人物疗治的途径,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隐喻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
三、《上帝救助孩子》中的创伤隐喻
(一)人名隐喻与身份构建
一个人的名字是其身份的代名词。要探究自我的秘密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同一或分离关系,关键就是身份。小说主人公原名卢拉·安(Lula Ann),然而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厌恶自己的名字。从她一出生开始,浅肤色的母亲就很讨厌她,因为她的皮肤很黑,“像苏丹人一样黑”(注:笔者译)[6]3。母亲责备她 “并对待她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不仅如此,像对待敌人一样”(注:笔者译)[6]5,并且不允许她叫她“母亲”。相反,孩子被指示直呼其名字。所以,原名卢拉·安隐喻的是深受种族主义和色彩主义戕害的母亲对女儿童年留下的伤害,以及儿童在成人世界的挤压下失去了的自由生存空间。
后来,卢拉·安在上大学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布莱德(Bride)。“布莱德”(Bride英译有“新娘”之意)这一名字,隐喻的是纯洁、快乐和美丽。卢拉·安是曾经的那个黑人小女孩的身份标签,改名成布莱德,表明主人公要与过去割裂、开启新生活、重建自我的决心,并寻求身体的解放和精神上的些许慰藉。卢拉·安的改名揭示了黑人在种族主义的奴役下,在身份荒野中流浪和追寻的生存状态。
此外,小说中的其他人名也极具隐喻意蕴,如母亲的名字Sweetness(英译为 “甜蜜”)实则是一种反讽隐喻。她虽名为Sweetness,但她本人并不甜蜜。她拒绝根据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来命名,也拒绝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她的女儿没有得到真挚的母爱。
再者,布莱德在寻找男友布克途中偶遇了小女孩瑞恩(Rain),她的名字也具有隐喻意蕴。Rain 英译有 “雨” 之意,雨有润泽万物的作用。布莱德和瑞恩的相遇是一段具有转折性的插曲。分享各自痛苦的童年让她们在情感上联系在一起,瑞恩唤起了布莱德被压抑的种族排斥感,使她开始从受虐待儿童的身份转变为受虐待儿童的保护者和养育者,让这个曾经遭受严重虐待的孩子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托尼·莫里森为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赋予了迷人的象征性名字。
(二)身体隐喻与主体认知
在托尼·莫里森的多部作品中,身体一直是着重赋予特殊寓意的意象。身体书写是后殖民文学文本中常见的种族主义对个体创伤的见证,用身体来隐喻小说主题和人物主体认知是很多作品中一种普遍的书写现象。小说中描述,在几天的时间里,布莱德的男朋友布克(Booker)离她而去,她受到了因她做假证而入狱的前教师的严重攻击。然而,在布莱德决定去寻找布克并面对他时,她发现自己正在经历一场令人费解的身体变化,她逐渐变回 “一个害怕的小黑鬼女孩”(注:笔者译)[6]97。托尼·莫里森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布莱德失去她的腋毛、她的乳房和她的耳洞,甚至体型也缩小到孩子的大小,她的身体似乎又回到了青春期。布莱德的身体退化,隐喻的是她终于敢面对自己、找回自己。小说结尾处,布莱德和布克重新和好后,她的女性性征回归,这预示着她的重生和她真正的成长。托尼·莫里森将魔幻与现实相融合,利用她一贯钟爱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布莱德的身体隐喻,说明了人若要真正成长,必须返璞归真,重回童真,如此才能拥有对自己的正确认知。
(三)颜色隐喻与文化霸权
小说里,布莱德一出生就是一个肤色极黑的女孩,她的母亲讨厌她,她的浅肤色父亲也因此怀疑布莱德是否亲生而抛弃家庭。黑色在布莱德的童年世界早早就被赋予了彻头彻尾的 “讨厌、反感、歧视” 的隐喻义,它象征着美国社会文化价值对黑人人性的压迫以及对黑人生命的压抑。然而,和黑色相比,托尼·莫里森花更多笔墨描写的是白色。白与黑的对立矛盾,是纯净与肮脏的共生体,是主人公身份异化的转变。长大后的布莱德开始只穿不同深浅的白色衣服,来强调她黝黑的皮肤,因为她的设计师杰瑞(Jeri)声称 “黑色是新的黑色”(注:笔者译)[6]33。彼时的美国,奴隶制已被废除,反种族主义也被正式写入美国法律,美国全国上下似乎都在流行 “黑即美” 的审美和价值取向。然而,作者的寓意并非到此而已。布莱德对黑色肤色的态度转变、对白色服饰的狂热追崇,恰恰反映了黑人对白人审美标准的盲目遵从。无论是“白至上” 还是 “黑即美” 的审美价值观,都反映了白人的主流价值观对黑人自身的身份认同影响极大,这是黑人内部殖民化的外在表现。托尼·莫里森通过使用 “黑—白”这一两极对立隐喻,揭示了在白人文化霸权下,黑人遭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黑人自身的身份意识变得模糊,审美意识发生异化、文化意识也逐渐丧失,象征着黑人内心的迷茫和困惑。
(四)乐器隐喻与 “言说” 疗治
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最有代表性的乐器是布克的小号。作者用小号这一乐器隐喻布克的人生状态。小号连接布克的过去和未来,暗示他的伤痛和成长。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中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过去创伤对现在的影响。随着小说叙事的慢慢推移,读者慢慢了解到布克是一个备受折磨的黑人小号演奏者,在虐待儿童问题上,曾受到过极其黑暗的创伤,即使那看似只是间接的创伤。当他和他哥哥都是孩子的时候,布克崇拜的哥哥被一个恋童癖者、一个连环杀手杀害,这是布克挥之不去的人生悲剧。布克前半生一直在与童年的创伤作斗争,小号是布克应对创伤的一种方式。
在小说的最后,在姑姑(Queen)的开导和鼓励下,布克和布莱德互相倾诉各自的童年创伤经历,消除彼此的误会,重归于好。布克通过 “言说” 的方式积极与人交流,彻底解开自己的心结,最终走出因哥哥受害带来的伤痛的阴影。此时的他内心回归平静,不再需要借助小号来抚慰自己,他把小号扔掉这一情节象征着布克真正从创伤中得到了治愈并获得了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