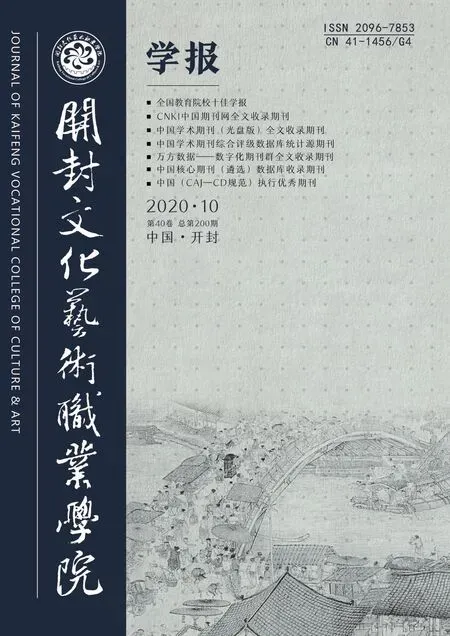论《我的妹妹,我的爱》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张 莹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一、文本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把事实与作者的想象杂糅在一起;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交织,作者不时 “闯入” 文本并与之对话,有意地向读者透露其创作意图。从这些角度出发,可以发现欧茨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文本。
(一)真实与虚构的融合
《我的妹妹,我的爱》是欧茨受一起在美国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的触动而创作的。1996 年12 月26日,样貌可爱、得过多项儿童选美冠军的6 岁女童蓝西被发现陈尸在科罗拉多州家中的地下室,身上有被性侵、勒颈和虐待的痕迹。警方调查认为,蓝西是在圣诞节当天被杀害的,但采集现场DNA 后,只发现其属于一名身份不详的男性,21 年之后的今天,真相亦未大白于世。小说基本上还原了这场凶案,将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融入故事,构筑情节,营造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但又远远超出历史,作者不仅更改了现实中的人名、地名,而且在故事接近尾声时进行了一个重要的改动,为历史上这桩悬案大胆想象出了一个令读者出乎意料的结局:女孩的妈妈因为愤怒误杀了她。这种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在重返现实的过程中,也给我们提供了可能存在的 “另一种事实”,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相。此外,与那些看似非虚构的新闻报道对案件喋喋不休的争论形成鲜明对比,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用艺术的手法对现实的解构无疑对纪念这位6 岁的选美小皇后蓝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叙述文本与评论文本的融合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实践策略是借用文本中的叙述者传递作者的思想,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把握小说的主题。在《我的妹妹,我的爱》中,史盖乐以 “自传” 的形式对故事情节展开了叙述,回忆自己的少年时光和妹妹被谋杀的惨案。而作家的创作意图则是由史盖乐以作者思想媒介的形式在注释中向读者说明,比如“提前交代故事的结局,然后再叙述事情发生的始末,破解容易解读的悬念,这是畅销小说的真正价值”。此外,还有两处注释值得注意:第一,“在蓝派克家里,你觉得自己永远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尤其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应该和你在一起”;第二,“好奇的读者可能会问,史盖乐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在过去约十五年的时间里碰巧是他母亲或曾经是他母亲的中年女人呢?这个女人究竟对史盖乐又怎样强大的支配力呢?”[1]362-366作者向读者展现了父亲比克斯家庭责任感的缺失和母亲贝西强大的控制欲,这是男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心声,也是小说的主旨之一。因此,通过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的融合,读者能进一步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二、媒介伦理的缺失
波德里亚将后现代社会称为 “仿真社会——一个由广告、电视新闻等大众媒介所制造的符号社会,这个符号社会看起来像现实社会一样,甚至比现实社会还要真实完美,但这只是一个无法区别真伪、现实与非现实的超现实世界”[2],后现代大众传媒用各种不道德的手段制造大众的消费欲望,媒体伦理的缺失也极大地推动了悲剧的产生。
(一)大众传媒的炒作
小说中,布莉斯在纽瓦克战争纪念中心的滑冰场上赢得比赛,成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无数忠实或疯狂的崇拜者。当然,除了个人的努力外,她的成名也离不开大众媒体的极力热捧。赢得比赛后,各类电视采访和广告代言不断涌来,同时,蓝派克一家也因为布莉斯头上的光环而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出尽了风头。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成名的同时也意味着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下,毫无隐私权可言。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边沁的圆形监狱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社会存在的真实机制的缩影,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这样的全景敞视中。”[3]盛名之下的蓝派克一家逃脱不了公众的全方位审视,而公众的猎奇心态也为后续的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的共谋奠定了基础。
(二)大众传媒的暴力
布莉斯去世后,蓝派克一家沉浸在布莉斯离世的悲伤中不能自拔,然而不良媒体的主观臆断和恶意扭曲让他们的痛苦与日俱增。在小说中,专门有一章罗列了各类小报的相关报道。“如果你能忍受这些废话连篇的报道,那很好,但我却不能。那些哗众取宠的小报经常刊登一些真假难辨的新闻和照片,让人读后心绪难平,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1]在史盖乐的眼中,蓝派克一家人被囚禁在由小报构筑的地狱里。这些小报媒体不择手段地满足观众对他人隐私生活的窥视欲,以死缠乱打的方式为观众挖新闻。媒体的夸张渲染也使史盖乐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可以说,正是由于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在以逐利为目的的消费主义社会熏染下逐渐消退,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舆论影响。
三、人的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认为,人类历史有两重性,它既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的提高的历史,又是人类日益异化的历史。异化指的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力量作为外部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人类。”[4]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的异化现象一般表现为三种方式,即兽化、物化和奴化。作者大体上是要创造一个思想匮乏、行为幼稚、可供人嘲弄的形象。
(一) 兽化的父亲
著名的教父奥古斯丁认为:“性欲是人类邪恶中最肮脏、最不洁净的,最能表明人对上帝意志的不遵从,它能彻底摧毁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是人所驾驭不了的最基本、最普遍的邪恶。”[5]78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具有思维和理性而动物仅有感知。理性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可靠,能更加有效地区分开人和动物,因此人的存在依据也在于理性。然而,在本能欲望的驱动下,比克斯一味寻求感官刺激,多次做出背弃婚姻道德和责任的行为,发展婚外情。比克斯的财富和权力,使他不论在哪里都能勾搭上年轻漂亮的女性,即使在等儿子史盖乐体操课下课的过程中,都能肆无忌惮地与一位女性发生性关系。人一旦被欲望所控制,个体就会失去道德理性甚至泯灭人性,人也会随之异化。
( 二)物化的母亲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切都变得可以被商品化,人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拓展人际关系网络,甚至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以价值来衡量。在小说中,母亲贝茜完全把自己的儿女当成了工具,没有一丝的母爱。当发现女儿布莉斯的滑冰天赋后,她就把全部的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然而,她也并没有放弃对她儿子史盖乐的掌控,精心规划着史盖乐与丽山上层阶级孩子的交往,她把儿子当成了实现她金字塔社交过程中的一枚棋子。贝茜的功利化教养使自己异化成了一心想着进入上流社会的机器。
(三)奴化的女儿
布莉斯展露滑冰天赋之前叫埃德娜·路易斯,那时的她是长相一般的小女孩,是个让母亲不耐烦的任性的怪孩子,而史盖乐才是妈妈的小男子汉。贝茜把所有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史盖乐的身上,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母亲的冷漠和忽视自小就在布莉斯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所以当母亲在滑冰上对她表现出极大兴趣时,她知道这是获得母亲关注的唯一方式,为了不让母亲失望,即使在训练时扭伤脚踝,她也会坚强地说:“妈妈我没受伤,妈妈我想滑冰,妈妈我真想滑冰!” 她更加刻苦训练,以获得爱和关注。渐渐地,布莉斯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滑冰工具人,成为任由母亲摆布的玩偶。
结语
《我的妹妹,我的爱》中出现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维度,小说解构了 “文本是现实的镜子” 这一传统观点,把真实的案件与作者的想象融合在一起,为事实的真相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此外,小说中体现的媒介伦理的缺失以及人的异化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泛娱乐主义、社会责任感的消解以及对工具理性的重视等后现代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