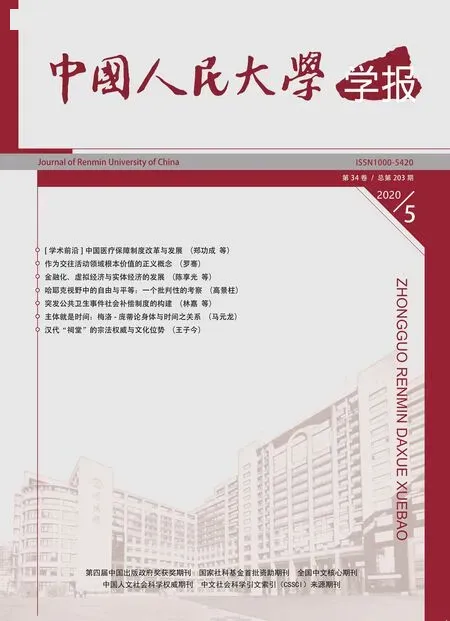“批判”与“重建”
——秦汉文艺思想的内涵与本质
孙少华
秦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艺高峰,它为后世文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究竟如何去认识与书写秦汉四百余年的文艺思想史?如何认识秦汉文人在该时期文艺思想发展中的作用?这是本文着力思考的问题。
秦汉文艺思想展开的历史背景,是秦统一六国,这个时期文艺思想的总特征,其实可以用“批判”与“重建”来概括。同时,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文艺思想的总特征。我们之所以将二者并提,是因为任何一次“重建”,无不伴随着深刻的“批判”。
“文艺思想”,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但有一点我们不必怀疑,即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文艺思想的变化,无不是随着当时政治、学术的变化而变化的。除了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汉魏之际的王朝更迭,四百余年的秦汉历史中,和平时代占据主流。“时政平则文德用”(1)范晔:《后汉书》卷四七《班梁列传》,6册,15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秦汉时期的“文德”,体现在秦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秦汉文艺思想的把握,不可能单纯从后世“纯文艺”作品中去探求。
秦汉时期的王朝更迭、政治改制、经学形式与内容的变化、史书与子书的撰述,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艺思想,从而为我们把握秦汉时期文艺思想的变化提供了可能。就此而言,本文所说的“文艺”,应该是包含经、史、子、集在内的“大文艺”,尤其是秦汉文人更加强调“道”对“文”的作用,这是从“大文艺”观念认识秦汉文艺思想的基础。
一、秦汉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
秦汉学术批判与重建的历史过程,其实就是话语权在国家、地方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在这种博弈与平衡的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对“道”的存在之强调。具体到秦汉人对“道”的内涵的认识而言,就是古代文人对“天道” “人事” “文心”的解释与运用,及其对当时社会秩序、政治统治、皇权巩固所具有的意义。这是秦汉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努力揭示秦汉文艺思想中“天道”“人事”“文心”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认识秦汉文艺思想传统和思想体系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书写秦汉文艺思想史的关键。
“道”与“文”之关系,在刘勰《文心雕龙》中有系统阐述。“道”有“文”,其与“天地并生”,故刘勰赞叹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除了“道之文”,还有“人文”,刘勰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这就将“人文”视作“道文”的核心。刘勰又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的说法,提炼出“道——圣——文”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秦汉历史语境里,刘勰所言其实就是“天道”“人事”与“文心”的关系;在秦汉文艺思想语境里,则是“文心”对“天道”与“人事”的认识、协调、平衡与应用。
秦统一六国前,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吕氏春秋》,高诱认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这是认为该书与孟轲、荀卿、刘安、扬雄等人具有共同的著述思想。然《吕氏春秋》首列“四季”,以“天”为首,将诸家思想置于“天道”之下,显然具有为文“始于天、终于人”之观念。该书称“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3)吕不韦著,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提出“天道”“地理”“人纪”之观念,其背后或隐含编者对“人事”的干预。这是一个自战国孟子、荀卿至西汉刘安、西汉末年扬雄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后来《淮南子》首列《原道》,司马迁《史记》首列“儒者或不传”之《五帝本纪》,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春秋》,刘向、刘歆说灾异,都是这种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文人以“文心”对“天道”“人事”的理解与运用,本质上皆有对王朝或皇权之政治用心,且具有明确的政治教化功能。陆贾《新语·术事》认为著述的目的,即在于“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4)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具有明确的“学为汉家”之目的。其后,两汉经学上有公孙弘、董仲舒、郑玄、马融之流,史学上有司马迁、班固,子学上有刘向、扬雄、刘歆、桓谭、王充、仲长统、蔡邕、应劭,辞赋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其著述思想、文本内容或书写目的虽有差异,但其著述维护汉家王朝的政治目的、其文本蕴含的政治教化功能则是一致的。例如,刘向编纂《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所取内容为“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或“传记行事”,具有明确的“戒天子”“陈法戒”等社会教化目的。(5)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7册,1957-19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汉武帝时期汉赋的出现,除了歌功颂德,另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配合封禅的需要,其背后则是强烈的为皇权服务之政治用心。
汉成、哀之后,文艺主流思想受到了来自经学方面的双重冲击,一个是古文经学的发现,一个是谶纬、符命的出现。由此,汉赋创作陷入低谷,古文经学、谶纬、符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皇权与外戚之间、外戚与外戚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这种著述思想的背后,无论是对皇权的限制或维护,还是对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的破坏或稳定,都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王莽以符命代汉,光武帝以符命续汉,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文艺思想的进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即使那些看似非常“个性化”“个人化”的著述行为,其实也与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分不开。如李斯《谏逐客书》、贾谊《吊屈原赋》,已经具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两汉体物小赋、抒情小赋,或者说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具有较高个人色彩的五言诗,以韦氏家族为代表撰写的具有家族训诫色彩的四言诗(6)许结:《西汉韦氏家学诗义考》,载《文学遗产》,2012(4)。,都具有典型的个人情感色彩。但此类著述,与秦汉民间经学的传授或东汉王充等人的“疾虚妄”思想一样,皆未脱离当时社会、学术大环境的需要。汉代民间学术最终与国家学术的合流,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秦汉不同文艺形式之间,皆具有思想上的共性。这是秦汉文艺“思想传统”“思想体系”形成与完善的基础。例如,汉画像砖上的长生观念,与辞赋、诗歌作品中的神仙思想是一致的;东汉末年蔡邕等人的音乐思想,与王褒《洞箫赋》、傅毅《舞赋》、马融《长笛赋》、侯瑾《筝赋》体现的礼乐思想是一致的;王充“疾虚妄”、王符论“潜夫”,其实与董仲舒“士不遇”说、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之间,皆有思想上的逻辑联系。司马迁《史记》将贾谊与屈原同传,在将汉赋与楚辞勾连起来的同时,也为汉人理解、建构汉赋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后来《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辞赋有“古诗之义”(7)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6册,17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以及班固《两都赋序》提出的“赋者古诗之流”(8)萧统:《文选》,上册, 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都是沿着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诠释思路进行的。另外,桓谭提出的“短书”“小说”之“妄作”“虚诞”的特点,虽然与儒家多有不同,但却为王充“疾虚妄”的提出开辟了道路。(9)孙少华:《诸子“短书”与汉代“小说”观念的形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3)。也就是说,秦汉文艺思想看似不同的背后,却有着共同的撰述思想,这就为我们从各个方面研究秦汉文艺思想提供了可能。
二、秦汉文艺思想批判与重建的理论前提
“道”是先秦诸子讨论的哲学范畴。《吕氏春秋》所言“天道”“地理”“人纪”,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天道”“人事”“文心”,都可以算作“道”之内涵。其中,“人事”与“文心”亦可纳入“人纪”之范畴。秦汉文人用“天道”解释“人事”,用“文心”解释“天道”与“人事”之关系,并非抽象的迷信或单纯的技术应用,而是对基于“伦理学而不是物理学”(10)马伯乐:《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1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的认识与运用。汉代星象、谶纬、阴阳五行、符命与文艺思想的结合,也是对相关科学知识运用的反映。秦汉文艺思想的批判与重建,就离不开对“天道”的认识与运用。
秦汉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证明“道”在当时的文艺思想中具有支配作用。“道”在秦汉文本书写中的隐与显,则使得文本与思想之间产生了矛盾,从而决定着秦汉文艺思想批判与重建的走向。秦汉文人以“道”构建秦汉文艺的思想体系与文本结构,以“道”解释“天道”“人事”“文心”之关系,以“道”平衡政治、社会与人伦之关系,从而在社会与文艺思想领域催生了“新”“旧”之别。这既是推动秦汉文艺思想革新创造的内因,也是秦汉文艺思想批判与重建的理论前提。
具体到秦汉文艺思想而言,《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天道”统领全书,董仲舒以阴阳说《春秋》,司马迁仿《春秋》作《史记》,汉大赋中神仙、星象之描写,扬雄拟圣而新著述,西汉末谶纬、符命之兴起,王充之“疾虚妄”,乃至东汉马融、蔡邕对音乐之重视,鸿都门学对艺术之推崇,皆与“道”有或密或疏之关系,其背后则隐含着深刻的“批判”与“重建”意识。“新”与“旧”的思想交锋,则成为这种意识的典型表现形式。
《吕氏春秋》首列“天道”,将“人事”“文心”皆置于其下,这必然带来政治、文化等思想领域的矛盾。另外,秦穆公以来施行的文化与人才政策,客观上在秦政治与文化的背景中形成了一种“客卿”文化(11)孙少华:《韩非、李斯之死与周秦之际文学思想的变化》,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因此,嬴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多元文化。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出的“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12)的批评,以及“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13)司马迁:《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8册,3086、30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的建议,实际上是在延续秦穆公以来的客卿政策的前提下,提倡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与人才政策。但这种多元、包容,必然带来秦旧文化与外来新文化的对抗与冲突,文艺思想中无疑具有较强的“批判”意味。
入汉之后,陆贾《新语》直接提出“新”之命题,这是批判基础上的“塑汉”尝试。此后,整个西汉时代,贾谊、晁错、刘向、桓谭等人无论是从行动上还是从写作思想上,都继承了陆贾“新”之思想(14)孙少华:《西汉诸子的“尚新”传统与“新学”渊源》,载《文学评论》,2012(1)。,证明这种思想“批判”与“重建”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
贾谊则从国家制度层面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这是“去秦化”的尝试,故《史记》记载“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15)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8册,302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此处贾谊还是具有较为“革新”的思想的。尤其是这个“悉更秦之法”,与当时遵循“汉承秦制”的旧军功掌权者产生了直接矛盾,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因为,贾谊提出的“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这个时间,恰好也就是《史记》所言“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16)之时。这些位在将相公卿之“军吏”,多数被司马迁评价为“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17),可见当时这种新旧思想的冲突,还是非常尖锐的。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陆贾、贾谊更多代表的是楚文化。所以说,大汉初建,甚至到汉武帝前期,基本上延续着秦以来多元文化的共生局面。说到底,其实也就是此时还没有属于“大汉王朝”特色的文化。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时政治实际情况,决定了文化、学术或文艺不可能是汉王朝亟须建设的目标。《史记·张丞相列传》称:“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18)司马迁:《史记》卷二四《张丞相列传》, 8册, 3249、3253、32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其实,汉武帝前期以上的汉家王朝的丞相,多数带有鲜明的“旧军功臣”性质。我们曾统计分析西汉九十余年内自第一任丞相萧何至第二十二任丞相石庆的资料,发现《史记》《汉书》忽略了庄青翟之前的田蚡、公孙弘、李蔡,直接将武帝时期的庄青翟、赵周与此前的丞相并列,主要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高祖功臣之后的出身。对于这些旧军功者后代,司马迁批评他们“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说明这些具有旧军功之“军吏”,包括汉初崇尚黄老无为之贵族,不可能有更加积极主动的革新之举,更无心留意于文事。汉高祖不重儒、周勃“不好文学”,只不过是这种风气的具体代表而已。
第二,汉初文人不同的战国文化背景,导致了当时不可能很快建立“汉朝”特色的文化、学术。汉初至武帝中期,文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导致战国时期六国文化在汉代的交错、碰撞。例如,律历方面,高祖初定天下,以汉为火德(19)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卷一《高祖皇帝纪》,上册, 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张苍以汉德同秦,当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儒学方面,陆贾、郦食其皆服以旧制儒服,叔孙通变儒服为“短衣楚制”,是正式从思想上认同“楚”为主流文化的转变。而公孙弘与董仲舒有醇儒之争,他们一齐人、一赵人,或者代表着战国以来不同地域的学术思想。另外,曹参、陈平之黄老文化,属于齐文化;高祖与六代丞相皆沛人,背后也有楚文化的深刻影响;淮南、梁国属于吴楚文化圈。
如此看来,汉武帝之前的主流文化中,起码有秦、齐、赵、楚、鲁、吴等不同地域文化思想的影响。此种情况下,要形成统一的文化政策或文艺思想,是比较困难的。但总体上看,在学术或文艺方面,无论背后是哪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汉王朝的统一与政治统治。反映在经学、文学方面,无论各家争论如何,其本质都是为了维护汉家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先秦诸子思想中的“百家争鸣”,仍然是汉初思想的主流;而这也是先秦、汉初文艺思想的主流。
这种近似于“保守”的政治体制与文艺思想,反映在文化层面,则是汉家王朝对战国、嬴秦文艺“旧秩序”的延续,这恰是秦汉文艺思想的批判前提。秦文化实际上并未彻底完成批判与重建的任务;入汉之后,以楚文化为主的汉初文化,尚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汉文化”特征。要建立一种完全属于“大汉”特色的文化,就需要在这种批判“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大汉”文化。与之相关的属于汉王朝自身特色的“汉文艺思想”的建立,也迫切需要这种批判工作的展开。
三、西汉文艺批判的展开与重建工作的尝试
汉武帝时期,学术上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上提倡大赋制作,无论其效果如何,客观上都是为塑造“大汉特色”服务。刘勰称汉赋具有“兴楚而盛汉”(2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1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的作用,可谓知音。
纵观整个西汉,对“汉化”工作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或者说具有“文艺批判”精神并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者,当属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父子、扬雄等人。他们分别代表了西汉文艺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总结分析。
第一,汉初文艺思想的“汉化”尝试。
汉承秦制,入汉后很多方面沿袭秦制,但在文艺思想方面,汉初文人也进行了积极的“汉化”工作,体现了文人个体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陆贾对汉初文艺的贡献,就是积极推动儒学发展,故司马迁称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21)司马迁:《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8册,32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角度看,陆贾实际上是将儒学、经学国家化的重要推手之一,其背后则是对旧思想、旧势力的坚决批判。《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陆贾赋三篇”,其下列枚皋等二十人之赋,皆汉武帝至汉成帝之间的赋家,可知《艺文志》以陆贾赋为醇正之汉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亦称“陆贾扣其端”,此“扣其端”,应该是就真正意义上的汉赋而言。班固称陆贾“身名俱荣,其最优乎”,可知陆贾文学、政治上皆有所成,这是汉人在建构陆贾在汉赋体系中的地位。
司马迁《史记》将贾谊与屈原同传,又列其于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序列而同好辞赋。(22)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8册,30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汉书·艺文志》将“贾谊赋七篇”列入“屈原赋之属”,亦认同贾谊与屈原赋之关系,并且认同贾谊赋与楚辞具有思想渊源,这实际上是“楚辞汉化”的理论归纳。刘勰将屈原、荀卿、宋玉、陆贾、贾谊依次罗列(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1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即继承了这种思想认识。
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学《尚书》于济南伏生。贾谊之后,以对策著名者以晁错为高。而班固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24)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8册,2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可知晁错此人在儒学、对策(文章)方面皆有成就。
综上,从文艺思想的角度看,汉初陆贾、贾谊、晁错三人,是西汉初期子书、辞赋、奏议文的重要代表,是积极推进文艺思想“汉化”的重要人物。这应该是汉初文人集体行为的缩影。他们在“旧制”与“新命”的特殊时代,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他们在将秦文化“汉化”的过程中,在将“旧”转变为“新”的过程中,承担起了时代文人的责任。
第二,汉武帝时期文艺思想的“楚变汉”。
汉武帝之前的大汉王朝,具有浓郁的“楚文化”遗存色彩,如汉高祖的《大风歌》,就被认为是楚歌形式;汉高祖等人不喜儒服、儒生,叔孙通变儒服为楚衣,也体现了“汉”背后的“楚”文化背景。
汉武帝时期,距离具有浓厚楚文化记忆的汉高祖一辈,已经过去了五代。对汉高祖、楚旧功臣之后代而言,对“大汉”感情已经超越对“楚”的记忆。“楚变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集体心理。整合全国人才,不仅仅使用楚旧功臣子弟,从而为变“楚”为“汉”创造条件,成为汉武帝考虑的首要事情。此时,旧军功者及其后代逐渐凋零,他们的守旧思想,也已经无法适应时代与汉王朝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此,汉武帝擢公孙弘于布衣,用梁孝王旧臣韩安国、司马相如等人,体现了用人政策的多元化趋势。
《史记》所记汉武帝时期人物,董仲舒在《儒林列传》,公孙弘与主父偃合传,却为韩安国、司马相如单独立传。韩安国、司马相如皆梁旧臣,包括后来的枚乘等人,汉武帝所用多出自梁,而韩安国曾位至御史大夫。《史记》“太史公曰”称:“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史记索隐》“述赞”则称:“安国忠厚,初为梁将。因事坐法,免徒起相。”(25)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列传》,9册,34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司马迁之所以如此重视韩安国、司马相如这两个人物,是因为他们对汉武帝时期的文化、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被《史记》认为是汉兴以来最明《春秋》者,故《儒林列传》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26);然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27)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10册,3799、37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以阴阳五行与灾异之变说《春秋》,具有很高的“革新”意识。就此而言,“批判”精神与“重建”意识,在董仲舒身上可谓兼而有之。这显然是公孙弘之类的旧儒所不能理解、更无法做到的事情。“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是汉家王朝认可了董仲舒的学术“革新”对维护其统治的积极意义。
公孙弘、主父偃皆齐人,齐本为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汉武帝用此二人,或者有这方面的考虑。然汉武帝同时使用了双方之间互有矛盾的公孙弘、董仲舒、主父偃,既体现了当时尖锐的社会阶层矛盾,也体现了复杂的经学思想矛盾。
窦婴为相时,“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28)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9册,34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窦婴、田蚡“隆推儒术”,无疑具有鲜明的“变汉”意识与“批判”精神。在此情况下,窦太后废窦婴、任功臣之后且保守的许昌为相,无疑是对这种“变汉”行为的遏制。窦太后死后,田蚡任相,对推动儒术具有重要作用。然田蚡之后,又是功臣之后的薛泽;薛泽后是纯儒家色彩的公孙弘;其后之李蔡为文帝、景帝旧臣,庄青翟、赵周为功臣之后,皆具明显的保守色彩。这种丞相任、废之争,体现了儒学发展的起伏与曲折,更体现了“变汉”过程中“变”与“守”、“新”与“旧”的思想冲突。
在儒学的推进或革新已经受到很大阻力的情况下,汉武帝采用文、武两种手段,打开了“变汉”的局面:文学上,信用司马相如等人,以“赋”作为“大汉”之“德”;军事上,信用卫青、霍去病等青年将领,征伐匈奴,以军事作为“大汉”之“功”。这两个方面,皆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大汉”特色,同时带有鲜明的“汉武时代特色”。这种成功,无疑应归功于汉武帝及其周围一批文武人员的彻底批判精神。
客观上说,汉武帝时期,最成功的“变汉”标志就是汉赋。司马相如本在京城学赋,因汉景帝不好辞赋,故游梁,从枚乘等人学赋;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归蜀,后为汉武帝所用,又为武帝作《子虚上林赋》。在此,司马相如之赋,已经是融合了京城宫廷赋、吴梁赋(枚乘等人先在吴,后入梁)、蜀赋为一体(29)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载《冈村繁全集》,1卷,1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最后可能又在楚赋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赋体形式——“大汉之赋”。
第三,汉成帝时期文艺思想的“汉代集成”。
至西汉成帝时期,大汉王朝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文艺思想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形式与内容。从总体上整理以往的文艺形式,反思以往的文艺理论,进而为大汉王朝建立一种“集成性”成果的工作已迫在眉睫。在这个过程中,刘向、刘歆父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成帝时,刘向奉命召集文人整理古书,具有重要的统筹全局的作用。其中,刘向所做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30),实际上是起到了“总编辑”的作用。刘歆先从其父刘向整理古书,并在哀帝时统领全局,最后完成全部工作。刘歆所做的“总群书而奏其《七略》”(31)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6册,17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32)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7册,19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实际上是起到了统编定稿的作用。
刘向、刘歆的这个工作,后人总以为具有将先秦文献“汉化”的倾向。但从学术史意义上看,他们的工作,无疑又具有将汉成帝以前的文献“汉代集成化”的重要特点。这是从官方层面展开的文化整理,对后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奠基与启蒙意义。
从士人或民间层面看,两汉之际扬雄校书天禄阁、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以及他对方言的搜集、对汉赋理论(如提出“劝百讽一”等)的总结,都有将个人学术进行“集成化”的特点。
扬雄与刘歆走了一条不同的学术道路,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文艺思想。刘歆遵从孔子“述而不作”思想,以整理古书为主;扬雄则认同“前圣后圣”观点,认为汉代也应该有属于“大汉”的圣人,故以新著述为主。刘歆、扬雄这种“旧述”与“新作”之别,代表着当时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在从不同角度将个人的学术进行“集成性”反思与总结。而桓谭对扬雄“西道孔子”的说法,也体现了部分文人对扬雄“圣人心态”的认同。客观上说,儒家士人对“圣人”的认识,实际上也是汉代儒学思想集成性的重要体现。刘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之说,就是对此类思想的总结性认识。
西汉文艺思想的“集成”特点,在汉赋中有集中体现。汉昭、宣、元、成四世,汉赋成为体现“汉德”的重要工具,至汉成帝时,汉赋创作达到高峰,出现“千赋”之说,如西汉扬雄有“能读千赋则善赋”(33)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东汉班固《两都赋序》有“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34)萧统:《文选》,上册,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有“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3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1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汉书·艺文志》将“歌诗”附录在“赋”后,除了“杂录”之安排,或者“集成性”思想也是造成这种分类法的原因之一。
另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汉末兴起的谶纬、符命之学,无疑是一种力量巨大的“思想批判”工具,同时也是经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与灾异、天文、阴阳五行等思想高度融合之后的“集成性”结果,具有很强的“汉化”特征。同时,谶纬、符命之学,在政治上成为一种争权夺利的工具;在与经学的关系上,则对经学具有一定反动作用;在人类思维的开拓上,则启发人们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客观上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思想支持。就此而言,谶纬、符命对汉人想象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开拓意义,不容忽视。
这种文献、经学、谶纬层面的“集成性”,对人们的思维具有重要的影响,反映在文艺思想层面,则是启发了文人从一定的高度思考问题。例如,汉赋理论至此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扬雄的赋论,前承刘向“不歌而颂谓之赋”、后启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体现了西汉末年汉赋的理论化趋势,同时也体现了汉赋作品的大总结。
四、“汉学”的建立与东汉文艺思想的转向
在天统、学术与文艺思想上,东汉对西汉有“以子承母”(36)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的自觉认识。整个东汉的学术任务,就是努力建立真正属于“大汉”的学术体系,也就是要建立后人所说的“汉学”体系,这是实实在在的“汉化”进程。
其实,就礼乐制度而言,东汉人认为西汉并未彻底建立完整的“大汉之制”,所以东汉文人的责任或者说目标,就是建立真正属于“大汉”的学术体系。这里有两个证据:
第一,《汉书·礼乐志》认为:“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37)班固:《汉书》卷二二《礼乐志》,4册,10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此出班固之语。其中所提及的人物至西汉末刘向,代表了班固时代东汉文人的共识。《后汉书·曹褒传》进一步认同了班固的说法。(38)
第二,根据《后汉书·曹褒传》“论曰”之记载,自西汉叔孙通以来直至汉章帝时期的曹褒,虽然其间经过了贾谊、董仲舒、刘向等人的努力,但仍然未建立完整的“大汉”礼仪制度。所以,曹褒父曹充曾上书光武称:“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39)范晔:《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5册,1205、1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这个“大汉当自制礼”,说得非常透辟,即西汉并未建立“大汉”自己的礼仪制度,东汉需要为此进一步予以建设。这虽然是针对礼乐而言,却侧面反映了东汉文人对西汉的批判、超越意图与创新意识。
但是,东汉所谓的“大汉自制”之学,力图恢复的其实是西汉末年汉成帝以来直至新莽时期的礼乐思想。这是因为,西汉末年与新莽时期的学术变革,给东汉带来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整个东汉的学术与文学思想,主要源自西汉末年或新莽时期。
西汉末年,王莽逐渐掌握政治局势之时,学术发展已经有古文经学化倾向,带有明显的新莽学术特征。政治上,自汉哀帝立,王莽已经对政治具有很大控制力;平帝立,“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则各种制度已经按照王莽等人的理想有所设计,因此,西汉末年之学,其实就是新莽之学。就此而言,东汉在天统上名义上是“续汉命”,而在学术上则具有明显的“续新莽”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重建“大汉”文化的努力,实际上延续的是王莽以来的学术传统。
东汉几个儒家大族(如杨氏、桓氏、袁氏等)多学西汉末或新莽之学,如学刘歆《左传》者有桓谭、郑兴、李守(李通父)、贾徽(贾逵父);其他家学,亦源自西汉末年之学,如伏湛为伏生后;贾复学《尚书》于王莽末之舞阴李生;范升为王莽时学者;陈钦学贾护,王莽学陈钦,而陈元学其父陈钦。
桓荣学西汉末之朱普,与其子孙桓郁、桓焉、桓典、桓彬等世传家学,直至汉末,出桓门之著名弟子有杨震、黄琼、杨赐、丁鸿。
杨震学桓郁,与其子孙后代杨秉、杨赐、杨彪四世传其家学。《后汉书》称“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40)范晔:《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7册,17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则杨氏、袁氏成为东汉末年两大最为重要的经学与政治家族。加上桓氏家族,可以说,东汉中期以后的经学或政治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这三大家族手里。
这就是说,后汉非常著名的儒学宗师,其经学思想渊源皆可追溯至西汉末或新莽时期,甚至整个东汉,历代学者努力恢复的也是新莽以来的学术体系。例如,西汉末年刘歆、王莽、桓谭等人倡导的古文经学,一直是东汉学者致力建设的目标。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自范升、陈元直至马融、郑玄,接近二百年的时间内东汉学者一直倡导并努力建设古文学,其中所言“古学遂明”之言(41)范晔:《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5册,1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说明了东汉学者理想的“古学”的完全建立。这是后人所言“汉学”的思想基础。
在这个长期的经学变革过程中,批判与重建工作是不断在反复、曲折中前行的。而“古学”经过近二百年才最终重建的事实,也说明了经学领域的批判与重建工作,是何其之难。其他思想领域的工作,同样如此。以礼制为例,按照《后汉书·曹褒传》的说法,虽然经过了西汉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刘向等历代人的努力,但并未建立属于大汉自己的礼制;东汉曹褒,受诏制礼,但“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擅制《汉礼》”,即说曹褒等人欲图建立“新秩序”,属于“重建”层面的工作;“破乱圣术”,即说明曹褒等欲图破坏“旧传统”,属于“批判”层面的工作。而“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42)范晔:《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5册,1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的结果,证明了曹褒等人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工作遭到了失败。
东汉学西汉,是一个不断革新、不断扬弃西汉传统的过程。这种“变”,是多层次、多领域的;而这种“变”带来的思想影响,则是深刻的。例如,经学上的革新,就有一个长期的、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讲经方面,徐防在推进章句之学方面有所贡献:“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又上疏称:“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李贤注引《东观记》徐防疏称:“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于此弘广经术,尊重圣业,有益于化。”(43)范晔:《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6册,1500-15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这是对“章句”不断变化的认识。而对于烦琐章句不利于经学发展的事实,桓荣、桓郁则有实际的贡献。《后汉书·桓郁传》称:“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44)范晔:《后汉书》卷三七《桓郁传》,5册,12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这是在撰述思想上对章句的改变。
经学或政治上的“变”与“不变”,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东汉人学西汉,也是在“不变”之中孕育着“变”。例如,陈宠的律令之学,源自其祖陈咸,而陈咸历成、哀、平、王莽,其律学亦汉末之学。其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陈咸在莽时却“犹用汉家祖腊”,这是时代变化中的“不变”;然入东汉后,陈宠却为鲍昱撰《辞讼比》七卷,并在汉章帝时,“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45)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6册,1547-15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这就是律令之学随着时代、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此类变化,无不体现着“批判”与“重建”的力量。
东汉末年的时局变化,带来了经学思想的变化。在经学上,马融、蔡邕都有“反俗儒”“矫时弊”的行为。马融时代,“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所以他“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46)范晔:《后汉书》卷六〇上《马融传》,7册,1954、19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故意从生活方式上做出有悖世俗之礼的行为。蔡邕的认识与马融相仿,即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所以才提出了“正定《六经》文字”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学习石经者多“后儒晚学”(47),显然与马融、蔡邕心中的“俗儒”完全不同。这是马融、蔡邕之辈,在汉末经学庸俗化的背景下,努力探索一条崭新的经学道路。这也是经学与政治媾和之后形成的陈陈相因,导致了经学自身内部产生了强烈的革新需求。
可以说,无论是经学层面还是政治制度领域,东汉都较西汉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如经学而言,这种不断的“变”,是西汉经学家不可想象的事情。而这种“变”,首先来自时代变化的动力;其次,这种变化之后带来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必然带来文艺思想的深刻变化。也就是说,本来主要体现在经学、政治上的“变”,却随之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革新,并对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各个领域带来了重要影响。可见,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批判”与“重建”的意义与作用是共通的。
例如,艺术方面“鸿都门学”的设立,虽然《后汉书》认为后来出现了有悖于经学传统的倾向,但这种不同于以往对艺术人才的集中召集与使用,则是东汉文艺思想的一大变化。首先,这种文艺思想的出现,还是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并且鸿都门学中人员的构成、范围,不仅限于经学、文赋,还包括更广泛的文艺层面,是以《蔡邕传》称:“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48)。这种变化,体现了东汉社会文艺思想发展的丰富性,本身就是对社会思想的一种解放。其次,鸿都门学本质上还是以儒学为号召,故《蔡邕传》称:“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49)范晔:《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7册,1990、1991-1992、19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这就证明,东汉文艺思想的本质,实际上是以儒学为思想根基,其创作、接受与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也离不开儒学的指导与影响。另外,此处所言“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可以有两种角度的理解:从儒家传统角度看,是当时传统儒家士人耻与鸿都门生为伍;从“文赋”“尺牍及工书鸟篆”的角度看,传统儒家士人接受的教育,已经使得他们无法适应这种“新才艺”的出现,客观上造成了他们的“落伍”与“陈旧”,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此而言,鸿都门学的设置,本身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儒家士人中间,造成了一种“新思想”与“旧观念”的思想对立。值得注意的是,鸿都门学对“文赋”的格外重视,客观上对“文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文赋”的倡导到具有“文学”意义的“文章”命题的提出,已经仅有一步之遥。
东汉文章主要学西汉末年之文,如桓谭学扬雄(50)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崔骃、崔瑗、刘騊駼、胡广皆续补扬雄箴;王充学班彪,其子书与仲长统一样,实学桓谭;张衡学扬雄《太玄》、学班固赋;蔡邕学两汉人赋。就班固、张衡京都赋而言,已经是对西汉赋的一种超越。
今所见《古诗十九首》,据信为东汉人所写定,其中大量对个体心理活动的描写,应该代表着两汉文人在文学上从关心政治到对生命意义追问的变化。从此“文学”正式走下政治神坛,全面进入人们的日常与精神生活,并赋予“文学”以全新的意义。
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论衡》、班固《白虎通义》等讨论的“情”“性”“志”“命”等命题,与《诗大序》“诗言志”、王逸《离骚经序》“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等,皆有内在的文艺思想联系,其背后则是先秦两汉诸子一直讨论的“辞”“理”之辩。(51)孙少华:《先秦两汉诸子“辞”“理”之辩的理论范畴与文学实践》,载《文史哲》,2013(3)。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之“颂德”观念,亦与汉赋“讽谏”“赋心”“赋神”说,具有思想上的传承性。(52)孙少华:《由“讽上”到“颂德”——以〈鲁灵光殿赋〉为例论汉赋文学功能的变化》,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孙少华:《汉代赋论的文学实践与时代转换——以赋心、赋神、赋情为中心》,载《文学评论》,2015(5)。可以说,东汉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文艺批评思想,上承司马相如、扬雄、刘歆,下启魏晋、南朝的诗文评,是东汉文艺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经学上的“熹平石经”,到鸿都门学的“文赋”与“尺牍及工书鸟篆”,东汉文艺思想一直在不断的新变中寻求突破。“新思想”与“旧观念”的对立与对抗,势必形成新一轮的“批判”与“重建”。汉末的文艺思想观念,势必也在这种“新”与“旧”的“批判”之中,“重建”一种新的思想秩序,从而为东汉文艺思想的转向提供契机。从包括经学、“文赋”“尺牍及工书鸟篆”等各种思想中独立出来,并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文章”“文学”转型,从而为魏晋诗歌的产生铺平道路,这是东汉文艺思想转向的标志。
一言以蔽之,秦汉文艺思想史的书写,离不开对“天道”“人事”“文心”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与揭示;秦汉文艺思想史中每一个进程的书写,则离不开对当时文人“批判”与“重建”工作的认识与揭示。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文人而言,无论其学术思想、流派,或者秉持的理念有何不同,其所肩负的“批判”与“重建”的责任是一致的。研究秦汉文艺思想史,就是要努力揭示秦汉文人的这种工作成效,为当下文艺思想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