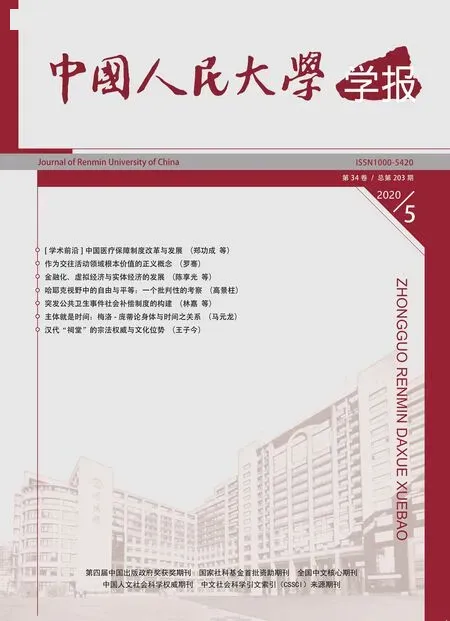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保障
王甫希 习怡衡
在世界范围内,以平台用工、外包、劳务派遣为主要形式的非标准工作(又称为临时性工作)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改变了许多人的雇佣关系的性质。现代社会由于工作方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突破了传统劳动法的范畴。零工经济推动下的非标准用工和临时性用工,已经很难再用传统的雇佣标准来衡量,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的雇员和自我雇佣者之间的界限已逐步消失。新业态就业人员的工作保护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劳动法的一个新难题。2019年12月24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指出,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支持劳动者通过临时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式实现就业。(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2/24/content_5463595.htm。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谈到“新就业形态”时指出,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保障问题,要顺势而为,补齐短板。(2)《习近平谈“新就业形态”:顺势而为、补齐短板》,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5/23/c_1126023919.htm。本文拟分析数字时代对企业经营方式和雇佣关系的改变,探讨平台就业者劳动关系的判定标准及其法律保障问题。
一、新型企业的概念、商业模式和特点
(一)新型企业的概念和商业模式
“雇员”(我国劳动法称为“劳动者”)的法律概念根植于前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的到来,雇佣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传统法律规则的适用在网络环境下产生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使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基于按需经济或分享经济,致力于将客户与个人服务提供者直接联系起来的新型企业正在涌现。这些企业通过建立一个虚拟平台吸引就业者,但不直接对劳动者进行严格管理,“搭建平台的企业”和“通过平台接到工作的人”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支撑起平台核心业务的从业者被定义为“自我雇佣者”,企业采用去劳动关系化的方式摆脱劳动法对企业用工责任的种种限制。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被称为“零工经济”或“线下众包”。众包工作是指将传统由一名员工完成的工作以公开邀约的形式外包给不确定的多数人。从理论上讲,这些新技术企业只是通过数字平台直接将客户与执行任务的个体劳动者进行匹配。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种外包是很难实现的。这些企业致力于建立一个在线平台,比如网络、App等,在这个平台上,客户可以直接找到一个或多个劳动者来完成任务。平台企业声称自己只是帮助服务提供方和服务需求方搭建了联系的一个数字平台,平台企业与平台从业者之间并无从属关系,因此将从业者界定为自我雇佣者。在缺乏劳动法保护,特别是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的情况下,客户可以获得更加便宜的服务。
新商业模式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范围更为广泛,比如滴滴出行(城市交通)、管家帮(家政服务)、点匠(建筑服务)、美团(上门餐饮)、全国导游之家(导游服务)、货拉拉(搬家服务)、易教网(家教服务)等。高技能的灵活就业者(如建筑师、软件工程师等)可以通过程序员客栈、开源众包等平台工作,而低技能的灵活就业者(如司机、送货员等)则可以通过美团、饿了么、滴滴出行等平台工作。这些工作都只是需要在本地线下进行,这些企业也都属于某个特定行业,客户可以通过平台寻找到特定的服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事某一特定服务的平台企业希望控制工作的完成方式,如同传统企业所期望的那样,这些企业希望劳动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因此,平台企业必须确保劳动者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尽管如此,这些平台企业仍然将平台从业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或自我雇佣者。
中国网约车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滴滴出行定位于一家一站式移动出行平台企业。滴滴出行拥有一个虚拟平台,乘客可以通过该平台获得乘车服务。在免费下载滴滴出行应用后,任何用户都可以用它通过GPS找到最近的司机并要求乘车。滴滴出行不雇佣司机,而是由加入平台的司机来完成这些工作。想要加入滴滴出行的司机必须向平台发送申请并通过测试,才能获得授权。授权程序包括要求司机发送他们的汽车牌照、汽车保险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等。滴滴出行要求司机驾龄在3年以上、车龄在8年以内。司机必须承担所有的日常开支包括汽油、保险、税,并承担发生事故的所有责任。(3)《加入滴滴的条件说明和承诺》,参见滴滴出行官网,https://www.didiglobal.com/contact/recruit。但在一些城市,司机可以享受滴滴提供的低价保险和加油优惠。在一些城市(如成都),车辆可以不由司机自己提供,而由滴滴出行提供。客户乘车的价格完全由滴滴出行决定,滴滴出行每单抽成19%—30%不等,每单收取0.5元的保险费,外加1.77%管理费。(4)欧阳李宁:《滴滴详解网约车亏损原因:车费抽成19%,成本占21%》,参见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30145。与Uber不同的是,滴滴出行允许乘客给司机一定的小费。乘客可以评估乘车感受,评估结果会向其他乘客公开。如果评价都是负面的,滴滴出行可以限制司机对该平台的访问权限。滴滴出行也可以因为其他原因,例如在社交网络上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等,限制司机对该平台的访问权限。司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时长,也可以拒绝提供出行服务,但一旦接受订单就必须完成任务。此外,滴滴出行期望司机能尽快到达约定地点接载乘客,如果司机单方面有责取消订单会被扣分,从而影响后续派单。在2018年发生了滴滴司机性侵、性骚扰甚至杀害乘客等严重安全事件后,滴滴出行完善了安全方面的措施,例如,设置“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全程录像”“分享位置”等功能,取消了没有证件的私家车司机,严格限制司机的接单次数,开车前需要先进行人脸识别,删除个人隐私等相关信息的显示,最大限度地杜绝人车不符情况。(5)《滴滴持续升级安全保障:短信报警扩至12城,车内录像加密试行》,参见滴滴出行官网,https://www.didiglobal.com/news/newsDetail?id=576&type=blog。
(二)新商业模式的特点
第一,对劳动者的依赖性更低。新型企业的特点是不需要实时管理和监督平台劳动者的工作。利用技术,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工作评估结果做出是否解雇的决策。同样,企业也没有动力为从业者提供培训,因为任何人想要从事这项工作,他们需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与传统工作相比,新的工作方式具有更少的从属性和更大的工作自由度。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了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供高质量和标准化的服务,这些新型企业仍要对从业者的工作方式保有部分的控制,包括对其配送代理商所雇工人也实施一定的控制。
第二,具有规模经济或群聚效应需求。新型企业运作的基础是积累大量的平台从业者和客户。事实上,由于平台拥有大量从业者,企业也就不需要具体规定上下班时间,而客户也总能在任何时间通过平台找到可以提供服务的人。群聚效应往往会导致垄断企业的出现。
第三,可以开展全球业务。平台和品牌一旦建立起来,其推广扩张至全球市场将变得相对容易和便宜。全球扩张使企业能够利用规模经济,让一个品牌获得世界各地用户的信任,这使得企业很容易获得所需的群聚效应。如滴滴2016年收购Uber中国,2017年1月海外租车服务正式上线,2018年1月收购巴西出行平台“99出租车”,在澳大利亚、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开展出行业务,全球业务扩张迅速。此外,它与软银集团合作成立了合资公司,提供网约出租车服务。(6)袁伟 :《Uber上市难解四面楚歌 软银持股16.3%或成最大赢家》,参见凤凰财经网,http://finance.ifeng.com/c/7mX5VmtX3cO。
第四,业务范围超越提供数据库服务。关于这些新型平台企业的性质,它们到底只是提供供需数据的一个数据库还是在某一特定领域提供服务的企业,仍是争议的关键。同城必应(一家货物配送平台企业)表示,他们不是物流配送企业,因此拒绝对闪送员提供的服务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拥有平台的企业被认为仅仅是信息服务企业,只是提供数据方便供求匹配,那么这些企业就无需对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问题和损害承担责任,同样也没有义务遵守相关行业法规,而且在“提供平台企业”和“在该平台上工作的人”之间很难建立起雇佣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法院裁定同城必应不能被视为一家信息服务企业,因为它对闪送员的配送工作完成方式实施了具体干预。(7)《李相国与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53634号,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079ab95686943698324a955001cfae5。除了匹配供给和需求,这些新型企业为控制工作质量,要求劳动者的工作符合相应的管理规范。此外,这些企业的收入不是来自对其数据库的访问,而是对客户完成任务的收费。(8)Aloisi,A.“Commoditized Workers.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u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Gig Economy’ Platforms”.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2016,37:663-690.归根结底,消费者使用这类平台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可以提供所需服务的从业者名单,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平台提供的特定服务。这意味着企业的声誉取决于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平台会遣散表现不佳的劳动者。
二、新商业模式对劳资关系的影响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即在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中,雇员的法律概念是否仍然有效;第二个问题涉及劳动政策的调整,即是否有必要扩大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使平台劳动者这一自主性劳动群体也受到法律保护。另外,还必须考虑的是,新型劳动者所需要的保护与传统从属性或控制性劳动所需要的保护是否相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可能需要一种新的法律保护。
(一)劳动法适用范围与平台劳动者
传统上,自我雇佣者被认为是直接为市场工作的人,即为一家或多家企业提供服务而又不属于这些企业雇员的人。自雇者拥有自己的生产劳动资料,比如提供服务所需的工具、资源等,他们有高度的自主性并自行承担所有商业风险,独立决定是否接受某项工作。通过在线平台工作的新型劳动者,也拥有工作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工作以及工作多长时间。因此,他们似乎更符合自我雇佣者的范畴,而不是传统雇佣关系中的雇员。过去,劳动法在应对此类新挑战时,根据新的工作方式扩大了对雇员的定义,即当一个企业对劳动者有控制权时,即使这个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也会被归类为雇员。因此,判断在线平台劳动者是否仍在企业的组织范围内并处于企业的控制之下是至关重要的。最先在这一划分上出现争论的是美国和英国。美国劳工部、劳动关系委员会以及司法裁决确认了平台劳动者的“独立承包人”地位,认定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不构成劳动关系,不享有劳动法上的权利。但根据2019年9月美国加州颁布的劳动关系认定的新标准——“ABC”判断标准,平台劳动者有很大概率被认定为雇员,享受最低工资等一系列劳动法权利。(9)赛思·D·哈瑞、汪雨蕙:《美国“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4)。英国将平台劳动者界定为“工人”而非雇员、自雇者。涉及平台劳动者的分类标准的争论,必然会影响到各国劳动法及其对雇员和自雇者之间传统二分法的理解。平台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各国劳动法学和司法裁判的一个难题。
与很多国家的劳动法(或雇佣法)一样,在我国现有劳动法框架下,平台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要么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要么被认定为劳务关系(民事关系)。如果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劳动者就能享有“五险一金”、带薪休假、加班工资和就业保护等各项权利。如果被认定为劳务关系,则属于自由职业者或自雇者,将无法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带来的是劳动保护的“全有或者全无”。目前,我国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主要根据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从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企业规章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安排、所提供的劳动是否有偿、是否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等方面判定。但显然这一判定标准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新的工作模式变化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关于平台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9)规定,网约车平台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这一规定仍然回避了之前关于平台企业与网约车驾驶员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争论。(10)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xxgk.mot.gov.cn/2020/jigou/fgs/202006/t20200623_3307798.html。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会结合网约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接单情况、是否以此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等情形来确定。法官对有争议的案件的个人态度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也导致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平台企业和平台劳动者之间从属关系的隐蔽化给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了挑战。毫无疑问,在新的商业模式下,平台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和日程安排上享有更大的灵活性,甚至在执行任务的方式上也享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不可否认,他们仍受到平台的直接控制。平台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归类为法律意义上的雇员或自雇者,已经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范畴,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特殊的雇佣关系,依据如下:
内行星轮的齿顶圆与齿圈的齿顶圆要留有一定的间隙t,如图6所示,要求内行星齿轮gn1,gn2和gn3与齿圈R的齿顶不相互干涉.对于非变位双星行星机构,其各齿数间的关系可表达为
(1)新的监督模式。在传统的组织结构中,企业监督控制劳动者工作质量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对劳动者进行具体培训、严格执行工作标准规范、监督指导规章制度的落实等。中层管理人员为了实现最优的监控水平,往往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但在平台企业中,这种控制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平台企业通过评价系统委托客户对劳动者进行监控,评估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做出终止劳动者平台使用权限的决定。事实上,企业不需要给出具体要求或控制工作方式就能确保工作质量,即使企业只对如何工作提出建议,不遵守这些建议的劳动者也很容易被剔除,因为客户可以对不遵守规定的劳动者给出较差的评级。事实上,对这些平台劳动者的监控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格,因为他们的工作时时刻刻都处于被监管之下,而且没有成本。简而言之,在新的商业模式中,企业不需要施加官僚性的组织控制权,监管权已经下放给客户,而监管水平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企业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监管,只是因为劳动者现在要服从的是结果监管而不是手段监管。
(2)必需的控制。虽然平台劳动者对企业的从属性已经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自我雇佣者。一定程度的工作自主性并没有彻底改变劳动者对平台企业的从属依赖关系,并且这种自主性是由工作本身的性质所带来的。因此,重要的不是雇主行使多少控制权,而是雇主保留行使多少控制权的权利。平台企业允许劳动者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时间表,是因为科技进步使企业没有必要再发布工作指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归类为自我雇佣者。因为企业可以发布工作要求,而劳动者应该服从,所以企业选择不行使权力,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权力。
(3)不平衡的谈判权。劳动法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经济实力较弱的一方。戴维多夫(Davidov)认为,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情境下的劳动者,无论其从属性如何,都应当以雇员身份受到雇佣合同的保护。(11)Davidov,G.A.Purposive Approach to Labour Law.Oxford:Oxford Monographs on Labour Law,2016.然而,近年来,雇佣合同的法律概念已经转向不考虑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社会状况或政治因素,而单纯以法律文本规定的要素来确定雇佣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认为在认定劳动关系的时候,应该考虑劳动者的社会状况(经济从属地位)和雇员的法律概念(及对其保护)之间相关性。(12)Cherry,M.A.“Beyond Misclassification: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Work”.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2016,37:544-577.这种思维方式坚持劳动关系应该适用于任何客观上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无论他们是自我雇佣者还是与企业存在从属关系的雇员。
(4)加入外部组织。还有学者认为,劳动者的从属性不是由企业是否直接发布工作指令决定的,而是由他是否被外部组织所雇佣决定的,换句话说,是建立在他不拥有自己的组织的基础上。从这方面讲,自我雇佣者只能是那些没有被其他组织雇佣、自行提供服务并独立承担业务风险的人。而如果从业者隶属于外部组织并遵守其雇佣规则时,他/她就会成为“雇员”。在新的商业模式下,平台企业实际上控制着组织的运行和商业模式,劳动者要么接受这些规则,要么失去工作,拥有平台的企业可以对劳动者强制实施一系列管控。
(5)缺乏创业机会。通过在线平台获取劳动机会的劳动者没有任何创业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我雇佣者可以从工作中获得经验、培训、知识和技能。而为平台企业工作的新型劳动者,他们除了提供劳动之外,并不能通过服务增加任何工作价值,只是必要时,企业通过技术手段将“建议”或必要的指示传递给他们。(13)Cherry,M.A.“Working for (Virtually)Minimum Wage:Applying the Fair Labors Standards Act in Cyberspace”.Alabama Law Review,2009,60:1077-1110.事实上,使用这些自雇者而不是雇员仅有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这可以使平台企业能够提供更便宜的服务。相反,真正的自雇者应该有机会获得自己的客户,拓展业务,拥有公平发展的机会。因此,将只提供劳动而没有任何机会获得资本收益的劳动者认定为自我雇佣者是不合理的。
(6)生产工具和资料不再是雇佣关系存在的表征。在决定劳动者是处于雇佣关系之中还是自主创业时,拥有劳动工具、生产资料以及承担商业风险并不是判断从属关系的有效标志。雇佣合同产生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来自工厂的时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雇员永远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然而,由于今天的生产资料可以是一辆汽车或一辆家务手推车,即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因而缺乏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再是判断雇员身份的标识,成为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意味着你不需要保护。事实上,在新的商业模式中,真正的生产资料和工具是技术和信息。通过新技术投资创建一个在线平台,才是生产资料中成本最昂贵的部分,相比之下,劳动者拥有的工具和生产资料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雇员的概念是弹性的,必须允许它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14)Felstiner,A.“Working the Crowd:Employment and Labor Law in the Crowdsourcing Industry”. Journal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Law,2011,32:663-690.
(二)如何将符合一定条件的平台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司法实践总是先于立法。在法院对互联网平台用工的裁判中,不少认定劳动关系的案例都与“工伤”有关,单纯“认定”劳动关系的并不多见。关于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我国的司法裁判模式主要有三种:
(1)不认定劳动关系。在(2019)沪0106民初27907号一案中,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5月27日期间,尤培娥在河狸家网络平台(北京河狸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以手艺人“康而美”的身份从事上门美容服务。该美容工作室由郭某某在河狸家平台设立。尤培娥接受郭某某委托在河狸家平台接受顾客订单提供上门服务,并由郭某某结算服务费,河狸家网络平台代为支付。尤培娥认为自己与河狸家平台形成了劳动关系,要求平台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延时和双休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认为,该互联网平台是为美容师和消费者提供网络交易的场所,美容师没有接受平台的管理和指挥,与平台不存在身份、财产上的从属和依附关系,尤培娥在选择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形式、获得工作收入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性,从属和依附关系较弱,因此不足以认定为劳动关系,不支持尤培娥的诉求。(15)《尤培娥与北京河狸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其他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沪0106民初27907号,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站, 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e195c9325e4e494ebe46ab8f00c951d7。
(2)认定劳动关系。在(2017)京0108民初53634号李相国与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李相国是在该平台公司注册的一名配送员,2016年7月24日在进行闪送业务时发生交通事故。李相国认为自己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要求享受工伤待遇。而同城必应公司则认为,李相国在工时安排、工作量、在线时长以及服务区域等方面享有完全自主决定权,双方属于平等的合作关系。法院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等论证了双方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认为平台公司告知了李相国具体工作方式、工作特点、收入计算、奖励等,对劳动者工作有一定的标准要求。李相国每天从事闪送时间达10小时左右,主要收入来自闪送工作。虽然劳动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单、具体工作时长以及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等,但这种灵活性并不排斥劳动关系,公司不能因为采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和新的经营方式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边界而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最终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李相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16)《李相国与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53634号,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站,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079ab95686943698324a955001cfae5。
(3)不认定劳动关系但需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在(2018)沪02民终565号一案中,2016年8月24日,罗某以“饿了么”(拉扎斯公司的简称)的名义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交警支队认定罗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拉扎斯公司与礼记公司签有《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授权礼记公司经营“蜂鸟配送”业务。礼记公司又与张静超签有《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授权张静超经营“蜂鸟配送”业务。张静超雇用了罗某。罗某使用自己的电动车及标识有“饿了么”的送餐箱及制服进行配送,发生了交通事故。最终,法院没有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判决平台企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罗某具备为“饿了么”服务的外观表征,其收入实源于拉扎斯公司。拉扎斯公司与礼记公司之间、礼记公司与张静超之间均系合作关系。根据协议,拉扎斯公司有权对礼记公司合作业务进行监督管理及做出相应处罚,礼记公司亦须接受监督并支付保证金。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拉扎斯公司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17)《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礼记餐饮有限公司、杨再科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8)沪02民终565号,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站, 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1fc9ae8b92824a4a9dcba8d30122fc04。
通过对互联网平台用工案件的梳理不难发现,发生伤害类事故往往是引发平台企业与平台劳动者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起因,在认定劳动关系方面,法院审核的要素有相似之处,只是最终判别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时所采取的标准不同。就“从属性”这一关键要素而言,法院主要审查:(1)用人单位的指导和监督。比如,是否能够自主决定接受或拒绝工作要求和工作内容,是否对工作过程和行为有指导、监督或管理,是否必须在特定时间段工作,是否必须在特定场所工作,是否可以找人替代,等等。(2)收入。比如,是否属于付出劳动的对价,工资是否固定、有规律的发放,是否承担相应经营风险,等等。(3)个案考量因素。比如,报酬支付主体和方式,是否提供劳动条件生产工具,是否发放工作证、工作服等证明身份的证件,是否有底薪、社保,培训是否以入职为目的,公司经营范围是否包括劳动者所从事的业务,等等。然而,试图从司法案例中提炼某些一定会被认定为劳动关系或者一定不会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要素的尝试被证明是徒劳的。无论是单一要素、核心要素还是综合要素的比对,似乎都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类案不同判”在互联网用工领域比较普遍,相同公司的案件,有认定构成劳动关系的,也有不认定构成劳动关系的。法院强调个案审查得出结论,由于不同法官对通过特定在线平台执行线下任务的劳动者的分类标准有争议,就产生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从司法实践可以看出,虽然平台用工并不完全符合现行劳动法有关工作时间、最低工资以及社会保险等的相关规定,但在实践中法院并没有因此拒绝向劳动者提供基本权利救济,而是采用更加灵活折中的方式解决平台劳动者所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比如,在闪送员李相国诉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案件中,法院认定劳动关系所支持的仅限于交通事故的工伤赔偿责任。
事实上,雇佣保护法应该倾向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观点已成为劳动法学术界的共识。通过这种对雇佣合同的目的性解释,法院试图保护所有自主性被削弱的劳动者,而无论是否存在从属关系。(18)Cherry,M.A.,and Aloisi,A.“‘Dependent Contractors’ in the Gig Economy:A Comparative Approach”.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17,66:637-689.然而,在现行制度框架保护范围偏窄与保护手段“一刀切”配置互为因果的情况下,这一立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法院一旦将这些劳动者确定为雇员,其法律后果将是有必要对他们适用所有的劳动法规,而其中一些规则并不适合这种新的商业模式。这将会导致法院在面临此类裁决时无所适从。因此,探索这一特殊雇佣关系的认定标准以适度扩大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并谨慎选择劳动法的保护手段,仍有其现实可行性。立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深入讨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应该享有哪些权益。
三、行动逻辑框架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的规制
(一)新的劳资关系模式需要新的保护
根据劳动关系行动逻辑(logic of actions)的理论框架,对于平台劳动者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取决于三种不同的行动逻辑的强弱程度和相互作用,即市场竞争的逻辑(logic of competition)、就业收入保护的逻辑(logic of employment-income protection)和产业和平的逻辑(logic of industrial peace)(19)Frenkel,S.,and Kuruvilla,S.“Logics of Action,Globalization,and Changing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China,India,Malaysia,and the Philippines”.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2002,55(3):387-412.。“市场竞争的逻辑”是指资本会争取最大程度自由调配劳动力,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根据“就业收入保护的逻辑”,劳动者会采取措施限制雇主的行为,争取持续获得公允的劳动报酬。由于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目标存在冲突,双方需要寻求途径化解矛盾,以政府为代表的主体,为寻求缓和冲突、化解矛盾的一系列制度框架而采取的措施和努力,被称为“产业和平的逻辑”。不同的行动逻辑代表了三方主体在核心价值观引导下的战略选择。基于就业收入保护的逻辑,简单地将平台劳动者直接认定为“雇员”以提高其就业保护,会抑制灵活就业,给平台企业带来经营压力。但如果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逻辑,以最大化用工灵活性的手段追求经济发展,无视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也会引发平台劳动者、工会、非政府组织等主体提出政治诉求,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共享经济的发展。现行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带来的平台劳动者劳动保护的“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市场竞争和就业收入保护的逻辑之间寻求一个平衡,针对当前新业态企业的不同用工类型进行分类规范、区别施策。
关于如何解决不确定的非标准工作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法,许多解决办法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雇员和自雇者之间考虑新的权利分配和保护。(20)Freedland,M.“Application of Labour and Employment Law Beyond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2007,146:3-20.20世纪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只为那些为了谋生而不得不接受临时就业的劳动者提供保护,忽略那些目的相同而自己投资创业的人,但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过时。现在应该让所有劳动者(包括非雇员)都拥有一些“核心权利”。这一观点由权威学者提出,如马可·比亚吉(Marco Biagi)提出的“工作法规”和马克·弗里德兰(Mark Freedland)提出的“个人雇佣合同”的构建等理论。欧盟法院(CJEU)似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推动欧盟劳动法,法院基于工人自由流动的前提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工人概念,扩大了就业保护法规的范围。(21)Menegatti,E.“Mending the Fissured Workplace:The Solutions Provided by Italian Law”.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2015,37:112-116.欧盟法院对欧盟劳动法中规定的就业权利范围采取的做法,必然会影响到各国的劳动法及其对雇员和自雇者之间传统二分法的理解。
应当将平台劳动者作为一类特殊雇员纳入就业保护范畴,反之,排除平台劳动者意味着劳动法忽视了这一劳动者主体,而劳动者正是劳动法从诞生之初就试图保护的对象。法律必须根据每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加以解释,必须继续提供不同的方案来保护劳动者,不能固守过去的单一劳动关系概念,要允许多重劳动关系的存在。不过,我们认为在新的商业模式中,对平台劳动者实施所有现有的就业保护法规并不合适。平台劳动者面临着与传统劳动者不同的风险,他们需要一种量身定制的法规。这种特定的法规仅适用于这一类型的劳动者,并且适应这种新的行业特征。
将平台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也并非完全符合就业收入保护的逻辑。平台劳动者和传统工人所需要的保护并不相同。新的商业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工作时间的灵活性,而传统的保护工作条件的规则并不完全适合这种模式。在新的商业模式下,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间工作以及工作多长时间,而保护传统工人的工时制度(如工时安排、法定休息时间和休假制度)无法适用于平台劳动者。在工作时间方面,平台技术解决了市场竞争逻辑和就业收入保护逻辑之间的矛盾,使企业灵活用工和劳动者休假权的保护同时得以实现,但这一商业模式使得保护劳动者的固定工资和最低工资制度难以实施。集体谈判的运用也有其困难,很难在一个在线平台上建立议价实体,因为不太可能确定劳动者的数量,他们可能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上工作。在一个劳动者彼此不认识的行业,如何建立相互信任并就工会代表权达成一致也是一个挑战。(22)Brescia,R.“Regul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New and Old Insights into an Oversight Regime for the Peer-to-peer Economy”.Nebraska Law Review,2016,95:88-144.此外,这种商业模式所依赖的劳动者拥有的未被充分利用的物品(如电脑、汽车、网络连接、电话、相机等),事后要求企业报销这些物品的费用似乎也不合理,但有些完全由工作产生的费用(如汽车的运行费用等)要求报销则可能是公平的。
(二)制定专门的保护平台劳动者的法律
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劳动法律制度中,针对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劳工条例,这就是所谓的特殊劳工法。例如,对高级管理人员、运动员、销售人员、艺术工作者和律师等特殊劳动者有专门的规定。这些特殊劳工法的目的是使就业条例适应某一职业的具体需要。借鉴这一制度安排,可以将符合一定条件的平台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前提是对那些与这种新商业模式不相容的规定进行修改。应在不妨碍行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平台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研究平台劳动者特殊就业保护的应对思路:
(1)劳动者无须接受直接指令。对劳动者的直接指令不应再作为判断雇佣关系是否成立的准绳。这类新型劳动者不管是否得到如何执行工作的指令,都应该受到保护。通过在线平台工作的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性较小,受平台的控制程度较低,这意味着平台只能发布必要的指令,让劳动者能够自由选择如何工作。如果平台对劳动者有具体的工作要求,即劳动者工作自主性较低时,应该适用传统的就业保护规定。监管程度低这一特征在特殊劳动合同中并不罕见,比如,远程工作就不适用标准工时制度的约束。同样,推销员、高级经理、表演艺术家就不适用标准工时制度的约束。
(2)劳动者有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的权利。应该允许劳动者拥有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的权利,这是互联网行业用工的主要特征。然而,雇主应有权设定每个劳动者每周在本平台的最长工作时间,例如有权决定需要兼职还是全职劳动者。与此同时,应规定总的最长工作时数,不论这些工作时长是为同一平台工作还是同时为其他平台工作。设定上限的目的是鼓励工作分担和降低失业率。
(3)劳动者有在多个平台上工作的自由。为了促进市场的自由流动,应防止一个平台和一个劳动者之间的排他性协议,否则很容易导致垄断,让新企业没有机会进入这个市场。如果每个劳动者只能在一个平台上工作,这将会减少竞争,并降低消费者获得优质服务的机会。
(4)最低工资。平台劳动者是否有获得最低工资保障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劳动者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工作,工作多长时间。对企业来说,提供有保障的最低工资是昂贵的。尽管如此,企业仍然应当在劳动者为客户工作的时段为其支付最低工资。争议在于等待时间。当劳动者在在线平台上等待客户时,应不应该获得报酬?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是把等待时间看做是劳动者在公司工作(随叫随到)但没有效率的时间。例如,西班牙劳动法规定,雇主必须为这种非生产性时间支付工资。然而,作为一项特殊规定,应该强制企业履行这项义务,为这种非生产性时间买单,但它应该同时遵循双方集体谈判的结果。因此,集体协议可以将等待时间的工资支付减少到最低工资以下,甚至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取消劳动者领取最低工资的权利。(23)肖竹:《第三类劳动者的理论反思与替代路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6)。
(5)费用报销。平台有权对通过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或劳动工具制定相关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可以要求劳动者拥有一部手机、一辆车、一台电脑等,而这些“未充分利用”的资产不应由平台支付。但是,执行工作所需的消耗品应由公司报销,比如运营成本等。因此,固定成本(由工人支付)和运营成本(由公司支付)将会分离。
(三)对平台劳动者进行“兜底保障”
(1)制定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政策。我国主要的社会保险项目是以劳动关系存在为前提建立的。这样的制度安排迫使在对于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关系的治理中,必须在市场竞争和就业收入保护的逻辑中取其一。如果要化解这一困局,做到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灵活就业者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政府就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政策,设计与劳动关系脱钩的社会保险项目,加强对平台劳动者工伤、养老和医疗保险权益的保护。在未明确平台劳动者的雇员身份前,应允许他们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参保,政府可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减轻其缴费负担。在险种选择方面,应优先实行工伤保险,将平台劳动者以一种特殊劳动关系的形式归入职工工伤保险。修订《工伤保险条例》,将新业态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增设“重大职业伤害保险”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24)王全兴、刘琦:《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挑战和法律规制》,载《法学评论》,2019(4)。对于平台劳动者的养老、医疗保险,可以将其归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在费率方面予以适当降低。考虑到平台劳动者的特殊性,职工社会保险的规则未必都适用于他们(25)谢增毅:《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载《中外法学》,2018(6)。,应当根据平台劳动者流动性较强等特点设计必要的特别法规则,例如,探索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险种之间有效衔接机制,对于工作时间超过一定期限的劳动者可要求平台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工伤认定条件应弱化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因素而突出职务或业务行为的意义,等等。对现阶段不能参加工伤保险的,应通过商业保险方式为劳动者提供基本医疗和意外伤害保障,对因工作原因受到突发的、非疾病的事故伤害进行托底保障。
(2)允许通过集体协议进行自我监管。集体协商的权利是新业态劳动者的一项基本人权。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由工会与雇主、雇主组织集体协商制订约束劳资双方的行为规范,不失为保护平台劳动者权益的一种好办法。平台企业和工会在推动灵活就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应当创新治理方式,强化各方责任,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和新业态企业的健康发展。例如,可以协商规定旨在保护劳动者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时间上限,避免因过度劳累而产生的职业伤害风险。发挥行业联盟和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用工规范和劳动标准,探索通过行业协会推动企业签订相关劳动用工倡议书或者行业公约来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龙头企业制定企业行为守则来带动整个产业链或者行业内的企业规范劳动用工行为。这一制度设计也遵循了劳动关系行动逻辑框架中的产业和平的逻辑,即通过抑制产业冲突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3)推进平台劳动者组建工会。在数字化劳动环境中如何把劳动者组织起来是一个挑战。平台劳动者通常分散在不同的地点独立工作,彼此间存在直接竞争,而且在线工作通常是短期的或者任务导向的,劳动者经常会在不同平台之间转换,流动性较大。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劳动者通过组建工会维护共同利益的意愿,也抑制了平台劳动者集体组织行动的开展,因为劳动者很难接触到其他平台劳动者,也很难参与到平台劳动者的集体行动中。2018年以来,全国总工会和地方总工会大力推进平台劳动者等群体组建工会,试图通过工会服务以及集体协商提高平台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解决目前平台劳动者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基于分享经济,致力于将客户与个人服务提供者直接联系起来的新型企业,通过建立虚拟平台实现供需之间的匹配。这些企业认为它们对平台劳动者没有任何控制权,因而应该将平台劳动者归类为自由职业者。然而,本文认为,平台劳动者虽然在工作时间和日程安排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性,甚至在执行任务的方式上也享有更大的灵活性,但不可否认,他们仍受到平台的直接控制。平台劳动者已经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范畴,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特殊的雇佣关系。通过立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群体进行保护,是劳动法从产生之初就确立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法律应当根据数字时代企业商业模式的变化,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平台劳动者提供不同的保护方案。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对平台劳动者适用所有现有的劳动保护法规并不合适。平台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和工作中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与传统雇佣劳动者不同,他们需要一种量身定制的法规。本文建议应针对平台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制定涵盖这类新型劳动者并适应这种新的行业特点的法律法规。
对平台企业用工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意味着这类新企业无需付出适用劳动法的成本,也意味着它们能够以低于传统企业的价格提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施新的特别雇佣保护标准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还将防止不公平竞争和社会倾销。否则,这些新型企业将垄断市场,排挤传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