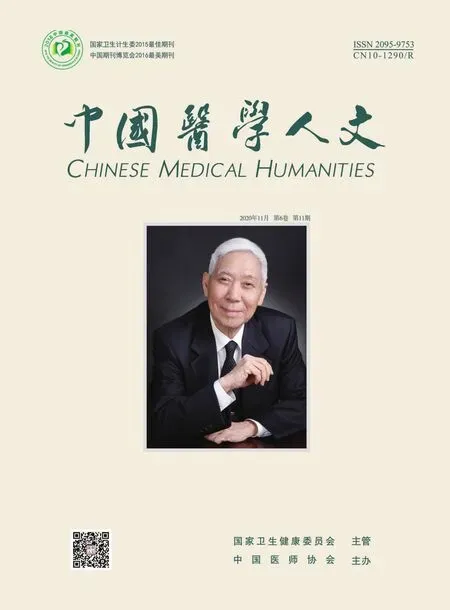没有死亡就没有美德
文/陈嘉映
编者按:2020 年9 月27 日下午,第四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医学与文学论坛在京召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现象学家陈嘉映教授在会上作报告,他从哲学角度阐述了对死亡的看法。
中西方哲学家对死亡有很多思考,比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哲学这个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为死亡做准备,或者是在练习死亡。20 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整个生命是向死存在的。很大程度上,这些思考是希望人们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克服死亡恐惧有种种途径。各种各样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藏教等通常有不同的克服死亡恐惧的做法。而哲学家与他们不同,大范围来讲,哲学是通过思考来克服死亡恐惧的。从古到今也发展了很多不同的克服死亡恐惧的论证,非常突出的一条论证:灵魂不死。而苏格拉底所说的练习死亡,也是和灵魂不死相关联,这点需要我们联系哲学慢慢地去领会、理解。德意志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的三共设中有一个就是灵魂不死,他也做了“炸弹性”的论证。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关于死亡的论证,即死亡与我们无关:当我存在,死亡尚不存在,当死亡存在,我尚不存在。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想法,《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庄周之作,其中《庄子·知北游》中写到:“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元待也。皆有所一体,有元异道也。”后世的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论证进行补充:我们跟死亡完全不相干,乃至于我们有时会想象死亡,但这种想象不合逻辑。因为想象中你总还是在场,你还是将活的自己放在其中,你可能什么也没干,你可能躺在棺材里,而实际上你想象不出你死亡之后会怎么样。卢克莱修用这个论证来支持伊壁鸠鲁这样一个基本命题:死亡跟我们生命是没有交集的。
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死亡是遗憾、可憎、可怕的,这种感觉会不会因此被消除了呢?也不一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消除对死亡的憾恨(这里是指遗憾的“憾”,恨铁不成钢的“恨”)?
有两位哲学家对伊壁鸠鲁的命题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其中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认为死亡之所以非常可憎,并不在于我当事人是否能“听见”它,而是因为它剥夺了我当事人原有的能力。试想一下一个人正当盛年,突然发生一场事故。这场事故一下把他的脑袋撞坏了,但他并没有死亡,之后他可能还会在生活中表现出傻乐的状态,因为他自己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损失。虽然他自己生活在一个快乐的状态中,但是那些爱他的人们会感到很大的损失。因为他正当盛年,有能力做很多事,而现在无法去做了。因此当一个人的能力和潜能不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话,这样一种损失才是我们憾恨的原因。实际上,一个人的状态,无论是生是死,快乐与否,都不是以这个人的感知为标准。关于伊壁鸠鲁命题的第二种进一步思考:一个叫欧利特的哲学家认为伊壁鸠鲁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按照伊壁鸠鲁的想法:生命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到了死亡这一点,生命就受到了限制。而欧利特认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不断移动的现在,我们是生活在希望和计划里,生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有希望,因为你正在做某件事,且你正在做的事是一个计划中的事,而死亡之所以可憎是因为死亡打破了你的计划,打断了你正在做的事情和整个计划的完整性。
这两种死亡观的背后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其中伊壁鸠鲁认为时间是一个现在的线性移动。20 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提出“绵延”的时间观,它非点的移动,是一种立体的时间观。我们是生活在绵延之中,而非点中,我们的种种计划、情感都有它特定绵延的界限。用通俗的时间观念来说就是它们有特定的长度:一件事情可能在明天结束,另外一件事情在1 年后结束。有些人生计划可能伴随着我的一生,直到我们死去才会结束,而有些人生计划并不是以我的死亡为终点。如宋代诗人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一生就希望统一北方,他的必生追求就绵延到死亡之外。
其实伊壁鸠鲁的死亡观中也有克服死亡、减轻死亡恐惧的办法——“今朝有酒今朝醉”,即你永远活在现在。这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克服死亡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伊壁鸠鲁手把手教给你的克服死亡恐惧的办法,它的代价非常大:一个立体的生活就会变成点式的、现在的、以移动式的生活,这样生活的人叫单维或者一维的人,就是一个线性的人。另外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处境:你用这种方式可能会减轻或者克服对死亡的憾恨,但是你不一定会接受它,结果就是让你为了你所珍爱的东西(你的希望,你的计划,你对世界对亲人的爱)不得不接受死亡憾恨的一部分。
死亡对于我们人生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一方面他让我们感到可厌、可憎、可怕,另外一方面它也使得我们周围的一切珍贵的东西变得珍贵。如果没有死亡的话,我们可能会有长生不老的想法,我们所珍爱的一切将不复存在,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它才会是珍贵的。《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是全希腊人心中的英雄典范。亚里士多德说:据说只有在人间才有阿喀琉斯,天上的众神里面是没有阿喀琉斯的。因为希腊众神是不死的,这是神与有死者(希腊中用来代替人的)的区别,也是人的一个本质。我们总是认为这是人不如神的地方。但是他反过来说:这是我们人优于神的地方,因为众神中没有阿喀琉斯,而终极的勇敢、终极的爱就是面对死亡,他们是不死的所以没有也不需要这样的勇敢。因此,我们人类珍爱的美德,我们珍爱的那些最深厚的感情,在那个意义上,人的有限性——我们作为人的缺陷或者遗憾,也正是我们人之为人的值得荣耀、值得珍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