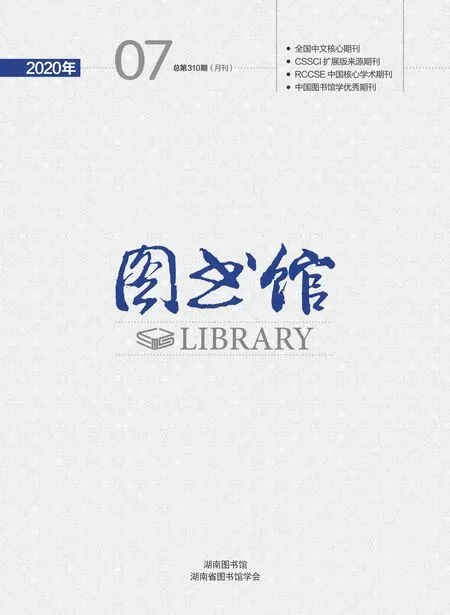20世纪30年代中叶图书馆与出版界发展状况研究*
郭 超 刘 平 周 熠
(1.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长沙 410100;2.湖南大学 长沙 410082;3.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 410005)
近代以来,图书馆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原来的以“藏书”为主逐步向“实用”转变,并向全体大众开放,成为教育、益智之地。许晚成先生称赞图书馆:“学问之府车,智识之源泉,大学之魂灵,学生之参考室,教员之研究室,理论之实验室,万事之问津处,实为无价之宝藏。”[1]6图书馆功能的转变,使得人们不必买书也有书看,这就必然会影响到出版界的图书销量,出版界因而并不乐于帮助图书馆的建设,至于所出版的图书是否符合图书馆的需要,出版界并不在意。所以在1932年,鉴于图书馆发展数十年来“出版界和圕绝无联络的表现”这一事实,杜定友先生在《出版界与圕》一文中指出:“出版界和圕都是以图书为对象。经营手续上虽略有不同,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出版界推销图书,其动机也许为谋利,但目的是提倡文化,与图书馆的目的正复相同。因此可见出版界与圕同为社会上文化服务的机关,目的在提高民智,阐扬文化,而同时供给社会人民一种高尚的消遣,于德育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彼此的联络合作,在社会上也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图书馆的目的在于养成民众的阅读习惯,所以图书馆对于出版界的力量,比任何广告方法较为有效。此外图书馆每年举行读书运动周,图书展览会,或于馆内附设售书部,并代内地人民采办图书杂志等等,于出版界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2]他认为图书馆和出版界息息相通,建议图书馆和出版界应该彼此展开合作,相互促进。《所望于出版界者》一文总结了出版界的使命:“一为提高文化,一为普及文化,以此来增进中华民族的智识与实力。”[3]图书馆和出版界同为文化服务机关,在提倡文化、增进民智方面具有共同的责任和使命。图书馆不仅能够影响出版界,图书馆的发展也能带动出版业的繁荣,因此图书馆和出版界有相互了解、相互合作的必要。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1936年间,图书馆事业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顶峰。同时,出版事业也在此期间与图书馆事业相呼应,书籍、报刊在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图书馆和出版业的共同发展,印证了杜定友先生对两者是相得益彰关系的论断。
1 20世纪30年代中叶图书馆之发展
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决议,请当时的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地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并提取每年经费的百分之五以上作为购买图书的费用。此议案的实施,大大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据中华图书馆协会1935年前先后4次对全国图书馆数量的调查,1925年为502所[4],1928年为642所[5],1930年为1 428所[6],1931年为1 527所[7]。另据1932年的《申报》记载,1930年教育部统计的公私立图书馆数量为2 935所[8]。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比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的数据多出整整一倍,其原因就在于教育部的统计包括了民众教育馆,并且将规模较小的书报处也计算在内,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统计则没有包括民众教育馆。也许是吸取了这两项统计数据相差甚远的教训,申报年鉴社于1934年进行图书馆数量的调查时,将调查表分寄各省市教育厅,请各省市教育厅填报,并依据各省市教育厅填报的调查表(因种种原因,调查表只收回一半),同时参考前三年的不同数据,又分列图书馆(包括国立、省立、县区立、私立之单独设立者)、民众教育馆、机关附设图书馆、学校附设图书馆(中等以上公私立学校)四类,最终统计结果为:单设图书馆1 543所,民众教育馆1 073所,机关附设图书馆142所,学校图书馆3 115所,总计5 828所[9]1074-1075。另据1936年出版的《申报年鉴》记载,1935年全国各种图书馆数量总计5 196所,其中单设图书馆1 502所,民众教育馆990所,机关附设图书馆162所,学校图书馆2 542所[10]1236-1237。
1935年教育部以“图书馆教育,系培养民族意识,且为探讨高深学识之工具,其功能极为重大”为理由[11],下令全国各省市调查所属之图书馆概况及数目。教育部根据各省市教育厅及其他设有图书馆之机关所填报的调查表,并且参考旧的档案和有关图书馆的出版物,加以整理,按性质分为普通、专门、学校、民众、流通、机关、私家(藏书楼)七项,统计出当时公私图书馆有4 032所。其中学校图书馆为1 963所,民众图书馆1 255所[12]。1936年8月,教育部根据各省市所填报及调查材料,统计出全国各类图书馆总计4 041所[13]。中华图书馆协会鉴于民众教育馆的不断发展壮大,于1935年进行第5次调查时也将民众教育馆包括了进来,截至1934年12月,全国图书馆总计2 818所,其中民众教育馆1 002所[14]。另据1935年10月出版的《全国图书馆调查录》一书记载:“东三省(暂时)不能调查外,而全国图书馆不满三千,并调查全国大中小学校,计大学中学有四千余,每一大学中学设立一图书馆,已有四千余所,我国对于图书馆事业,急谋进展。”此次调查,“或一馆而采问数次,或一疑而悬候累日,远道通函调查,往往发函十数次,而总无覆寄,挂号快函如雪片飞去,亦有始终不睬,切托该地友朋,实地探问,始达目的”。一方面可以看出此项调查之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调查录之真实可靠。最终收录图书馆2 520所,包括公立图书馆2 005所,私立图书馆515所,“所列图书馆,皆以有固定名称及组织,并有相当人员管理者为限,一橱一桌可称图书馆者,概不列入”[1]7-8。
根据以上资料,民国时期对全国图书馆的统计在1935年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既有官方的教育部,又有中华图书馆协会这样专门的图书馆行业团体,还有申报年鉴社以及个人,都对图书馆的实际数量展开了认真调查。但因为调查的方法和标准的不同,得出的数据也有所不同,加上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就更加使得数据难于精准。早在1932年,陈豪楚先生就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调查结果表示了怀疑,指出它错误百出,遗漏颇多。当时由于对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提倡,民众图书馆和乡村教育馆增加了不少,尤其以河北江浙诸省居多,统计图书馆数量时当然不能将它们全部排除在外。据他的统计,仅河北一省遗漏的就达35所之多[15]。又如在学校图书馆的统计上,中华图书馆协会调查大中小学校馆共计497所,教育部统计学校图书馆有1 963所,而《申报年鉴》统计中等以上的公私立学校就达到2 542所,许晚成更是在前面就推断全国大中学校图书馆有4千余所[1]8。尽管调查所得的数据相差较大,但人们对图书馆调查统计所作的努力值得肯定。中华图书馆协会先后五次,历时十年,对全国图书馆调查表进行了修订。申报年鉴社也有专门调查图书馆的人员,陈训慈就是人员之一。他应《文化建设月刊》之邀请,撰写了《民国廿四年之我国图书馆事业》一文,叙述了1935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许晚成先生更是凭借个人的努力详细记载图书馆藏书总数、何种图书占多、采用何种分类法、每日阅览人数、馆长和职工等信息,内容之详实令人佩服其调查之功。
20世纪30年代初,图书馆统计事业并不发达,一方面与当时的统计方法不成熟有关,一方面也与图书馆本身的发展程度相关。1935年图书馆调查统计逐渐受到重视,图书馆事业也取得了较大进步,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结合图书馆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1935年、1936年这两年图书馆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官方、社会以及个人的关注。但在1937年之后,图书馆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正如时人蒋复璁所言:“我们知道在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在东南各省损失了近二千所的图书馆,图书损失在一万万册以上,并且所损失的多是战前最完善的图书馆。”[16]严文郁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书中也说到:“25年(1936年)时有图书馆5 169所,36年(1947年)时仅有2 700余所,可以想见图书馆在抗战中遭受破坏之钜。”[17]因此,20世纪30年代中叶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顶峰。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图书馆数量上的增长,还体现在馆藏图书以及入馆人数这些数据上。其中,1935—1936年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发展情况和相关数据保存完善。下文将以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发展为个案分析,以窥当时图书馆事业之状况。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学部的京师图书馆,1929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称国立北平图书馆,聘请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从这年开始到1938年,蔡元培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达十年之久。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据有关资料记载,1931年在30万册以上[18]。另据许晚成所编《全国图书馆调查录》统计,1935年该馆藏书达40万册[1]180。但陈训慈记载的该馆1935年藏书的数据是:中文普通书30万册,文津阁四库全书8万册,西文书约9万册,日文书约1万册[19]。可见当时藏书不止40万册。另据《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一书的统计,除1931年新馆建立新入馆藏图书量较多,为67 185册外,1935年新入48 204册,多于1934年的38 645册,以及1936年的14 609册[20]。新入馆藏图书主要由各方赠书和本馆年度购书两部分构成,1935年的馆务报告中有“各方赠送图籍书目较上年为尤多”的表述,同时也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赠送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卷帙为最钜”的记述。
至于入馆浏览人数,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6月这四年中,每年总数分别为440 490人、329 070人、475 058人、497 018人,平均每日分别为1 200人、1 224人、1 323人、1 348人,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京报》对此也有记载:1935年的上半年,阅览人数达到2万多人,平均每天1 470多人[21]。每日入馆人数的逐年增多,说明这一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对国民阅读、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影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也正因为人数的增多,北平图书馆在设施和读者服务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和调整,如改良出入馆凭证,扩充期刊、新闻阅览室,设立一系列专门研究室,设立新书阅览室,以及为阅览人士提供参考咨询等服务,其现代图书馆的特色越加明显。
2 20世纪30年代中叶出版业之繁荣
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图书馆出现短暂鼎盛的同时,出版界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依据王云五先生《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文的介绍:1934—1936年全新出版物的册数分别为6 197册、9 223册、9 438册。由于1933年前缺乏真实的数据,故他推断1917年到1933年新出版物册数在1 500册到3 000册不等,与1935年前后数量上的差距甚是明显[22]。
当时图书出版工作一般由书店兼营。1930年12月,上海有书店114家[23],1935年增至260家。《上海市年鉴》记载:市教育局为弄清本市书店数量及其内容,曾派人员分头调查并于1935年5月编印书店调查录,全市大小书店共计260家[24]。 “我国出版家十之八九在上海”,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三家出版社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三家出版社。这三家出版社在1934年至1936年间的出版物册数分别为3 786册、5 752册、6 717册,占当时全国三年间新出版物册数的65%[22]。《上海市年鉴》记载的这三家出版社新版书籍(包括一般读物、大部书籍、教科书)的总数,1935年为6 910册,1936年为7 895册,其占当年全国总出版册数的比重比王云五统计的还要高,足见这三大出版社在当时出版界的影响和地位。另据《上海市年鉴》的统计,1934—1936年上海市新版书籍(不包括大部丛书和教科书)的种数分别为746种、814种、1 072种。两项数据都表明这三年出版书籍的册数和种类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自1937年开始,由于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进行,处于全国中心的上海出版业深受重创。由此可见,1935—1936年间是民国出版业的黄金时期。
1935年和1936年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新版册数,与大部丛书的出版密不可分。根据《上海市年鉴》的统计,1935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书店出版的大部丛书册数分别为3 106册、1 921册、18册,总计5 045册,占到当时新版书总数的一半以上。大部丛书可分为三类:一是系统之丛书,如《万有文库》《中学生丛书》《幼童文库》等;二是专门的大部丛书及词典,也可以称为分科丛书,内容涉及法律、数学、化学、医学、音乐等方面,如《实用法律丛书》《算学辞典》《大众音乐全集》等;三是大部古书,最为典型的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由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由该馆印行,在1935年出书1 089册。此外还有《丛书集成》《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十几种大部古书的翻印。而在大部丛书中,大部古书所占比例最大,甚至形成了翻印古书的潮流,1935年因为古书翻印最为兴盛,还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古书年”。根据《上海市年鉴》的统计,1935年至1936年,不只是大部丛书的出版,其他社会科学类、大中小学教科书类、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类的书籍等也都有所发展。
除了书籍,报纸杂志也有较大发展。内政部统计,1931年9月至1932年底在内政部登记的新闻纸及杂志累计有1 403种[25],1933年底累计有3 331种[26]。据《申报年鉴》记载,内政部截至1934年底新闻纸及杂志的历年登记表显示:1928年9月至1932年12月,新闻纸为867种,杂志为136种;1933年4月至12月,新闻纸为686种,杂志为500种;1934年1月至12月,新闻纸为500种,杂志为450种;共计新闻纸2 053种,杂志1 095种,总计2 948种[9]1113。截至1935年2月,内政部统计的报纸和杂志的数量共计4 745种[27]。到了1935年6月,新闻社、通讯社、杂志社在内政部核准登记累计(包括自动停刊或注销登记的)4 503家,现有4 012家。其中报社2 283家,通讯社724家,杂志社1 005家[28]。登记对象的转变是这次统计的特点,登记单位也由原来的“种”换成“家”。因内政部的统计不太准确,《申报年鉴》又在内政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校正,改为报社1 764家,通讯社759家,杂志社1 518家,累计4 041家[10]1287-1290。另据王云五的记载,截至1935年底,到内政部登记的报纸有1 763种,对比1934年底的1 008种,增长较快;杂志更是从1934年的450种增至1935年的1 486种,一年中几乎增长了四倍[29]。如果参照内政部的历年统计,王云五关于杂志一年内增长了四倍的说法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1934年的450种是一年内的增长量,而1935年的1 486种应是当年的杂志种类总量。根据1936年3月内政部的统计显示,全国有报社1 503所,通讯社788所,杂志社1 875所,共计 4 166 所[30]。
这一系列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33年开始,报纸杂志有了明显的发展,尽管后来的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总的来说还是保持了数量上增长的趋势。1934年还被时人称之为“杂志年”。报纸杂志数量的增长与人们关注国内外时局密切相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众希望通过报纸杂志来了解时局的发展,同时也愿意通过报纸杂志来发表自己对时局的意见,再加上报刊的价格比书籍便宜,且易于购买,于是报纸杂志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据代售杂志最完备的现代书局所发表的目录,上海就有数百种杂志,其中季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无不具备。刊物内容也比较丰富,有发表政见的,有讨论学术的,有发表文艺作品的,有专门登图画的等等。1934年上海创刊的杂志比较重要的有《词学》月刊、《文学月报》等数种。舒新城指出在1934年杂志的销售中,小品文性质的刊物销量最大,其次是画报[31]。《成人阅读兴趣与习惯研究》一文显示,1935年成人在杂志阅读方面,多以短篇小说为主,其次是长篇小说[32]。
3 20世纪30年代中叶图书馆与出版业的合作和交流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在《四十年来之中国出版界》一文中将1901年至1940年间的出版界分为五个时期,其中第三个时期是“图书馆运动时期”,时间在1928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这几年,这一时期图书馆的发展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法令和经费支持,还有“出版界方面加以赞助”。例如,商务印书馆主编的《万有文库》一、二集合计4千册的书,“一举解决了普遍推行图书馆运动时所遇到的三种困难,即经费支绌、缺乏管理人才及相当图书之难致。全国因《万有文库》而成立的新图书馆,至少在一千五百所以上”[33]。《万有文库》之所以能成就如此多的图书馆,与当时的政府法令密切相关。1932年10月,为了开发民智,让人们有读书的机会,内政部、教育部令各省民政、教育两厅转饬所属的每一县市政府及各省民政教育两厅、各市社会教育两厅,必须购置《万有文库》,存置各教育局中,以充实地方图书馆设备[34]。1933年,教育部又选定中学生阅读参考图书目录:国学基本丛书、国学小丛书,其版本均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35]。加上王云五对《万有文库》的宣传以及积极与各图书馆联络等行为,使得销路不畅的丛书转为畅销,《万有文库》第二期的预约更是超过第一期的印数,甚至预约晚了还要延迟两个月才能拿到书。大部丛书对促进图书馆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图书馆界读书界的影响颇大。可以看出,“图书馆运动时期”图书馆得到了出版界的支持,同时也对出版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图书馆和出版界同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更离不开这个时期它们间密切的合作和交流。首先,体现在出版物的信息交流上。图书馆和出版界的相关刊物通常会分别介绍对方的信息。在图书馆出版的刊物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为各书店刊登的广告和出版新书的介绍。例如,1935年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的《图书展望》为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开明书店对各图书馆六折优惠、儿童书局对学校六折特售等打广告,还设有“新书提要”栏目刊登新书介绍。有的图书馆期刊还开辟了“图书馆与出版界”的栏目,刊登出版方面的文章,如《中国出版事业之统计的观察》《一九三六年中国出版事业的回顾》等。还有些期刊每期设置专栏公布出版界的消息,如《图书展望》的“出版琐闻”栏目,《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的“出版界消息”“国内外出版界珍闻”等栏目。而在出版界的刊物中,也可以看到图书馆学文章。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刊登了俞爽迷的《中国图书馆漫谈》和马宗荣的《怎样研究图书馆学》等文章。甚至还出现图书馆为增强出版界和各界的联系、介绍和宣传书籍而创办的刊物,如浙江流通图书馆发行的《中国出版月刊》,在发刊词中明确该刊的目的和责任:“做读者和出版界的连锁,做全国图书馆图书部的顾问,做全国出版物的陶冶者、整理者、广扩台。”[36]内容既有图书馆学方面的研究,又有对图书、杂志的介绍和推荐。
其次,图书馆和出版界也增强了专业交流和合作。较为突出的是在翻印大部古书这方面,因为珍本、孤本类的古书大都收藏在图书馆之中,这就需要出版社和图书馆进行合作。例如,前面提到的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另外,中华书局在筹备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的过程中,就曾向浙江省立图书馆商借所需古书,后赠送该馆《图书集成》《四部备要》各一部。商务印书馆也将从浙江省立图书馆商借的馆藏宋刻本《名臣碑传琬琰集》,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之中。而浙江省立图书馆则邀请商务印书馆前编译所所长何炳松作了《今后中国出版业之趋势》的演讲。可见,当时图书馆和出版界之间,通过影印大部丛书,增进了交流和合作。
图书馆不仅在丛书的出版上贡献了力量,在丛书的销售上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图书出版中大部丛书占的比例较大,但因价格昂贵,其销售对象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各类图书馆。时人陈豪楚在《谈图书馆所需要的书》一文中就提到,当时《四部丛刊》和《古今图书集成》定价都为八百元,“这样的价格,实在是超出了一般人购置力,于是只有图书馆来为民众购置”[37]。当时的福建省、浙江省、云南省、上海市、北平市等行政部门纷纷发布训令,要求各级学校和民众教育馆、图书馆酌量采购《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丛书,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必备某一类丛书。例如,福建省教育机关鉴于“各县图书设备远不及省市,多数有图书馆之名无图书馆之实”[38],要求各县立图书馆最小限度购置《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各一部。毫无疑问,各类学校、图书馆购买大部丛书和新书籍,对于出版界能够大量出版新书是极大的支持,促进了书籍出版在数量上的繁荣。反过来,新书的出版、针对图书馆购书给予的专门折扣等,又使图书馆的藏书更加丰富。正如王云五所说:无论是丛书的编印还是新书的出版,除商务印书馆外,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生活及法学编译社等,“对于补充图书馆用书一事,都曾做相当的努力”[33]。
但对于购买哪一类的丛书更适合,有的学校似乎并没有理性的认识。如河北省省立天津中学购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两浙盐务中学购买《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琼海中学购买《四库全书》等等,其实这些并不适合学生们阅读,花费大几百甚至上千的经费购置一些不适合学生阅读的大部古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而这并非个例,从当时国民政府的提倡甚至要求来看,有很多图书馆尤其是中小学图书馆都购买了这些大部的古书。至于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处发布公文所称的“倘此书(《四部备要》)分布全国,行见国学盛行,国粹保存,文化复兴,民族复盛”[39],更是不切实际的怂恿。每个图书馆即使都藏有不适合学生们阅读需要的《四部备要》,这不仅在经费上是一种浪费,而且对文化、民族的复兴也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出版界、阅读风气、图书馆三者紧密相连。在当时的文化建设中,为了“造成全国好学风气,及提高人民文化水平”,1935年4月1日中华文化建设协会特发起为期半年的全国读书竞进会。在4月8日至4月22日之间,还举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读书运动大会”进行宣传,全国各图书馆和出版界都积极参与其中。例如,浙江省立图书馆就积极响应杭州市读书运动周的举办,不仅参与商定读书运动的办法,更是在运动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读书运动中图书展览一项就由浙江省立图书馆负责,使人们有机会饱览馆藏精品,“每日参观人数,颇为踊跃”[40],并主动邀请知名学者展开如何读书等问题的演讲。此外,为了推进教育文化,考虑到省内其他图书馆规模不足,浙江省立图书馆特举办“省内通讯借书及市内递送借书”服务。读者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依据有关流程,就可以借到想看书籍,这样一来就便利了全省各地读者的借阅,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也积极响应北平举办的读书运动宣传周,公开举行为期一周的图书展览[41]。上海市立图书馆同样积极支持读书运动,购买书籍两千余种,除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珍本》《二十五史》这些大部书籍外,还有文艺小说和自然科学等书籍。为了方便市民阅读,还创办“巡回文库”,配备两台巡回车载百余种书籍,主要为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人们提供免费阅读[42]。天津市立通俗图书馆劝市民加入读书竞进会,因活动能使失学青年及经济困难的民众,均能得到读书乐趣,所以每日对来馆的民众讲解读书竞进会的意义,鼓励他们加入读书竞进会,以养成良好学风[43]。全国十五家出版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等也积极赞助读书运动,在大会期间专版书籍一律五折销售。另外,报刊杂志、各地分会及教育机关亦踊跃参与,推广读书运动。报纸纷纷转载读书运动大会开幕词和简章,大力宣传读书运动大会。《文化建设月刊》《学校生活》《现代出版界》《申报》等刊物设置专门的读书运动专栏,邀请专家学者介绍不同专业的读书方法、经验,讨论读书的意义以及读书运动和文化建设的关系等。
在举办全国性读书运动的文化环境下,图书馆事业获得了发展。正如陈训慈所说:“最近中国图书馆事业之所以有相当的进步,整部钜籍之出版,读书运动的提倡,以及学校教育的进步,也多是促成的因素。”[44]“大抵二十四年一年中,国内图书馆继承前绪各方面皆有实质的进步。盖学校教育与一般事业之进步,既足为促进图书馆事业之因素;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于去年倡为读书运动,亦为推进图书馆效能之一有力刺激焉。”[19]出版业也需要借助读书运动的契机改变不景气的现状,正如时人为解决出版事业惨败问题建议:“急宜普及平民识字运动,在最近期间肃清文盲。各地负责指导文化的机关,应从速组织读书竞赛会,鼓励青年读书的兴趣。全国公私图书馆,应规定经费,充实内容,领导各地的读书运动。”[45]全国读书运动的氛围引发了时人的读书兴趣,半折的书籍也利于图书馆和人们购买,对出版业也是益事。由此,文化建设协会之后的一系列读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既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又缓解了出版业之颓势。
但脱离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的读书运动,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仍未获得深远影响。这一时期,图书馆数量的增加、出版书籍数量的突飞猛进,都难掩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事实。在救亡成为当时最大任务的时候,读书必然要和救亡问题联系起来。而出版书籍的出版界和提供读书场所的图书馆,应以促进抗敌救亡、民族独立为己任。正如时人所言:“民族国家到了存亡关头,救亡的呼声已普遍全国上下,出版界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中,就应该特别负起时代前驱者的责任:介绍国防和建设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宣扬举国一致的精神,团结御侮。”[46]当时的出版界以营利和为国民政府服务为主,对救亡的重视程度不足。而关于图书馆的藏书,有人则叙述到:“凡是我们青年真正需要的书籍,是完全看不到的。凡是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及抗敌御侮的理论书籍、实际行动的书籍更是完全不备。”[47]可见当时图书馆对于救亡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图书馆负有保存文化的责任,更应有增进民智、为民众提供救亡所需知识的使命,要以实际的行动为民族的解放作贡献。例如,《量才流通图书馆馆刊》刊登有关救亡的文章,提倡青年将读书与目前的救亡问题联系起来,呼吁青年人将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出路相结合[48-49]。到了全面抗战初期,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还开设了抗战读物阅览室[50]。
4 结语
综而观之,从1935年、1936年图书馆的发展来看,图书馆事业在这两年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鼎盛。同时,出版界在农村经济破产、自身发展不景气的势头下,也迎来了表面的繁荣。之所以有如此发展之状况,与国民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提倡国民教育,对民众教育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图书馆得到了发展;为民众教育提供所需书籍、报刊等的出版行业自然也得到了数量上的明显增长。图书馆和出版界也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和合作。但是,文化上的复古现象愈演愈烈,出版界喊着流传古籍、发扬文化的口号,实际是为了营利。出版事业真正的繁盛应该是各种类型书籍、报刊都能得到均衡发展,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之所以出现以某一种或者某一类书命名的“杂志年”“古书年”,都与出版业追求利益相关,书店唯一的出路就是追随潮流出书以维持经营。樊仲云就直言:“就出版界言,翻印古书与编译教科用书,在营利主义上,诚不失为有利的方法,但是讲到提高文化水准,即出版家对文化界的任务,究竟是无意义的事。”[51]在古书的翻印成为潮流时,大部类的古书、一般的古书都得以畅销。而大部古书对于普通识字民众和中小学生意义不大,面向普通大众的图书馆大量购置的这些古书,只会成为图书馆的摆设。“什么珍本、集成、几十几十史之类伟大的出版物,普通的读者是没有那样的经济能力与富裕的时间去采索那些金窖银藏。那些是图书馆装门面的东西,收藏者或者学者用来自己欣赏的。”[52]而一般的古书,多是小说笔记类的,如果图书馆购买此种书籍,那就只是供人消遣而不是传授知识了,也不利于良好阅读风气的养成。在此种文化复古的氛围中,图书馆的数量和藏书量以及出版界的出版量,虽然都获得了增长,但是否真正对大众教育起积极作用存在很大疑问。在民族危亡之际,图书馆和出版界都成了国民政府进行思想专制的工具,为错误的文化政策服务,这些都是在表面繁荣中所展现出来的弊病。
国民政府当时内外矛盾突出,国民经济受到重创,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物价的上涨及经费的不足,都使得出版业表面的繁荣收效甚微。例如,1934年的杂志销量比较可观,出现《东方》《申报月刊》《新生》等杂志销量在数万份以上的情形,销量两千份的杂志就更多了。而到了1935年,“杂志年”明显就过去了。当时上海的定期刊物平均每天不足十种。定期刊物的销量也从平均三千份,减少到一千五百份[53]。那些专门出版定期刊物的出版商不得不另谋出路。在新书出版方面,古书翻印潮流使得除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几家大的书店出版新书外,其他书店基本上没有多少新书出版,这也是前面三家书店出书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原因。而其他书店的日子并不好过,北新书局艰难度日,开明书店举债,世界书局穷困,大东书局不能维持,这些都是出版界艰难度日的表现。图书馆界则面临着购书经费不足的问题。1936年上海全市图书馆共229所,购书共计18.8万余册,平均每馆约823册。购书经费共计30.6万元,其中商务图书馆有5万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有3.5万元[54]。这样算下来,上海市其余图书馆平均购书经费不足1千元。同年,浙江省全省公私图书馆322所,购书共计18.8万余册,平均每馆约583册。购书经费44.1万元[55]。这样算下来,包括省立图书馆等大的图书馆在内,每馆平均购书经费约1 366元。当时政府还明令或倡导图书馆、学校购买大部丛书,1千元的购书经费在购买一部《万有文库》后就所剩不多了,而且这只是平均的购书经费。如果将占较大份额的省立图书馆和市立图书馆除外,那其他馆的购书经费更加紧张。杂志销量锐减、大部分书店举步维艰、图书价格混乱、图书馆购书经费不足,这些问题暴露了表面繁荣下出版界和图书馆事业的种种危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表面的繁荣也遭到阻断,发展趋势自然也就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