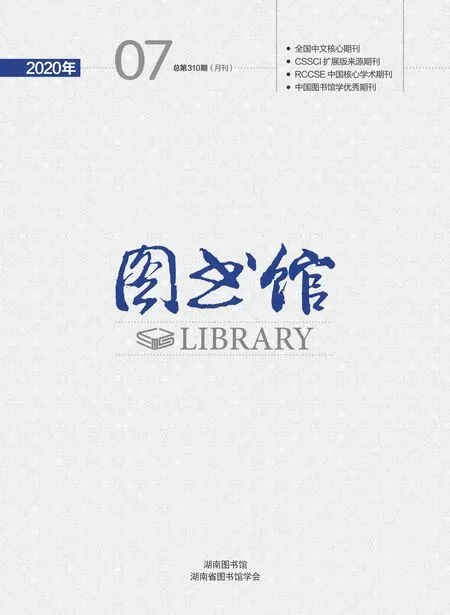目录学的方向走错了
王子舟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目录学成“没落学”了——这是十年前某次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上一位学者发出的哀叹。近二十年来,许多图书馆学专业将《目录学概论》从专业核心课调整为选修课,开设目录学课的图书馆学专业也越来越少,目录学正在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逐步被边缘化。图书馆学中从事目录学的研究者也纷纷转向其他学术领域[1]。在连年举办的中图学会年会上,目录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分会场,其会议主题与目录学关联越来越弱。更有学者感叹:“如今写一篇目录学的文章,想寻求一家专业的刊物发表竟然都找不到,即便与目录学相近的图书信息之类的刊物,也很少设置目录学栏目,就是说目录学在当今几乎没有了存在的现实或者空间。”[2]
1 目录学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目录学走向没落,我认为有两大主要原因:一个是外因,即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书目工具有替代性;另一个是内因,即目录学研究者走错了方向,背离了传统学术的合理轨辙。
先说外因的替代性。当新事物能够取代旧事物的时候,替代就发生了,旧事物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情况在技术领域里尤为明显,如电灯取代蜡烛,数码相机取代胶卷相机。当新事物只能替代旧事物部分职能时,旧事物可能会受挤压而被边缘化,而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成分,就有可能顽强地支撑旧事物长期存在,如电视对广播的替代、西医对中医的替代就是如此。出租车司机开车要听广播,广播电台通过办交通热线、心理咨询、子夜倾诉等做市场细分,坚持活了下来。我们的图书馆正在被网络、微信等部分取代。如果网络能够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即读者能在网上随意浏览新书、看新电影、查找资料,那么图书馆就要关张了。图书馆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要增加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或称核心竞争力)。中医的发展也是这样,图书馆学专业的发展(包括目录学的发展)也应如是。
目录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书目工具。古代图书馆藏书书目经过编辑,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面貌进入正史,既体现出中国史书在保存社会记忆时,重视保存精神文化记忆,也表明其有“以文化人”的实用目的。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之所以成为治学之门径,广受天下学人看重,主要原因是在图书馆不发达的时代里,读书人读书、学者治学需要有指引,以便能按图索骥,通过借、抄、购的方式阅读所求文献。所以随着《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彰显大用,目录学也渐渐成为显学,从校雠学中脱颖而出变为取代校雠学的概念(校雠学、文献学等概念则退立到了灯火阑珊处),甚至一度撷取了学术王冠的地位。进入近代,随着新式图书馆普遍设立,馆藏目录普遍使用,人们查阅书籍方便了,《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书目因有了替代产品,其需求有所减弱。目录学在以西方新学为主体的现代学术体系中,被归入了图书馆学并成为其核心知识内容之一。尽管目录学研究者中一直有人认为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是并列学科,但从科学建制的角度看,目录学还是从属于图书馆学的。目录学在林立的现代科学中,失去了身上的诸多光环,已不再鹤立鸡群。进入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全文检索数据库等强大的查询、检索功能,成为了人们贴心的知识助手,大量的书目工具被替代出局,目录学也就逐渐走向式微。
随着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古代书目工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宗旨也开始有了替代物。进入现代教育分科教学以及学者们分科治学的阶段,科学分类、学科分类通行,各科学术都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内容体系,这就对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起到了替代作用,而每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学术史、研究综述,这也对目录学的“考镜源流”起到了弱化作用[3]。
再说走错方向的内因。外因我们不能左右、掌控,但是内因却可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掌控好自己的方向,在行进路上离开了正途。目录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形态是书目工具。换言之,目录学的任务就是编制出适用的书目,做学子案头无声的老师。我们研究古代的目录学思想、方法等,都是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知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为载体,来探讨古代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宗旨,也是在对这些书目进行一番研究后提炼出来的。因此,研究目录学,就要继承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结合现代科学方法,编制出更为先进、适用的书目工具。民国时期柳诒徵先生主持编纂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1949年后顾廷龙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等,还算这一路径之余绪。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作为目录学研究的专业领域,即图书馆学专业里的目录学研究,却偏离了这个方向。学院派的目录学研究者,放弃了书目工具编制,而埋头于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史两个方向,在这方面出版了不少教材、论著。而书目工具编撰实践,只有部分图书馆工作者还在做。目录学本质上属于经验之学,其精髓全部来源于观念与方法的创新,而且只有体现新观念、新方法的书目工具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目录学的价值才能彰显出来。目录学是工具之学,仅靠目录学研究论著、目录学史教材那是提振不起目录学的。专注于目录学理论方法、目录学史研究而放弃书目编制实践,即背离了目录学学术传统的正途而走入偏径。
在这一点上,顾廷龙先生可谓颇具慧眼。1984年王重民先生遗作《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出版时,其夫人刘脩业请顾廷龙先生写个跋。顾廷龙先生在跋中写道:“君夙主‘从事目录学史研究,不可忽视书目工作实践。’其言最为深切,盖实践多,则体会深。研究目录学而不事深入实践者,是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古人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君之学皆从实践中来,诚足以信今而传后也。”[4]王重民先生从事目录学研究,曾编出《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敦煌古籍叙录》等,他的目录学研究与书目工作实践互为里表,这与顾廷龙先生体会是一致的,因此顾先生才有如此言论。当时学院派的目录学研究者乃至图书馆学者,多不注重实践,不重视开发新的书目工具。他们的文章写得漂亮,理论分析、新鲜术语纯熟,但缺书目编制实践,无有力的书目工具问世。这对目录学的发展来说,于世不济、于事无补。尤为可惜的是,顾先生对目录学研究的批评,即他对目录学“踩”的这一脚,并未引起学院派的足够重视。学院派仍在偏径中行进,越走越远。中国目录学的大本营在学院派的图书馆学专业里(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分支)[5],大本营行军所犯的方向性错误,最终导致目录学集体走偏。
试想一下,若无《汉志》《隋志》《总目》等系列书目工具,安有目录之学?若无体现中国人文传统的书目工具,安有中国之目录学?治目录学者当深思矣!假设当今目录学借助网络技术生产出来一批知识检索、评价工具,并广为天下学者们使用,那么目录学岂不就是另外一种繁荣景象了吗?
笔者想起过去学习目录学课程的过程,至今仍有切肤之感: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史学了不少,目录编纂方法却不懂。为什么不讲授编纂方法,让学生动手编制书目呢?图书馆学有诸多课程存在知识含金量不高问题(这也是其他学科不太瞧得起图书馆学的地方),如《工具书使用法》,内容讲各种书目工具怎么查阅,这怎么会有知识含金量?教师应该讲工具书怎样编制。编制原理、编制方法讲透了,检索使用还用讲吗?编制才有学问,使用有什么学问呢?笔者出版一本书时,曾尝试编了一个书后索引,原来没觉得有什么难,结果一上手,才知道里面的知识、方法有很多,还真不是“小儿科”。
2 目录学真的无用了吗
目录学真的是被替代了吗?真的就没有用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虽然网络搜索引擎、图书馆集成检索、数据库检索工具对书目工具有替代作用,但至少掌握目录学知识还可以了解古代学术分类、学术源流、各类古籍状况、古籍检索方法等。这些年“四库学”在国内搞得热热闹闹,这不也说明《四库全书总目》等古代目录学成果还是很有学术价值吗?
不过,目录学的功用不能停留在研究古代、使用古籍的层面上。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原理、方法、功用应该是古今都适用的。笔者前不久看到一部书目《甲骨文书籍提要》,收录410部甲骨文著作,所收著作按著录、考释、研究、汇集、其他等五类进行排列。“著录”部分收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如《铁云藏龟》《甲骨文合集》等;“考释”部分收释读甲骨文的著作,如《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选注》等;“研究”部分收录利用甲骨文进行研究的著作,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等;“汇集”部分收录有关甲骨文的工具书,包括字书、诗联、目录、索引、年表等;“其他”部分收录不易入上述四部分的著作,如《安阳发掘报告》《罗振玉评传》等。该书的提要不仅撮述书之内容,还能述其学术贡献、书评文章、参考价值。此种提要编写法继承了目录学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令人赞叹、佩服,对其他学科编撰当代学术著作书目提要也有借鉴意义[6]。
笔者再以亲身体验为案例来讲一下目录学的用处。我平时读书颇杂,也爱做读书笔记,看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中有关图书馆学的内容就记下来。后来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在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编一个《图书馆学关联书录》。该书目收录的图书,悉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图书馆学”(G250)类以外类别中的著作。内容分历史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三大部分,简以“史、论、法”称之。三大部类下再分一级、二级类目。所有书录都分别依类归属,凡涉及图书馆学的资料,可以排入相关的类目里。现举两条书录为例。
示例1:先秦图书史
[汉]许慎.说文解字[M].[宋]徐铉,校定.影印清陈昌治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索书号:H161/55b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编成《说文解字》初稿,后与刘珍、马融等在东观校书中继续潜心完善,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由其子许冲上奏于朝廷。该书共十五卷,收9 353字、重文(异体字)1 163个,共10 516个字,为汉字建立了540个部首,释字时先列小篆写法,讲本义,再讲字形、字音,如“简,简牃也,从竹,间声”;有时还有描写和叙述,如“册,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行,凡册之属皆从册”;“典,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讲字的本义,有助于阅读和理解先秦古籍的用字,而分出部首则奠定了后世字典、辞书的编纂范式。《说文解字》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文字学、字典学的正式成立。我们通过该书中大量有关书籍的字词,可了解上古文献的称谓以及形态。
示例2:文献学理论
[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脚注趣史[M].张弢,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索书号: B5/227
不知在版编目数据为什么要将本书分入“B5”(欧洲哲学)类。作者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对书籍与阅读历史有较深研究。他在此书中探讨了脚注的产生与流变,说明脚注的普遍使用不仅能扩展读者的阅读,还丰富了文本表达方式。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脚注这种注释文字的使用,还将作为艺术的历史学与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区分开来(233页),脚注提供了陈述来自可识别史料的一种保障(234页),以加强文本内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脚注从兰克时代发展至今,已演变为标准学术规范、博大精深学问的一种徽章了。不过,也有批评家不喜欢脚注,极端者如英国的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他将被迫去阅读脚注比喻为中断性爱而下楼去给别人开门(92页)。本书原书名为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1999年)。
我编纂《图书馆学关联书录》的初衷,其实就是想复活中国古代目录学“互著”“别裁”的观念、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整体,研究内容甚至研究方法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有些对图书馆学有用的珍贵资料,即章学诚所谓“书之相资者”,常常隐藏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类别的某些著作里面,所谓“玉隐石间,珠匿鱼腹”,不易见到。在平时阅读中,我每遇到这些资料,便随手将其搜寻出来,再将其分类排比罗列,就形成了能为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研究者扩大阅读提供参考的关联书目。我给本科生上“图书馆学概论”课,多年来布置的课中作业之一,就是让学生编制本专业的关联书目。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的学生,分别从其他专业书籍里,找到与本专业关联的书来做关联书目。我勉励同学:坚持数年,必有收获。
这两年出现了大数据概念、大数据专业,我觉得大数据研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数据本身,而在于数据之间发生关联,产生流动。还有数字人文的研究,如能汲取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互著”“别裁”等观念、方法,也会有所收获。
目录学是有用的。但是要使传统的目录学发挥新的作用,老树开新枝,一个前提就是要弄清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学术精髓究竟是什么。
3 怎样继承目录学传统精髓
我先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不辨学术传统则无益学术发展。前不久笔者撰写了一篇小文,给2015版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提修订意见[7],文中说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在责任者项中取消国别、朝代,取消著作方式的做法是不对的。标注责任者国籍、朝代,标注图书的著作方式(如编、编著、注释、口述等),无论在文史研究领域、图书馆学界、书刊编辑学界,均为文献著录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特色,受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作者、读者的普遍认可。因此希望今后在修订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时,保留这一著录传统。我在文中还提到,“卷”“册”不分,都放在题名项作为附加成分著录,这也是错的。“卷”是内容结构单位,类似后世的“章”,是作者厘定的,故应随题名项著录,这是中国文献传统自身的特点,应该予以尊重继承;但“册”是页数容量扩张而衍生出的单位,出于装印者之手,在著录时应该与页码等联系起来。换言之,卷、篇等内容划分单位应在题名项里详细揭示,而书籍的册、页等形式上的信息单位,则应统一放在出版年后面的页码位置。此虽微不足道,也反映出作为国家标准的著录规则若忽略了中国的人文传统,一样会伤及其自身发展的科学性、实用性。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制定体现科学性要求是对的,但它不仅应该追求科学性方向,还应追求人文性方向。体现人文性就是要体现中国传统文献揭示活动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而找到这个优良传统,我们要下一番“考镜源流”的功夫才行,因为引用文献的方法,是在经验积累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那么中国目录学的传统精髓是什么呢?或问中国书目编制的学术宗旨是什么呢?广为学界所认可的就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8]。这是公认的目录学核心价值,前人之述备矣。高校图书馆学硕、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经常会出题让考生解释这两句话的含义。依我的理解,“辨章学术”是指厘清一种学术或文本的性质、特征及其在学术体系中的位置,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空间上、静态上的理解;“考镜源流”是指察明一种学术或文本是怎样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现状如何等,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时间上、动态上的理解。一横一纵,动静结合,就将目录学追求的本质特征表达出来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照的是文本内容、学术体系,强调的是对象的内在性而非外在性,表现出中国目录学在内容与形式之间更青睐内容,即“道”先“器”后。文本的形制、数量、编号、排序等命题,相比之下不是特别需要重视的,这是和西方目录学有差别的。
中国的目录学与西方的目录学都重视实用,但学术旨趣有别。西方目录学的科学性强人文性弱,而中国目录学的人文性强科学性弱。这与整个中西方学术的特点也相似,即西学的精神偏于求真,中学的精神偏于求善。西学重事实真相、逻辑思维,能够穷微极化;中学则重社会关系、道德修养,力求中庸和合。余英时先生尝言:中国学术秉持的是道德传统,如孔子把“仁”放在“知”前面,且重视实用性;而西方秉持的是知性传统[9]。钱穆先生甚至曾说:中国人天性是和合性大于分别性,西方人天性是分别性大于和合性。中国人看重人际关系,重人伦、讲仁义,体现和合性(西方人的人权讲的是分别性);版图演变总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也是讲究和合性;文史哲相通,也表现为和合性;甚至“中国菜是一种和合味,而西洋菜则多是一种分别味”(指中国菜放的作料多)[10]。目录学的特质,学界研究也有这方面的揭橥,如傅荣贤指出西方目录学有客观知识的取向,注重事实,旨在解决是非,是实证的(positive)目录学;中国目录学注重价值观念和道德,旨在回应应该或不应该,是规范的(normative)目录学[11]。总体说来,中国目录学偏重通过叙录对文本内容进行揭示,强调文本价值和传承,走的是人文主义路径;而西方目录学偏重通过编目对文本形式进行揭示,强调文本秩序和传播,走的是科学主义的路径。
当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概括中国目录学的宗旨,这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如作为目录学的价值所在,虽然精辟,但有未尽之感。目录学家汪辟疆在总结传统目录学的特点时说: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为目录家之目录;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为史家之目录;主张鉴别旧椠校雠异同者,为藏书家之目录;主张提要钩元治学涉径者,为读书家之目录[12]。目录家尚且可以划分数类,目录学精髓也可以细辨,如此方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目录学的传统特色有哪些。
仅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除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甄别知识的价值,即批评功能也是十分显著的。如子部小说家中收明人高拱的《病榻遗言》二卷,提要言:“是编备述与张居正先后构隙之端,一曰顾命纪事,二曰矛盾原由,三曰毒害深谋。以史考之,亦不尽实录。”[13]1221因其“不尽实录”,四库馆臣将该书入了“小说家”类。又如集部别集收明人陈绍儒的《大司空遗稿》十卷,提要言“其文有意刻画韩柳,而往往失之粗率。诗则音调谐美,亦学唐格而过于摹拟者也。”[13]1592再如,集部总集中所收《成都文类》五十卷,是有关成都地区诗文的一部总集,凡一千篇有奇,分为十有一门。提要点评道:“每类之中,又各有子目,颇伤繁碎。然《昭明文选》已创是例,宋人编杜甫、苏轼诗,亦往往如斯。当时风尚使然,不足怪也。以周复俊《全蜀艺文志》校之,所载不免於挂漏。然创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视之。且使先无此书,则逸篇遗什,复俊必有不能尽考者。其蒐辑之功,亦何可尽没乎?”[13]1699其中“创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一句,实为精当之语。
除了学术批评,《四库全书总目》还特别注重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关系,如觉得有益于扩展参考者,则以案语、参见等表达方式予以揭示。如在史部传记类《素王记事》一书,提要言此书“摭拾《阙里志》为之,亦茫然无绪。盖当时书帕之本,本不以著书为事者也”。因句中有“书帕本”一词,为明其义,该句下即加一条案语:“案顾炎武《日知录》曰:昔时人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谓之书帕。又曰:历官任满则必刻一书以充馈遗,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陆深《金台纪闻》亦称有司刻书,只以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今藏书家以书帕本为最下,盖由於此。”[13]532。又,《总目》将经史笺释之作,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如《史记疑问》附《史记》后,《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以便相互参考。一人著作两收或多收,会在提要里提及,以建立关联关系。如宋人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诗》九十一卷,提要中特别说明“迈有《容斋随笔》,已著录。”[13]1697再如洪迈《经子法语》二十四卷,提要里说明“迈有《史记法语》,已著录。”[13]1116等等。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除了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宗旨外,它还有“褒贬得失,缀联相关”的人文关怀、学术价值在里面。黄侃先生说过:“目录之学,一撮旨意,二定是非,三辩真伪,四考存亡。”[14]黄侃先生也是力求以简约的方式,来阐述中国目录学的传统精髓。以我的理解,综而言之,中国目录学的传统精髓至少应含括以下几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识断真伪,记录存亡;褒贬得失,缀联相关。”其中“褒贬得失”包含了黄侃先生所谓的“定是非”,“缀联相关”包含了“互著”“别裁”方法。当然,这些传统精髓中的要素,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陟黜,如书目对现代图书“记录存亡”的已经很少了,我们可以代之以“记录藏址”。又如书目不具备“褒贬得失”的批评功能,就会被书评取代,分化出书评学。金恩晖先生曾力主书评归图书馆学研究范畴[15],遗憾的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总之,窃以为当代的目录学只有把握住中国目录学的精髓,同时吸收西方目录学之优点,并能运用于书目工具的编制,才能焕发其独有之风采。“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以往目录学研究在理论上不断追逐前沿、热点的行军速度,可以缓一缓、煞一煞了。改革开放以来,目录学的新理论、新概念增加了不少,新的前沿领域也开辟了不少,但是文本和学术的性质、良莠如何甄别,知识与知识的关联怎样搭建,知识发现的路径如何选择等,已经没有一本目录学教材能够深入讲解了。目录学一旦没有了故乡,就会如同一个流离失所、满面茫然的人,它衰落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