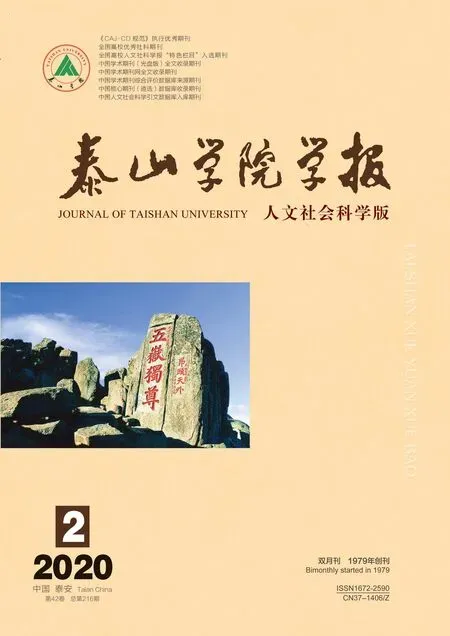以文觉世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民众动员
——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为例
张道奎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前言
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动员民众的政治力量,促进民众的觉醒是戊戌维新以来最具时代特色的历史动向之一,而引领近代中国历史潮流的往往是那些时代使命感最强烈的知识分子。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再到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虽然成败兴衰不同,道路方法各异,但他们都敏感地意识到了国家的问题,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他们进行理论创新和救亡图存的努力,就是把理论运用到社会变革实践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由个别先知先觉人物的宣传鼓动,到一些人的响应追随,再到广泛传播、产生行动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理论创造者—宣传者—受众的宣传梯队。在戊戌维新中康有为是创造者,梁启超、陈千秋、王觉任、韩文举、麦孟华、徐勤、何树龄等人追随响应,及至公车上书、创办《时务报》、组织强学会,变法维新思想于是蔚为大观。在革命活动中,孙中山为主要倡导者,黄兴、汪精卫、胡汉民、宋教仁等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进一步联络团结华侨、留学生、会党、新军,逐渐壮大革命的势力,所以吴稚晖评论说“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1]正是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才有武昌起义和革命风潮的席卷全国。这一运动过程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中也有迹可寻,首倡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逐渐汇聚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高一涵等青年学生,进行写作实践和广泛的新文化宣传,新文化新文学的主张于是迅速扩张到全国,扩大到广大青年学生和市民阶层中。毛泽东也曾指示全党,“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所以,尽管中共的革命实践更为复杂,但大致上也存在这么一个民众过程。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在上述具体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再扩大一点,就会发现,近代中国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时间跨度更长、影响更为深远的民众动员过程,或者说是民众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救亡的直接刺激下对时局的不断回应,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救亡的时代需要。这一民众动员过程真正开始于康梁的维新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展示了它的巨大力量,至文革而走上极端状态,横跨了中国近代史中政局变化最为剧烈的30年。清帝国上层的儒生首先具有了危机意识,由他们把这个危机意识扩张到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一般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救亡图存的思潮,这个思潮又扩大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参与中。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取向和政治斗争,从国家层面来看,这一过程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要求,符合现代国家重建的时代任务。直至今天,这种较为彻底的社会动员与国家管理,仍是我们巨大的政治财富。
二、梁启超新史学的救亡鼓动
近代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从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开始,通过维新运动时期的探索思考,逐步从西方学来“议院”这一新式武器,逐渐意识到民众参与的力量,继而在探索新的国家制度的维新运动中鼓吹“开民智”对中国政治的重要性。然而维新运动具有脆弱性,不仅在于主张提出的仓促与不成熟,还在于他们实际上处于向上向下都无所依靠的孤立处境——向上的官僚集团听命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皇室和地方督抚,向下的下层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此时尚未有足够的参与意识,仍处在“蛰伏”状态。这一时期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基本上处在一种盲目状态,作为这一时期民众政治意识的表现,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下层民众对自身境遇的一种抗争,无论是斗争目标还是运动方式,都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政治重建价值。“这两次叛乱(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均显示出极端分子的潜在势力,不过都未能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就终止了。它们失败了,不仅因为反对的力量更强大,而且因为叛乱的领袖们(徒众就更谈不上)没有新秩序的明确规划。农村强烈不满所孕育的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类型的领导下变为现实。”[3]
当清政府的自救运动失败,列强侵略逐步加深,国内局势持续恶化的时候,扮演着“先知先觉”角色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社会探索一条新式国家道路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民众参与所能形成的强大力量。尽管在维新运动时期“民主”还不被士大夫们认可,开民智、兴民权、行议院还没受到普遍重视,但维新派梁启超等人开时代之先声的鼓与呼,使“群治”观念从严复等少数士大夫的著作里走向更多的知识分子心中。维新运动中的宣传,让知识分子进一步意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即“开民智”的重要性。维新派对普通民众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他们对知识分子救亡意识的激励,对“民”与“群”的宣传,预示着一条新的历史动向。
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各省举人和中央大员身上,维新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这些人,这从强学会会员和《时务报》《知新报》的读者群中清晰可见。以北京强学会为例,列名会籍者主要有:陈炽(户部郎中)、沈曾植(刑部郎中)、文廷式(翰林学士)、杨锐(内阁中书)、张权(主事,张之洞之子)、张孝谦(翰林编修)、袁世凯、徐世昌等,明确支持学会的则有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之洞、刘坤一、聂士成、李提摩太等。[4]很显然,康有为的联络目标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僚,这在启蒙对象上具有局限性。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守旧思想过于强大,放弃了早期坚持的开民智、设议院的主张,这是维新运动思想主张的局限性。
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的思路比较开阔,在思想上和启蒙对象上都比维新运动时期更近一步。这一时期梁启超虽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革命,但在新史学的提倡上还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一方面倡导“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的“三界革命”,另一方面又鼓吹“史界革命”,提倡新史学,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一年(1902年)他创办《新民丛报》,而且写下了几篇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字,像《论国家思想》《新民说》的一部分、《新史学》等。这些文章应该被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大多关心两个问题:‘国家’及‘国民’。”[5]具有家国情怀救亡意识的梁启超一生都怀有极大的政治热情,即使在政治生命终结以后以学术为事业,仍“以史论为政论”[6]。梁启超作为维新老将,“言论界的骄子”[7]而提倡新史学,对史界革命的论述是颇有开时代之先的领军意味的。今日学者在讨论中国的新史学时,大都把梁启超放在首位。梁启超认为旧史学的六弊三恶是史界革命的原因,而他把眼光聚焦于史学的动因则是“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8]然而史学现状却是“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9]这段话可以视作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启蒙民智的初心。
经维新运动思想的洗礼,在西学东渐思潮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在此时不约而同地主张新史学。20世纪初,有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夏曾佑、马叙伦等先后倡导史学革新,“以满足人们从历史上探讨西方之所以强盛和中国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寻找富国强兵之道。”[10]新史学试图克服旧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弊端,以平易晓畅的语言,进化的史观,世界的眼光,科学的态度重新叙述中国的历史。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近代中国,新史学作者们对民众爱国心和自信心的培养愈加重视。新史学后继者张荫麟在自序中介绍做《中国史纲》的目:“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11]钱穆在《国史大纲》自序中则更明确指出为时局而作。此时新史学面向群众的写作指向已从梁启超等人的设想落实到了实际中。新史学面向普通民众,描写普通民众的斗争史、社会史以激发民众的历史认同和爱国情结的发展方向,最终形成了救亡图强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
三、胡适白话文学的启蒙工具意义
维新运动期间及之后,梁启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12]的文章不胫而走,影响渐及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外的一般知识分子。“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时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13]这从侧面说明了在维新运动前后梁启超文章的流行范围。这一时期梁启超等政论家的言论传播范围仍然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言论和思想难以在普通民众中间扩展。而文言和俗语的差别,无疑是横亘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获得了政治上的正义性,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提高,“开民智”的平民教育思想得到发展。为了打破文言和俗语之间的鸿沟,民国教育部于1916年设注音字母传习所,1917年成立国语研究会,1919年颁行《国音字典》,同时白话报也得到迅速发展,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渐成合流。新一轮白话文运动热潮大约始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倡议,经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宣传而为知识分子知晓,白话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方面获得了比维新时期更广泛的认可和更强烈的响应。“五四运动的狂潮,打破了中国古旧沉闷的空气,唤起了一般青年对于时代思潮的醒觉。遂由‘爱国运动’扩大而为‘新文化运动’。这种运动的洪涛一时扫荡了全中国,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部分,自是进行尤为猛烈。这时候采用白话文提倡新文学的刊物,好像雨后春笋遍地丛生。”[14]胡适在一演讲文章中一再提及他对白话文学的首倡之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以后白话文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这一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新的意义就在于白话文开始作为一种成熟的表达工具广泛应用,它不再是作为知识精英“开民智”自上而下宣传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了被下层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使用以实现自我表达的可能性。这可能就是胡适所认为的作为一种“有意主张”的白话文学,文学上不再区别“我们”与“他们”的意义[15]。白话文学真正走向普通民众并成为他们自我表达的媒介,具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鲜活的时代特色,也就被赋予了“活的”生命特征。“从今以后,文学成为替民众喊叫,民众替自己喊叫的一种东西。这样的时期,快要来了。”[16]语言工具的革命,为一般知识分子与广大基层群众的紧密结合创造了条件:“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以后,新思想、新观念便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广大的城市读者群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17]
新式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文学革命,与普通民众在话语、思想上的融合便成为可能,阶层间的隔阂被逐渐消除,真正打破“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普通民众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可能,无产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可能。[18]“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要变化,即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力图鼓励并控制这种动员的新的超党派组织所企求的。与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19]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思想武器,白话文成为党动员群众传达指示的宣传工具。
白话文广泛传播的原因,除了知识分子为救民族于危亡的鼓与呼,报刊杂志作为一个产业逐渐发展[20]以外,还与持续动荡且不断恶化的政局密切相关。不断演进的国内外局势是白话文乃至近代一切思想文化运动的最大推动力,它限定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的大方向。
四、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早期发展的十年间(1917—1927)的地位,并不次于梁启超在晚清舆论界的地位。据《陈独秀年谱》的记载,1923年12月16日北京大学做了一次民意测验,1000余人参加了对当下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评选,陈独秀仅次于孙中山排在第二位。[21]正如郑超麟所描述的那样,“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首届总书记。他是中国的不断革命的活的化身,象征着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迅速过程。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22]陈独秀不仅意识到了青年学生在政治探索中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明确的引导青年学生的意识,陈独秀认为,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的觉悟——“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吾人最后之觉悟。”政治的觉悟有三,第一,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的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第二,“出于多数国民自觉与自动”的共和宪政建设。第三,伦理的觉悟,“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23]从民众的觉悟到共产主义的认同有着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但正是陈独秀等人带领着一批苦苦探索中国出路的青年学生,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也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24]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具有经世致用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的拯救中国的新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探索中,陈独秀是重要的领路人。
从维新变法开始,一般知识分子具有了时务概念,战败、割地、赔款、新政、革命、复辟、军阀混战,动荡的局势也培养了普通民众的新闻意识。在乱世之中为性命生计奔波的民众都在思考国家危亡的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但有了新闻意识而又识得文字的民众阅读白话报是可能的。“五四”运动中首先觉悟了的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引导教育下的青年学生,其次是商人、市民、工人。而力量更大,人数更多,革命要求更彻底的农民阶级的动员,则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这主要是由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在革命锻炼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共产党人完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结合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党在工作中也意识到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意义:“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5]此时白话文的运用也更纯熟,党的文件全是用简洁的白话写成,领导人的语言也带有乡土气息。人民战争和民众动员的要求,就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党的文艺工作的目标,“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26]因革命的需要,文艺活动几乎完全服务于民众动员的要求。
五、结语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纯学科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或史学革命是不存在的,学科内在理路的演进在近代动荡的环境中不可能成为推动某一学科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史观派的新史学与史料派的考据史学的兴替是一例,古文与白话文的消长也是一例。普通民众不断被觉醒被动员,是近代中国最鲜明的政治动向之一,它经历了一个从上层官僚精英知识分子到普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沿海大型城市到内陆封闭农村,从市民阶层到工农群众阶层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国人民苦难的深重与抗争,伴随着中国社会不断自我修复与艰难转型。时代感最敏锐的知识分子在每一次巨大转型的历史时刻经常性地充当着“先知觉后知”的领路人角色,从少数先觉者的徒呼奈何,到觉醒了的民众自觉地寻求自我解放的道路,寻求国家富强个人幸福的道路,这是近代中国最深刻最漫长的变革。正是通过先辈知识分子有意识的改造,把中国传统的文学和史学改造成为白话文学和新史学,成为民众自我表达、自我认知、自我教育的工具,这也许是文学革命和史学革命最深刻的意义。通过这些工具,民众具有了自觉的意识,理性的爱国心,责任意识下的自由,这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
现代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完成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文字与思想的融合,消融了阶层间文学层面的隔阂,顺应了“言文合一”的语言发展趋势。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精英与大众的距离也在慢慢扩大,雅俗文化也正在各自不同的群体中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限于时代需要应是以普及为主,但今天优秀文化的再造不应该以知识精英与人民群众相脱离为代价。文明重建需要更精深优质的文化,民众精神追求的提高也需要引导,但是内容的深刻性与形式的平易畅达并非不可并存。知识精英独特语言的形成,语言的再次等级化持续发展,将可能使阶层文化鸿沟再次形成。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在今天,简明流畅活泼生动的语言作为人民群众与社会精英共同使用的语言,无疑在优秀思想文化的社会垂直传播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共同的历史认知更有利于培育整个民族共同的认同感和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