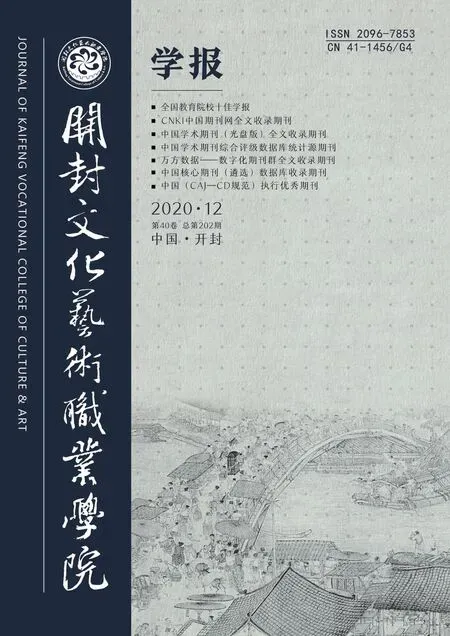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唐 汶
(陇东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也是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家。虽然她认为现代主义小说应该让女性“书写女性”,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义作家很难得到评论家和观众的一致认可。在主流男性叙事权威的压迫下,伍尔夫以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成为获得主流评论界认可的女性作家。随着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典叙事学过度重视形式主义规则的缺陷慢慢显露出来,而女性主义的发展也出现感性有余理性不足的特点,作为经典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女性主义叙事学应运而生。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重点研究叙事形式中所富含的性别意义,探讨性别与意义的联系,强调叙事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引用创新的研究方法,重新划分叙事声音种类,探讨女性社会声音得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学条件,以及作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取向、种族的联系,以经典叙事学为基础,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文本、作者和读者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关联上[1]52。本文探讨在经典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中,作者伍尔夫如何从女性主义出发并结合女性主义的感性特点和经典叙事学的理性特征,以新叙事声音为切入口,通过女性叙事主义建立自己独特的叙事权威。
一、运用叙事技巧,聚焦女性视角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Susan S.Lanser),她在20世纪80年代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2]。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指出伍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而这“并没有消抹掉作者的距离”[1]33。在兰瑟对伍尔夫叙事声音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到灯塔去》中的独特叙事技巧。在文学作品中,自由间接引语是指一种第三人称叙事方式,处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常用来描述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通过自由间接引语叙述者把人物的思想活动与自己的表达结合起来,既带有“间接引语”旁观和客观的特点,又能体现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和对事件的态度。据统计,在《到灯塔去》中,间接引语的使用占总篇幅的44%,其中自由间接引语占多数。伍尔夫将叙述者的声音与角色感受融合,使得叙述者的声音变得自然松弛,也使得她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和女性主义没有那么明显。如书中描写,拉姆齐夫人在镜中看到自己“灰白的头发、憔悴的面容,才五十岁啊,她想道,也许她本来有可能把各种事情安排得好一点”,由此她联想到她的丈夫以及家庭经济等问题,但她“对于自己所作的决定,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后悔,她从不回避困难,也不敷衍赛责……”[3]46。这段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表现出拉姆齐夫人虽出身高贵、谈吐优雅、生活勤勉、态度坚定,但生活中依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全家的经济状况,她的丈夫一事无成,且只想着自己,这都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沮丧和挫败,在50岁竟已满头灰发,面容憔悴。这段叙述表明拉姆齐夫人是个被生活“折磨”的人,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磨平了棱角,使得她在对镜自照时发出如上感叹。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经常还会有反讽和同情的作用。自由间接引语体现的是人物和叙事者共同的声音。因为自由间接引语具有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在叙事者声音和读者声音之间摇摆,会让读者难以判断。《到灯塔去》中第一部分使用自由间接引语较多,如拉姆齐夫人正在给儿子詹姆斯读渔夫和他老婆的故事时拉姆齐先生走了过来,文中写道:“拉姆齐夫人真希望她的丈夫不要选择这样的时刻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为什么他不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去看孩子们玩板球呢?”[3]136通过这种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读者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人物的特征和人物的用词特色,读者甚至可以加入书中人物的意识流动,感受人物的情感思绪和体验。
此外,在《到灯塔去》中,作者还通过内心独白来展示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作为意识流小说中常用的写作手法,通常用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思想和感受。文中对于拉姆齐夫人内心独白的描述非常细致入微,如小说第一部分描写拉姆齐夫人的内心感慨:“我们的幻影,这个你们借以认识我们的外表,简直是幼稚可笑的。”她认为真正的灵魂是处于“在这外表之下”是“一片黑暗,它蔓延伸展,深不可测”。然而,“正是通过那外表,你们看到我们”[3]148。这段独白展现了拉姆齐夫人对生活的深刻认知,即便她身兼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尽心尽力而疲惫不堪。每次她通过思索、独处回归自己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她希望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独立,不被岁月洗刷和打磨,也不被男性权威打压,不为了成就别人而牺牲自己。由此可见,内心独白不仅体现出当时人物的内心活动,也从侧面体现出当时社会的生活画卷。这种叙述特点会让读者感到叙述者的声音藏在人物言语的背后,因此也就有了距离感,也正是这种距离感,使得作者型声音可以藏匿其中。这种伍尔夫作品中特有的女性特质话语也为建立“真实性原则”的作者型声音提供了基础。
二、摆脱视角局限,建构女性写作权威
在《到灯塔去》中,作者型声音被消抹(effacement)在角色的各色情感之后,叙述者独立于故事之外,可以游离于不同的场景获取人物的发言权,不仅可以自己说,而且可以代替人物表达他们的感受。叙述者可以穿梭于不同人物的意识,保持理性和距离感来叙述人物,评论其言行。在阅读中读者会感到叙述者隐藏在人物之后,无处不在,又无所不知。例如,在文中第一部分讨论明天是否可以去看灯塔时,拉姆齐夫人对焦急期盼的儿子詹姆斯说“要是明儿天晴,准让你去”,但她丈夫却斩钉截铁地说“明天晴不了”,体现了成人的理性和孩子的感性之间的冲突。看到孩子失望而焦灼的情绪,拉姆齐夫人又不断地安慰说:“但是说不定明儿会天晴,我想天气会转晴的。”[3]41在这个不断讨论明天天气情况的过程中,叙述者把各种人物活动穿插其中,除了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先生和詹姆斯,还有他们的朋友无神论者塔斯莱对于风向的预测,并穿插人物和场景的转换,如加入拉姆齐夫人邀请塔斯莱先生一起进城办事,两个人一起散步时的交谈和内心活动等。最后场景又再次切换,回到家里的窗边,拉姆齐夫人的丈夫站在那里再次强调说“明天灯塔可去不成了,詹姆斯”。这种叙事技巧将读者不断带入不同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转换的外在场景,展现出伍尔夫女性意识的流动之美,挣脱有限视角限制,引入自己的女性主义视角,通过获得读者认可取得叙事权威。
如同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全知全能型叙述者一样,《到灯塔去》中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一般无所不知的角色,并对所有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中肯的评论。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并没有全篇使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也没有单一角度的叙述。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她采用多角度叙述,叙述者自由穿梭在不同人物的内心活动里,时而进入应邀在拉姆齐家度假的画家莉丽的内心活动,时而又来到詹姆斯的童真世界,时而进入拉姆齐夫人的万千思绪中。这样更能表现叙述者的距离感和权威。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也体现在她追逐这种叙述权威的过程中,她试图消解男性的叙事权威,以女性的视角表现女性内隐的自我,从而成功构建自己的女性写作权威。
结语
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的创作立场与她本人的女权主义者的思想紧密相关。除了主张反抗男权社会的父权制,着力于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和文化霸权外,她并没有使自己的女性主义变得狭隘和固化,只片面追求女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平等权利,而是引入了“双性同体”这一概念。她认为在父权制的社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样痛苦,因此主张追求两性的和谐统一。以此为角度,《到灯塔去》中的叙述者在书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作者的真名实姓[2]。与此同时,她并没有直接暴露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而是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分散在各个人物的话语和言行之中慢慢显露。由此可见,在当时父权社会的压制下,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各样男权的束缚。作为现代文坛新的叙事艺术的先驱和领路人,伍尔夫摆脱了传统文学作品对于时间、地点、人物的限制,注重描述人物意识流动,竭力开创一种蕴含男性思维方式的女性写作方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来捕捉生活细节,通过书中女性人物来观察评论男性人物的言行,书中男性人物不再是高高在上毫无瑕疵的,他们性格中的缺点比如自私和卑鄙的一面也暴露无遗。这是对长期以来男性叙事权威的彻底颠覆,伍尔夫由此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女性叙述权威,体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特点,为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