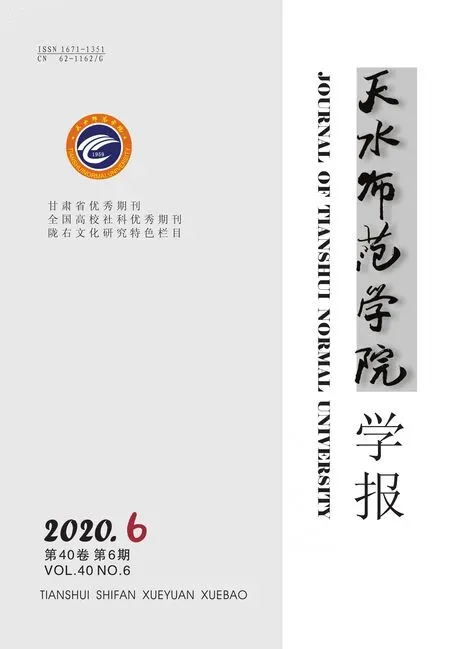陇东南城隍信仰及演剧探究
张维平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一、城隍信仰的起源及发展
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紧密关联,城隍为城市保护神。“隍”的意思是没有水流的护城壕沟、城堑。城隍意义源自上古“八蜡”中的“水庸”之祭。《礼记》中记载天子有祭“坊”与“水庸”之事。“水庸”为八蜡之一,是保护城池的沟壑。城隍是由“水庸”衍化来的,其最初神格是保护城市的水庸神,渐变为城市之守护神。
“水庸”祭祀先秦时期已经存在,但城隍祭祀出现较晚,在诸多护佑城池的城隍神话影响下,城隍信仰逐渐确立。有关城隍的神话最早出现在《北齐书·慕容俨传》中,记载慕容俨得到城隍帮助击退敌兵的事迹。
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欻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约复以铁锁连治,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瑱移军于城北,造栅置营,焚烧坊郭,产业皆尽。约将战士万余人,各持攻具,于城南置营垒,南北合势。俨乃率步骑出城奋击,大破之,擒五百余人。[1]
《广异记》《太平广记》和元代以来碑刻或笔记中也陆续出现城隍故事。“唐以前主要是些名流死后担任城隍、地方官向城隍祈祷晴雨,以及在危难中城隍保护城池的传说。宋以后,城隍神话渐次向多方面发展,其中阴阳表里之公案故事最为百姓所喜闻乐道,似乎地方官应做之事城隍也都在做,由此,城隍终于成了中国自社会上层到底层民众都大受欢迎的神。”[2]城隍祭祀,源于官方祭祀,自上而下,走向一般城市,走向民间,成为城市护佑之神,逐渐形成城隍信仰。
城隍最后衍化为阴间的地方行政长官,因此,各地城隍一般为当地去世的英雄或名臣。把他们立为城隍,希望能够护佑百姓。如唐代庞玉能征善战,执掌地方行政后惠泽于民,浙江会稽奉庞玉为城隍神;宋代广西邕州苏缄抵御交趾入侵而殉国,南宁和桂林一带百姓建庙修祠,奉为城隍神;明代浙江廉吏周新被谤仍刚直不阿,获罪致死,杭州敬奉周新为杭州城隍神。可见,不同于佛教、道教及其他宗教信仰所祭之神的特定性,各地城隍因历史地理及地方官员、地方精英意志,所祀之城隍神格不尽相同。从最初具体的城郭“水庸神”到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守护神城隍,其神格与各个地方历史名人关联,产生当地具体的城隍信仰神格。
陇东南地区城隍祭祀主要神格为与陇东南地区有关的历史名人,例如纪信、陈寅。纪信,汉刘邦时大将。纪信“荥阳误楚,身殉汉皇”的事迹,《史记》《汉书》都有记载,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宋人赵与时《宾退录》指出,镇江、庆元、襄阳、复州、华亭等地城隍明确为纪信。今甘肃省兰州市和天水市秦州区、清水县等地城隍神均为纪信。明代以来,陇东南地区城隍信仰普遍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与城隍信仰有关的演剧及其他活动也流传下来。
二、明代城隍信仰的兴起
明初的文化政策是保守的,对民间的钳制非常严密。但从具体措施上来看,官府依然不得不定期地进行民间祭祀,朝廷通过官府及地方士绅在祭礼中的主导作用来巩固其统治。同时对长幼、宗族秩序进行礼教宣传,通过“社祭”来加强区域的联系和文化的控制。因此,民间基层的社祭活动一直延续下来。这样的客观条件,实际上为民间信仰开启了方便之门,使各种迎神赛会的禁令名存实亡。基层祭祀活动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灵活进行,不拘泥于官方规定的内容和仪式,从而发展成各种不同规模的迎神赛社活动,甚至被官府所禁的非法的“淫祀”也大量涌现。
《大明律》第181条:“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3]从国家法律层面,对于民间迎神赛社明文禁止。但例外的是,“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客观上为民间祭祀及各类赛社活动留下发展空间。
“统治者把特定的神灵祭祀与统治秩序的维持、官方权威地位的巩固联系起来的企图,也在实践中遭到很大程度的扭曲。其祭典的简朴化和神圣化而非‘庸俗化’和‘荒诞化’的企图,也不可能实现。以城隍神为例,它本来是对应各级行政官僚机构的神灵,是用来强化现实官僚体制的东西,即使如此,也不允许它成为‘渎礼不经’的偶像,因此必须抛弃塑像,换以木主,祭祀是按严格的礼仪程序由官员进行。但因与民众信仰神灵的心态和需求极不相同,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官方规定的从上到下一年三次祭厉,变成热闹非凡的‘三巡会’,祭祀城隍的活动被演化成各地最大规模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4]在民间现实操作层面,官方主导的城隍祭祀需要依靠广大百姓支持来实现,民众参与的强化使得庄重的城隍祭祀仪式掺杂了世俗的成分,为神敬献的戏曲演出,真正的观众却是世俗社会里的广大民众,其演出内容及艺术形式自然向民间百姓倾斜。商业、娱乐、各类社会活动与祭祀活动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形成“庙会”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城隍祭祀也因此有了一代代的笃信群众,被继承下来。
从社会经济角度考虑,城隍庙会活动正是因为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戏曲演出活动交融在一起而具有生命力。单从戏曲演出活动来看,庙会演出每年进行,基层社会组织按人头或按户摊派祭祀和戏曲演出费用,客观上使神庙剧场演出进入经济良性循环中,持续推动了戏曲的发展。
三、陇东南城隍信仰及演剧活动
陇东南境内有关城隍信仰的文物遗迹主要有:西和县城隍庙及戏楼、天水市秦州区城隍庙及戏楼、武都区城隍庙戏楼、礼县城隍庙戏楼、清水县城隍庙戏楼,此外,麦积区社棠镇、利桥镇和吴呰村有城隍信仰遗迹及相关祭祀活动。陇东南地区还有与城隍信仰及演剧活动有关的碑刻十余通。
西和县城隍庙及戏楼是有文献记载的陇东南地区最早的城隍信仰遗迹。“西和县城南街城隍庙始建于南宋赵理宗赵昀(公元1228年)以后。这是西和人民为纪念陈寅,尊他为‘福神城隍爷’而建造的城隍庙。并在庙前院东向西修建古戏楼一座,每年四月八演戏四昼夜。”[5]“陈寅,南宋赵理宗宝庆年间西和知州,夫人杜氏。‘绍定(1228年)初宋理宗赵昀宝庆末(1227年)即金哀宗完颜守绪五年(1228年),北兵入寇西城,城垂陷。寅顾谓夫人曰:若速自为计。杜历声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顾王事者?遂药二子及妇俱死母旁,一门全节。墓崆峒北山,祠节烈’。《西和县志》又云:‘蒙古兵扑西和城,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不至,城遂陷,寅伏剑而死’。”[5]338以上史料及历史文物遗迹说明,陇东南地区在城隍信仰方面与中原及其他地区同步,城隍信仰较早地在陇东南地区出现,陇东南地区城隍信仰又具有自身特点。明代以来陇东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使城隍信仰在陇东南地区更加普及并深入发展,“娱神”的戏曲演出活动也发展延续下来。
陇东南地区自明嘉靖以来,地震、蝗灾、火灾、水灾、旱灾、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灾害往往导致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情况。仅秦州一地的灾情就很能说明情况,“据《直隶秦州新志》卷六记载,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到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年),秦州共计发生大旱17次。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因大旱而饥,人相食。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秦州各县大旱,人相食。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大旱,死者不计其数,人相食。有些大旱持续一年甚至数年,终年无雨。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至二十三年(1487年),持续了三年大旱。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七年(1549年)持续两年大旱。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清水县秋八月大旱,一直到次年七月才下雨。秦州各地发生的水患、冰雹灾害共计11次。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秦州自夏逮秋,大雨雹,造成大饥荒。宪宗成化八年八月,汉水涨溢,高数丈,城郭民舍俱淹没。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五月,冰雹伤田,城中有些地方冰雹深达二三尺。而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初四日鲁谷水冲中城,后寨、官泉人畜多有漂溺。”[6]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现实中又找不到具体的解决之道,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各个地方的神祇,城市保护神意义上的城隍在百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
武都区城隍庙戏楼原址在武都区隍庙街,明代隆庆年间与城同时建立,1955年拆除。礼县城隍庙戏楼始建于明代,坐南面北,山门式戏楼,明神宗戊午年重修。“同治四年,天旱无雨。当时官民都迷信‘神能降雨’,曾率众唱戏祈雨,并楹联曰:‘天本无私,勿忘修省;神能降福,共迓和甘。’”[5]337西和城隍庙戏楼“始建于南宋赵理宗赵昀绍定(公元1228年)以后。这是西和人民为纪念陈寅,尊他为‘城隍爷’而建造的城隍庙。并在庙前院坐东向西修建古戏楼一座,每年四月初八演戏四昼夜”。[5]279陈寅为南宋赵理宗西和知州。蒙古兵入侵西和城,陈寅率军民苦战,寡不敌众,最终城陷而死。天水城隍庙戏楼坐落于天水市纪信祠(城隍庙)院内,城隍庙原为成纪县治所。成纪县废于明初,改建为城隍庙,庙内祀汉初纪信。城隍庙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两层单檐歇山顶。“西秦鸿盛社等著名戏曲班社,均曾在这里演出会戏。”[7]“甘谷城隍庙戏楼坐落在甘谷县城西街城隍庙院内,修建年代不可考。戏楼坐南朝北……城隍庙会戏为每年古历五月初七,唱戏四天四夜,戏楼于1957年拆除。”[8]
除过城隍祭祀及演剧活动记载及遗迹外,清水县近年在原城隍庙址重修了城隍庙,主祭神祇为汉忠烈侯纪信,并为城隍祭祀活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步恢复清水县自清代以来的城隍祭祀活动。清水县城隍祭祀仪式从农历四月二十七到五月十一,祭祀“隍爷”“隍婆”“山神”“土地神”等。“隍婆”应为当地百姓从俗世衍生而来,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城隍祭祀的同时,开展文化娱乐、商品交流大会。会长由县城附近村镇轮流推选,会前由本届会长召集人员召开筹备会,各分会会长分工筹备庙会。正式斋醮道场分为阳事道场和阴事道场,阳事道场为百姓消灾解难、祈福延寿。阴事道场为拔度久处阴司的亡魂,使其脱化入天、超升仙界。农历四月二十六,由民间“善士”为“隍爷”和“隍婆”准备“隍衣”“隍被”和棉布鞋、绣球、香炉以及各类献菜。道士做幡,准备烛火,写祭文,搭神坛。二十七日十二点,由高功道士主持,各会长给“隍爷”“隍婆”敬献果品,上香,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道士行书拜礼,邀请诸位大神,扬幡挂榜,诵念升幡经文。然后高功引导,信徒跟随。由一人身担水桶往县城东取“神清泉”水,道士唱诵“迎水曲”,吹奏唢呐曲《将军令》。农历四月二十八祭祀大典正式开始,早晨九时开始道士早课一个时辰,然后,举行恭迎城隍神像仪式,念诵经文《食供养》。中午十一时举行“三献礼”大典,由大会长主持行大礼,焚香化马,并恭读祝文。献八大件拼盘、水陆十三花、干果、素菜、面点等108盘。献礼结束后举行城隍出巡活动,信众把城隍神像从庙中请出,前呼后拥沿街巡游,百姓夹道欢迎。巡游结束后,请秦腔大戏班给城隍爷献戏上寿。下午二时开始诵念《灵宝大忏》,晚八时信徒手持香火、灯笼,道士诵念《游寒林》,沿街东游,诵念晚课。同样仪式,农历四月二十九同样沿街西游。三十日下午揭彩道神、回坛,然后开设法坛,超度亡魂,举行阴事道场,给信徒香客施粥饭,给亡人化纸,道士诵念《施食韵》《救苦大忏》等经文。
清水县城隍祭祀仪程及演剧应当是明清以来清水城隍祭祀的延续。“该县最早的‘马家戏班’创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当时城内大土豪马玉堂(人称马老爷,赐进士)即着手创建私人戏班。以后该班担负着每年四月二十八日城隍庙和五月初七娘娘庙及城附近泰山庙三月二十八日等庙会演出,是当时清水唯一的戏班。”[8]27陇东南地区城隍庙演剧活动还有天水市秦州区城隍庙乐楼演剧活动和甘谷、武山县等城隍庙演剧活动。“该楼(秦州区城隍庙乐楼)虽为清代建筑,但梁架、斗拱仍明显带有明代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与五十年代初,‘鸿盛社’等名戏班常在此楼演出会戏……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陕西汉中秦腔演员赵安邦、汉中李,来甘谷置办了一副戏箱,组织起甘谷(主要是安远镇)、武山演员,经常在甘谷城隍庙、蔡家寺、安远,有时也到秦安、通渭演出。”[8]497且甘谷县城隍庙演出日期及天数都有明确记载。“五月初七日,县城隍庙神诞辰,演剧赛会六日。”[8]497“该县(武山)自从有了第一个秦腔班社(成立于清道光十年的宁远班子)以后,便开始了戏曲活动的新纪元。这一时期主要演会戏,城隍庙的神戏演出时间在每年正月初一至初三,上九会;天爷庙的会戏演出时间在正月初九至十二;五月十七城隍庙的会戏和九月十三老爷庙财神爷的会戏(连续三天),四方客商聚集,八方观众如云,甚是热闹。”[8]23
可以看出,明清以来陇东南地区城隍信仰非常普遍,各地城隍祭祀及演剧活动时间不尽相同,但神庙祭祀活动中,戏曲演出活动是基本内容,既“娱神”又“娱人”,以祭祀活动为基础,逐渐演变为浩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和商贸活动——庙会。以此,神庙剧场戏曲演出把更多的社会成员凝聚了起来,作为民俗活动,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四、陇东南城隍信仰及演剧活动特点
城隍信仰作为古代陇东南地区普遍存在的信仰活动,自上而下,由官方肇启到民间普遍流行。陇东南城隍信仰与陇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紧密相关,既表现出与其他地区城隍信仰的一致性,又显现出陇东南地区城隍信仰自身的特点。
陇东南地区为较早兴起城隍信仰及演剧活动地区之一,西和县于南宋赵理宗赵昀(公元1228年)朝就有城隍信仰及演剧活动。其城隍神格为抵御外族侵略、保卫城池而不幸罹难的当地英雄,与城隍信仰原始意义一致。天水市秦州区、清水县城隍庙神格为“汉忠烈侯纪信”,清代重修城隍神庙记之凿凿。“粤若郡之有城,城之有隍,城隍之有神之庙,海甸皆然,而是州独有异焉。按:州城系羲皇名地,即成纪郡旧址也。相传,其城隍尊神为汉忠烈侯纪将军,盖成纪人也。方刘项相持时,荥阳一役,高祖几不免,侯为毅然捐躯以代之,汉祖遂得脱围,以开四百余载之祚。”[9]
陇东南城隍信仰及演剧活动的普及与陇东南地区明清以来各类自然灾害频发密切相关。秦州区城隍庙碑刻有对城隍祭祀原因的记载。“尝攷,祀典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凡以有功德于民者,无不血食千秋,抚绥一邑也。矧我城隍之在汉为汉祚之所攸系者哉!夫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神之在天下,犹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况我城隍生于成纪,殁于王事,而赦封于秦,为国家捐躯,为桑梓生色,而为全秦之所庇也乎!”[9]125
陇东南地区城隍信仰及演剧活动与当地社会经济紧密关联。城隍信仰相关文物遗迹及演剧活动也体现出陇东南当时经济活动情况。秦州区城隍庙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城隍庙功德碑记载,为重修城隍庙及演剧而“奉钱”的商家有40多家,除“合成当”“合盛当”“晋泰当”等当铺外,还有梭布铺、山货店、丝绸铺、酒铺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商铺,说明清代陇东南地区商贸活动兴盛。“晋”字号商家较多,表现出古丝绸之路上山西商人的商贸足迹,并在当地有自发商会组织“山西会”。“晋升恒号一千文、任文耀一千文、诚信店一千文、复成班二千文、王□□□□文、□□焕五百文、李可栋五百文、三合酒店六百文、高明义五百文、补头班一千文、捕〔一〕班一千文、山西会一千二百。”[9]121
自明清以来,陇东南城隍信仰演剧活动都在国家祀典范围以内,由地方官府牵头主持祭祀、演剧、香火供奉。地方士绅响应参与,各地商家百姓共祭。以此区别于非官方批准的地方“淫祀”。通过合法化的地方祭祀仪式,维护社会稳定,构建自上而下的社会关系。甚至在陇东南地区,还出现了县治以下的城隍庙宇,如麦积区利桥镇、社棠镇及吴呰村城隍庙及碑刻遗迹。说明自明清以来,城隍信仰在陇东南地区影响深远。同时,政统神系的城隍信仰逐步衍生出强烈的民间化、民俗化特点,衍化为当地的文化庙会活动,如清水县城隍祭祀及紧随其后的演剧及庙会活动,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城隍信仰活动成为明清以来陇东南地区社会生活重要内容之一,“娱神”的戏曲演出活动由此延续下来,戏楼也成为庙宇建筑不可缺少的部分,神庙剧场吸引了大量中国传统戏曲观众,成为中国传统戏曲发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陇东南地区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城隍信仰,到明代,由于地方迎神赛社活动的普遍流行,加之各类自然灾害频繁,促使陇东南地区城隍信仰兴盛,与城隍信仰有关的演剧活动繁荣,城隍信仰活动成为陇东南地区至今仍然延续的民间文化活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