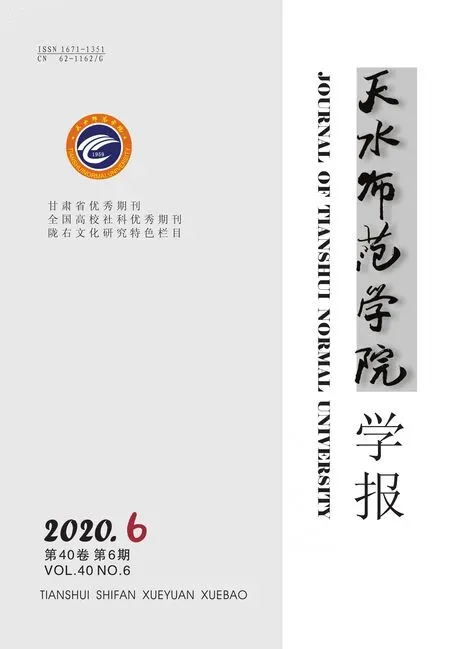说《秦风·无衣》之“衣”与“无衣”
张崇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秦风·无衣》一诗,除王夫之《诗经稗疏》及陈子展《诗经直解》力主乃秦哀公为申包胥乞师而作外,一般多认为是一首秦地的军歌。其中既体现出秦人尚武逞勇的风气,又洋溢着秦国士兵团结一致、互助友爱、共同对敌的精神。正如朱熹《诗集传》所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1]79清人陈继揆《读诗臆补》更将其与秦灭六国相联系,说:“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2]1092所谓“开口”,即此诗首章之开头两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接下两章也分别以“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开头,都是同样的气概。而诗中所言之“袍”“泽”“裳”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服装?它对秦国士兵具有怎样的意义?秦国的军队又为何会出现“无衣”的问题?以下便试为解析。
先说袍。袍是由襦演变而来的。襦是短上衣。《说文》:“襦,短衣也。”《急就篇》颜师古注也说:“短衣曰襦,自膝以上。”如《榖梁传·宣公九年》记陈灵公与其大臣通于夏姬,“或衷(贴身穿)其襦以相戏于朝”,其所谓“襦”即是短上衣。襦有单、复两种,复襦双层,内有絮。《汉乐府·孤儿行》说孤儿“冬无复襦”,所谓“复襦”,也就是有絮的襦。襦一般仅达于膝上,而长至足背者即是袍,又称长襦,相当于后世的长袄。袍都是双层的,内絮以乱麻或旧丝绵。《后汉书·舆服志》说:“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可见袍在周初即已经出现了。而到了汉代,则“下至贱更小吏,皆通制袍”。[3]不过,古代富贵者冬季所着乃是裘即皮衣,而普通人御寒所穿的服装才是袍。《论语·子罕》记孔子的话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可见穿袍者要比衣裘者显得贫寒些。至于下层社会的贫苦人,如奴隶之类,所穿的是褐。褐是粗麻、粗毛织成的粗布,手工编织,类似今天的麻袋片,而且多是“短褐”。《诗经·七月》讲到奴隶们冬天的生活时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孟子·滕文公》也说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汉代赵岐的《孟子注》谓褐“若马衣”,可见其粗劣。
古代秦国士兵御寒所穿的既不是裘,也不是褐,而是袍。这种战袍较一般人所穿的袍稍短,白天穿在身上,到了夜晚则可当被子来用,相当于后世的军大衣。故袍对于士兵来说,应是最重要的服装,而《无衣》言衣之首曰“袍”,当不是偶然的。
不过袍到了汉代,情况又有所变化。东汉开始出现的绛纱袍及皂纱袍又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朝服了。[3]后世官员所着之“蟒袍”,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当然是后话了。
再说泽。泽,《齐诗》作襗,即贴身所着之内衣。泽有污浊之义。如《离骚》“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为亏”,即以“芳”与“泽”对举。又,《礼记·曲礼上》说:“共饭不泽手。”也是因为古人吃米饭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所以手不能脏。古人所穿内衣因常受汗泽,故以“泽”名。《释名》:“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诗》谓之泽。作之用布六尺,裁足覆胸背。汗衣滋液,故谓之泽。”秦地冬季寒冷,故士兵除穿袍外尚须着内衣,这样才能御寒。犹记余少时居齐鲁乡间,因家贫,冬季只着一件薄棉袄常觉冷风刺骨,后贴身加穿一件内衣便暖和多了,是同样的道理。
再说裳。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援华的物资上常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及“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字样,前者出自记载鉴真事迹的《鉴真和尚东征传》,[4]而后者即见于《秦风·无衣》。
古人称下衣为“裳”。但裳不是裤,而是裙。裳古代亦写作“常”,《说文》:“常,下裙也。”又说:“裙,下裳也。”可见裳就是裙。古代男女皆着裳,也就是穿裙子。《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这是小男孩穿裙。《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诗言一少女让河对岸的小伙子撩起裳过河来跟她相会,这是少年男子穿裙。《诗经·七月》:“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这是贵族男子祭祀时所着之裙。《礼记·曲礼上》:“暑无褰裳。”意思是说到人家做客大热天也不要把下面的裳撩起来,这是社交场合穿裙。至于女子着裳更是普遍,如古代美女罗敷的打扮便是“湘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汉乐府·陌上桑》)。
关于裳的形制,东汉刘熙《释名》说:“裙,群也,连接群幅也。”《礼记·丧服》“裳内削幅”郑玄注更具体地说:“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古代布帛幅宽二尺二寸,而周尺、汉尺约当今之0.23米,这样,七幅也有3.5米左右了。这与江陵马山楚墓所出土的战国女性单裙的长度正相仿佛①其墓中出土之裙上腰横长1.81米,如是,则裙之周长当为3.62米,与郑玄所说及余之计算基本一致。(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古代军人上身穿袍,下身亦着裳,即所谓“战裳”。《无衣》所说的就是这种战裳。与普通的裳多以布制成不同,军人的战裳常常以皮革作衣料,即所谓“甲裳”。《左传·宣公十二年》记邲之战中,晋军统帅赵旃战败后弃车而入林中,楚军统帅“屈荡搏之,得其甲裳”。所谓“甲裳”,即以皮革制成的裳。这种裳直到后代仍为军人的常服。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的下身除着裳外,里面还要穿袴。这一点军人与普通人是一致的。不过先秦时期的袴是没有袴裆的,只有两只袴腿,穿在腿上后,再用丝绳系于腰际,很像后世的套裤(又称叉裤)。1982年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中,就发现了一条女主人穿在裳内的无裆袴。[5]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北方一些农村有时还能见到这种袴,不过只是春秋季节供老年人穿在单裤外面罢了。
此外,古代士兵在作战时还要于袍外披甲,头上加胄。胄,后世又称“兜鍪”,因其形状似炊具鍪故名。古代士兵都要戴兜鍪,所以兜鍪又常被用来指士兵。如辛弃疾《南乡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便是以兜鍪指士兵。先秦时期秦国的士兵都是佩有甲胄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写秦师欲袭郑国,在过周(洛阳)北门时,为了向周襄王表示敬意,“左右免胄而下”,便是明证。而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身上,也是上着袍,下着裳;袍外罩甲,裳内有袴的。
最后谈谈“无衣”的问题。当兵而“无衣”的记载,三百篇中仅见于《秦风》。此当与秦国的兵制、社会风俗、政策导向及士兵着装特点等方面的因素有关。
按照史学界一般的说法,《诗经》产生的西周至春秋时代属奴隶社会,当时各诸侯国所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种“井田制”,照孟子的说法便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6]井田制又称“助”,即郑玄所说的“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7]亦即奴隶无偿为奴隶主(即“公”)进行耕种,实际是一种劳役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为了更多地役使和剥削劳动力,他们是不准奴隶们离开土地去当兵的。而有资格参军作战的则是平民和一些小奴隶主。又由于古代服兵役者须自置服装及甲兵(直到南北朝时之木兰从军仍如此),即所谓“自赋”②《孟子·滕文公》:“国中什一使自赋。”《周礼·地官·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贡赋。”郑玄注:“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所以也只有平民和小奴隶主才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但秦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秦国所实行的是“爰田制”而不是井田制。[8]74-80所谓“爰田制”,即不分公田、私田,仅将土地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分配给奴隶耕种,然后由劳动者将产品按照“彻”的形式(即十分抽一的税率)上缴给奴隶主。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增加收成,奴隶主便采取了“易土爰居”的办法,[9]即定期(一般是三年)更换每个劳动者的土地和居住地。这样,由于爰田制下的奴隶主只管收取产品而不顾及奴隶的生死,所以到了战时便允许这些奴隶去当兵。兼以秦地尚武之风的盛行及秦国对军功的奖励①秦国一贯实行奖励军功的制度。如《韩非子·定法》云:“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商君书·境内》亦云:“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所以奴隶们也便欣然前往。但这些奴隶出身的士兵与小奴隶主和平民出身的士兵不同,他们是没有能力置备服装与甲兵的,只能穿着褐去打仗,这样一来,“无衣”(实际是没有军衣)的问题便出现了。而这也就是“无衣”现象只见于秦国而不见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顺便说一下,古代士兵的服装是统一的,而卒衣都有题识。《说文》:“隶人给事者为卒。卒,衣有题识者。”《方言》(卷三):“卒谓之弩父,或谓之褚。”郭璞注:“言衣赤也。”是所谓“题识”,即染衣为赤也。而之所以“衣赤”,据《周礼·春官·司常》“通帛为旃”,郑玄注说:“大赤,从周正色。”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秦国从军的奴隶要置办一套完整而合规范的军衣以及甲兵,实在是一笔难以负担的费用。而奴隶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不得不去当兵,这就难怪《秦风·无衣》中会反复出现“无衣”的歌咏了。条件虽然艰苦,但秦军士兵的互助精神还是可嘉的,所谓“同袍”“同泽”“同裳”,便是士兵们团结互助、共同克服困难的誓词。而直到后世,军人间仍互称“袍襗”,更可见此种精神影响之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