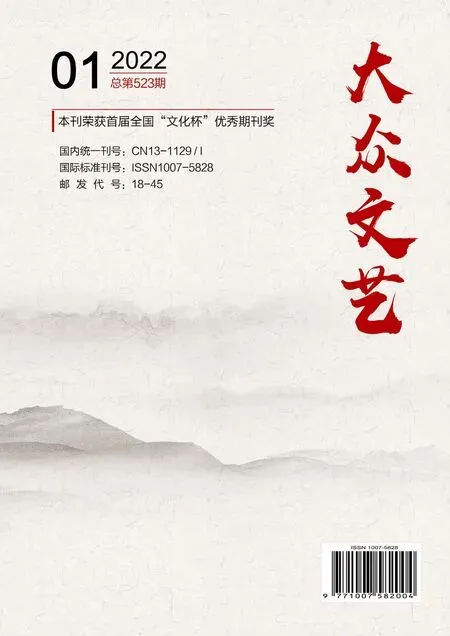汉娜·霍赫作品中的“隐喻性”研究
(西南大学 400715)
汉娜·霍赫于1912年在夏洛腾堡的艺术学院有过短暂的艺术学习经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结束了她的学习生涯。战争爆发后,她于1915年进入了柏林的装饰艺术博物馆学校继续学习,随后她一边进行着艺术实践,一边给出版商乌尔斯坦的女性杂志做兼职插画家和版面设计师的工作,这为她后来开始以蒙太奇手法进行创作埋下了伏笔。在1915年他遇到了捷克的流亡艺术家豪斯曼,他将她带入柏林的先锋艺术圈子。
1920年,她与多名艺术家参与了激进的达达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运动中,她是唯一一位女性艺术家。尽管如此,除了哈特菲尔德以外,她比任何达达艺术家都更大程度的发展了照相蒙太奇。这一时期的作品她经常用“半机械人”这一形象来探索改变周围世界的现代化科学对人身份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她正式奠定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开始参加众多展览,她更多的从对政治的关切转向了对女性主义与种族问题的关注。纵观其艺术生涯,她持续不断的创造了各种生动有力的图像,为身份主题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作品中“隐喻性”的浮现
隐喻本身是语言学中的修辞概念,是人类认知思维的一种方式。视觉形象存在于看与被看之间,形象与对形象的阐释之间。因此观看与各种阅读形式(解码、阐释)就成为了同样重要的问题。
在当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照相术的普及使得柏林达达主义者立刻转向他们所称的新材料,即任何一种他们能直接从现实中提取出来的残片、印刷品以及碎片化的报纸、杂志、海报等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元素进行创作,这些元素比起传统的绘画更具有话题性、真实性以及碎片化的功能,代替文字从而成为了隐喻中的多义文本,因此媒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同时新的媒介极大的推动了蒙太奇手法的出现,蒙太奇本身的含义是将某些东西放在一起,有构成、配置的意思,可理解为有意识的进行人为剪切、拼贴的手法。这种手法最大限度的发挥了不同隐喻链接的自由组合,也可以说蒙太奇的本质就是隐喻,因此这使得作品中的图像相互发生对话的同时,在运动中产生断裂和跳跃使得整体的意义发生连续性的流动。达达主义者将蒙太奇作为主要表达策略,运用各种视觉材料的混合,重新组合形象来暗喻社会现实,鲜明的表达他们的极具政治化的立场。
二、作品中隐喻的视觉表征
拼贴作品《用达达餐刀切开魏玛德国最后的啤酒肚文化时代》Cut with Knife Dada through the Last Weimar Beer-Belly Cultural Epoch of Germany)是霍赫最为著名的作品,在画面中(图1)她将威廉二世的形象加以解构,用一些碎片以及金属零件重组他的身体,但是他的眼神以及姿态依旧象征着权利与控制。同时在画面中她将豪斯曼的身体和一个笨重的机器结合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笨重的金属状的东西盖住了豪斯曼的头部,他身上穿着笨重的潜水服,呈现出奋力向前冲的姿态,但是过长的手臂以及安有假肢的双手,看起来没有任何战斗力。假肢代表了对身份差异的思考。这种残缺不全的形象再现了战争中德国的伤残士兵,一方面,实际上身体上的脆弱,已无力抵抗,另一方面,表面上又极其自信,这种内心与外表的不一致同时体现在一个形象中。这一时期人与机器结合的“半机械人”形象所呈现出的双重矛盾意义隐喻着她对于德国战后的动荡时期的批判态度。她通过这些重构的元素像我们叙述一个新的图景,是对政治尖酸刻薄的嘲讽,是对个人身份的迷茫的思考。这些被霍赫创造的新形象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环境的一系列正面或负面的变化。

图1 《用达达餐刀切开魏玛德国最后的啤酒肚文化时代》

图2 《驯兽师—姿势统治》
在魏玛时期之后,汉娜·霍赫就更加深入的探索了关于女性主义与种族的问题,从功能上来这两个主题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如作品(图2)《驯兽师—姿势统治》(Dompteuse)是汉娜·霍赫对女性主义最模糊和复杂的描述,中心人物是一个身穿无袖背心的男子双臂交叉的坐在画面中心,露出具有肌肉线条的手臂,象征着男性气质,而造成巨大差异的是模特的面部却一张细腻的女人的脸,穿着红色的上衣与裙子,坐姿显得十分妩媚,这个符号隐喻了一种女性气质,主体人物凝视着右下角的海狮,海狮也在往后偷看,这就说明了与驯养员之间的防备、抵抗的关系。这些碎片巧妙的拼在一起,她用蒙太奇手法去刻意营造性别差异的混乱,试图消解传统的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世界,有意将男人女性化,以此颠覆、统治这个旧有的社会、阶级等,从而寻求女性身份的话语。
在这一阶段她也创作“人种志博物馆”系列。她经常将不同背景、种族和民族的女性的面部或身体作为主要元素重构在一起组成新的混血人种。她用简化的艺术手法对人物进行了处理。作品(图3)《半纯种》(Mischling -Half Breed)中,作品展示了由白人和黑人拼贴的肖像,她的脸颊上流着眼泪,下巴下方的一个切口勾勒出了她的下颌轮廓,霍赫将她的黑色长发和肩膀被剪掉了,这些碎片被粘贴在矩形棕褐色背景上。她的前额和头颈两侧有一条波浪状的浅色带子,从形式上充当了头发的补充物。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长发这个物象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义性和隐喻性的符号,来源于宗教。弗洛伊德认为头发是纺织的起源,是从社会分工以来留给女人东西,因此剪掉辫子是一种阉割行为。在作品中霍赫将图片中的女人剪掉辫子,模糊性别,又叠加了一条带状物,其和脸部的边缘似乎就像是带了头巾的修女,隐喻了一种对父权制等级的社会秩序提出挑战,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批判。作品站在当时社会人们对待不同种族之间的态度,向我们呈现了那一时期有关身份问题的诸多思考。

图3 半纯种
三、结语:身份的隐喻
汉娜霍赫是一个极具先锋性的人物,在近几年中成为西方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对象,且身份问题也是当代艺术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模棱两可的隐喻成为了她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所创造的各种身体形象已然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一系列完整的符号,不仅是对自身的再现,更是对政治、阶级、社会的折射,并且她试图去破坏了所有二元对立之间的界线,从而追寻身份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