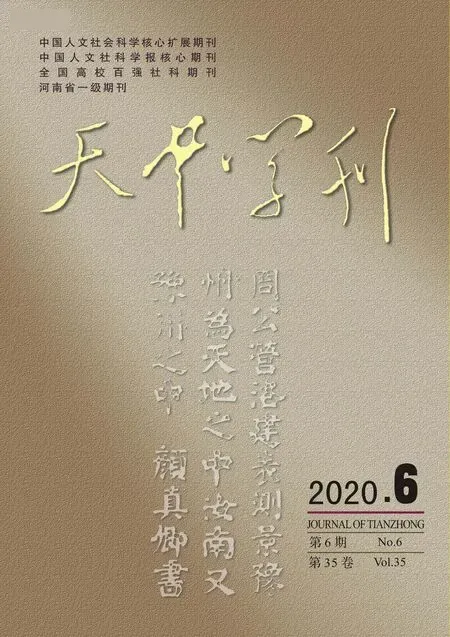民国时期辞赋批评体系转变论
靳田田,孙福轩
民国时期辞赋批评体系转变论
靳田田,孙福轩
(浙大城市学院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15)
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演变,文学批评亦多关注其“文学性”。此于辞赋批评而言,表现于两端:一是宏观层面的从政教观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变,二是微观层面从文章学到现代鉴赏体系的转变。对辞赋“文学性”的关注构成了民国文学批评体系的重要一环。
民国时期;辞赋批评;转变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中国从封建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期。而伴随着社会的整体变迁,文化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文学研究也随之革新。在从古典赋学到现代赋学的转化中,赋体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人们对其艺术性价值的评价与鉴赏标准也经历了一个重塑过程,由传统的注重政教功用与辞章技巧的品评体系,转向新文学观念下对赋体本身文学价值的衡量以及对其语言、修辞、用典等具体方面的现代性诠释。
一、从政教观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变
在古典赋学中,对赋体艺术性进行鉴赏评析的前提是对其价值的认可,而在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研究语境下,赋体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赋体正式定型时在汉代经学背景下被赋予的政教功用,这是古典赋学中的重要批评传统“诗源说”的由来。
这种价值判定从赋体诞生时的西汉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在民国时期还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如清末民初的赋论,文论家们出于对清代赋学宗法唐赋的反思以及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所提出的赋论呈现出“祖骚宗汉”的复古倾向,古文家林纾在其《春觉斋论文》中论述赋体本义: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一立赋之体,一达赋之旨。为旨无他,不本于讽喻,则出之为无谓;为体无他,不出于颂扬,则行之亦弗庄……故有以骚为体者,亦有以对偶排比为体者,虽极于雕画,苟不定以旨趣,均不足以传播于艺林,驰骋于文圃。[1]
林纾引刘勰语,从赋体与赋旨两个角度来定义赋体,认为讽喻之旨才是赋体的根本,这是以政教观念对赋体进行价值判断。同时,林纾进一步分析了汉魏六朝的赋作,以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两京赋》为例,分析了这两篇赋作在东汉迁都洛阳的政治背景下所起到的平复人心的社会功能,并认为左思《三都赋》也是承此旨而作。民国时期的第一部辞赋专书——陈去病的《辞赋学纲要》,其第一章《总论》以“班固有言,赋者古诗之流”开宗明义,秉承诗教观对赋体进行价值判断,推崇汉赋,而在其序言中评价六朝赋为“绮靡”,认为唐宋赋更无足观,“李唐嗣兴,号称鼎盛,然偏工帖,括绝少弘辞。赵宋卑卑,更无足论。而讽谏之旨,由是斩也”[2]。这体现的正是以政教观念统摄赋体价值判断的传统批评思路。
民国以来,随着社会整体的现代化,有关文学的观念与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杂文学观念逐渐被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取代,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评价标准逐渐脱离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转变为对其抒情性、思想性与美感等艺术特质的注重。在这样的文学观念转型的语境中,赋体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价值判断标准与古典赋学中的“讽谏之旨”全然不同,而体现在当时的赋学研究中,主要是对赋体抒情性的重视,以及对赋体独特的审美价值的考察。
(一)对赋体抒情性的重视
民国时期的“文学”概念中,抒情性是最被强调的一个特质。民国时期的许多文学史开篇就是对“文学”这一概念的辨析,如1930年版的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其《绪论》第一节《论文学》,就对章太炎所主张的近于文章学的“文学”定义表示反对,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定义,给文学下了几条界说:“一、达意达得妙;二、表情表得好;三、描写真实,而合于科学方法;四、不剿袭而有创造的精神。”[3]其中表达了对文学表情达意功能的重视。再如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对文学的定义更加简洁,即“文学是情感的产物”[4]2,并明确地提出“文以载道的说法是错误的”[4]3,强调文学“言情”的艺术特质。
以上述文学观念来观照赋体,因讽谏之用而被推崇的汉赋难以得到认可,而在古典赋学中一向被鄙薄为“绮靡”的六朝赋的文学价值被重视起来。
这一时期的赋学研究因秉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对汉赋多有论述,而六朝赋论及较少,但在一些持主情文学观的文学史著作里得到很高的评价,较之以往的赋论,可以算是其批评研究的一个变化。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专列一章《六朝辞赋》,认为六朝赋“复兴了辞赋的‘诗趣’”[5]194,对六朝时的许多名篇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评祢衡《鹦鹉赋》为“引物以譬人,写得那样可怜”[5]194,评曹植《洛神赋》为“那么的有风趣,已不是徒以奇字丽句堆砌成文的了”[5]194,评陆机《叹逝赋》为“真情流露,诗意充溢”[5]194,等等。郑氏评价了汉赋与六朝赋的不同:“汉人每喜夸诞的漫谈,其失也浅薄。六朝人却反了过来,专爱在伤感的情绪上多着力,遂多‘哀感顽艳’、‘情不自禁’之作。”[5]196正是主情的纯文学观对六朝赋抒情价值的发现与认可。再如1944年出版的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再编本,也对六朝赋有着类似评价,赞潘岳“《闲居》、《秋兴》诸篇,意趣极为隽永,《寡妇赋》则因自己的鳏旷、矜怜到寡妇不可告人的幽怨,尤以辞意凄绝获得读者的同情”[6]39,并盛赞陶渊明的赋作,引其《闲情赋》中的语句进行赏析,“抒情文写到这样婉转敦厚的地位,除此公外,简直不曾有过”[6]40。
(二)对赋体审美价值的考察
在众多学者将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引入并进行译介的过程中,审美价值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概念,如黄人在1904―1907年间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所言“文学以美为目的”①,周作人发表于1908年的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之一“具神思、能感性、有美致”[7]等,都可以体现审美价值在纯文学观念中的重要性。在民国时期以美学视角观照赋体进而发掘其中意蕴的,主要以闻一多和朱光潜为代表。
据郑临川回忆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课上的讲义而述成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一书,无赋学专著的闻一多在讲解《〈楚辞〉·天问》时也论及汉赋,认为研究辞赋要结合其时代背景与“共同精神”,汉赋“以大为美”。
闻一多指出,《诗经》与《楚辞》为两个时代的产物:《楚辞》产生的时代与《诗经》产生的时代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人类性灵的觉醒”和“对真和美的认识”,还有人的“自信心”的增强。而他所定义的“《楚辞》时代”,向前可移至田氏代齐的战国初年,向下延伸到罢黜百家前的汉武之世,这是一个包括了庄子、《易》、邹衍、屈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等文化巨子与著作在内的大文学时期,实际上包括了从战国的诸子争鸣至西汉大赋兴盛的文学时代。而为《楚辞》作者与汉代赋家所欣赏的“共同精神”,就是以大为美的风尚。
闻一多对汉赋的认识基于他对《天问》的理解,他在将《天问》与《诗经》《庄子》等的比较中高度评价了《天问》的价值:
此篇的作者,的确是古今中外的最大诗人,他问尽了古今宇宙时空的最大问题,气魄之大,罕有人比,只有《尔雅》、《易传》、《邹子》、《庄子》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妙。拿《诗经》境界和它相比,相去何啻天渊哩![8]65
闻一多认为汉赋就继承了《天问》的这种大气魄,并提到当时的文学史对汉赋评价的问题,“汉赋不为文学史家所重视,如以读《天问》的观点去读它,便可看出它的伟大实超过其他文体”,然后引用具体的汉赋作品进行分析:
《上林赋》是司马相如所独创,它的境界极大。但和邹子、《天问》相比,已是强弩之末,在邹子大九州岛的地图上仅是一小点而已,然这一小点比后代诗人所写的境界已不知大了若干倍。凡大必美,美其无以名之,此太白“白发三千丈”一句所以受评点家的密圈了。后来的《两京》、《三都》诸赋,无非仿自《上林》、《子虚》,由此可知在当时的人还懂得大就是美,所以那些大赋还能受到称赞。[8]65
从“大的境界”将司马相如《上林赋》与前后时期的作品做比较,接着进一步论述了司马相如《大人赋》,以及贾谊《鵩鸟赋》、枚乘《七发》等重要赋作,又提出“有积之大”与“无积之大”的区别:
读《天问》这类大作品,不可无一,亦不可有二,读时应从技巧方面入手。如读司马相如《大人赋》,须知他写的是无积的大,庄子的大,为想象的空间的大;而《子虚》、《上林赋》,则是写有积的大,《天问》的大,它的笔调变换也极尽其美。
枚乘《七发》同样是写大的作品。贾生《鵩鸟赋》,为哲学的诗,意境也大,他把整个宇宙当作一座熔炉看待。[8]66
在这里,闻一多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汉赋,完全摒除了那种狭隘的政治道德功利观念,从而道出了汉赋作品“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闻一多提出的汉赋“以大为美”的独特观念,在当时重个人化抒情叙事的文学观念下,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挖掘出了汉赋独特的审美价值,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极大。
朱光潜以美学家的敏锐来考察赋,也得出了别开生面的观点。朱光潜的文艺美学专著《诗论》中有许多论赋内容。首先他认为赋是诗的一种,引用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和其《汉书·艺文志》里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认为这是“赋最古的定义”,“赋本是诗中的一个体裁”,并在后文中以文本的实际出发去寻找赋的定位。但朱光潜所谓的“诗”是现代文体分类意义下的概念,而班固说的“诗”是专指具有政教功能的《诗》三百,所以朱光潜是在用现代“诗”体的标准来审视赋体的特征,于是得出“赋是状物诗”“描写诗”的看法,如:
赋是状物诗,宜于写杂沓多端的情态,贵铺张华丽……赋大半描写事物,事物繁杂多端,所以描写起来要铺张,才能曲尽情态。因为要铺张,所以篇幅较长,词藻较富丽,字句段落较参差不齐,所以宜于诵不宜于歌。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9]182
赋与一般用来抒情的诗不同,就内容而言,赋是状物诗,是“一种大规模的描写诗”,侧重于铺张地描写事物,这明显就是针对铺陈体物的汉赋而言了。因为要铺张,所以篇幅要长,且“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9]183。随后,朱光潜还举出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和左思《三都赋》来说明,“都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地铺张”[9]183,所以赋是近于图画的,近于空间艺术。
朱光潜以现代的文体观念、审美体系去考察《诗》三百和赋体,将赋体的根本性质定位为诗,以美学的思维方式考量赋体的特点,对赋体的艺术特色做出了独到的解释,那些被民国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所排斥的“铺陈”“藻饰”等特点,在朱光潜的解释下都找到了其审美意义,从而发掘了赋体独特的审美价值。
二、从文章学到现代鉴赏体系的转变
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文章学”,包含“文字(音韵)”与“词章”两大部分。由此而来,传统的文学研究,就致力于对文字的训诂、考证、释义和作文技法的探讨两个方面。如20世纪初期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文学”一科的教材,其内容就包含了历代书法、音韵学及名义的变迁,修辞与作文法,经史子集的文体,骈、散文的变迁与发展等,这就是古典文章学研究思路的体现和延续。而与正统的“文学”研究相对,诗话、词话、文话这种漫谈式的评点,通常被视作“怡情之术”,不被看作严肃的研究,但以现代的文学研究眼光看,却是内涵极为丰富、更接近文学本质的批评研究。
对应于赋体,古典赋学中对赋体的文学性研究,也集中体现为对赋体语言文字等内容的考索以及对赋体创作技法的探究。前者如唐代李善及五臣注《文选》中的赋篇部分,对《文选》中所载的赋作不仅进行了注音、释词、疏通句意等方面的工作,并对其中的语词典故、山川地理、名物制度、风土人情等做了考索与研究;后者如清代涌现出的许多分析律赋创作技法的赋论专著,囊括了律赋结构、制题、用韵、用典、句法、字法等诸多方面。而从依附于诗话、文话,至清代独立成为赋话形式的赋作评点,也是构成古典赋学中赋体艺术鉴赏体系的重要部分。民国时期的赋学研究,随着文学观念的转变与现代性“文学”学科的建立,赋体的艺术性评判标准发生变化,品评体系也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承接着传统文章学研究的思路与成果,逐渐朝向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文学鉴赏与批评的范式进行转化。从具象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赋体的艺术品评体系逐步建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赋体语言、文字艺术的发掘
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赋体所呈示的文学性,是民国时期赋体艺术鉴赏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汉赋的语言和用字,刘勰即有“铺采摛文”[10]的泛论,清末民初时章太炎有“小学亡而赋不作”[11]之论,关注到了汉赋中独特的用字现象并将之与文字学联系在一起,但没有多作论述。
民国时期的研究者对这一现象则做了更深入的探讨,他们继承古典赋学在音韵、辞章方面的研究成果,借助现代研究的科学化和专题化,得出更加系统的研究成果,如层冰的《汉赋韵笺》、段凌辰的《论赋的封略》、贺凯的《汉赋的新解》等。然而,最值得推介也经常为后来学者引述的万曼的《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从语言学和文学的发展史角度对汉赋的语言、用字艺术做出了新的解释:
辞赋,这文学形式,便是由口语文学转移到书面文学的一个主要枢纽。在辞赋的时代以前,文学作品多半是口语的记录。辞赋时代以后,文学作品才完全是书面写作。[12]19
文章联系中国文学在上古时期的具体状况,提出辞赋作为书面文学的特性,并追溯到春秋“行人”辞令之美,将文学性的语言记录归纳为“用诗”“口赋”两类,前者神趣类赋,后者颇近赋旨,但赋体的形成则要在完成从语言到文字上的飞跃,即屈原赋的出现后才能实现,而汉赋诸家的成就便在于将赋体发扬成纯文字的制作,使赋由附庸而蔚然大观,也使得赋体得以在比诗歌更大的篇幅中铺陈伸展。这篇文章对汉赋语言艺术的理解角度十分新颖,成为20世纪汉赋起源研究的典范之作。
对赋体语言、文字本身美感的发掘,也是民国时期赋体鉴赏的重要一部分。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以《上林赋》为例来分析汉赋的语言艺术,认为其中“双声叠韵”即联绵词的运用“极尽形容的力量”,“加以名物之繁夥,不独使增加文字之声容色泽,并且使意中所预言者,皆能曲折写出。这种伎俩,谓之侔色揣称,可以说是文章第一能事,唯有赋家最擅长”[13],对汉赋的联绵词运用以及铺陈物象的特点做出了赏析。张世禄从象形文字之美看待赋用奇字的现象,认为“吾国文字衍形实从图画出,其构造形式,特具美观。词赋宏丽之作,实利用此种美丽字形以缀成”,因而“词赋之体,乃根据文字形体之美丽以形成者”[14],将汉赋用字的繁丽延伸到视觉层面,更增加了汉赋美感的新意蕴。
(二)对赋体用典的考辨
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赋体因其丰富性而被视为一种展示才学的文体,在北魏年间,人称北朝“三才”的魏收就有言曰“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15],且赋体诞生时的汉代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辞赋的创作与研究也受到这一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核心的影响,熔铸经典、翔集子史也成为赋体创作的一种要求。因此,古典的赋学研究十分重视对赋作典故的考证,将其当作赋体释义的重要部分。
及至民国时期,关于赋体用典的研究仍然在延续,但不同于传统的如治经一般的纯粹考辨,民国学者的成绩主要在科学分类、个案深入和专体探讨三个方面,目的不仅在于对赋体的必要释义,而且在于展示用典在文本中所发挥的艺术效果。这一类的研究,当以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一文为典范。陈文开篇回顾以往对《哀江南赋》的用典研究,论及庾信所用之“今典”: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16]
陈寅恪所谓“今典”,即庾信作赋所处历史时代的故实。陈寅恪以史实为依据,考订出《哀江南赋》直接的创作缘由是庾信读了当时同样淹留北周却得以南归的沈炯之《归魂赋》,补济前人笺释该赋名源于《楚辞·招魂》之“魂兮归来哀江南”语。通过古典与今事的互参解读,既彰显典故之美,也深入发掘了赋作本身的情感厚度,增添读赋的意趣。
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也在现代学科建设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研究者对历史典故的认知更为深入,这为赋体用典的理解增添了学术的深度,某种程度上为赋体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趣味。如对宋玉《高唐赋》的考释,有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和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两篇文章,都对“神女”典故及楚王会神女的行为进行考证解析。闻文依据《墨子·明鬼》所言“楚之有云梦”即“宋之有桑林”的说法,认为宋玉《高唐赋》与《神女赋》所写“云梦”处所及“兴云致雨”都是“性”的隐喻,是祭祀生殖女神的圣地[17]854;陈文通过对原始宗教的神圣祭坛“社”的分析,结合《周礼·地官·媒氏》和《礼记·月令》的相关记载,阐述出其中“会男女”的原始宗教意味[18]463。两篇文章都着眼于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以现代的学术思维对传统的“神女”典故提出了新的解读,在释解事典的同时增添了赋文品鉴的趣味。
(三)对赋体文本的鉴赏
在传统的赋论中,对赋体文本的艺术性鉴赏主要体现在赋作评点中,形式上呈现为漫散的点状评论与只言片语的感悟,内容上则是神韵、气格、文势、笔调等传统的辞章学概念。这种品鉴方式作为一种批评传统,在民国时期未曾断裂,常见于评论家的笔下,如黄人《中国文学史》中的两汉文学部分,在录入的赋文之后偶尔穿插评点,其评贾谊《吊屈原赋》“借酒浇块垒,语语吊屈,却语语涉己”,评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出于《逍遥游》”[19],涉及赋作手法与风格,但只是点到为止,未做深入探讨。
然而这一时期的传统赋体品鉴也有着渐渐转向现代鉴赏方式的倾向。如清末民初旧式学者徐昂于1929年出版的《文谈》是一部讲义性质的普及性文章学著作。《文谈》卷三《论制作》中有非常丰富的赋体品评内容,体现出传统评点与现代分析系统的融汇。他评潘岳《秋兴赋》,“‘四运忽其代序兮’一语,为总挈下文‘冬索春敷,夏茂秋落’之笔,‘彼四戚之疚心兮’一语,为总承上文送归远行临川登山之笔”[20]60,这是对结构的分析;“‘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先说送归而后说远行,先说临川而后说登山,与上文先远行而后送归,先登山而后临水,次第皆颠倒,此一美也”[20]60–61,由结构的自然顺承而反观次序“颠倒”之美,是对赋作技法的鉴赏。更能体现新意的是徐昂在文本品读中打通视、听二觉:
铺陈景物,于状态或光采之外,可兼写其声音,文字之胜图画者在此。“蝉蝉嚖嚖而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熠耀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此数语皆重写声,而次第不同,前二语先写声而后写状,次二语先写光而后写声,后二语先写声而后写光,有循环错综之妙。[20]61
调动视觉、听觉来感受赋体构造情境的艺术性,尤其体现出现代性的文本赏析性质。徐昂对赋作的品读,承接于传统的辞章学对文本技法的研究,又生发出现代分析的新意,是民国赋学在赋体艺术性鉴赏方面从古典走向现代的生动体现。
民国赋学更为鲜明的转变和发展,体现为这一时期有关专题论著中以系统的方法和现代的语言对辞赋文本的赏析。如陶秋英分析王褒《洞箫赋》,专就其艺术的想象发论:
那种想象力的丰富,绝不是司马相如的只有铺叙者可比。而这种想象,也与《离骚》《九歌》不同:《离骚》《九歌》并不把所想象的东西“感情化”,《洞箫赋》则把他感情化了。这就是顶大的特点。有了“感情化”的想象,再加上他清丽的描写、刻意的解释,于是《洞箫赋》成为了兼祧屈、荀两家的作品,成为骈四俪六的鼻祖,是王褒的一点成功。[21]
将此赋的艺术特点归纳于感情的想象与清丽描写、刻意解释两翼,既简明通俗,又演绎细腻。这种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已与传统的评点和辞章学研究划出疆界,是典型的现代鉴赏批评。再如许世瑛品读萧绎《采莲赋》,赏析其描写莲子、莲蓬的手法:
“素实兮黄螺”,想象力太高了,素实是指白的莲子,而黄螺却是说那挖去莲实,所剩的各个空莲蓬的各个空隙都是黄色而成螺纹,用黄螺比拟真最好也没有了。这种巧譬又岂是寻常弄文墨的所能想到呢。[22]20
赞美赋家的想象力与所用的比喻手法,其所言“想象力”“比拟”“巧譬”等都是现代评论术语,与传统的技法分析有学理性的区别。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辞赋鉴赏方式虽未能发展为完整的体系,但已形成了雏形,为此后的赋学鉴赏理论建构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辞赋批评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① 黄人《中国文学史》总论的第一章《文学之目的》开宗明义,表明本书的文学观念,“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而所以达此目的者,学是也。真也者,求宇宙最大之公理,如科学、哲学等。善也者,谋人生最高之幸福,如教育学、政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而文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语出黄人著、杨旭辉点校《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1] 林纾.春觉斋论文[M].范先渊,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9–50.
[2] 陈去病.辞赋学纲要[M].上海:国光书局,1927:1.
[3]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M].上海:光明书局,1924:3.
[4] 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M].上海:群学书社,1932.
[5]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平:北平朴社,1932.
[6] 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M].上海:光明书局,1944.
[7] 邬国平,黄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699.
[8]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郑临川,述.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9] 朱光潜.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10]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4.
[11] 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2.
[12] 万曼.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J].国文月刊,1947(59):19–21.
[13] 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39:151.
[14] 张世禄.中国文艺变迁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62.
[15]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34–2035.
[16]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G]//王钟陵,彭黎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25.
[17]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J].清华学报,1935(4):837–865.
[18] 陈梦家.高禖郊社祖庙通考[J].清华学报,1937(3):445–472.
[19] 黄人.中国文学史[M].杨旭辉,校点.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287.
[20] 徐昂.益修文谭[M].南通:翰墨林书局,1929.
[21] 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34:144.
[22] 许世瑛.读赋偶得[J].艺文杂志,1994(12):17-21.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 Fu Criticism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N Tiantian, SUN Fuxuan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15, 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discipline system, literary criticism also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ts “literariness”. In terms of Ci Fu criticism, there are two changes: one is the change from the macro level of political education to the modern literary concept; the other is the change from the micro level of the article to the modern appreciation system. Thi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i Fu criticism; transformation
I206
A
1006–5261(2020)06–0066–07
2019-12-26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8BZW113)
靳田田(1993―),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孙福轩(1971―),男,山东济宁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