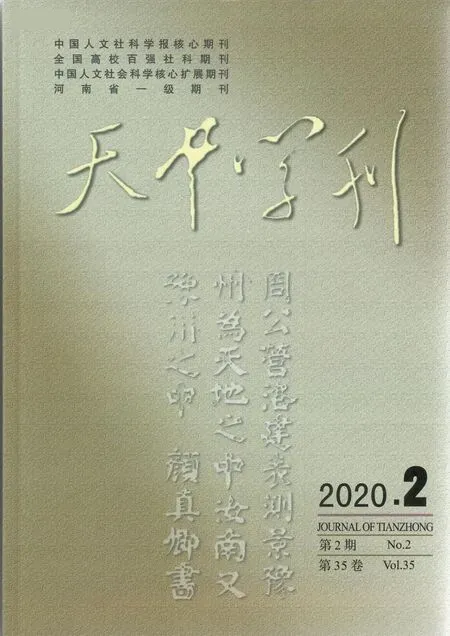简析近代小说中的湖湘文化内蕴
侯运华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们不仅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更迭中留下矫健的身影,也给湖南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结构、民间风俗。当近代作家描述文明冲突、展现社会动荡、建构武侠世界时,总是绕不开湖南这个精彩的对象,因而留下了关于近代湖湘文化的多维书写。学术界尽管有很多关于“近代小说”“湖湘文化”的研究成果,但将其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发表。本文撷取近代谴责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中关涉湖湘文化的文本,希望借此剖析中国近代小说中的湖湘文化内蕴及其价值。
一
晚清以来,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引导改良变法,湖南总是走在全国的前列。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以汉族身份帮助满清政府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一方面使很多湖南人靠军功跻身社会上层,改变了湖南社会原有的架构;另一方面也引发同代和后世民族意识强烈者的不满,讥讽其甘为满族统治者奴才。陈宝箴主湘以来的改良举措和创办时务学堂,既招揽了梁启超等维新干将,使湖南成为维新变法的试验田,也使谭嗣同、唐才常、蔡锷等杰出人才脱颖而出。这些人事,均成为近代小说创作的素材。
正因为湖南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实践的领先省份,所以即便不是湖南人,要表现维新变法思潮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不得不将叙事空间置于湖南。江苏常州人李伯元1903年创作的《文明小史》共60回,前12回叙述湖南永顺府发生的故事。小说第一回即暗示时代背景:“他在京时候,常常听见有人上摺子请改试策论,也知这八股不久当废。”[1]3柳知府的话,告诉我们叙事时间应当在庚子事变至作品发表的1903年前。当时的永顺府是什么状态呢?“却说湖南永顺府地方,毗连四川,苗汉杂处,民俗浑噩,犹存上古朴陋之风。虽说军兴以来,勋臣阀阅,焜耀一时,却都散布在长沙、岳州几府之间,永顺偏处边陲,却未沾染得到。所以,他那里的民风,一直还是朴陋相安,执固不化……所以,到这里做官的人,倒也镇日清闲,逍遥自在。”[1]1这段描述一方面凸显出永顺府民风的纯朴,为后面外国矿师被抓铺垫;另一方面,以偏僻之处尚有传教士来此凸显湖南近代社会变迁。那么,全局观察,湖南省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小说叙述柳继贤知府到任前,70多岁的老友姚士广为其饯行,柳讨教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姚曰:“要兴一利,必须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谈。就以贵省湖南而论,民风保守,已到极点,不能革旧,焉能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话,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头,原因我们中国都是守着那几千年的风俗,除了几处通商口岸,稍能因时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一处不是执迷不化,扞格不通呢?总之,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1]2从一个饱学之士口中对湖南省整体情况进行概括,描绘出士人眼中的湖南镜像,并提醒好友,不可操之过急。显然,李伯元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应该慢慢改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对于湖南当初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改革措施是有所保留的。
李伯元并未参与湖南的维新活动,而且对以开矿、办学堂、训练警察等为标志的改革措施并不熟悉,也不认可,如何表现方能扬己所长、抵达真实境界呢?身处上海、谙熟中西文化冲突的李伯元选择了传教士及其活动导致的生活嬗变这一巧妙视角。独特维度的选择,使文本以文化切入表现对象,展示出近代中国偏僻一隅发生的巨变。《文明小史》第2回通过握手这一细节,描述了柳知府的略通洋礼节与永顺县知县不懂洋礼的窘迫:“见面之后,矿师一只手探掉帽子;柳知府是懂外国礼信的,连忙伸出一只右手,同他拉手……末了方是首县,上来伸错了一只手,伸的是只左手,那矿师便不肯同他去拉,幸亏张师爷看了出来,赶紧把他的右手拉了出来,方算把礼行过。”[1]9京城来的与湖南本地的,差别还是很大,能否适应洋礼节,已经成为评判官员水平的标准。在《文明小史》中,作家明显是肯定异质文化的:第15回在洋关码头,看到外国人执法认真,赞扬其“真正是铁面无私”;第16回借姚老夫子的口,赞扬“外洋各国”“并不把唱戏的当作下等人看待”。第8回传教士告诉刘伯骥:“这个佛教,是万万信不得的。你但看《康熙字典》上这个佛字的小注,是从人从弗,就是骂那些念佛的人,都弗是人。还有僧字的小注,是从人从曾,说他们曾经也做过人,而今剃光了头,进了空门,便不成其为人了。”[1]56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否定其非人类特征,亦即解构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即便是在体现文化基础的物质层面,作家也能选取特定对象凸显两类文化在湖南永州的差异,如在谴责小说中,西装不仅是御寒遮羞的工具,还是身份的标志,也是文化载体。《文明小史》对西装的多重价值有详细展示,如第8回叙述刘伯骥被傅知府追捕,向传教士求救后,换一身西装,便换了身份,不仅原来排斥他的和尚惊讶,他还随传教士到府里成功救出了同伴,可见西装所具有的强势文化色彩。
在《文明小史》里,传教士们往往极力了解、熟悉中国文化,以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西方文化;同时,他们利用外国侵略者在战争胜利后逼迫中国当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治外法权,干涉地方政府的司法权、人事任免权等,有时也能保护百姓免受地方官员欺压。《文明小史》第8回所写的外国传教士即如此,他不仅把“我们中华的话……学得很像,而且中国的学问也很渊博。不说别的,一部《康熙字典》,他肚子里滚瓜烂熟”。当刘伯骥请求他帮忙时,他并没有因为素不相识而拒绝,而是尽力帮助刘伯骥。《文明小史》第15回里,贾氏兄弟在苏州附近一个小镇上遇到的站在路边向行人发放“劝人为善”书籍的外国人,应该也是教会人士。显然,在李伯元的认知里,与外来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已处于劣势,因此无论是在价值判断还是道德取舍方面,作家均倾向于西方文化。唯其如此,小说中的地方官员才特别惧怕外国人,且对于学习外语的行为持肯定态度。小说描写地保纪长春来报,西门外高升店里的店小二打碎了外国人一个茶碗,知府便让首县跟他一起去拜访外国人,并送两桌燕菜酒席,以免外国人需索。当听说首县的两个儿子在跟着姓张的西席夫子学英语时,马上说:“原来世兄学习洋文,这是现在第一件经世有用之学,将来未可限量,可喜可贺。”[1]6这个情节耐人寻味——既表现出湖南偏僻地方也开始学习洋文,外来文化的侵入已经成为事实;也凸显出国人对外国人的恐惧。当然,这是文化隔膜造成的恐惧,但其中也隐含着对外来文化的悄然认同。
对外来文化的恐惧与认同,加上庚子事变后地方官员对待外国人态度的谦恭,使得传教士等能够蔑视政府官员的权威,干涉地方政府的执法。《文明小史》第9回叙述到衙门要人,教士道:“我如今问你要几个人,你可给我?”“我们传教的人,于你们地方上的公事本无干涉,但是这几个人都是我们教会里的朋友,同我们很有些交涉事情没有清爽,倘或在你这里,被他逃走,将来叫我问谁要人?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找你知府大人,立时立刻就要把这几个人交我带去。”傅知府表示他们是会党,还没有审问,有所犹豫时,教士道:“这几个人,同我们很有交涉,你问不了,须得交代于我,上头问你要人,你来问我就是了。”“这些人是同我们会里有交涉的,你不给我,也由你便,将来有你们总理衙门压住你,叫你交给我们就是了。”[1]57–66传教士口气不容置疑,显然没有把知府放在眼里,因为他已经非常熟悉中国国情:“原来这传教士自从来到中国,已经二十六年,不但中国话会说,中国书会读,而且住得久了,又很喜欢同中国人来往。”[1]56这里,凸显出永顺府虽然偏僻,毕竟也被外国势力浸染已久;传教士熟悉地方官员的畏惧心理,知道利用洋面孔和背后的国家力量行动,且毫无顾忌。最终,传教士成功带走了那几位想要的人。因此可以说,《文明小史》真实呈现了湖南地方的中外文化冲突整合景观,再现了近代湖湘文化的艰难处境与挣扎镜像。
局部的中西文化比较,已经在李伯元的小说中分出高下,整体的中西文化考察,则具有更重要的文学价值。身为湖南作家,向恺然的武侠小说就具有鲜明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作为主要表现侠客行侠生活的小说,武侠小说一直以中国传统武术为叙事焦点,部分文本涉及道家、佛家文化的比较,却很少涉及西方拳击术。《近代侠义英雄传》则将西方大力士作为刻画霍元甲形象的陪衬写进文本。小说描述两位西方拳师比武的场景:“两人出场,对着行了一鞠躬礼,并不开口说话,分左右挺胸站着。随即有两个西人出来,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西装中国人在后面,先由中国人向看客说明比武的次序,原来用种种笨重的体育用具,比赛力量,最后才用拳斗。”[2]776仅仅是出场情景,就与中国传统比武情况差异巨大。第50回描写他们开始拳击比赛时,无论其所戴拳击手套,还是立在中间的两个西洋裁判,抑或是白力士与黑力士斗拳的场面,都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观感。与西方拳师交手几次、对其技击特点有所认知后,霍元甲比较中西技击的异同:“外国武艺,在没见过的,必以为外国这么强盛,种种学问都比中国的好,武艺自然比中国的高强。其实不然,外国的武艺可以说是笨拙异常,完全练气力的居多,越练越笨,结果力量是可以练得不小,但是得着一身死力,动手的方法都很平常。不过外国的大力士与拳斗家,却有一件长处,是中国拳术家所不及的。中国练拳、棒的人,多有做一生一世的工夫,一次也不曾认真与人较量过的,尽有极巧妙的方法,只因不曾认真和人较量过,没有实在的经验,一旦认真动起手来,每容易将极好进攻的机会错过了。机会一错过,在本劲充足、工夫做得稳固的人,尚还可以支持,然望胜已是很难了。若是本劲不充足,没用过十二分苦功的,多不免手慌脚乱,败退下来。至于外国大力士和拳斗家,就绝对没有这种毛病。这人的声名越大,经过比赛的次数必越多,功夫十九是由实验得来的,第一得受用之处,就是无论与何人较量,当未动手以前,他能行所无事,不慌不乱,动起手来,心能坚定,眼神便不散乱。如果有中国拳术的方法,给外国人那般苦练出来,我敢断定中国的拳术家,绝不是他们的对手。”[2]1033–1034如果向恺然不是精通中国传统武术,也知晓外国拳击的行家,是不可能进行如此透彻的比较的。小说中对西方技击重实践特点的肯定,凸显出作者对西方文化实证特征的认同。同时,小说叙述黄石屏接连治好德国患者戴利丝和雪罗的赘疣,而她们均为被德国医院院长诊断非得动手术才能治好的病号。黄石屏用几根金针所展示的神奇折服了这位六十八岁的院长,他不但向其虚心请教,还让黄石屏在他身上点穴实验,以体会中医医术的微妙处。可见作者并不盲目排外,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体验,对中西文化进行客观、理性的评判。这样,其小说所描绘的武侠世界就不再停留于技击层面,而是进入文化的深层结构,解析中西文化的优劣,进而使其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较深的文学内蕴。
二
湖南能够在中国近代领风气之先,起主导作用的是湖南人。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还是维新变法兴起前后,湖南先贤皆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豪气、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舍生取义的精神。近代小说《洪秀全演义》《近代侠义英雄传》等就成功塑造了曾国藩、谭嗣同等湖南人形象。透过这些形象,我们可以剖析凝聚其中的民族意识、侠义情肠和牺牲精神。
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连载于1905年在香港创刊的《有所谓报》和1906年出版的《香港少年报》附张,是一部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小说。作者黄世仲是位革命家,其小说既有鲜明的革命意识,也有明显的民族立场。他在“例言”中直言:“惟是书全从种族着想,故书法以天国纪元为首,与《通鉴》不同。”坦言创作该小说的目的是“以传汉族之光荣”。受种族思想制约,该书以歌颂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将领为主,对曾国藩形象的刻画就别有内涵了,如叙述曾国藩准备组建团练时,“一面修书致罗泽南、杨载福、塔齐布三人,说明奉旨兴办团练,求他相助的意思。那三人原是一勇之夫,自接得曾国藩的书信,那懂得民族的大道理,只当有一个侍郎肯抬举他,好不欢喜,都不约而同,先后到曾国藩宅子里听候差使”[3]137。作者将三人参与操练团练归于不懂“民族的大道理”,亦即不明白民族之别,视之为情愿做异族的奴才。第17回写道:“且说洪秀全大军既定了衡州,立即出榜安民,一面赏恤各军士。此时湘省人民皆知洪氏大势已成,且又知得光复山河的道理,都恭迎王师,助粮馈饷的不计其数。于是洪秀全声威大震,移檄各郡,远近多来归附。”[3]150湖南百姓拥护洪秀全的大军,显然是因为其为汉族队伍,这表现出作者对湖南人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否定态度。这里,有广东籍作家不理解湖南人的原因,也凸显出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尴尬处境:站在国家立场上,曾国藩等人是挽大厦于将倾的盖世英雄,平定了叛乱,使百姓重归和平生活;站在民族立场上,他们是民族的叛徒,帮助异族镇压汉族同胞,是双手沾满汉族人鲜血的刽子手!可以看出,在中外文化冲突维度之外,还有满汉民族冲突的内蕴存在。
湖南人生存于中外文化冲突和满汉民族矛盾的夹缝中,便有了较外省人更激烈的主体意识。他们一方面怀有救世情怀,希望先开一省新风,然后扩大到神州全境;另一方面,一旦改革失败,他们也承受了远超负荷能力的重压,于是,产生了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即如此。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第1回就从谭嗣同就义写起,提到他的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后,推测“两昆仑”之一是大刀王五,展开叙述其学武成名的故事。第4回再次写谭嗣同在北京的生活。谭嗣同生性极好武艺,十几岁的时候,就长恨自己是个文弱书生,不能驰马击剑,每读《项羽本纪》,即废书叹道:“如今的人,动辄借口剑一人敌,不足学的话,以自文其柔弱不武之短,殊不知要有扛鼎之勇、盖世之气的项羽,方够得上说这一人敌不足学的话。如今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岂足够得上说‘学万人敌’的吗?”[2]56可见,谭嗣同是一个胸有大志、抱负非凡的男子汉,他蔑视天下男子没有项羽的气概,接着反思荆轲只有吞并秦政的气概而缺乏制胜的技能,为其空有大志、壮志难酬而感慨不已。这样的描写,是借项羽、荆轲等传世英雄来衬托谭嗣同,尽管此时的谭嗣同还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
小说刻画谭嗣同的形象时,并没有聚焦他如何参与维新变法活动,而是描写他如何醉心剑术、热心接纳武艺高强的好汉,包括大刀王五。第4回写到王五认识不少宫中人,在谭嗣同就义前几天,就得到了信息,连忙送信给谭嗣同,表示愿意亲自护送他到安全的地方。在这生命攸关的紧急时刻,谭嗣同不是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是决心从容就义。他笑道:“这消息不待你这时来说,我早已知道得比你更详确。安全的地方,我也不只有一处,但是我要图安全,早就不是这么干了。我原已准备一死,像这般的国政,不多死几个人,也没有改进的希望,临难苟免,岂是我辈应该做的吗?”[2]57慷慨赴死,决心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沉睡的民众,凸显出谭嗣同超越同侪的觉悟和看淡生死的品质。王五被深深感动,既惭愧自己不读书,“不知圣贤之道”,也后悔自己差点热心办错事:“我很悔不该拿着妇人之仁来爱你,几乎被我误了一个独有千古的豪杰。”[2]57谭嗣同被杀以后,深受感动的王五哭了三天三夜,甚至不愿意待在北京了,一个人跑到天津客居,因为他不想听人们谈论谭嗣同的事。这样的描写,直接呼应了谭嗣同的少有大志,将其形象完整凸显出来了。从描写手法看,既有正面的语言描写、行为刻画,也有侧面烘托,从而将一位舍身报国的湖南志士形象留在了近代小说人物形象画廊中。
从曾国藩到谭嗣同,作为近代小说形象系列的组成部分,湖南人形象的数量不算多,但价值却不容忽视。曾国藩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敢于担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立下了举世罕见的功勋,其意义在于维持了已有的政权和统治秩序。谭嗣同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传的维新变法思想,立足于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是要撼动封建统治大厦中他们认为不合理部分,其意义在于除旧布新,实现君主立宪制。这两个形象的延续,建构起中国近代小说人物形象的有序延伸,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缩影。
三
近代小说中的湖湘文化内蕴,不仅表现在中外文化的冲突整合、湖南人物形象的凸显方面,也表现在近代小说对湖南社会现实、民间风俗的描写方面。小说中或直接描绘或间接刻画的现实场景和风俗画卷,可以让读者认识到近代湖南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独特的民风、侠风,进而让读者理解湖湘文化的深层内涵。
前述《文明小史》对湖南永顺府中外文化冲突的表现,属于特殊的现实存在。这种存在落实到社会现实中,就不仅仅是传教士从官府要走几个人那么单纯了,反而会融入很多细节之中。如小说对金委员越位擅权、柳知府心存厚道的描写,就反映出近代中国地方政权权威的解构与懂洋务者挟洋自重、干预执政的社会现实。金委员是何来头呢?“且说那湖北制台派来的金委员,是个候补知州,一向在武昌洋务局里当差。从前出过洋,会说英、法两国的话,到省以后,上司均另眼相看。”[1]11柳知府处理涉外事件而耽误了武童们的科考,武童围攻高升店后,“柳知府又吩咐首县,把捉住的人,就在花厅上连夜审问,务将为首的姓名查问明白,不要连累好人。金委员嫌柳知府忠厚,背后说这些乱民拿住了,就该一齐正法,还分什么首从?柳知府晓得了也不计较”。带头闹事的黄举人被抓住了,提了上来,不肯认罪,金委员就要打他,首县说:“他是有功名的人,革去功名,方好用刑。”金委员翻转脸皮说道:“难道捉到了谋反叛逆的人,亦要等到革掉他的功名方好办他吗?”首县无奈,只好先打他几百嘴巴,又打了几百板子。柳知府因为没有革去黄举人的功名就打他的板子,心上老大不愿意,说:“如果打死了外国人,我拼着脑袋去陪他,金委员不该拿读书人如此糟蹋,到底不是斯文一脉!”第二天,柳知府便说要自己审问这桩案件[1]20–21。柳知府想保住读书人的颜面,是传统观念;金委员强势干预,强调法律至上,是西方理念。表面看来,金委员是正确的,其实不然。金委员没有任何执法权,却干预政府执法,表现出其挟洋自重的心理优势以及其背后所依靠外国势力的强大。这种现象的直接描摹,揭示出永顺府虽然位居偏僻之处,仍无法抵挡外来势力的侵扰。长沙、常德等湖南大城市中,所受外来势力的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即便是言说侠义的武侠小说,也借武侠故事凸显现实。《江湖奇侠传》通过赵家坪之争反映出清末民初乡村争夺良田的现实。赵家坪是“一块大平原,十字穿心,都有四十多里”,“这坪在作山种地的人手里,用处极大。春、夏两季,坪中青草长起来,是一处天然无上的畜牧场;秋、冬两季,晒一切的农产品,堆放柴草”[4]30。杨天池返乡寻养父母时帮助平江人击败浏阳人夺得赵家坪,无意间将昆仑派拖入与崆峒派的对立之中,此后正邪各派加入,导致江湖上门派林立,纷争不断。纷乱世相实为向恺然对民初中国政治现状的摹写。《江湖奇侠传》第5回所叙杨祖植夫妇江中失去儿子(杨天池)后花费1400两银子买裁缝钟广泰的小儿子(杨继新)的情节,既凸显了杨祖植夫妇作为世家子不愿老太爷、老太太因为失去孙子出现意外的孝心,也透出贫穷人家只能卖儿养家的困境。第16回描写向闵贤到衡阳书院读书时,专门提到“那时衡阳书院的老师,是当代经学大家王闿运”,显然这是作者有意在武侠小说中融进现实生活的内涵。
湖湘文化存在于文化构成的各个层面,蕴含民族心理深层内涵的民俗和独特的江湖规矩,均承载有值得探究的文化内蕴。《文明小史》第1回概括当地风俗:“这永顺府一共管辖四县,首县便是永顺县,此外还有龙山、保靖、桑植三县。通扯起来,习武的多,习文的少,四县合算,习文的不上一千人,武童却在三千以外。”[1]11开卷即重点介绍永顺府的特点——重武轻文。也正因如此,该地形成了强悍好斗的民风,稍有委屈就爆发冲突。当柳知府因为处理涉外事件而延缓考试时,那班武童便群起闹事:“且说那班应考的武童,大都游手好闲,少年喜事之人居多,加以苗、汉杂处,民风强悍,倘遇地方官拊循得法,倒也相安无事,如若有桩事情,不论大小,不如他们的心愿,从此以后,吹毛求疵,便就瞧官不起。即如此番柳知府提倡新学,讲究外交,也算得一员好官。只因他过于巴结洋人,擅停武考,以致他们欲归不得,要考不能,不免心生怨望。”[1]12由此凸显出此地民风的强悍和居民性格的刚烈。想一想沈从文笔下的虎雏、柏子,想一想近代慷慨捐躯的谭嗣同、陈天华等湖南人,就能感受到湖湘文化熏陶出的刚烈特质。
近代社会的风云激荡,不仅赋予湖湘文化以开放、慷慨的特性,相对自信的文化选择和偏处一隅的湘西环境,也使湖湘文化具有排外、保守的性格。《文明小史》描写当地居民得知外国矿师来探矿,他们或抱怨柳知府要将所有的山卖给外国人,“咱们没有了存身之处”,或因为祖坟在山上,外国人来挖矿,“岂不要刨坟见棺,翻尸掏骨”[1]13?或认为自家房子要拆,或认为风水要被破坏等,纷纷起来闹事。这种描写,一方面表现出湘西人对外来文化的不了解,唯恐外来势力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官方忽视民情,对所做决定没有任何解释,造成误会。如此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很明显的,它会促使地方势力更加团结,一致对外,如第4回描写绅士们得知金委员没有待黄举人革去功名就打板子时,联合起来找柳知府理论:“忽见门上拿了一大把名帖,说是合城绅士来拜。柳知府忙问何事?……门上道:‘也不知为的那一项?恍惚听说是为了黄举人没有详革功名,金大老爷就打他板子,所以大家不服,先来请示老爷,问问这个道理,倘若不还他们道理,他们就要上控。’”[1]27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政权,是由地方绅士维持的,当外来势力侵入时,他们必然会极力抗拒,以保持原有的规矩,稳定已有的秩序。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形成的独特景观,同样是地方风俗的组成部分。
然而,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表现出的民俗就直观得多了。向恺然年轻时曾游走各地,亦熟悉江湖规矩,因此,其武侠小说中便充满各种风俗的展示。例如在《江湖奇侠传》中,有对争水陆码头旧例的介绍:“他们争水陆码头的旧例,只要是行走得动的,不论老少男妇,都得从场去打;不过老弱妇孺在后面,烧饭、挑水、搬石子、运竹竿、木棍;不愿从场的,须出钱一串,津贴从场的老弱。”[4]44有对迎接御赐全部道藏真经习俗的描绘:“襄阳府的陆知府大老爷,三日前就传谕满城百姓,要虔诚斋戒,焚香顶礼的迎接。所以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外摆设香案。”[4]693有对押镖行船规矩的叙说:“照行船的惯例,凡遇顺风,总得行船,风色不对,就得停泊。”[4]720有对江湖规矩的简介:“你不知道各处水旱的强人,最踌躇不敢轻易动手的,只有三种人:第一是方外人,如尼姑和尚之类;第二读书人,譬如一个文士装束的人,单独押运多少财物;第三就是这类单身珠宝行商。因这三种人的本领,平日在江湖上都少有名声,不容易知道强弱。”[4]1078–1079还有对湖南婚俗的叙述:“湖南的风俗极鄙陋,凡是略有资产的人家,不论如何不成材的儿子,从三五岁起,总是不断地有人来做媒。若是男孩子生得聪明,又有了十多岁,百数十里远近有女儿的人家,更是争着托了情面的人来作媒。”[4]1115其他还有对苗族法师作法败敌和苗族人喜欢骑马射猎、擅长施毒等的刻画,皆可看出向恺然写民俗、叙规矩均有明确的目的,即为表现人物性格、推动叙事情节服务。《近代侠义英雄传》亦聚焦风俗展示,如第7回先详细介绍掼交的制服与规则,再交代了黄包袱的典故:“江湖上的规矩,不是有本领的人,出门访友不敢驮黄色的包袱。江湖上有句例话:‘黄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泪。’江湖上人只要见这人驮了黄包袱,有本领的,总得上前打招呼,交手不交手听便。有时驮黄包袱的人短少了盘川,江湖上人多少总得接济些儿。若动手被黄包袱的打死了,自家领尸安埋,驮黄包袱的只管提脚就走,没有轇轕。打死了驮黄包袱的,就得出一副棺木,随地安葬,也是一些没有轇轕。”[2]101若非熟知内情的人,是很难明白其中规则的。向恺然的武侠小说不仅写江湖规则,还描述行业习惯,如第28回描写湘阴县米贩子的行规:“凡是当米贩子的,每人都会几手拳脚,运起米来,总是四五十把小车子,做一路同走,有时多到百几十把。不论是抬轿挑担,以及推运货物的小车,在路上遇着米车,便倒霉了。他们远远的就叫站住,轿担小车即须遵命站住,若略略的支吾一言半语,不但轿担小车立时打成粉碎,抬轿的人,坐轿的人,挑担的人,推小车的人,还须跪下认罪求饶,轻则打两个耳光,吐一脸唾沫了事,一时弄得性起,十九是拳脚交加,打个半死。”[2]420–421看似平铺直叙的叙述,却把特定社会里米贩行业的规矩展示了出来,同时也彰显出湖南民风的强悍。
综观中国近代小说中的湖湘文化,相关小说非常鲜明地凸显出湖南人的纠结,即在对待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上会有相互矛盾甚至截然相反的认知。不仅仅是对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即便是对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所以,湖南人的纠结,也是中国近代志士仁人的纠结,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纠结:从国家层面论析,我们都是中国人;若从民族意识论析,则有满汉之分。探究成因,有四个方面:其一,在国家意识尚未建构成功之际,人们的国家意识无法凸显,往往以相对狭隘的民族意识评判是非;其二,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关口,国家意识自觉凸显,民族意识隐退,所以曾国藩、左宗棠们挺身而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赢得生前身后名,也招来众多非议声;其三,若从民众心理考察,两百多年的奴才教化,使得人们没有自主意识,产生苟活乱世的不可取的心理,所以存在普遍渴求所谓太平盛世的心态,对任何可能引发冲突、暴乱的元素均持排拒态度;其四,尽管已有梁启超等人倡导公民意识,但是近代中国公民意识的产生极为艰难,更不要说普及了,即便是到了当下,公民意识的缺失依然是文明社会建设的重大障碍。因此,苛求当时的作家对笔下人物采取客观、科学的态度不可取。但是,矛盾现象的存在却启发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进而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
从流派角度论述近代小说的价值,则发现这些反映湖湘文化内蕴的小说,分属于谴责小说、旧派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而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翻新小说等流派中没有典型文本。究其成因,乃近代湖南人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故对谴责现实的作家而言,自然选择其作为表现社会思潮、中外文化冲突的对象,尽管李伯元并非湖南人。身为湖南人的平江不肖生,则充分发挥熟悉湖南武林故事、民间风俗的特长,利用两度留学日本所建构起的中西文化积淀,于文本中表现风俗,为湖南社会画像,并展开中西文化比较,凸显出开阔的文化视野。至于《洪秀全演义》中涉及的曾国藩形象,实在是因为要描写洪秀全的人生经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根本绕不开湖南人曾国藩,对其民族意识的剖析,恰恰说明湖湘文化中保有传统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