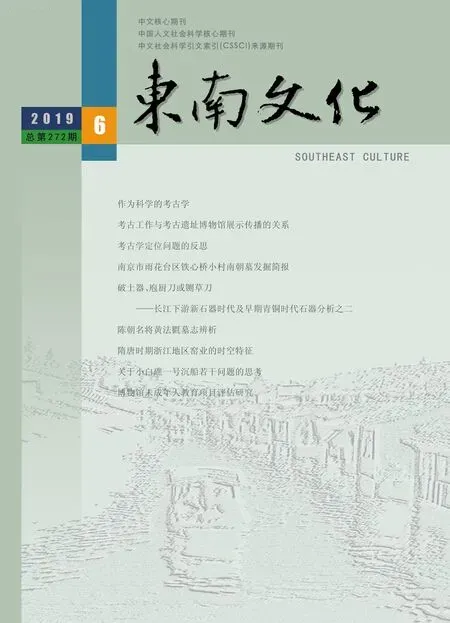历史文物的解读与信息主导型陈列的构建
魏 敏
(成都博物馆 四川成都 610000)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服务理念、现代媒体技术和新型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博物馆展览模式由传统的以实物为核心的艺术品陈列向信息主导型陈列转变。系统的、综合性的文物解读对于构建展览故事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金色记忆——中国出土14世纪前金器特展”“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等文物专题展围绕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展开,以文物组合的形式传递信息,使专题性的文物展示得以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结合,同时注意将重点文物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点安排在展线的重要位置,起到调动观众观展情绪和控制展览节奏的作用。
一、信息主导的博物馆展览模式
博物馆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而“展示”的模式却一直随社会发展而变化。传统意义上博物馆以古代艺术品为展示核心,对艺术品的解释遵从就简原则,即尽量减少其他辅助信息,让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展品本身。而这种仅从视觉观赏的角度营造展陈氛围和通过展柜、灯光、展具的优化设计来烘托展品的展示方式,对于大多数不具备鉴赏能力和相关历史背景知识的普通公众而言,难免显得晦涩。同时,现代媒体技术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也使传统的以实物为核心的展示方式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20世纪80年代,新博物馆学代表人物路德米拉·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指出,“博物馆展览中的物品必须被视为‘去脉络化’(de-contexting)的普通物品,只有为其重构信息脉络,才能让参观者重新认知它们,使其能够在建立记忆、联系和想象空间中发挥作用”[1]。大卫·狄恩(David Dean)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信息主导型展览”(information-oriented exhibition)的概念[2]。在新的展览体系中,展品本身不再是展览的唯一焦点,其已转变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实证,且这种展览模式比简单的器物排列显然更具教育意义(图一)。莉萨·罗伯茨(Lisa C.Roberts)也认为信息在展览中应该发挥核心作用:“选择、分类、安排展品仅仅是基础性工作,展品本身起到的作用取决于展览的设计者希望它们传达的信息。”[3]
近年来,信息主导的传播模式也逐渐成为中国博物馆展览的发展趋势。但从目前来看,中国博物馆的信息主导型展览多见于以民俗文物或近现代文物为主的展览,这类展览的共同点是展品观赏性不强,但文化内涵丰富,与现实生活联系较为紧密,因此不得不深入挖掘展览内涵并依靠大量辅助设施来对文物内涵进行阐释。虽然浙江省博物馆“越地长歌”、南京博物院“江苏古代文明”、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等不少以历史文物来表现区域文明发展史的历史文化陈列,都体现出信息主导的特色,但是大量历史文物专题展却仍有相当强烈的“艺术品展示”的意味。尽管不少以历史文物为主的展览中也采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或希望通过新颖的标题来吸引观众,但是在展览结构和展品组织方式上仍未有实质性突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物阐释视角和方法的限制:在展览中,历史文物大多被视为脱离原生环境的物品,按照其时代、类型、质地、用途或出土地等形成的分类方法和展示体系无法揭示文物与文物之间、文物与遗址之间乃至遗址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5]。同时,对考古材料几乎不作任何加工的直接使用,导致展示内容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物的本体信息,无法对其内涵、价值及背后的文化、思想进行深入解读,难以达到“透物见人”的展示高度。因此,根据展览主题,即展览所希望传递的文化内涵来合理地甄选、组织文物,并以考古学为核心,对博物馆展陈中的考古文物和资料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系统阐释,使文物能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相联系,赋予其情节性和故事性,才是信息主导型陈列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信息主导”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文物尤其是精品文物在展览中的地位。相反,文物所带来的历史真实感和实证意义是任何辅助展项均无法取代的,精品文物在展线中的合理定位对于调动观众情绪、控制展览信息的传递节奏至关重要。而如何才能在“信息主导”和“文物展示”之间找到平衡,合理规划展览的主题线(信息线)与文物展示的重点线、亮点线?近年部分文物专题特展的展览策划或可为探索信息主导型传播模式提供借鉴。
二、展览策划中的文物阐释与信息传递
中国作为文化遗产大国,博物馆以丰富的、高品质的各类文物为题材的文物专题展相当普遍。这与文物本身作为文化标志和文明象征物的特殊地位有关。文物自身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足以令人惊叹,因此文物解读多围绕文物本体的纹饰、铭文和器物组合展开,反映器物的制作工艺及其代表的文化属性和文明高度。而这种相对单一的解读模式所导致的信息传递的程式化,最终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若将文物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思考,打破以考古出土地为单位的原生器物组合,将其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相联系,是否可以为人们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现象提供新视野?
1.文物组合与文化阐释
在各类文物专题展中,青铜文明展最引人瞩目,展览或通过各个时期青铜器组合反映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或集合某一特定区域、特定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精品反映区域青铜文明的发展面貌,均带有强烈的艺术品陈列的色彩。而成都博物馆于2018年推出的原创性展览“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特展”(以下简称“秦蜀之路展”)却打破了以往青铜文明展的展览范式,在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川陕两地青铜文明的特异性和文化联系。“秦”指秦岭及其以北的八百里秦川;“蜀”指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古蜀族聚居区域;“路”则指由关中南下,翻越秦巴山脉,进入四川盆地的早期蜀道。据文献记载,蜀道成为国家官道是在战国晚期金牛道开通之时,而要探究战国之前的蜀道发展史,则需从考古材料入手。青铜器作为商周时期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物,对于构建商周时期秦岭南北“早期”蜀道的发展面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展览框架的搭建以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时代和叙事主题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分为“序篇(云横秦岭)”“蜀与中原”“凤鸟齐鸣”“秦入西蜀”“尾声(大蜀道)”五个部分。“云横秦岭”阐释了秦岭在中国地理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交代了由秦岭、巴山地分割而成的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三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蜀与中原”旨在通过商代汉中平原、关中平原、成都平原三地青铜器的组合所体现的文化关联性表明当时从关中平原南下,越秦岭经城固、汉中平原到成都平原,已是沟通蜀地与中原地区的重要路线之一。“凤鸟齐鸣”以凤鸣岐山、周人兴起为背景,讲述早期中央王朝的中心从河洛地区转移到关中地区,穿越秦巴山脉的原始谷道对于沟通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作用日趋重要。与此同时,蜀文化的中心由三星堆转移到金沙,迎来了古蜀文明的第二次发展高峰。该部分通过关中出土西周青铜器与成都平原金沙、十二桥文化的相关器物形成对比,阐明西周时秦岭南北青铜文明的文化互鉴。“秦入西蜀”以成都平原和汉中平原出土战国青铜器为展示重点,反映从秦国、蜀国南北并立到秦并巴蜀、秦人治蜀的历程,着重介绍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蜀道——“金牛道”的开通、发展和重要作用。最后以“大蜀道”作结,阐释了商周时期秦岭南北就已开启的文化交流对战国之后蜀道发展的深远影响。在文物组合和阐释方面,展览打破了常规的以区域考古发现或遗迹单位成组展示的模式,根据各个部分所需体现的时代特征和主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作为切入点,配合其他能够与之联系的、反映主题的文物进行展示,阐释商周时期秦岭南北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展览期间,策展团就通过文物组合来表达展览主题所传递的有效性进行了观众调查,对现场观众发放了350份观众问卷。在问及对展览主题的理解时,275位观众将答案锁定在“商周青铜文明所体现的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这一选项上,即近80%的观众能够有效理解展览主题,而在现场随机进行观众访谈的结果也表明观众对展览所要表达的主题是高度认可的。
无独有偶,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于同年推出的“金色记忆——中国出土14世纪前金器特展”(以下简称“金色记忆展”)虽然汇集了国内40家文博单位的350套先秦至元代的文物精品,以时代为序梳理了中国金器的发展脉络,但展览关注的并不限于金器的器型发展和工艺演变,而是将其置于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来考察其意义,从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碰撞,中西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同地域、民族的审美意识、生活情趣与观念信仰等方面阐释中国独特的黄金艺术。序厅的图版分别介绍了“世界最早的黄金制品”和“中国黄金的起源”,奠定了整个展览文化交流的基调。整个展览按时间线分为“初现——夏商西周时期”“盛放——春秋战国时期”“融汇——秦汉时期”“耀世——魏晋隋唐时期”“异彩——宋元时期”“专题展示:黄金面具”等部分,每个部分既在时代背景下解读金器的发展面貌,又通过考古出土的金器解读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如“盛放”部分通过对西北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北方长城沿线的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以及南方荆楚地区出土金器的风格、工艺进行对比,既体现出当时中国南北文化的多样性,也显示出春秋战国时期空前频繁和活跃的文化交流,并特别强调了欧亚草原文明对中国西北、北方地区金器制作的影响;“融汇”“耀世”两个部分以汉唐丝绸之路兴起、发展、繁荣为大背景,阐释金器所呈现出的中西方文化交相辉映的繁荣局面及最终在唐代迎来了中国金器发展的巅峰;“异彩”则在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城市生活高度发展的时代特征下,阐释了金器艺术与当时社会风貌、观念意识的密切联系,同时展现西夏、辽、元等富有民族特色的金器。更难能可贵的是,策展团队在展品组织上高度契合了文化交流的主线:明清金器作为皇室贵族的身份象征,其繁缛华丽代表了中国金器制作的另一个高峰;但其与文化交流的主线不符,因此将展品的时空范围划定至元代,以多域的文化视野,阐释14世纪之前中国出土金器的发展历程。这实际上也暗合了信息主导型陈列的策展原则,即根据展览主题而非文物本身的精品程度来组织展品。
2.历史考证与故事讲述
如前所述,“秦蜀之路展”以考古发掘和研究为基础,对战国之前早期蜀道的发展面貌进行勾勒,围绕器物组合展开的叙事性解读构成了展览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而“金色记忆展”根据不同地区考古出土金器的面貌勾勒了14世纪前中国金器的发展历程,并将大量历史学、民族学资料充实到图版中,与考古材料共同构建了展览所涉及的庞大历史文化背景。与上述两个展览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整合来构筑展览故事线的做法不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合西南地区十三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以下简称“盛筵展”)以《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内容为主线,采用文献与文物互证的形式,通过文物组合讲述史书中的历史文化故事。
展览根据《史记》的成书年代将展陈内容的时代下限定在西汉中期以前;“大西南”的提法扣住了展览空间范围;“见证”一词阐明了此次展览采用文献与文物互证的表达形式,即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展览框架的搭建将考古发掘、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紧密结合,以时代为序,以空间为叙事单元,呈现西南夷各族群独特的文化面貌及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最后以“中华一统 丝路延绵”作结,通过“秦灭巴蜀”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两大历史事件,阐述西南青铜文化消亡和君长林立局面的终结。展板中数处引用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用以辅助观众找出展出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实例(表一)[6]。例如,展览的“滇王受印 笙歌宴舞”部分结合《史记》中“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等滇王受印的记载来组织展品。滇王金印(复制品)采用独立柜展出,并配合贮贝器、铜鼓、铜俑、铜枕、扣饰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还原古滇国独特的文化风貌。再如,“中华一统 丝路延绵”的主题阐释结合了《史记》中“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的记载。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开辟了一条北起犍为、南达平夷的交通大道,可乐是必经之地。展览选取了赫章可乐的“武阳传舍”铁炉作为该部分的重点展品。“武阳”是在今天的四川彭州,属犍为郡,“传舍”即古代驿站,是反映汉代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的实证。由此历史故事、历史考证与考古文物被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展览亦通过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来提起观众的观展兴趣。如“夜郎自大”是家喻户晓的成语,策展团队采用动画的形式还原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汉使者出使滇国、夜郎国时都被问及“汉与我孰大”的场景。展览现场的定点观察发现,观众对这个媒体展项表现出极高的兴趣,有效缓解了观展疲劳[7]。

表一//“盛筵展”文物与文献互证表
针对该展览的观众调查,结果显示80%的观众都曾阅读过《史记》,无形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相对于“秦蜀之路展”和“金色记忆展”依靠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构筑故事线的做法,这也是该展览的最大优势所在,即绝大部分观众在观展前就对展览所涉及的时空背景有所了解,为理解展览的主题和思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3.信息传递与艺术欣赏
强调展览的主题阐释围绕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展开,以文物组合的形式传递信息,但并不意味着展览放弃了对精品文物的重点阐释和艺术烘托。相反,精品文物应作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点被合理地安排在展览的重要位置,起到调动观众观展情绪和控制展览节奏的作用。“秦蜀之路展”将国宝级文物“何尊”的展示位置安排在展览序厅,采用了典型的艺术品陈列方式,其用意是在展览之初就激发起观众的观展热情。而不同于传统艺术品的展示,何尊临近的展板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对其铭文内容进行了解读,并以本次参展的青铜器图片在何尊展柜后悬空拼成了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图二)。这一设计不仅突出了何尊本身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虽然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含义不同,但这一词组的出现表明当时“中国”的概念已经萌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这与展览所要传达的商周时期早期“蜀道”的开通对文明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展览主题是高度一致的。“盛筵展”将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房屋模型铜扣饰作为反映滇文化的重要实物置于第四单元“滇王受印笙歌宴舞”展示内容中。文物置于中心柜,背景展板上附有房屋模型铜扣饰的照片、线图及说明文字。文物正左方有等比例放大的房屋模型铜扣饰模型。同时,放大的模型也能使观众更好地观察文物细节信息,加深观展印象。由此,重点文物的艺术化展示与文物的信息阐释充分结合,给观众带来文化与视觉的双重享受和观展体验。
更为经典的案例是湖南省博物馆于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对公众开放的特展“根·魂——中华文明物语”(以下简称“‘根·魂’展”)。展览以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为序,分“文明起源”“青铜时代”“文明奠基”“天下一统”“文化交融”“大唐气象”“宁静致远”“太和盛平”“开启新纪元”等九个部分,却只选用了30件精品文物置于13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中,每件文物都享有超过40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充分渲染了展品的可看性和观赏价值。而突破传统展陈方式的是每一件展品都被置于立体的历史时空当中,从展品的器型纹饰、社会功用、艺术演变脉络、社会影响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策展人认为“中华文明的进程呈多向度、多维度展开,而非单线延展……将展品还原于时空坐标中,多向度梳理其发展脉络,查找其在各个坐标体系中所在位置,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位解读,以此呈现文明的绚丽多彩”[8]。例如,“文明起源”部分选用了甘肃省博物馆藏鯢鱼纹彩陶瓶,除了对文物的常规性说明外,展板上还介绍了器物的特征、主体纹饰的历史演变和象征意义,同时以点带面地阐释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彩陶文化的发展面貌;再如“青铜时代”部分选用了湖北省博物馆藏曾侯乙墓铜鉴缶,文物解读包括曾侯乙墓的介绍、器物铭文和纹饰、奇巧设计(结构),最后延伸拓展介绍了战国至清代温酒器的演变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策展人照顾到了普通观众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将专业性的描述用图解的方式非常细致、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亦值得其他文物专题展借鉴。
三、小结与探讨
“秦蜀之路展”“金色记忆展”“盛筵展”的展品组织虽都采取文物专题的形式,但又与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专题展有着本质区别:从对展品的解读到展览故事线的构建,再到通过具体的展陈设计来平衡文物组合的信息传递和重点文物艺术审美之间的关系,专题性的文物展示得以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结合,使其带有强烈的“信息主导”色彩。“根·魂”展的展品组织虽不局限于某一类文物,在展示手法上有典型的艺术品展览的意味,但展览对文物的解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亦是将艺术赏析和信息传递完美结合的经典案例。这些展览的策划思路和基本方法也可为其他类型的文物专题展提供借鉴。
1.多学科的综合解读
博物馆展览的阐释方式从不是独立发展的,它始终以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将复原文化历史、复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重建文化过程作为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三个目标。以伊恩·霍德(Ian Hodder)等为代表的后过程考古学家则认为在考古材料的阐释方面,应该更加关注人类的世界观和认知因素的解读。“秦蜀之路展”的文物解读即跳出了器物研究的表述性框架,赋予其文化意义;同时,多学科研究的发展也使博物馆对文物进行多层次的综合阐释成为可能。例如“盛筵展”虽然从《史记》的视角出发,但内容却高于史书记载,囊括了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丰富、立体地重构了先秦至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文化面貌。
2.展览故事线的重构
对文物或文物组合进行的多学科综合解读,并不是将各种研究成果简单叠加置于观众面前,而是希望由此科学地构建一条能够为普通观众所理解的展览故事线,并通过相应的文物组合讲述故事。“秦蜀之路展”的策划以考古学为基础,通过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和重构为观众呈现了先秦时期一条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文化通道,并围绕这条道路的起源、发展、兴盛展开;而“盛筵展”则将《史记》与真实的考古材料紧密结合,将历史故事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两种展览故事线的构建方式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专题展也有借鉴意义。
3.重视文物本体的解读
如前文所述,强调展览的主题阐释围绕打破原生遗迹单位的器物组合展开,并不意味着展览放弃了对文物本体的解读,重点展品在展线中的合理穿插对于调动观众情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秦蜀之路展”的观众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在问及观众希望展览能够补充哪些内容时,350名受访者关注的选项按人数多少依次为“青铜器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77人)、“不同历史时期青铜器造型、纹饰、工艺演变”(74人)、“青铜器用途、功能介绍”(67人)、“青铜器制作工艺介绍”(49人)、“区域文明所体现的文化交流”(42人)、“青铜器铭文内容介绍”(42人)等(图三)。针对“盛筵展”的观众访谈也表明大部分观众并不满足于展厅中的文物信息介绍[9]。可见,对于大多数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普通观众而言,对历史文物本身的描述性、知识性的阐释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点。而如何通过多样的、生动的展览形式将大量晦涩的文物信息转化为观众所能理解的形式,则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思考。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博物馆需要通过实践来建立历史文物的阐释模型:根据展览主题将“碎片化”的学术信息通过故事脉络的重建进行整合,同时围绕文物本身的历史、艺术价值进行细节阐释,而且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信息阐释应有机结合并合理放置在展览信息的各个层级上。阐释模型的构建不仅涉及千差万别的历史类博物馆,还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考古文物进行系统分类梳理,才能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机制,这需要在长期实践中进行探讨。而历史文物的阐释模型能否在大众传播中有效应用,尚需进一步的观众研究作为评价依据,通过大量的观众抽样分析、研究和数据统计,才能达到客观评估、科学验证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此为契机,建立文物信息传播的观众评估体系,并建立博物馆展览研究与实践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致谢:本文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特聘教授李明斌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1]Ludmilla Jordanova.Objects of Knowledge: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Museums.The New Museology.London:Reaktion Books Ltd,1989:25.
[2]Gary Edson,David Dean.The Handbook for Museum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153.
[3]Lisa C.Roberts,quoted in James W.Volkert.Monologue to Dialogue.Museum News.1991,70(2):46.
[4]Gary Edson ,David Dean.The Handbook for Museum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153.
[5]李林:《从信息到故事:浅谈博物馆展览的传播策略》,宜宾市博物院《西南半壁》,文物出版社2018年。
[6]表格引自彭学斌:《策展人对一个展览标题的解读》,重庆三峡博物馆官方微信推文,2018年12月6日。
[7]资料由国家社科基金“博物馆展陈中考古文物的信息解读与重构研究”课题组提供,调查时间:2019年1月,调查人员:李林、任琳、陈家宝、周茜茜、史霄曜、刘雨曦。
[8]湖南省博物馆:《根·魂——中华文明物语》,岳麓书社2019年。
[9]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