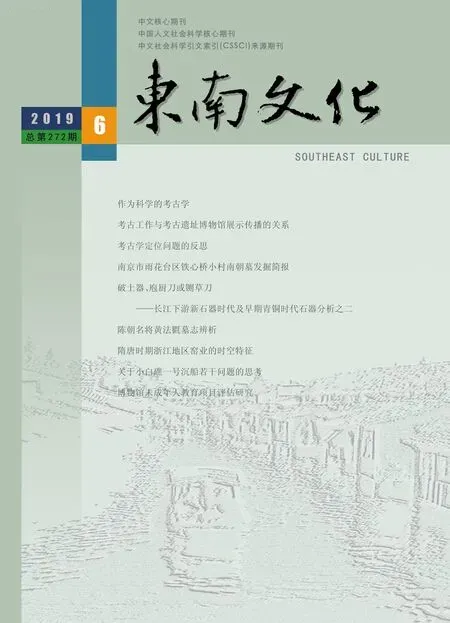宗教物件在博物馆展览中的意义变形
——以“深河远流——南传佛教文化特展”为例
李精明
(1.莆田学院工艺美术学院 福建莆田 351100;2.台湾艺术大学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所 台湾新北 22058)
内容提要:物件从原生场所转移到博物馆后,物件意义的生成会导致意义变形。物件的意义变形,打破了真实再现的理想。庙宇中的一部分宗教物件被赋予了神圣性,但是当宗教文物转移到博物馆之后,便会产生意义变形。以“深河远流——南传佛教文化特展”为例,宗教物件从庙宇到博物馆展览,再配合网络在线展示,宗教物件的神圣意义转变为知识性、美学性以及娱乐性。为了建立物件与神圣性的关联,策展方可以通过现地保存、举行宗教仪式、展示原生环境的场景、营造神圣氛围等手段来达到加强物件与原生文化脉络联系的目的。
一、真实再现的理想与意义变形的现实
1958年,台风将台湾阿美族的太巴塱Kakita’an祖屋吹倒,雕刻着神奇传说的柱子被转移到“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博物馆。对于博物馆来说,这些柱子是珍贵的民族志文物,应该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以免百年后消失殆尽。而祖屋柱子对于太巴塱部落来说是祖灵安身之处,它们应该回到部落并由部落的祭师对其举行仪式,从而留住祖灵。物件从宗祠转移到博物馆常导致物件意义的改变,继而引发文化的冲突及其后续的协调工作。又如,西非某国某部落仪式中所使用的一件雕刻品失窃后,辗转流入美国一家美术馆,“沦落”为一件艺术品。以至于该国古物部长埋怨,“这件雕刻品原先对该部落的意义已荡然无存,留下的不过是它的艺术价值而已”[1]。
宗教物件从庙宇转移到博物馆,不仅是场所的变更,还意味着意义变形(metamorphosis)。所谓变形,意在表明一种质的变化,如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2],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Jean-Baptiste de Pan⁃afieu)的《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描述的生物形体变化[3]。变形是一种剧烈的变化,当神像从庙宇转移到博物馆,它的神圣性可能消失,世俗的意义生成,即产生了意义变形。与意义变形相违背的是真实再现,一些博物馆声称通过收藏和展览,再现了某一地的文化,如在展览中以场景模型(diorama)呈现物件的原生背景,达到真实的再现。一般观众对博物馆声称真实的再现也并不怀疑,尤其新闻媒体反映了博物馆真实再现的刻板印象,例如,“博物馆再现”常见于新闻标题中——“印第安纳博物馆再现历史”“古道博物馆再现青海灿烂历史文化”等标题。然而,在博物馆的真实性,只能是物件的真实性,而非原生文化的真实或意义的真实。弗德利希·瓦达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认为博物馆物件的真实性是指“直接证实它与事件过程(有担保的、求证过的)之间的关系,因它本身与过程有关”[4]。物件的真实性不能保障物件脉络和意义不变,相反,博物馆还原物件脉络,追求真实的再现,已成为一种理想状态。物件一旦被博物馆收藏,“它的意义会产生决定性变化”[5]。
现代博物馆使命的转移突出了博物馆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的价值。传统博物馆注重物件的搜集、保存;现代博物馆注重观念的表达,“博物馆并不只处置物品,更重要的是处理我们暂时可以称为观念的东西,即关于世界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的看法”[6]。近年来,新成立的以移民、战争、人权、性别等议题为导向的博物馆,诠释了博物馆如何处理观念,即博物馆通过物件的收藏和展示发表观点。博物馆愈是追求真实,“愈是剥夺博物馆自身的诠释性”,“丧失博物馆的主体性”[7]。博物馆真实再现的理想背后,是意义生成的现实。曾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甚至认为博物馆是各种变形的汇聚之所,“它取消帕拉狄昂的意义,取消圣徒与救世主的意义;排除对神圣性的联想,排除有关装饰与财富的特性,以及有关相似或想象的特性”[8]。
如何才能观察到物件的意义变形?生物变形可以通过观察生物结构、机能的改变而发现,如虫化茧成蝶。语言的意义变形可以通过不同脉络下语言的意义比较而发现,如成语“空穴来风”在不同历史时期意义的变化[9];语言的意义变形还可以参考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关于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关系的理论[10]。符号的意义变形可以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关于意指作用的言谈方式中找到线索[11]。实体物件的意义可以放在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但由于实体物件与观众的互动、情感层面更明显,因而物件的意义不是语言学、符号学能够充分探讨的。
物件意义变形的前提是物件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且物件具有多种意义的可能性,“一个物件值得一千种意义”[12]。物质存在的不变,并不能担保意义的不变,如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分析图腾信仰来源时所表明的,“事物的神圣性质实际上与它的任何内在属性并不相关”[13]。从不同视角理解物件,如历史的、艺术的、经济的、地理的、科学的、文化的视角,物件的意义则变得不同。不同人、不同时间和怎样使用物件等因素都可能改变物件的意义[14]。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Smith)认为物件的意义易受多种形式的意义建构——设计、背景对象、视觉和历史表现形式、整体环境等,甚至不同观众各自的不断阐释也是意义的来源[15]。从亨里埃塔·利奇(Henrietta Lidchi)在《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一文中的论述来看,博物馆机构、物件的符号意义、展览文本、展出方式等影响着物件意义[16]。宗教物件的场所改变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意义变形?哪些因素影响物件的意义变形?以下以宗教物件为例,分析物件在庙宇、博物馆展厅、博物馆网络平台三个不同场所的意义。
二、宗教物件神圣性的来源与博物馆的仪式性
既然物件与意义不是固定的,一个物件具有多种意义的可能,在物件客体上找不到意义来源的根据,那么宗教物件的神圣意义如何产生?依据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的观点,神圣性来源于事物在信奉者心中激发的宗教情感,“这种感情赋予了事物神圣特性”[17],这是一种崇敬之情,其中混合着爱和感激。当一个客体“在人类心中表达它的表象具有自动引起或抑制行为的力量——而不顾任何有益或有害后果的考虑——时,这个客体就激起了崇敬的感情”[18]。宗教情感是在信奉者心灵中产生的集体情感,“事物的神圣性是由集体对该事物的情感建立起来的”[19],并且集体情感只有依附于物质客体时才能被人意识到。通过仪式等行为赋予物件神圣性,“举行仪式的地点、仪式中使用的器械、祭司和苦行者都是由此获得神圣性的”[20]。神圣性不固定在单一物件上,物件分享了神圣性,物件是神的外在可见形式。
仪式及其物件之所以能激发信奉者的崇敬之情,是由于信奉者对安慰、依靠的需要。社会的压力以精神的方式施加于大众,由于这种作用方式迂回、模糊,普通大众无法看到在人自身之外的威力如何作用,于是,信奉者想象“优于自己并为自己所依据的存在”[21],即神的存在。信奉者在社会生活中本身具有崇敬的情感,崇敬的情感使神性依附于物件。宗教物件激发了这种情感,并对信奉者产生内在的、精神的压力作用(图一),把神圣性赋予实体物件,使得该物件转变成为优于凡俗的物件。宗教极力把神圣性的物件绝对隔离于凡俗的物件,形成了神圣与凡俗的对立。两者的对立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两者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二是神圣的事物被认为是更优秀的东西,凡俗的事物禁止接触神圣的事物[22]。
综合上述分析,博物馆的展览物件能否激发崇敬之情,赋予物件神圣性,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博物馆是否为一个仪式性空间,能否激发集体崇敬情感;二是展览设计是否体现了神圣与凡俗的隔离;三是参观者是否具有崇敬之情,例如是否为宗教信奉者。首先分析第一个因素,博物馆的空间是否如同庙宇,从而将观众引向神圣性的体验。博物馆与庙宇在词源、建筑实体等方面确实有某些关联。Museum的词根来自希腊语mouseion,原意是供奉司艺术与科学的九位缪斯女神的神庙[23]。黄光男认为,“不论希腊时代的神庙(mouseion)就是日后的博物馆,或是近代的博物馆很多来自寺庙的演化,在两者之间有依存关系”[24]。两者不仅在建筑上有关联,博物馆与宗教似乎还在精神追求上有某种相似性。史蒂芬·威尔(Ste⁃phen Weil)认为,美国博物馆作为公共建筑,“体现了当代社会文明最高雅的渴望”,“当代美术馆已经逐渐取代了过去大教堂的社会角色”[25]。在艺术家追求永恒和无限、不断超越的创作中,评论家在艺术家身上发现了找寻人类精神的力量,因而,艺术博物馆被视为世俗宗教或“沉思的殿堂”[26]。然而,庙宇与博物馆的关联仍旧比较薄弱,主流的观点认为博物馆仍旧是教育的、休闲娱乐的场所。例如,胡珀-格林希尔(Hooper-Greenhill)认为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充当教育和学习的资源[27];塔奇·罗斯会计事务所(Touche Ross)对英国的民意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博物馆应具有教育性和娱乐性[28]。
博物馆是否具有仪式性?卡若·邓肯(Carol Duncan)在《文明化的仪式:公共美术馆之内》一书指出美术馆空间不是中性或隐形的,而是一个仪式性的空间。不过,博物馆与庙宇既相似,又存在差异。邓肯认为博物馆由仪式构成,博物馆作为世俗的甚至反仪式的文化,“其实也充斥着仪式的情境和事件”[29],“就像绝大多数的仪式场所,博物馆的空间是谨慎的设计和隔离,并且被保留到特殊事件的使用场合性质”[30]。在博物馆,观众也需要遵循一套特定的礼节,博物馆的仪式也制造出了类似庙宇仪式的效果,即识阈性(liminali⁃ty)。博物馆的仪式性“如同民俗仪式暂时撤销了正常社会行为的限制性规则”,“打开一个让个人从实际生活考量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的空间”,“以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情绪来看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身的世界”[31]。仪式性的空间除了识阈性的特点之外,它还是一个表演的场所,“任何仪式的场所是一个设计好以便让表演发生的地方”[32]。在博物馆中,有顺序的展览动线、展示物的安排及照明和建筑上的细节提供了舞台和脚本,让观众在博物馆表演仪式。但这种仪式不同于宗教的仪式,正如作者在书名所暗示的,它是一种文明化的仪式(civilizing rituals),具有教化观众的作用。
博物馆的仪式性空间引导观众进行美学沉思和知识学习,观众通过博物馆的仪式激发的是愉悦、充实之感,而非崇敬之情。庙宇仪式的经验有特殊的目的,通过牺牲、严格考验或启发来“给予或翻新地位、纯净化、或重新建立对世界和自我的秩序”[33];博物馆仪式的结果与此类似,“看过博物馆后会有一种得到启发的感觉,或者在精神上觉得充实和完整”[34]。但两种体验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相信有一个作为我们依存的世界存在着;另一个建立在“生动和客观的理性”的基础上。博物馆也隔离了展品和生活中的功能性物品,使得两者在品味上隔离,前者比后者品味更高,但展品与功能性物件的区别并不属于神圣与世俗的隔离。可见,博物馆的仪式没有生成出如同宗教的神圣性。博物馆的识阈性空间产生的审美沉思,可以视为将神圣精神的价值转移到世俗化领域的做法,它以美学理论作为评判物件优劣的标准。博物馆的识阈性空间引导知识学习,则教育参观者以科学知识作为评判的标准。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两大面向组织和建构了物件的秩序及其意义。博物馆的哪些展示技术实现物件意义的变形?以下以个案分析。
三、庙宇、博物馆、网络场所对比:案例分析
台湾新北市永和区的世界宗教博物馆之“深河远流——南传佛教文化特展”(以下简称“深河远流”)展出的物件,以佛教造像、民间神灵造像、修养与信仰生活物件为主,其中佛陀像是该展览的大宗。展览除了博物馆室内的实体物件展示之外,还搭配了网络在线展示。以下对比分析庙宇、博物馆、网络三个空间中物件的摆设或展示的差异,从而考察宗教物件的意义变形。结合笔者在实地走访庙宇、参观“深河远流”、浏览“深河远流”官网所观察到的情况,从仪式性、摆设/展示、观者、物件、空间、制度、脉络等角度,比较物件在不同场所的特点。
(一)仪式性的强弱
庙宇本身作为举行仪式的空间,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博物馆虽然也具有仪式性,但比较弱,观众可以在博物馆比较随意地走动,少有跪拜、烧香之类的仪式举动。网络平台则完全没有仪式性,观众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网页,身体举动不受限制。
(二)摆设/展示的逻辑
庙宇中的物件按照信仰仪式的功能需要摆设,博物馆或网络则依据知识分类展示。“深河远流”主要物件的展示分为“风格与造像”“禅修与信仰生活”两大部分。“风格与造像”依据地域、造像风格、信仰类型划分为缅甸蒲甘王朝时期、缅甸掸族风格、缅甸曼德勒风格、泰国与柬埔寨风格、特纳民间神灵五个部分,这体现了知识分类的逻辑。神圣物件进入博物馆收藏,以世俗知识范畴进行归类,失去了神圣性[35]。
(三)标志性的身体动作
在庙宇的标志性动作是“拜”和“念”。庙宇是烧香拜佛、念想、沉思的场所,通过非日常的身体动作加强了场所空间的神圣性。在博物馆的主要身体动作是“观看”,它解放了身体的体力动作,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观看,引导参观者调动视觉审美和对知识进行思考。网络平台的身体动作为“搜”。物件图像不会自动出现在眼前,网民需要主动搜索想要查看的资料,并通过鼠标的点击进入或退出,它引导了观众主动挖掘、搜索文字和影像的兴趣。
(四)佛陀像的完整性要求
寺庙中的佛陀像力求完整性,禁止刻意破坏。在博物馆中常常展示残损的佛陀,而且博物馆中支撑和固定佛陀神像的方式在庙宇中不会暴露出来。“深河远流”中佛陀头像用一根金属插入支撑固定(图二),立像则用木架缚住两侧(图三)。在印刷品和网络图像中,有时刻意截取佛陀局部影像。“深河远流”网络展示中运用视觉传达的设计方法采用出血版、单张挖版图展示佛陀像(图四),这体现了博物馆对艺术审美的偏向。
(五)物件的背景
寺庙中的佛陀像背景常常是繁复的装饰图案,周围布置了各种器物;而在博物馆展示中,宗教物件通常背景颜色单一,常常没有背景装饰,突出了物件的造型(图五)。“深河远流”的物件摆放在纯白色几何形展柜上,背景也是白色,少数物件背后设计有河流的光影背景效果。在网络展示中图像经过挖版处理,背景为视觉设计的主色调,背景为代表河流的曲线图案(图六)。
(六)物件意义的参照
在庙宇中,物件的意义除了在实际使用中产生,一个重要的参照是佛教原典的阐释。博物馆和网络的展示中,物件或图像的意义常常受到策展文本的影响。如“深河远流”的主题为“佛教文化”,各部分的展览文本也以此为主轴,主要介绍造像特色和风格。
(七)展览中主客体关系
走进庙宇的人群以信徒为主,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信众与圣物(如佛陀)的关系。在博物馆,主客体关系则转变成观众与物件的关系;在网络平台则转化成网民与物件图像之间的关系。在庙宇和博物馆,圣物或物件禁止触摸;而在网络平台,网民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放大或缩小、上拨或下滑,增添互动的娱乐性。关系的改变也就表明了物件意义的变形。
(八)主客体距离与视角
物件在庙宇中的摆设营造了信众与佛陀的距离感。信众通常在有限的视角移动,一般不会绕到佛陀的背面或头顶观看。而在博物馆中观众可以自由移动,有时候展品会设置围栏,禁止触摸展品。很多情况下鼓励观众围绕着物件观赏,“深河远流”摆放在展场中间的佛陀像即可以从背面观看的。在网络上的物件影像则是摄影师选择了最佳视角呈现出来,观众可放大或缩小影像,观看细节。
(九)空间里的辅助纹样
在庙宇中,墙壁、柱子上有时雕刻有佛陀生平事迹等,而在博物馆或网络平台展示的纹样则是视觉设计的辅助图形。“深河远流”则以流畅的曲线构成的河流元素作为装饰纹样,在印刷品、网络影像上重复出现。
(十)禁止和保护措施保护的对象
庙宇禁止饮酒、大声喧哗,有时候禁止拍摄神像等,这些规定是为了维护空间的神圣性。而在博物馆中,“深河远流”禁止拍照时开闪光灯、禁止触摸,为神像设置保护架、在神像下面垫泡沫材料等,以保护文物的珍贵性。在网络平台则通过网页代码禁止复制文字和图像,以保护版权。

表一// 庙宇、博物馆、网络场所对比
(十一)物件的文化脉络
从宗教性的角度来说,庙宇是圣物的原生文化脉络,也是其首要脉络。当宗教物件被博物馆收藏,博物馆是它的衍续文化脉络,也是次要脉络,它叠加进入物件的生命史,并与原生脉络构成了物件的完整脉络。当物件在博物馆展览的同时,搭配线上展示,物件通过摄影转化成数位影像在网络平台展出时,物件衍生新文化。衍生文化由物件发展出来,与博物馆物件的次要脉络同时存在,属于新生的临时脉络,它不会随着博物馆脉络的结束而结束。衍生文化从产生之时起,就有了独立的发展过程(图七),各个脉络共同起作用,且以次要脉络为主导,共同塑造了物件的意义。
综合上述,不同场所通过仪式性、摆设/展示的逻辑、身体动作、佛陀像的完整性要求、物件的背景、物件意义参照、主客体关系、主客体距离与视角、空间里的辅助纹样、禁止和保护措施、物件的文化脉络等,形塑了物件对于观众的意义(表一)。物件从庙宇到博物馆、再到网络平台,完成了意义的变形:佛陀等庙宇内的圣物主要的意义是它们的神圣性;在博物馆的佛陀塑像则成为知识性、美学性的代表,如“深河远流”的佛陀像代表了南传佛教文化,也代表了南传佛教造像艺术;在网络平台的线上展示则进一步去除了神圣性,在知识性和美学性的基础上强化了娱乐性的内涵。
四、研究局限与展览建议
首先,物件从庙宇里的圣物到博物馆展品以及成为网络影像,场所的改变引起物件的意义变形。引起物件意义变形的因素有很多,如仪式性、摆设/展示、观者、物件、空间、制度、脉络等,它们确切起作用的精确模式还不得而知。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他们之间哪些因素主导了物件的意义变形,或是否形成了意义变形的网络,使得博物馆外的物件进入这个网络便产生了意义的变形,这些方面本文尚未处理。
其次,物件的意义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难题。物件的意义不仅是词典里的定义、专家指定的意义,还是普通观众在具体情境中感受到的东西,三者如何相互交织影响物件的意义及其变形成为难题。沙伦·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认为物件的意义不是确定的(definitive),而是暂定的(provisional),永远都要视脉络而定[36]。物件的脉络不像文本的上下文那样相对清晰。语言符号具有比较清晰的符码,物体世界意义生成的符码及其意义生成的脉络比较模糊,因而,很难确切地描述物件的意义,讨论物件的意义变形更加困难。本文仅仅从观众的角度作出阐释。
最后,宗教物件在博物馆的意义变形是以非信众的视角进行的反思。对于信众、特殊专业背景(如神学)的观众,宗教物件的展示的意义可能又有所不同。对于不同信仰、不同专业背景的观众,宗教物件在博物馆的意义差别也是本文没有考虑到的。笔者从物件及其展览场所出发,考察宗教物件的意义,而没有考虑观众的差异。意义的来源,除了物件自身、展览空间,观众也是重要的一环,所谓意义是在观众的参观活动中产生的。展览中的宗教物件在不同群体中引起的不同意义,是日后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物件的意义变形本身有其价值,如发表观点、讨论议题、娱乐观众、形成美学体验等。然而,对博物馆来说,物件意义变形也有其风险,如对某些宗教信仰者而言,博物馆的展示会给他们造成亵渎神圣、违背原生文化群体的感受,进而造成文化冲突。博物馆作为收藏、教育、研究、展示、交流、休闲等功能的场所,不同于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庙宇,但有时需要在展览设计过程中加强与庙宇原生文化脉络的联系。以下几点展览建议供参考。
第一,物件保存过程中,如能实现现地良好保存,则应该选择现地保存,而非转移到新的博物馆空间。例如,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吾主博物馆(Museum Ons’Lieve Heer op Solder)就是现地保存的例子。第二,宗教文物主题展示过程中,通过举行宗教仪式建立物件与神圣性的关联。当寺庙现地保存只能作为理想状态时,可将宗教仪式引入博物馆,“让宗教文物的灵光得以继续散发”[37]。例如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展览“山灵敬——回返祖灵智慧的人间净土”,开展前邀请花莲县阿美族里漏部落的祭师举行传统祭仪,连接了展览与原生脉络。第三,展示原生环境的场景,重塑神圣性。单个物件的展示容易偏离原意,场景展示更具感染力。例如,位于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展示妈祖民俗活动时,展示了妈祖巡游的队伍,使人身临其境。第四,展示设计上利用灯光的光影营造神圣氛围。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常设展“慈悲与智慧——宗教雕塑艺术”展场灯光较暗,重点处采用点光源照亮,笔者观察到在参观过程中有个别观众面对展览说明行鞠躬敬拜礼仪。第五,通过空间、声音、气味,建立展览与宗教的联系,营造展场的神圣氛围。例如,“深河远流”展览过程中,音响传出的低沉声音的念诵,让人联想到佛教。还可以在气味上做文章,如通过散发进香的香味进一步加强空间与神圣场所的关联。第六,在视觉上塑造崇高感,烘托神圣性。当物件的尺寸大到一定程度,摆放在比较庄重的位置时,能够引发观众的崇高感,并将这种崇高感赋予宗教物件。例如“慈悲与智慧——宗教雕塑艺术”展览中一处玻璃柜并排展出了三尊尺寸较大的佛像,佛像基座较高,观众需要仰视观看,引来少数观众驻足敬拜。
(本文写作过程中获得台湾艺术大学艺政所黄光男教授、赖瑛瑛教授以及世界宗教博物馆卓静美主任的帮助,在此特表感谢。)
[1]〔美〕史蒂芬·威尔著、张誉腾译:《博物馆重要的事》,台北五观艺术2015年,第143页。
[2]〔奥〕弗朗茨·卡夫卡著、李文俊等译:《变形记》,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3]〔法〕让-巴普蒂斯特·德·帕纳菲厄著、樊艳梅译:《超自然变形动物图鉴》,未读·探索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4]〔奥〕弗德利希·瓦达荷西著,曾于珍、林资杰、吴介祥等译:《博物馆学——德语系世界观点》,台北五观艺术2005年,第200—201页。
[5]同[4],第185页。
[6]〔英〕亨里埃塔·利奇:《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英〕斯图尔特霍尔编,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0页。
[7]林崇熙:《博物馆文物演出的时间辩证: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考察》,《博物馆学季刊》2005年第19卷第3期。
[8]〔法〕安德烈·马尔罗著,李瑞华、袁楠译:《无墙的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42页。
[10]〔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刘丽译:《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11]〔法〕罗兰·巴特著,许蔷蔷、许绮玲译:《神话学》,桂冠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
[12]Elizabeth Wood,Kiersten F.Latham.The Objects of Experience:Transforming Visitor-Object Encounters in Museums.Walnut Greek:Routledge,2013:133.
[13]〔法〕爱弥尔·涂尔干著,芮传明、赵学元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桂冠出版社1992年,第360页。
[14]同[12],第135页。
[15]Charles Saumarez Smith.Museums,Artefacts,and Meanings.In Peter Vergo ed.The New Museology.Lon⁃don:Reaktion Books Ltd,1989:9,19.
[16]同[6],第204页。
[17]同[13],第219页。
[18]同[13],第241页。
[19]同[13],第463页。
[20]同[13],第460页。
[21]同[13],第240页。
[22]同[13],第38—42页。
[23]〔美〕杰弗瑞·艾布特著、李行远译:《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王璜生主编《无墙的美术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24]黄光男:《楼外青山:文化·休闲·类博物馆》,典藏艺术家庭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25]同[1],第153页。
[26]同[1],第153页。
[27]Eilean Hooper-Greenhill.Museums and Their Visitors.London:Routledge,1994:140.
[28]Touche Ross.Museum Funding and Services—the Visitor’s Perspective.London:Touche Ross Management Consul⁃tants,1989:16.
[29]〔美〕卡若·邓肯著、王雅各译:《文明化的仪式:公共美术馆之内》,远流出版社1998年,第6页。
[30]同[29],第21页。
[31]同[29],第23页。
[32]同[29],第24页。
[33]同[29],第25页。
[34]同[29],第25页。
[35]廖静如:《宗教文物搜藏:神圣与博物馆化》,《博物馆学季刊》2006年第20卷第2期。
[36]Sharon Macdonald.Expanding Museum Studies:An In⁃troduction.In Sharon Macdonald ed.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2.
[37]李建纬:《历史、记忆与展示:台湾传世宗教文物研究》,丰饶文化社2018年,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