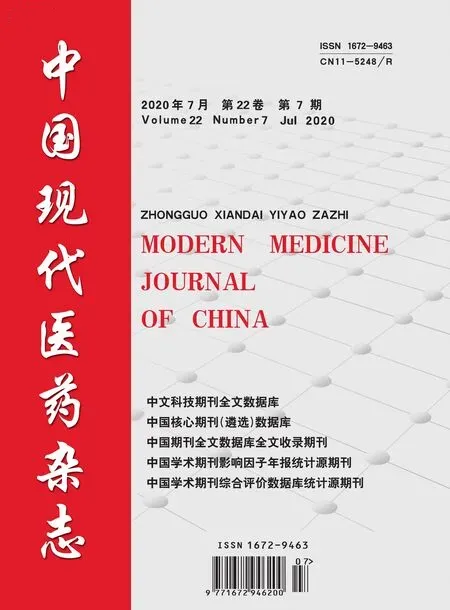分子病理学在结直肠癌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中的应用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病理学从组织学诊断逐渐发展到从细胞、细胞器到基因和蛋白分子水平检测,使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病理生理学等多个学科间相互渗透,从DNA和RNA 层面研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揭示疾病的内源性基因突变、表达异常以及外源性基因的存在,更深入、精确和全面地反映疾病的本质特征,使传统病理学从单纯的形态学诊断跨入综合性更强、更全面、更精准的分子病理学。传统的病理诊断技术不能用于结直肠癌早期诊断、指导化疗和靶向药物选择、疗效评估、复发转移监测,而分子病理学的应用增加了对结直肠癌本质的深入认识,使病理学从单纯形态学诊断延伸到精准的分子诊断与鉴别诊断、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及预后判断等方面。
1 分子病理学主要应用技术与结直肠癌分子分型
利用分子病理学技术包括显色原位杂交(CISH)、荧光原位杂交(FISH)、基因芯片(DNA 芯片或DNA 微阵列)及荧光定量PCR 技术等使病理诊断不再局限于单纯形态学检查,能够从基因和分子水平用于结直肠癌的临床诊断、个体化精准治疗和预后判断。液体活组织检查技术是基于血液、尿液、胸腹腔积液等体液样本,从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血浆miRNA 等方面检测肿瘤特异性标志物,具有无创、实时动态监测等优点,能真实反映肿瘤中基因突变频谱,用于指导临床方案制定、疗效评估及临床随访[1]。ctDNA 是由肿瘤细胞通过凋亡和坏死过程,直接释放进入外周血的DNA,检测少量样本中ctDNA的突变,可以帮助识别结直肠癌等肿瘤高危复发患者,通过动态观察治疗过程中ctDNA 的变化,帮助发现新的耐药机制,选择有效靶向药物,实时检测抗肿瘤疗效。ctDNA 表型与标准肿瘤活组织病理学检查比较,ctDNA 灵敏度为92%,特异度为98%,K-ras 和BRAF 基因突变的判读准确率为96%,为结直肠癌等肿瘤患者监测化疗反应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2]。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 repair,MMR)能够校正基因复制时出错的碱基,保持DNA 复制的准确性,避免基因发生突变,MMR 基因功能缺陷导致微卫星体长度发生变化,发生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e,MSI),参与结直肠癌发生[3]。根据MSI、K-ras、BRAF 的状态和MLH1 甲基化状态将结直肠癌分为5 种类型[4]:①pMMR,KRAS 和BRAF 野生型;②pMMR、K-ras 突变型,BRAF 野生型;③pMMR,BRAF 突变型,K-ras 野生型;④散发型:dMMR、BRAF 突变型,MLH1 超甲基化;⑤遗传型:dMMR、BRAF 野生型,无MLHI 超甲基化。结直肠癌的分子分型不仅阐明不同分子亚型结直肠癌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而且对结直肠癌的分子异质性、个体化治疗、疗效和预后判定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
2 分子病理学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与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
K-ras 基因是癌基因,在结直肠癌中主要发生第2 号外显子的12 和13 密码子突变,导致p21-ras蛋白的生长信号发生异常变化,过度的生长信号刺激细胞生长和增殖从而导致结直肠癌发生[5]。国外学者报道K-ras 基因突变率为30%~40%,突变见于第2 号外显子的第12、13 密码子(85%~95%),第3 号外显子59/6、117 和146 密码子(5%~15%)[6,7]。国内学者报道K-ras 基因总突变率为38.82%,K-ras基因第12 密码子突变率为29.7%,第13 密码子突变率为12.87%;N-ras 基因突变率为3.96%,第12 密码子突变率为0.99%,第13 密码子突变率为0.99%[8]。K-ras 基因突变与结直肠癌患者年龄、肿瘤位置、浸润深度、组织学类型及Dukes 分期无相关性,但女性或由淋巴结转移结直肠癌患者K-ras基因突变多见,结肠癌发生K-ras 基因突变多于直肠癌[9]。结直肠癌肝转移K-ras 基因突变率为42.5%,同时性肝转移K-ras 基因突变率为38%,异时性肝转移K-ras 基因突变率为47%,无复发转移结直肠癌K-ras 基因突变率为35%,K-ras G13D突变是结直肠癌异时性肝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10]。K-ras 基因突变使结肠癌患者对放疗的敏感性下降,而通过抑制结肠癌细胞K-ras 基因突变表达可提高放疗的敏感性[11]。在Ⅲ期结肠癌患者中,K-ras基因为野生型患者可以从5-Fu 联合左旋咪唑化疗中获益,而K-ras 基因突变者则不能获益,K-ras 基因第12、13 密码子为非天冬氨酸突变患者,较天冬氨酸突变患者可以从5-Fu 为基础的化疗中获得更长生存时间[12]。K-ras 基因突变后通过影响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刺激促进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扩散,且不受上游EGFR 的信号调控影响,对抗EGFR 治疗效果差,K-ras 基因突变型结直肠癌患者不能从抗EGFR 治疗中获益,K-ras 基因突变是抗EGFR 单抗疗效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以及靶向治疗的疗效预测指标[13]。 BRAF 是RAS-RAF-MEK-ERK 信号通路中RAS 蛋白的下游信号因子,是部分结直肠癌重要的原癌基因。国外研究资料表明结直肠癌肿瘤组织中BRAF 基因突变率为8.97%,均为V600E点突变[14],而国内研究数据表明结直肠癌肿瘤组织中BRAF 基因总突变率为4.14%,其中V600E占3.93%,V600G 占0.01%,D594N 占0.01%[15]。淋巴结转移的结直肠癌BRAF 基因突变检出率比无淋巴结转移结直肠癌高5~10 倍[16]。BRAF 基因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对EGFR 单抗治疗抵抗,BRAF 基因突变是判断针对EGFR 分子靶向药物cetuximab 或panitumumab 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亦是结直肠癌预后不良因素[17]。K-ras 突变结直肠癌患者不能从西妥昔单抗治疗中获益,PIK3CA 第20 外显子、N-ras、BRAF 突变与西妥昔单抗治疗反应率低相关,对K-ras 野生型的患者,增加PIK3CA第20 外显子、N-ras、BRAF 检测,可将抗EGFR 治疗获益人群比例从36.3%提高至41.2%[18]。3.2%~4.5%的K-ras 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发生PIK3CA 第20 外显子突变,是抗EGFR 靶向治疗的潜在不良预后标志[19]。Le 等[20]研究发现突变结直肠癌中K-ras 和BRAF 突变是互相排斥的,而且与左半结肠癌相比,右半结肠癌BRAF 基因突变率高,右半结肠癌免疫环境活跃,表现为MSI-H 比例高,PD-L1 和PD-1 的表达比例高。与MSS 大肠癌患者相比,MSI 型患者抗PD-1 治疗效果更好,MSI 型患者反应率为40%,20 周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为78%;MSS 型患者反应率为0,20 周PFS 为11%;MSI 其它型患者反应率为71%,20 周PFS 为67%。MSI 状态与Ⅲ期结直肠癌区域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7 个区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更多呈MSI-H 状态,而与结直肠癌患者肿瘤部位、分化程度、浸润深度、c-MET 表达和CEA 水平无关[21]。15%结肠癌发生MSI-H,尤其右半结肠癌多见,可引起结直肠癌对5-Fu 化疗不敏感,但预后好于MSS[22]。在以5-Fu 为基础的化疗方案对pMMR 和Ⅲ期dMMR 结直肠癌患者有效,可提高其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但对于dMMR Ⅱ期结直肠癌患者则无此疗效,甚至对MSI 结直肠癌患者有危害,显著降低其DFS 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23]。
3 分子病理学在结直肠癌预后判断中的应用
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治疗前后动态监测CTC 数目变化与患者预后相关,CTC 数目≥3 个/7.5ml 患者的肿瘤PFS 和OS 均显著短于CTC 数目<3 个/7.5ml的低检出患者[24]。治疗期间CTC 数目是结直肠癌患者PFS 和OS 的独立因素,进展期和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外周血中基线或治疗期间CTC 数目升高是肿瘤无复发生存(relapse-free survival,RFS)、PFS和OS 不良的独立因素[25]。外周血ctDNA 检测能实时反映肿瘤负荷水平及基因突变的动态变化,ctDNA 水平与结直肠癌预后呈负相关,在转移性结直肠癌中更为明显,突变型ctDNA 明显升高的患者预后更差[26]。BRAF 在结直肠癌中的突变率为5%~15%,在MSI-H 肿瘤中突变率明显高于MSS肿瘤,BRAF 突变多发生在第15 外显子V600E,BRAF 突变提示结直肠癌预后不良[27]。发生MSI结直肠癌患者化疗总有效率为11.4%,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为51.4%;MSS 组总有效率为7.7%,DCR 为41%,MSI 结直肠癌患者中位PFS 为19.9 个月,而MSS 患者中位PFS 仅7 个月。MSI 结直肠癌患者PFS 和OS 显著优于MSS患者,MSI 患者比MSS 患者有更好的PFS 和DCR,MSI-H 分型结直肠癌患者OS 和DFS 均优于MSS/MSI-L 分型患者,MSI 可作为PFS 的独立预测指标[28]。MSI 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明显低于MSS 结直肠癌患者,MSS 结直肠癌患者术后1、3、5年生存率为96.3%、72.2%、63.5%;MSI 患者术后1、3、5年生存率为100.0%、92.3%、92.3%。MSS 与MSI 患者术后1年生存率无明显差异,但MSI 患者3年生存率、5年生存率明显高于MSS 患者,具有生存优势[29]。K-ras 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无论使用何种靶向治疗方法,原发于左半结肠癌患者OS 和PFS 均明显优于原发于右半结肠癌患者[30]。K-ras 基因野生型结直肠癌患者中一线分子靶向药物cetuximab 或panitumumab 单抗联合化疗对携有BRAF 基因突变型患者预后生存明显短于BRAF 基因野生型患者[31]。携带PIK3CA 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可获得较长的生存期,而对野生型的PIK3CA 患者则无效,因为激活的PI3K 促进了环氧化酶2 的活性和前列腺素E 的合成,抑制结直肠癌细胞的凋亡,而阿司匹林对此有拮抗作用[32]。结直肠癌dMMR 缺失率为22.22%,淋巴结转移率高于pMMR 患者,dMMR 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为88.89%,pMMR 患者5年生存率为59.52%,二者5年生存率差异显著[33]。携带BRAF 基因突变同时存在MSI-H 结直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73%,而非MSI-H 的BRAF 突变患者5年生存率为46%,晚期直肠癌患者BRAF 基因突变提示预后较差,总体生存率仅为9~14 个月[34]。Ⅲ期结直肠癌Ras/BRAF 基因突变患者,尤其存在BRAF 突变的患者OS 和PFS 明显低于Ras/BRAF 基因野生型者,而N-ras 突变的患者预后较其他基因突变者好,Ras/BRAF 基因突变和MSI-L/MSS 状态是结直肠癌预后不良的预测因子[20]。具有BRAF 和K-ras 基因双重野生型的结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93%,而具有BRAF 或K-ras 突变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76%,BRAF 或K-ras 基因突变具有显著的预后意义,可作为MSI 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因子[35]。结直肠癌患者肿瘤组织和/或外周血RAS、BRAF 和MMR 等基因表达和功能状态的检测,在结直肠癌患者治疗预后评估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将MMR、MSI、K-ras、N-ras、BRAF 等分子检测用于结直肠癌诊断、个体化治疗和预后评估,使结直肠癌诊疗模式从传统的基于“群体化”诊治转向精准的“个体化”诊疗。分子病理学不仅用于结直肠癌早期诊断和精准的分子分型,而且能够为结直肠癌个体化、预见性治疗以及预后判断与监测提供科学依据,拓宽了病理学研究范围,能够从分子水平认识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形态特征、生物学行为。虽然分子病理诊断技术日趋成熟,但目前主要用于研究领域,真正用于临床结直肠癌等肿瘤检测的技术仍然较少,而且检测费用昂贵、操作复杂、影响因素较多,存在技术性假阳性和假阴性,仍不能完全取代目前的常规病理诊断方法,肿瘤病理诊断仍必须坚持以形态学为基础,分子诊断为辅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