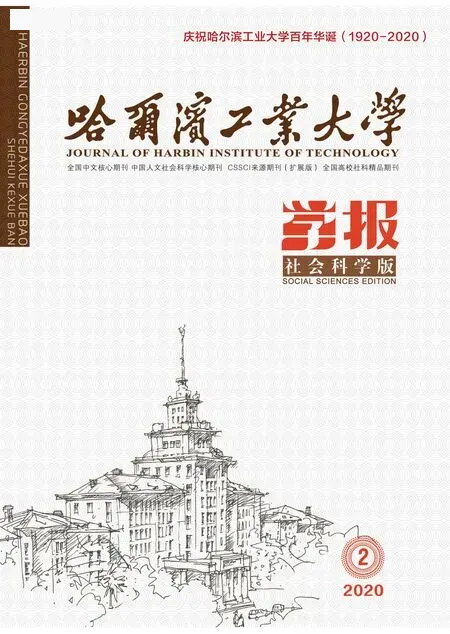双重驱力:偶像养成时代粉丝行为动机研究
——基于周杰伦和蔡徐坤双方粉丝打榜事件
韩传喜,黄 慧
(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周杰伦和蔡徐坤双方粉丝的超话榜首之争,始于“豆瓣”上“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的质疑,接下来双方又“转战”微博,演变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由周杰伦以1.1亿的影响力居于榜首而落幕。在此过程中,偶像均未公开发言,由双方粉丝合力推动此事演变为全网狂欢。针对此事,社会主流舆论中掀起了对“唯数据论”逻辑的批判热潮,从人民日报到澎湃新闻,从三联生活周刊到界面新闻,主流媒体在繁杂的舆论场中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避免此事由于参与主体的去个性化和匿名性等而陷入大范围的网络暴力之中。此外,还有对虚假流量背后的利益链的揭露,对谁是这场微博全民狂欢的制造主体的追问,以及对不同时代造就不同偶像的阐释,等等,众声喧哗,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空间。
此次粉丝打榜之争,某种程度上而言印证了当下“数据至上”的影响力判定逻辑,数据、流量、颜值等成为明星的主要衡量标准,既往所推崇的作品内容质量、明星德行等在当下似乎完全被颠覆,再加上被崇拜主体尚未在场且其中一方深陷被主流批判的境地,凡此总总,都折射出这场全民狂欢背后的深层心理动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中,周杰伦的粉丝主要以1988年到1997年出生的人群为主体[1],蔡徐坤的粉丝更偏年轻化,由此可见,成年人和青少年是粉丝打榜的主力。而处于青少年时期的群体,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和自我认知正处于动荡和不断调整的阶段,此时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又会作为其认知图式一直延续至其成年期甚至老年期。因此,对处于青少年时期的粉丝群体的价值观的引导尤为重要,对行为背后心理动机的洞察是引导其行为的前提。
一、偶像养成时代的粉丝
在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看来,粉丝是比普通人对所喜爱的对象更为狂热、程度更深的群体,其“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2]粉丝群体通过粉丝间的交流互动,实现对信息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和再生产,在此过程中创造出属于自己圈子的价值判断标准、行为准则和文化,是与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相左或冲突的文化样式。“当宰制性意识形态及其所提倡的主体性符合大众的利益时,大众便会顺从此类意识形态与主体性;反之,大众便会对抗或修正此类意识形态与主体性。”[3]费斯克强调的是粉丝行为的亚文化倾向,认为粉丝通过独具特色的“反抗”产生身体“快感”,在此期间对抗主流规训、彰显个性、实现自我。
就粉丝与偶像的关系而言,传统媒体时代,因信息传播的单向性、滞后性和传播资源的稀缺性等,粉丝与偶像间不仅在实际距离上,而且在情感和心理距离上都较为遥远,粉丝的追星与崇拜主要通过幻想和想象,是对遥远且神秘的偶像的仰望与膜拜的时代。伴随传播技术的迭代革新,人类传播进入新媒体时代,随之而来的是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参与性、共享性和传播权的普适性等变革,粉丝与偶像间的时空距离被打破,实现了类似面对面、频繁且即刻的实时互动。在此过程中,粉丝在海量与偶像相关的信息接收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即时表达对偶像的喜爱中,产生与偶像亲密无间的社交错觉,而事实上却是粉丝对“媒介人物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依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关系”[4]的“准社会关系”,这成为推动其不断投身于偶像崇拜行为中的重要驱动力。粉丝与偶像之间,借由传播技术带来的便利,建构出一种粉丝与偶像在情感上更热切、在行为上更主动、在心理上更亲密的关系模式,粉丝在此情境下陪同偶像从默默无闻到炙手可热的全过程,且因互动方式和双方关系的变化,成为其极具参与感与相关性的自我实现行为,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步入偶像养成时代。
偶像养成时代,强调偶像制造过程中粉丝参与的重要性,粉丝行为与明星的影响力、地位等具有直接相关关系,粉丝所崇拜的偶像由粉丝自主选择并通过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助力推选出来。从最早的《超级女声》中的李宇春等,到近几年大热的《创造101》中的杨超越等,再到近期蔡徐坤粉丝为其耗费精力和金钱打榜“做数据”,等等。偶像养成时代,粉丝成为明星造就的主力之一。周杰伦和蔡徐坤双方粉丝的超话榜首之争,是身处不同粉丝与偶像关系时代中的粉丝群体,就各自所拥趸的偶像进行的与其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等相关的竞争,成为当前极具代表性的粉丝群体事件。吊诡的是,双方明星均以表面不在场的方式卷入这场“地位争夺战”中,且蔡徐坤在之前因数据造假身陷主流媒体批判的漩涡。偶像养成时代,粉丝群体为了捍卫各自所崇拜偶像的地位,在想象性社交关系中所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等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的探究,对明晰其行为倾向的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二、内生动力与外部压力:双向动机驱使粉丝行为
(一)双重“快感”:反抗主流与“主流”收编
费斯克将粉丝对偶像狂热的喜爱和“越轨”行为,看作粉丝群体通过生产身体“快感”以抵制社会规训的能动性文本生产活动。粉丝文化作为由粉丝生产出来的、仅可在粉丝圈子内流行的文化类型,被费斯克归于青年亚文化的典型,是粉丝群体通过极具个性的行为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另类反叛,通过反抗成年人文化或父母文化,对主流社会准则和规训进行颠覆和尝试性再造,粉丝群体在此过程中产生“快感”、逃避社会规训,建构出一套符合所属群体利益的社会话语准则和价值观。此次事件中,双方粉丝在反抗主流和“主流”收编中彰显自我、产生身体“快感”。
首先,从粉丝群体与主流对抗方面而言,反映在社会主流舆论对此事的批判上。蔡徐坤及其粉丝因数据造假新闻、影响力与偶像自身实力不符等饱受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主流对亚文化反叛行为的规训和收编,通过传播主流所认可的价值观对此事中的粉丝群体施以规训以约束其行为。而面对社会主流舆论的批判,蔡徐坤粉丝对偶像的态度和行为似乎未受影响,反而呈现出“哥哥只有我们了”的悲壮心理,作为亚文化群体的蔡徐坤粉丝群,在与主流的对抗中通过拒斥其严肃规训,以对自身崇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行自我肯定。
其次,从粉丝群体内部的对抗方面而言,体现在不同年龄阶层的粉丝群体间的反抗与收编方面。此次事件中,粉丝的榜首竞争行为,是身处整个粉丝场域中的不同群体,因所处年龄生命周期、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时代背景等的不同而产生的认同障碍、群体隔膜甚至是代际冲突,双方就其身份地位、话语权等进行对抗与收编,在此过程中产生规训和摆脱规训的身体“快感”。且据场域理论,双方粉丝群体在同一场域中的斗争行为,是为了获取场域中具有话语权和制定规制权的有利位置而进行的权力争夺战。蔡徐坤作为偶像养成时代的明星代表,其粉丝多以“00后”为主,在经济、技术等的多重影响下,具有年轻化、彰显个性、敢于冒险但是非观、价值观等尚未明确的特点。而周杰伦粉丝以“80后”和“90后”为主,这一群体成员大都处于成年期,其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对社会事件拥有独立且成熟的认识和判断。双方的榜首争夺战是隶属于成年人文化的周杰伦粉丝,与归于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蔡徐坤粉丝之间,在粉丝场域中就彼此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行的收编与反抗行为,双方在此过程中产生收编与反抗收编的身体“快感”。蔡徐坤粉丝在挑战被视为主流明星的地位中陷入狂欢;而周杰伦粉丝则通过榜首之争证明自身地位和话语权,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对年轻群体的规训与收编,在此过程中实现另一种“快感”生产:在规训与收编亚文化群体中证明自身主流地位、彰显权威性。
(二)自我实现:情感卷入与角色追寻
桑德沃斯(SandVoss)将粉丝定义为“所有与文化文本及对象形成持续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消费者和用户。他们‘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5]。桑德沃斯强调了粉丝的情感卷入面向,再加之粉丝对偶像产生的单方面、想象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亲密感,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和维护成为由内生动力所驱使的、蕴含粉丝个体情感的自愿行为。另外,寻求他人关注和喜爱是人类天性,是个体实现归属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但个体在现实中却常是不被关注的渺小个体,这与其内心向往和追寻形成悖论进而产生失落感。在新媒体时代,因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传播权、表达权的扩大,似乎为大众带来被广泛关注和倾听的可能,但事实上却并未享有同等被倾听和关注的权利。拥有传播和表达权却不能实现被关注和倾听的个体,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借技术的便利对偶像倾注更多的情感,并将自我理想角色投射到偶像之上,偶像成为粉丝理想角色的外化,偶像对于粉丝而言是其内心深处不容侵犯的私域,是粉丝自我实现的重要场域。
此次事件中,双方粉丝群体的狂热行为,表面上是为了拥护其所热爱的偶像、为“爱豆”而战,实际上却暗含了粉丝个体对自我理想角色的维护,是寄托了粉丝个人情感的自我实现行为,粉丝在想象性社交关系的影响下为偶像的影响力和地位的维护付出个人努力,在浩瀚的网络世界中借由群体证明自身的存在感。正如周杰伦在居于榜首后,本人发布动态与粉丝远程互动,在周杰伦粉丝中再次掀起狂欢。这种看似亲密、实时的对话,实则是对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的模糊回应,但在粉丝心中却产生“偶像亲自与我对话、努力得到肯定”的狂喜之情,这对粉丝而言具有强效的激励作用。同时,对于散布在群体中的粉丝个体而言,其自我行为很难得到大范围关注,但将之融于集体后,集体行为获得有利地位或大获全胜时,基于成就折射效应,集体的成功会使个体产生与有荣焉之感,周杰伦粉丝经过几天“奋战”成功“登顶”后,粉丝QQ群中刷屏的口令红包、动态表情和周杰伦歌曲语音演唱狂欢[6]便是最好的证明。
(三)群体压力:身处粉丝圈子的个体
“社会群体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正如亚里土多德所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个人难以脱离群体,在与任何人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而存在。”[7]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与个体的自我幸福感、成就感等密切相关,群体规则因此对个体行为而言具有较强的影响和约束作用。偶像养成时代,粉丝在网络中围绕不同的粉都(粉丝崇拜的对象、客体)形成风格、喜好各异的粉丝圈子,各个圈子都有其主导性意见和群体规范,同时与其他粉丝圈子因情境不同产生竞合行为。“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圈子内关系强度很高,关系持续很久,社会网密度很大。”[8]粉丝圈子即是粉丝就某一偶像或崇拜客体而形成的人群聚合,粉丝圈子内部具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圈子成员关系紧密、互相影响,处于同一粉丝圈子的成员受圈子内核心成员的影响,与圈子内多数人保持一致而避免社会孤立或排斥。
1.社会影响:圈子核心成员左右个体行为
处于某一特定粉丝圈子的个体,其行为常受圈子中核心成员的影响。毕博·拉坦纳(BibbLatane)的社会影响理论认为:“来自他人的社会影响在某一特定情境下(他们的社会影响)的影响总量取决于三个因素:影响者的数量、实力以及与被影响者的接近性。”[9]其中,与影响者的实力相关的是其社会地位、所拥有的权力以及是否为行业专家等方面。当群体中影响者的数量占据优势、影响者的实力足以对群体内其他成员形成导向作用且影响者的行为与成员利益息息相关时,群体内个体的行为和态度便会受其影响、与之保持一致或保持沉默。
首先,就影响者的数量而言,体现在粉丝圈子内核心粉丝群和由粉丝个体演化成的新社会影响者群体方面。此次事件中,双方核心粉丝是发挥社会影响作用的主要群体,另有拥有一定社交圈和影响力的粉丝个体,借由技术赋权和社交媒体裂变式传播优势,在核心粉丝的影响下,随着参与行为的增加转变成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粉丝影响者,以其为中心在所属关系圈中传播相关信息以影响他人。周杰伦和蔡徐坤双方粉丝的打榜结果历经前者反超后者的戏剧化过程,体现了双方粉丝参与数量、参与热情和行动力的暴涨。此时,双方粉丝圈子由核心粉丝向外扩散,不断增加新的粉丝影响者,几乎涉及所有的粉丝人群,粉丝圈子的规模空前。
其次,就影响者的实力而言,体现在双方粉丝圈子中核心粉丝的实际影响力方面。核心粉丝因对所拥护偶像的资讯和日常信息的异常熟悉,在所属粉丝圈子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意见领袖,承担着对信息的传播、制作、解读和二次传播等重任,对圈子内其他成员的行为具有引领和引导作用。周杰伦和蔡徐坤双方粉丝中,均有核心粉丝作为打榜的引导者,负责打榜教程的制作和具有引导性的言论的发表和扩散。蔡徐坤粉丝以核心粉丝为主,多个小号“助力”打榜,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其边缘粉丝;周杰伦除核心粉丝的影响力外,还因其所表征的时代追忆,而使整个粉丝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剧增,粉丝个体受此影响不断为打榜“添砖加瓦”。在核心粉丝的影响和引导下,双方粉丝群体的参与度和为集体而战的信念不断强化,合力推动此事演变成全网狂欢。
最后,就影响者行为与群体成员的利益相关性而言,体现在粉丝打榜之争背后的隐含意味上。周杰伦和蔡徐坤双方粉丝的打榜之争,实际上代表两代人在明星阵营中话语权和地位的“争夺战”,是双方粉丝对自身理想投射对象的形象和影响力的维护与捍卫,且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此次事件亦是两代人自身话语权之争,打榜的胜利意味着自身话语权和地位的证实与彰显,这与粉丝个体具有直接相关性。身处不同粉丝圈子的个体,在社会影响力的效应下,促使个体不断为各自所属群体的制胜而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2.从众—认知失调—接纳:粉丝心理推及过程
特定行为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此次事件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与粉丝心理的逐层深化密切相关。首先,个体因对自我的不确定和惧怕社会孤立、对归属感的追求等而受群体内优势意见的影响,产生从众行为。所罗门·阿希(Solomon-Asch)对处于群体压力中个体的从众行为进行揭示,强调群体内多数意见对个体的影响。“人们相信,群体与自己相比,掌握着更多信息,具有更强的理解力”[10]。其次,从众行为会使对此事不了解或不赞同的个体产生认知失调感。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强调当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不一致时会产生不适和紧张感,个体为了调节自身知觉便会做出调整,从而保持二者一致以避免失调感。再次,在个体对失调感予以调节的过程中,起初因群体压力产生的从众行为,经由自我内部调节最后演变成发自内心的接纳。由从众行为到认知失调再到真诚接纳,体现出身处群体中的个体行为背后复杂的心理演化过程。此次事件中的粉丝行为背后具有同样的推进逻辑。双方粉丝先受各自群体内优势意见的影响产生从众行为,后因认知失调而采取措施,在不断的信息接收和自我调整与强化中,将其转化为内心认同之事,实现认知平衡。
在打榜过程中,双方粉丝圈子中除核心粉丝之外,在日常中不甚活跃的粉丝之所以踊跃参与,广泛传播打榜教程、制作表情包、转发与偶像相关的微博话题等,一方面是个体所属圈子中的大多数都已发起行动,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产生行动意识,即使一开始不关心或不赞同此事的个体,也可能因群体成员的影响而投入其中,形成大范围从众行为;另一方面随着事件影响力的扩大,个体的参与行为愈发频繁,起初参与意识不强的个体在多次打榜中所产生的认知失调感,随着事件的进展和参与行为的增加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逐渐将打榜之争内化为同所属粉丝圈子共同的话语权和地位之争,事关自身利益的粉丝将从众行为内化为真诚接纳之事。
(四)“部落”冲突: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
“部落”的概念源自麦克卢汉“重新部落化时代”的表述。在麦克卢汉看来,电子媒介的出现使我们重新回归部落化,人与人之间的时空限制被打破。新媒体时代,“部落”基于趣缘群体而形成,群体成员交往即时密切、互动性强,且因每个群体的喜好、风格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部落”群的场景。体现在粉丝群体中,即是以不同偶像为中心而形成的各式粉丝“部落”,不同“部落”因崇拜偶像和喜好等的不同,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和解读,“部落”间因之形成信息壁垒,彼此了解的程度远不及所属群体及偶像。且因消极事件的记忆和传播速度远大于积极事件的否定效应,粉丝“部落”常对与对方相关的消极信息记忆深刻,而关于其积极信息却不甚了解。在此消彼长之间,当偶像间存在分歧或利益纷争,粉丝“部落”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因之而增强。此次事件中,双方粉丝分属于不同的粉丝“部落”,他们的行为、意见和态度因“部落”中心不同和信息壁垒而出现偏差和隔阂。双方粉丝间的信息匮乏和负向评判尤为常见,并且,在社交媒体中随处可见粉丝间充满挑战性和攻击性的言论,这在信息相对隔绝的“部落”之间,是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粉丝对立行为的导火索。
粉丝“部落”间的冲突行为有其特有的心理机制。分属于不同群体中的粉丝,因群体的规制、对群体的认同和归属需求等而倾向于偏向所属群体,而排斥和否定其他群体,戴维·迈尔斯(DavidMyers)将其称为“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当内群体和外群体发生冲突时,群体成员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结于内在品质,导致群体服务偏差。”[11]在此期间,造成同一群体内对外群体否定观点和消极态度的不断强化,使群体间的竞争和冲突愈发激烈。此次事件之所以愈演愈烈最后扩大到全网狂欢的层面,与双方粉丝群体所受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心理作用密切相关,在此影响下不断强化既有态度。并且,在对对方行为进行归因时,也因群体服务偏差而主要进行特质归因,而忽略社会环境等的作用。正如社会主流媒体、周杰伦粉丝对蔡徐坤及其粉丝在数据造假方面的批判。可以肯定的是,数据造假属错误行为,理应受到管制和规范。但行为的发生常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社会环境。新媒体时代,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除了大众传播权和表达权的扩大等红利之外,数据和流量也逐渐成为评判媒体、明星、公司等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数据和流量已然等同于影响力。而对蔡徐坤及其粉丝的批评,却大都将其行为视作该群体的内在品质的不足和缺憾,而将社会环境等视为次要因素。减少或避免粉丝“部落”冲突,亦应从此方面入手,纠正群体服务偏差的倾向,综合考虑社会、环境等多方因素,如此,才可从根源上发掘造成此种倾向的深层次原因。
结 语
偶像养成时代,借由传播技术革新带来的红利,粉丝与偶像之间呈现出更加亲密、互动感和参与感更强的关系模式,粉丝的行为有着不同于既往幻想与膜拜偶像的时代的特点。究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粉丝个体的内在需求与所属群体的外在压力是促使其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粉丝在内外双重心理驱动力的作用下,通过偶像崇拜和追星行为进行自我理想角色和认同感建构。在对偶像养成时代粉丝行为中存在的非理智、狂热和冲突性等倾向进行批评和规范的同时,对其心理动机的探求有助于洞察粉丝行为倾向的根源:对自我认知的确认、对他人评价的关切以及对群体归属感的追求。
首先,此次事件中,相较而言更需加以了解和引导的是与成年人相对的青少年群体,处于此生命周期阶段的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尚处于不断调整的非稳定阶段,个体所认同的群体中他人的行为会成为其行为参照,而起初的模仿行为在长期浸润下又可能内化到个体的自我认知之中,成为个体自我认知图式的一部分。此次粉丝打榜中,粉丝个体的从众行为演化为内心的接纳和认同,印证了群体中他人态度和行为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形塑作用。其次,他人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人对个体的评价和意见是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参照和来源,关切他人评价并将之作为自身行事的重要参考,是个体用以避免因辜负他人期待而导致的社会拒绝和社会排斥的重要方式。此次事件中,粉丝因群体内他人行为和态度而进行自我调整,是粉丝个体重视他人评价和意见的外在表征。最后,居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一方面想要区别于其他人以彰显自我个性,另一方面又想与所属群体内成员拉近距离以获群体归属感。正如塔尔德所言,“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互相模仿的人组成的。”[12]作为社会动物的个体,对群体中他人行为的模仿是与群体成员保持密切关系、获得群体认同以此增加自我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渠道。此次事件中,大范围的从众行为即是粉丝个体为了获取所属群体的认同、避免群体排斥的行为表现。
综上,粉丝行为有其特定的心理动机,不论是内生动力还是外部压力,都是个体在社会中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自我实现行为,粉丝个体借此进行自我疏解、寻找情感依托。鉴于此,对粉丝行为中的消极面向进行批判的同时,亦要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疏通和引导。作为亚文化典型的粉丝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会随着自身影响力的提升而受到主流文化的收编,逐渐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一如“90后”群体在处于青少年时期时,其行为方式和文化亦受主流的批判,甚至一度被视为“垮掉的一代”。但随着该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其自我认知、世界观、价值观等逐步稳定并强化,早前的亚文化群体被主流收编,并成为当下主流群体中的中流砥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处于同一时代的偶像因历经年代不同而带有各式的时代印记,在对明星影响力的“唯数据”逻辑评判的同时,对粉丝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的洞察、疏通和引导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