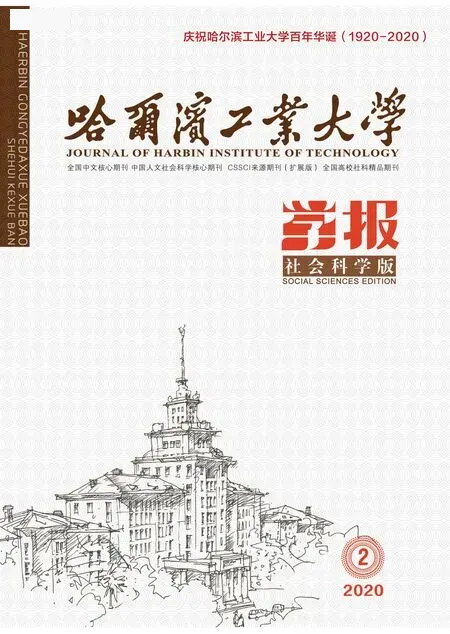贯云石文学新论
——以其在元仁宗朝的命运转向为视角
刘 育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贯云石(1286-1324),本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因父名贯只哥而依汉俗以贯氏为姓。经杨镰先生考证,其字浮岑,又曾以成斋、疏仙、芦花道人及石屏为别号[1]194-196。 《元史》卷一四三有传。在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元代,贯云石的散曲创作在其文学事业的整体版图中尤其瞩目。以最近三十余年的研究状况为例,在以贯云石为核心主题的论文中,有超过一半的成果都直接与其散曲作品相关。①这一结果来源于对中国知网上题名含“贯云石”的文献统计。具体而言,在近六十篇文章中,有三十一篇的研究对象与其散曲创作直接相关,另有七篇与此主题间接相关。从新近刊发的《贯云石及其散曲研究述评》一文中亦能够清楚看到,散曲一直是切入贯云石研究的核心角度[2]。
从姚燧惊叹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3]3422,程钜夫盛赞他二十岁时的诗文“妙年所诣已如此,况他日所观哉”[4]323,戴良评论本朝西北子弟的文学表现时直以“贯公云石”为“以诗名世”者之第一人[5],以及顾嗣立编选元诗时对他作出的“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6]等判断里都可见到,贯云石的文学才华显然不仅限于散曲。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由于其传世诗词文章的数量极为有限,如果只是着眼于这些文字本身,其实很难对贯云石的文学与人生样貌进行全面的把握和定位。因此,本文尝试将他各类体裁的创作置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综合考察,特别是关注到元仁宗朝在其命运转向上施加的某种影响,以期深入探索和理解文学本身对贯云石的意义,对其文其人作出更加细致和多元的解读。
一、“《离骚》读罢空惆怅”:贯云石在仁宗朝的命运转向
贯云石出身贵族,是元平南宋时功勋之将阿里海牙的孙子。虽然在他出生当年这位经历了传奇一生的祖辈以同样带有传奇意味的方式结束了生命[7],但武将出身的家庭背景和少数民族的自然天性仍然赋予了他优异的身体素质。友人欧阳玄在《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下文简称《贯公神道碑》)中写道:“年十二三,膂力绝人,善骑射,工马槊。尝使壮士驱三恶马疾驰,公持矟前立而逆之。马至腾上,越而跨之,运矟风生,观者辟易,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8]652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画面感十足,即使在数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让人不免为其中那个意气风发的习武少年惊叹。二十岁左右,贯云石袭父职担任了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以能力和职守的匹配度而言,这似乎是一个能够令其发挥所长的官位。《贯公神道碑》在回顾这一阶段时,以“在军气候分明,赏罚必信。初,忠惠公宽仁,麾下玩之。公至严令,行伍肃然,军务整暇”[8]652等语肯定了主人公仕途首秀的业绩,但同时也指出了他“意欲自适”的个性特点,暗示出这与严谨单一的军旅生活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性,进而为贯云石毅然解官、让位于弟的不寻常行为进行了解释。按照蒙元时期特殊的职官体制,达鲁花赤是地方政府拥有最高职权的官员,特别是元廷对充任这一职位的人提出的严苛身份要求[3]106,使得贯云石迈入仕途的起点较一般人而言其实高出许多。因此,他自主自愿地放弃这个对别人来说求之难得的官位,事件本身及其体现的道德内涵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伯夷、叔齐兄弟间的让国行为,以及孔子对此作出的“古之贤人也”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等评价[9]。从此后事情的发展来看,也正是因为贯云石解位让弟的举动中蕴藏着儒家思想所标举的高尚人格,使他纯粹个人化的这一选择引起了时为东宫皇太子、随后即将接任帝位的元仁宗的注意。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元世祖曾孙,他的父亲答剌麻八剌是世祖嫡长子真金的次子。与此前诸任成长于漠北草原的元代统治者不同,仁宗从小生活在汉地,少年时便以李孟为师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是元帝当中信用儒说和倚重儒士的突出代表,孙克宽先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延祐儒治”[10]之概念可说是概括仁宗朝统治特点的代表性表述。所谓“儒治”,既体现在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也可以通过客观评价的对比研究和仁宗主观言行的探查予以解读[11]58-59。简言之,早在仁宗即位大统以前他的思维模式就已明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仁宗在表达对一个人的好恶之心、判断其是否为可用之才时,儒家所崇尚的“贤”的品质就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标准。据杨载所撰《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记载,在仁宗朝得到高度青睐的文人赵孟頫就是以贤受知,于“仁宗皇帝在东宫,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贤,遣使者召”的契机下,[12]最终获得了“非他词臣之可比”[13]的宠遇。而对本文的主人公贯云石来说,也同样是因贤见遇:类同于伯夷、叔齐之贤的让位事件,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据《贯公神道碑》言:“仁宗皇帝在春坊,闻其以爵位让弟,谓其宫臣曰:‘将相家子弟有如是贤者,诚不易得!’”[8]652这个评价对贯云石来说想必意味着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很快,他就以此前所著的《孝经直解》进献于朝。在这部作品的序言中他写道:
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是故《孝经》一书,实圣门大训,学者往往行之于口,失之于心,而况愚民蒙昧,安可以文字晓之?古之孝者,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犹常礼之孝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者,其犹远哉。尝观鲁斋先生取世俗之语直说《大学》,至于耘夫荛子皆可以明之,世人视之以宝,士夫无有非之者。于以见鲁斋化艰成俗之意,于风化岂云小补!
愚末学,辄不自量,僭效直说《孝经》,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庶几愚民稍知理义,不陷于不孝之罪,初非敢为学子设也。[14]132-133
元代统治阶层特别重视《孝经》却又碍于语言障碍在理解上存在困难,这是研究者们解读此篇序言以及贯云石向上呈进《孝经直解》这一举动时普遍倚赖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以杨镰先生为代表的一种声音认为贯云石的用意是“企图用儒家经典沟通各族人民思想”[1]54,以王开元先生为代表的另一种声音则主要从中看出“贯云石对儒家思想的膺服推崇”[15]。作为贯云石屈指可数的存世文章之一,这篇序言无疑是能够直接反映撰写者思想动向的重要途径,但在民族融合与儒道传袭的视野以外,其实很值得从文本本身出发去一探究竟。
贯云石从三个层面阐述了他为《孝经》作白话注解的动机。其一,孝行与《孝经》于个人修养、社会风气、治国安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二,在他看来,现实中人们并不能很好地施行孝道,学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文化水平有限、根本无法阅读经典的普通人;其三,受前贤启发。应该说,前两点恰与上文提到的两种声音互有对应,而贯云石所述的第三层创作动机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从“愚末学,辄不自量,僭效直说《孝经》”的谦辞中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白话解经先例乃是促成贯云石仿效行为的关键契机。序言描述这样的心路历程说:“尝观鲁斋先生取世俗之语直说《大学》,至于耘夫荛子皆可以明之,世人视之以宝,士夫无有非之者。于以见鲁斋化艰成俗之意,于风化岂云小补!”在这里,贯云石一方面将许衡直解《大学》的成果当作尊崇的范本;另一方面,对前贤“化艰成俗”“于风化岂云小补”的赞叹,实际上更超越了直解经书的单一层面,表达了作者对许衡毕生事业的强烈认同与慕求。
许衡是元初著名的思想家,时人王磐誉之曰:“先生神明也……气和而志刚,外圆而内方。随时屈伸,与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书之堂。布衣蓬茅,不为荒凉。珪组轩裳,不为辉光。”[16]虽然他在仕途上“屈伸”多次,但却在有限的机遇中最大程度地发挥所长,在政治、思想、教育、历法等多个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特别是至元二年(1265)上疏世祖的《时务五事》,力陈“国家之当行汉法”[3]3719的必要性,从根本上回应了元初统治者面临的治国方略问题,得到了忽必烈的采信,可谓学以致用、修身治国的典范。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贯云石曾经学于姚燧,而后者正是至元八年(1271)许衡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的身份开展蒙古子弟教育时,亲自挑选为十二伴读的高徒之一。尽管没有文献明确显示姚燧对贯云石的指导中也包括老师许衡亲身践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士人理想,但写作《孝经直解》时的贯云石内心却显然有一个人生的榜样:
或曰:“汝得无欲比肩鲁斋公乎?”予曰:“奚敢!”[14]133
表面上,这仍是承接前引序言的内容在表达自谦,但是在一篇“自言自语”的文章中特意“制造”出一段对白,不可谓不“别有用心”。换个角度来说,贯云石在已经表明自己是“僭效”许衡的《大学直解》进行创作以后,本无必要再徒增一番莫须有的问答来占用篇幅。相反,在他一再的谦让里,许衡的多次出现起到了标杆式的作用,其中暗藏了二十岁的贯云石对未来的期许和抱负——年轻的贯云石和任何一个朝代的士人一样,都有一个做“大人”“格君心之非”[17]的梦想。 在此背景下便不难理解,主动辞去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一职的贯云石何以再次入仕,接受了仁宗朝给予的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官位。通过一则有关许衡的轶事,或许可以更好地探知将其视为榜样的贯云石彼时的心意:
许文正应召过真定,刘文靖谓之曰:“公一聘而起,无乃太速乎?”文正曰:“不如此则道不行。”[18]
被仁宗钦点,贯云石得到了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欧阳玄提到议行科举事宜时,贯云石“与承旨程文宪公、侍讲元文敏公数人定条格,赞助居多”,可知他很重视眼下的机会,对于职事用心经营。不仅如此,重新步入仕途的他很快写就了一篇万言书,对国家各个层面的事务提出了想法和建议,欧阳玄在碑文中用“未几”①“ 会国家议行科举,姚公已去国,与承旨程文宪公、侍讲元文敏公数人定条格,赞助居多,今著于令。未几,公上书条六事……”见欧阳玄《贯公神道碑》,《全元文》第34册,第652页。这样一个描述时间上承接之迅速的表述突显了贯云石这一时期的投入和敬业。虽然在元代时有臣子以此方式向皇帝进言,但是联系到许衡曾以《时务五事》赢得世祖认可、成就辉煌功业的故实,我们或可猜测贯云石此举背后也如撰写《孝经直解》时一样,有一个致敬的目标和一番高远的志向。
然而大约在延祐元年(1314),即上述万言书呈上却无果后不久,贯云石选择离开大都,归隐江南。针对《时事五书》不了了之的命运与其作者二次辞官之间的因果关系,已有研究者进行过细致的分析,②杨镰:《贯云石评传》,第70-72页;郝延霖:《贯云石生平焦点问题的评析》,收录于《西域文学论集》,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3页。兹不赘述。仅就贯云石当时“昔贤辞尊就卑,今翰苑侍从之职,高于所让军资,人将谓我沽美誉而贪美官也,是可去矣”[8]652的自白来看,这必然只是一言难尽的托词——若不是与现实有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所谓“辞尊就卑”,本不必等到现在。
二、“北望惟心一点红”:贯云石文学中的大都记忆
虽然贯云石的传世作品数量不多,但在有限的文本中我们已能发现,文学本身对于离开大都的贯云石具有特殊的存在意义,其命运转向为其文学注入的丰富内涵更成就了元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页。文学意味着对大都记忆的承载。贯云石至元二十三年(1286)生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卒于钱塘,人们总以为其远走江南的漫游时光是绝对美好的,淡泊名利、与世无争[15],但是综观他在此期间的诗、词、曲、文作品可以发现,那个他十余年间再也未曾回去的故乡以及其中的人、事,其实一直在他笔下,在他心上。其中有美好的过往,更有纠结的隐痛。以前者而言,《初至江南休暑凤凰山》和《翰林寄友》是两首尤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一首的诗眼说,“物华万态俱忘我,北望惟心一点红”,[14]109可知远离大都的贯云石虽然已努力放下一切,追求忘我的境界,但内心却仍旧记念着仁宗的恩情。换言之,当诗人选择长久地徜徉于自然山水之中时,他还始终记得曾经的理想以及那个为他提供过实现良机的君王。延祐六年(1319)为张可久的《今乐府》作序,贯云石称赞集中散曲“文丽而醇,音和而平,治世之音也”[14]138,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仁宗及其时代在作者心里的位置。至于《翰林寄友》,诗如其名,是贯云石写给当初一起在大都共事的同僚们的怀友诗,因其一次提到并评价了十位著名文人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其中诗歌结尾吟唱的“诸公衮盛时,忝会总知己。浓头一杯外,相思各万里”[14]116等语足以证明,曾经人才济济的翰林盛会早已成了诗人足以荣耀毕生的追忆。
不过,除了回忆里的美好,贯云石的文学还暗含了二次出仕岁月里的精神伤痛。如前文所言,《时事五书》通常被研究者认为是造成他逃离大都的导火线,因为“仁宗从来就不是一个从善如流、虚心纳谏的开明君主。尤其是议论了太子教育问题,更是触犯了仁宗那根帝王至尊的、猜忌的神经”[1]72,还有人说“诸如对‘至尊’言行的限制,对太子行为失检的不满,对具体国事的改革建议,都不是具有民族偏见的、‘饮酒常过度’的元仁宗所乐意接受的。……贯云石对元仁宗来说,似乎成了刺头”[19]。在这些观点背后,原本因“贤”之名称赏贯云石并让后者入职翰林的仁宗仿佛变身成了无法接受逆耳忠言的昏君。然而翻检史书可以看出,仁宗实际上非常善于甚至乐于纳谏[11]58。也就是说,真正让贯云石心灰意冷的原因恐怕并非是仁宗对其万言书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对于这一点,杨镰先生在毫不留情地批判仁宗的无所作为时却也不能不留下余地说:“关于贯云石第二次辞官,还有一些什么内幕被掩盖着,我们无由探悉。”[1]72-73无由探悉自然是因为缺乏相关史料,如此便只能从贯云石的写作中寻找端倪:
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14]47
这是贯云石所作《[双调]殿前欢》组曲的第二首,表面上作者是在否定屈原自沉的人生选择,肯定一种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的归隐出路。诚然,以屈原入创作是元散曲特有的一种现象,存在着可以模式化解读的情况[20]。但假如仔细回顾曲中吟咏对象屈原的遭遇则可以看到,对于曾经在大都官场上经历过风云变幻的贯云石来说,他对这一常见典故的使用有着套路以外的实感投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21]在司马迁笔下,虽然楚怀王的“不知人”①“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见司马迁《史记》卷八四,第2485页。之过理应被痛批,但来自奸佞之徒的谗害确也是一股导致屈原之“穷”、给他施加致命打击的关键外力。换言之,对于这首散曲的阐释,无论是“对楚怀王昏庸的愤恨和对屈原的怜惜之情”,还是“对他做事的态度和价值观的追求的不理解”,恐怕都还有些片面。因为即使贯云石以屈原为鉴“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新的理解”[22],他也始终未能将往事完全放下。
无独有偶,贯云石在《[双调]清江引·知足(其二)》中曾道,“荣枯自天休觊图,且进杯中物。莫言李白仙,休说刘伶墓,酒不到他坟上土”[14]35-36。 此曲的主题看似和“杯中物”关联甚密,或被解读为“人在有生之年要尽情畅饮”[14]36,或被分析作嘲弄李白、刘伶的放浪形骸[23]。然而,如果将此处以“荣枯自天休觊图”作为整曲定调之始,与作者在为怀念李白而作的《采石歌》中吟唱“我亦不留白玉堂,京华酒浅湘云长。新亭风雨夜来梦,千载相思各断肠”[14]105。相结合来看,便会发现“白玉堂”“京华酒”所指征的大都岁月,其实始终铭刻于贯云石心上。正如胥惠民先生在解读《采石歌》时提出诗人“借怀念李白,透露了他脱离当时政治斗争而避居江南的隐情”[14]104-105,二人在际遇和抉择上的相似性也得到了相关研究一定程度的探讨和证实[24]。以此联系钱惟善在《酸斋学士挽诗》中写“月明采石怀李白,日落长沙吊屈原”[25]31,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贯云石的友人将他和这样两个同样接受过君王优待却最终遭遇谗谤、愤然离去的历史人物进行关联,其实恰是在言说某种“内幕”。不仅如此,他在散曲中间或吟唱的“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识破幻泡身,绝却功名念,高竿上再不看人弄险”,“往事惟心知,新恨凭谁说”[14]31-56等语,显然也一再说明曾经在大都发生、迫使他远走的那些记忆从未在江南风光中彻底消解。
三、“欸乃声中别有春”:贯云石文学创造的精神家园
就在大都经历中的美好和伤痕不时渗入贯云石的创作,从而使文学于他成为一种记忆载体的同时,文学也意味着一道屏障,帮助贯云石隔离与生俱来的光环与荣耀,进而构建了他真正能够安于其间的精神家园。尽管祖父阿里海牙的突然辞世不可能不对这个家族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帮助世祖平定南宋的功勋以及外祖廉氏世家在当时的根深叶茂,都使得贯云石自小依然能够以贵公子的身份面对世界。只是,相较于沉迷纨绔子弟的生活,他似乎在其他方面投注了更大的兴致和精力。据程钜夫形容,贯云石在皇庆二年(1313)时就以所作诗文一卷出示于他,虽然当中具体数量无从得知,但这位曾替世祖赴江南访贤、有丰富识人经验的长者却通过“听其言、审其文”,非常精准地判断出“盖功名富贵有不足易其乐者。”[4]323换言之,贯云石无论是在言行举止还是文字创作上都很早就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固有贵族身份和功名追求的倾向。因此正如杨义先生所指出的,“大都和杭州,实际上是元中叶以后的政治首都和文化首都。两城间的选择,实际上是弃功名而追求精神自由”[26],贯云石最终选择远离大都前往杭州昭示着对于功名的彻底放弃,以及他终于能够以自己热爱的方式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了。而在友人的眼中,这份热爱投入的对象是清晰无疑的。仁宗朝中后期,邓文原在钱塘与贯云石相见,在读过其诗文集后欣然作序曰:“尝观古今能文之士,多出于羁愁草野。今公生长富贵,不为燕酣绮靡是尚,而与布衣韦带角其技,以自为乐,此诚世所不能者。”[27]在这里,邓文原不但重述了与程钜夫相同的意见,而且更明确指出对贯云石来说最具吸引力的快乐正来自文学。
如果说这些论见为我们理解文学之于贯云石的第二重意义提供了最初的参考,那么下面这条有关他的著名趣闻则可令人产生更为直接的感知。据《蓉塘诗话》记载:“钱塘有数衣冠士人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砍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28]贯云石能够出口成章,即时利用别人定好的调子进行个性化的创作,可以说故事本身首先已是对其文学才华的彰显和证明。与此同时,应声赋诗和同饮尽醉的情节则说明文学成为了连接贯云石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方式:他在文字的组合排列中怡然自得,随时随地享受着由此而来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快乐绝不肤浅,它来源于创作者对文学的根本认可与追求。
贯云石曾多次表示“荣华富贵皆虚幻”、“求名求利不多争”[14]46-48,而他认为真正实际的、值得在意的东西,就藏在《题练川书隐壁》这首诗里:
朝来策杖轻天涯,东风落脚山人家。悠哉野服弃俗态,萧然未受豪华加。儿兮子兮嬉且悲,灯昏小帐连依依。山人已有春微微,吾侪必欲留新题。[14]106-107
一个由冬入春的清早,一位“悠哉野服”的闲人,一番策杖走天涯的姿态,以及诗人在落脚人家的所见所闻,使这篇作品在关于贯云石的研究中一直被分析为“抒发了作者隐逸情怀,称颂了山民的质朴无华”。①参见胥惠民《贯云石作品辑注》第106页。另,近年有关贯云石诗歌的主题研究在论及这首诗时亦全持此说,并无二见,参见王瑞景《贯云石诗歌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32页。这样的解释虽然足够合理,但诗中一些细微而隐秘的情感却也被这种在贯云石研究中常见的对于“隐”的讨论遮蔽了。在笔者看来,诗人高唱的“萧然未受豪华加”不仅在于与“野服”“俗态”对应的物质层面,其实更是程钜夫、邓文原所言那种在精神层面上和“豪华”进行有意隔离的反映。在此观念作用下,所谓“山人已有春微微,吾侪必欲留新题”就不仅仅是对前一句山民生活描述的简单延续了,而是表现出贯云石作为诗人的一种敏感与自觉:他主动感受着自然与人心的变化,并且将记录这种变化看成是文学创作的使命。与此相仿地,在词作《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的下阙贯云石写道:“月落潮平,小衾梦转,已非吾土。且从容对酒,龙香涴茧,写平山赋。”[14]126从这里可以更进一步看到,文学如同他设立的自我保护屏障,不单能够借之撕掉富贵功名施于自身的标签,而且也有助于隔绝失落的情绪,在重新建构的空间里获得心灵的归属感。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贯云石不仅透过文学创设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更因此为古典文学的宝库添加了新的资源,产生了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据《元诗选·芦花被并序》记载:
仆过梁山泊,有渔翁织芦花为被。仆尚其清,欲易之以绸者。翁曰:“君尚吾清,愿以诗输之。”遂赋,果却绸。
探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欧阳玄撰贯云石神道碑云:云石尝过梁山泺,见渔父织芦花絮为被,爱之,以绸易被。渔父见其(以)贵易贱,异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公援笔立成,竟持被往。诗传人间。号芦花道人。公至钱唐,因以自号。[29]268
如前文所言,贯云石两次辞官和最终隐于江南的人生抉择,使得人们在谈及这个名字时首先想到的便是“隐”的概念。故此,在有关《芦花被》诗的这段典故里,一个隐士所当有的洒脱自得和渔父这一特殊形象中暗含的隐逸色彩就成了核心要义[30]。但是,仔细推敲贯云石在事件发生前后的行动举止以及渔父提出的特殊要求会发现,原本“卖药于钱唐市中,诡姓名、易服色”[3]3422,已经对个人特征进行了全方位改变以求不被发现的诗人,兴之所起,明知对方起疑却为了一床芦花被主动交待了自己的文人身份,这个矛盾是值得回味的:他选择付出的报酬本是正常不过的丝绸,而渔父后来“果却绸”的行为也清楚表明,以绸易芦花被,本是一桩双方默认可以进行的交易,至于赋诗则是额外的要求。即,贯云石如果要继续隐藏身份并不难做到,可他却欣然提笔,这显然不是为了渔父退回的绸;再从渔父一面来看,芦花被既然被看作以“清”为奇的特殊商品待价而沽,那么作为物主他能索取的报酬种类可以有很多选择,但两人最终却是在“诗”这个交点上达成了一致。借助这首《芦花被》,贯云石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不无得意,“援笔立成,竟持被往”的姿态很能说明问题。同时,也正是在成诗的前因后果中,其文人的身份和文学的意义藉由渔父及其提出的独特交换条件得以确认。
据《元史》记载,此后“人间喧传《芦花被》诗”[3]3422。 时人张昱的《题贯酸斋〈芦花被〉 诗后》写道:“学士才名半滑稽,沧浪歌里得新知。静思金马门前直,那似芦花被底时。梦与朝云行处近,醉从江月到来迟。风流满纸龙蛇字,传遍梁山是此诗。”[31]可见这首诗在当时传播广泛,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瞿佑的《归田诗话》又提到世有《芦花被图》,“盖模写酸斋梁山泺故事”[32],于是复有众人为图题诗。以下面数首为例:
自爱柔茵一榻平,岸霜都着楮囊盛。梦同宿雁经寒暖,身与浮云较重轻。待我鸡鸣分豆粥,笑谁鲸卷对藜羮。卧游江海平生意,布被公孙尚为名。[33](张雨《芦花褥》)
凌室冲冲已凿冰,两峰髙耸玉棱层。渔郎睡熟芦花被,冷照篷窗雪一灯。[25]13(钱惟善《雪夜(其二)》)
高昌野人见几早,发须不待秋风老。脱身放浪烟水间,富贵功名尽除扫。坐对渔翁交有道,青绫何似芦花好?从时拜赐芦花人,自云不让今古贫。高眠听梦梦更真,白月满船云满身。起来拍手波粼粼,款乃撼动人间春。[34](王冕《芦花道人换被图》)
君不见汨罗江边人独醒,捐躯博得千古名。又不见王戎钻李执牙筹,昼夜营营算不休。人生适意此为乐,何须苦觅扬州鹤。竹叶杯中阅四时,芦花被底舒双脚。[35](王佐《醉梦轩为钱公铉赋》节选)
在这些以“芦花被”为歌咏主题或特有意象的作品里,诗人们营造出的大都是一种清冷高洁之气,无论是“身与浮云较重轻”的道士,还是“冷照篷窗雪一灯”下熟睡的渔郎,又或者对本事里的主人公贯云石在云月之下高眠的想象,无不反映出创作者们与那个除扫富贵功名、以诗易芦花被的洒脱人物所共有的人生向往。曾经,一个“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桃花源充当着文人们求之难得的精神乐土;而今,只需卧眠于芦花被底舒展双脚就能产生同样的心灵慰藉,这是少数民族文人贯云石了不起的创造。诚如王汎森先生在论证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时以宋明理学为证讲道,虽然理学家们本是针对现实情境“提出解方”,“然而这并不影响那一套思想后来成为跨越时空的思想资源”[36]。对贯云石而言,他的借用文学安放内心自然也起因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床芦花被竟以主观情绪和感受上的共融调动起集体的唱和与回应,缔造出一个文学史上的新佳话。
结 语
综上所述,在仁宗朝经历的起落改变了贯云石的命运,也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一方面,从踌躇满志到被迫离朝,贯云石所经历的政治风波激活了那段久远的家族记忆。祖父阿里海牙年轻时曾豪言“大丈夫当立功朝廷”[3]3124,其后更以卓越战功实现了满怀壮志,对二十岁的贯云石来说,他的用世之心有前贤许衡的榜样示范,自然也不乏早已融入血脉的家世荣耀。但是,在他说出“富贵在于天,生死由乎命”[14]39时,祖父阿里海牙“自寻死路”的往事对他而言已不再是一段传说,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元史研究者在钩稽阿里海牙之死的事件时总结道,始作俑者要束木作为奸臣桑哥的姻党,“以公报私仇的形式迫使阿里海牙自杀,从而达到除政敌、取而代之的目的”[37]。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贯云石书写出“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时,内心可能经历过的旧痛新伤;也更加让人能够理解他最终“避风波走在安乐窝”的个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已完成进退抉择的贯云石在气象盛明的仁宗朝初期应时而出,追慕先辈功业意欲有所作为,然而却又险些如祖父一样罹奸邪之祸,只能远走他乡,这番二次进退中堆积起的对于仁宗、对于大都的复杂感受一同丰富了他的内心,深化了其文学创作的内涵。另一方面,正像时人袁桷所言,“昔之善赋咏者,毕穷涉历之远”[38],贯云石离开了具有约束力的官场,能够以更为自由的身份和心境在江南畅游十年,也从另一个层面为其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应该说,贯云石和他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力。正如陈文新先生所说:“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39]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贯云石文学作品中那些意味丰富的“言”,并将此与其人生际遇相勾联,便可深入到他为人熟知的特立独“行”背后,跳脱出元代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性、多元化等固有视角,发现一个具备经典意义的文人形象及其品格:他用文学咀嚼回忆、安抚自我,又以此种生活态度感染和影响后来者,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无疑,以上诸面正是贯云石的文学具有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