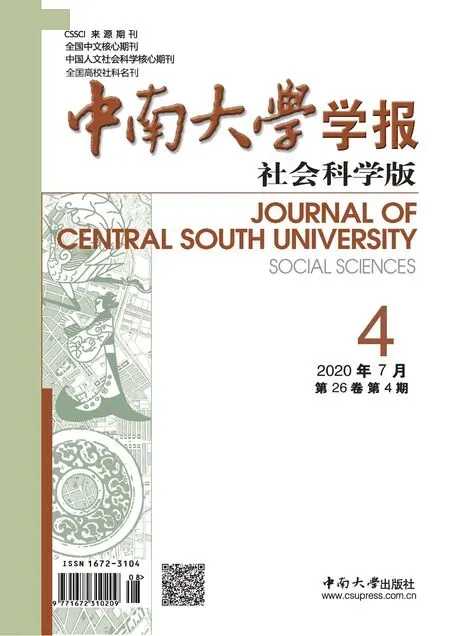七律结构论的模式化及其消解——以徐增的七律分解说及其创作实践为中心
蒋寅
七律结构论的模式化及其消解——以徐增的七律分解说及其创作实践为中心
蒋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徐增诗学历来被学者认为与金圣叹诗学一脉相承,关于律诗分解的论说也被视为只是对金圣叹七律分解说的接受,而未被注意到两者间存在的很大差异。其实徐增的律诗分解说对金圣叹的学说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造,扬弃了金说僵化、机械的成分,从而对律诗结构提出更圆通的解释和分析。这种认识不仅体现在他的唐诗解说中,更体现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上。考察徐增现存的所有七律,清楚可见其用更灵活的方式处理七律的章法结构,不仅大部分作品摆脱两段分解的结构,更有一些作品表现出脱逸常格、追求创变的趣向。这一结果验证了徐增在理论认知和写作实践两方面的一致性。徐增的诗论和诗作可以成为诗学史研究的一个经典个案。
徐增;金圣叹;七律;结构;分解说
元代诗学受经义“冒题”“原题”“讲题” “结题”四段论的影响,形成一种以起承转合说分析律诗章法的观念。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首列起承转合四字,并以“破题”“颔联”“颈联”“结句”相对应。傅与砺《诗法正论》转述范德机论起承转合之言,较杨载更为复杂,就绝句而言,首句为起,次句为承,三句为转,结句为合;就律诗而言,则首联为起,颔联为承,颈联为转,尾联为合。这种说法在元、明两代的蒙学诗法中陈陈相因,入人极深。金圣叹为破除这种僵化的结构论,提出七律前后四句分为两解的说法,并运用于《选批唐诗》和《杜诗解》,风靡一时。他的分解说并非全无道理,但固执地要以之通用于全部唐诗,就不免在打破旧的窠臼之余又堕入一种新的窠臼。他的分解说为他的同里后学也是热烈的崇拜者徐增所接受,在《说唐诗》中加以传承和发展。治诗学者都注意到徐增对分解说的传承,但未看到他对金圣叹分解原理的修正,因此我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专门就此作了论析[1]。当时让我好奇的是,不同于金圣叹分解之说的他,在自己写作中是如何处理结构问题的呢?一时未及考究,数年后才细读徐增《九诰堂集》,对上述问题求得一个结论。这里就将我研究的结果加以整理,供学界验证和参考。
一、徐增的诗学渊源及批评业绩
徐增(1612—1673)①,初字子益,又字无减,后字子能,别号而庵、梅鹤诗人。江南长洲人。明崇祯间诸生;能诗文,工书画,年未及壮即著诗文数十万言。13岁所作《芳草》三十首被其舅氏黄翼圣呈钱谦益,深蒙叹赏,后于崇祯七年(1634)执贽于门下。他在顺治九年(1652)《感怀诗》“虞山钱师牧斋谦益”一首中曾记其事,此后又不断有诗与钱谦益唱酬。钱氏罢归时作《钱牧斋先生南还喜赋二首》,崇祯十五年(1642)作《牧翁师问余近况赋呈》《牧翁师座上赠何士龙》,稍后又作《钱牧翁宗伯构绛云楼同河东君读书为赋》四首,顺治十二年(1655)上元前以黄牡丹诗请序,钱谦益复函有“才情烂发,翻江倒海”之评[2](193),顺治十六年(1659)作《寄钱牧翁师》六首,钱谦益八十寿诞作《奉寿钱大宗伯八秩》二首,后又作《钱宗伯来灵岩相会口占呈二首》,诉说了“一别门墙二十秋,病中身世总悠悠”的伤感[2](257)。徐增虽累经黄道周、曹学佺、陈继儒、王铎等钜公褒誉品题,才名鹊起[3],但不幸的是年甫及壮即患风痹,足不能行,钱谦益曾悬赏百金募医为之疗疾。为此,钱谦益卒时,他作《奉挽大宗伯钱牧斋老师四首》寄哀,其四云:“最初知己不能忘,说项人前姓氏香。小子偶传芳草句,大夫遂筑浣花堂。”[2](287)深情地缅怀了钱谦益对自己的知遇、关爱之恩。我在这里特别勾勒徐增与钱谦益的师承关系,意在说明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一直是在钱谦益的栽培和激励下成长起来的,在接触金圣叹的诗学之前,他已打下自己的诗学基础,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在论述徐增的诗学渊源时,过于集中在他与金圣叹的关系上,过多强调了金圣叹对他的影响,而未顾及他早年长久沐浴于钱谦益诗学之滋养的事实。如果留意到徐增与钱谦益的诗学渊源,就很好理解后来他虽然倾倒于金圣叹的魅力,热心学习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但终究未盲目信从和全盘接受,而是在批判扬弃的基础做了更圆通的改造这一结果。
病废后徐增并未沉沦,不仅常乘篮舆往来江浙间,还曾与友人商议生计。友人亟以文事相勗,从此他笃志于诗文,矻矻不倦地读书、写作、评选、编书。晚岁多与僧侣结方外之交,《留别去息和尚暨若如诸上人》诗“半世谬叨词客誉,一生只结道人缘”一联[4],适足概括他平淡而不平凡的一生。事实上,以文学为不朽之计的徐增,比一般士人更怀有绝大的抱负。当友人朱隗自陈“吾辈当为名家之诗,不当为大家之诗”时,徐增慨然曰:“吾愿为其难者。”[5](15)他的诗古文辞作品生前似已刊刻行世②,但今不见传本,仅有《九诰堂全集》抄本40册收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因我提议,现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从卷首所列王铎、钱谦益以降26篇当时文坛名流的序跋、一册赠诗及诗集中420首《感怀诗》,足见徐增在当时交游之广,毫无疑问是清初有广泛影响的诗人,同时也是有名的批评家。黄翼圣说,“时子能方逾弱冠,前辈如黄若木、陈玉立、陆履长诸公刻诗,皆属其为序,亦前此所未有也”[5](16),可见其声望非同一般。
徐增不仅留下二十五卷诗作,还留意于当代诗歌批评。鼎革后江南诗坛老成凋谢,徐增以成名日久,遂负时望,人多以诗集来求删订,包括无锡名诗人秦松龄。而徐增“辄对面改窜,神气扬扬,使人心满而后去”[5](17)。他曾感叹:“今天下非无诗也,无选诗之人;非无选诗之人,而无知诗之人;又非无知诗之人,而无平心论诗之人。嗟乎,今之人即周秦汉魏六朝四唐之人也,其诗又何必非周秦汉魏六朝四唐之诗也。少陵云‘不薄今人爱古人’,则今人果可尽非耶?”[6]为此他撰写了大量评论当代诗歌的序言题跋,并编有《诗表》和《元气集》两个专收时贤之作的选 本③。前者编于崇祯十一年(1638),黄翼圣说:“戊寅选《诗表》,时未有选诗者,自子能始。人为之奔趋,远近邮筒寄诗几充栋。所选二卷,人皆有志节者。”[5](16)后者编于入清后,是清人编纂本朝诗选的前驱。仅就这一点而言,徐增也是清初一位不可忽视的诗歌批评家。可惜,由于这两部选本都未传世,《九诰堂全集》也深庋贵邸,世莫能窥,后人仅由《而庵说唐诗》省识春风半面,不能不让人为之叹惋!
尽管如此,徐增还是以《而庵说唐诗》赢得了众多读者,至今这部诗评仍为治唐诗者所重。我更因为他说唐诗之法与金圣叹的分解说相表里,在《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列出专节加以论析。通过《九诰堂全集》中与金圣叹相关的篇章,我们可以确信,徐增曾是金圣叹死心塌地的崇拜者。他在《读第六才子书》诗中这样写道:“才子应须才子知,美人千载有心期。彩云一朵层层现,爱杀先生下笔时。”[2](194)他如此赞赏金圣叹的批评,自己批评诗歌也采用“说”的方式,就毫不奇怪了。据周亮工《题而庵先生小像》序记载,徐增还曾评论过周亮工的诗,不过像两部诗选一样也已不传,今天我们所能考究的只有他用力最深的《而庵说唐诗》。我们要了解徐增对七律分解说的理解,仍不能不由此书入手。
二、徐增对金圣叹七律分解说的改造
我们知道,徐增诗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与金圣叹一脉相承的律诗分解说,《而庵说唐诗》持以解说唐诗的得失,学界业已注意④。但学者们似乎为先入之见所主导,更多地看到徐增对金圣叹学说的继承,而未注意徐增对金说的改造。如吴宏一就根据《而庵诗话》中的议论,断言“徐增完全是就金圣叹之说而加以推衍”⑤,孙琴安也认为“徐增模仿金圣叹的痕迹尤其显著”[7],江仰婉则说“徐增是金圣叹忠实的继承者,其观念大多沿袭金圣叹,所以分解诗歌的做法也和金圣叹相去不远”[8]。研究者们似乎都未注意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偌大差异。
据我考察,金圣叹七律分解说的提出,缘于对宋元以来形成的起承转合结构论的反拨。源自宋代经义结体的起承转合之说,原是文本的一般结构观,但到了元代与律诗的四联对应起来,就变成一种机械结构论。金圣叹出于对这种僵化模式的反感,在说唐诗和杜诗时提出一种关于七律结构的分解说,意欲颠覆元明以来深入作者意识的机械结构观念。其大旨是认为七律前后四句分为两解,各自起意,各自收束。这确实是异于时俗之见的一种新思维。他断言近体诗“三四自来无不承一二却从横枝矗出两句之理。若五六,便可全弃上文,径作横枝矗出,但问七八之肯承认不肯承认耳”[9](514)。这就是说,前四句比较简单,后四句则变化复杂,最关键的是颈联两句。“五六乃作诗之换笔时也”,而诗的情绪也渐至高潮,所谓“作诗至五六,笑则始尽其乐,哭则始尽其哀”。从声韵上说,“诗至五六,始发亮音”;从结构上说,五六又是结的开始,“五六特为生起七八,非与三四同写景物也”。他甚至发现,“唐律诗后解七八,多有‘此’字者,此之为言,即上五六二句也”,意谓收束五六两句。为论证这一点,他竟举出五十一首唐诗为例[9](524−526)。
尽管他坚信分解说的“解分而诗合”更能凸现诗歌结构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但经过大量的分解实践后也体会到,唐人七律的组织之妙,整体性之强,有时甚至泯灭了前后分解的痕迹:“唐人思厚力大,故律诗本前后分解,而彼字字悉以万卷之气行之,于是人之读之者,反不睹其有出入起伏之迹也。”[9](512)这一发现不免使他对分解的看法变得矛盾而犹疑,以致说明分解的效用时,态度不得不有所保留:
弟念唐诗实本不宜分解,今弟万不获已而又必分之者,只为分得前解,便可仔细看唐人发端;分得后解,便可仔细看唐人脱卸。自来文章家最贵是发端,又最难是脱卸,若不与分前后二解,直是急切一时指画不出,故弟亦勉强而故出于斯也[9](500)。
这种苦衷就使他一方面在批评上张扬分解之说,一方面又在写作策略上重弹起承转合老调的原因。
徐增虽然接受金圣叹的学说,也很推崇分解和起承转合之说,但显然已洞见其中存在的拘泥不化之处,而有所调整和改造。我经过考察,将他的调整和改造归纳为四点:①分解的运用不再限于七律,而是推广到众多诗体;②在扩大分解说适用范围的同时,也取消了七律分解说的普适性;③重新解释七律两解之间的动力关系;④对分解和起承转合的关系加以补充说明。金圣叹分解的要义,是将诗的章句都理解为对结尾的奔赴,这不免忽视了颈联的结构作用,同时也漠视了唐代七律丰富多变的结构模式。徐增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缺陷,他首先强调,“律分二解,如关门两扇,开则相向,合则密缝”[10](367),这就是说,前后两解功能是一开一合,前解是展开,后解是收束。具体说来:
律分二解,二解合起来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个好朋友,赴一知己之召,意无不洽,言无不尽,吹弹歌舞,饮酒又极尽量,宾主欢然,形骸都化。后解,即是前解二十八个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略改换筵席,颠转主宾。前是一人请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请一人也[10](22)。
这一比喻较金圣叹更深刻地剖析了前后解意脉运动的不同趋向,也更清楚地阐明前后两解分别承担的开阖功能,从而更透彻地揭示前后两解构成律诗章法的动力学关系。通观《而庵说唐诗》的评析,可以看出徐增对作品结构的把握明显由章句转向意脉。这正是对金圣叹分解说的重要修正——强调意脉的结构当然比强调章句的结构更触及作品的有机性。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就不禁好奇,在修正了金圣叹的分解说后,徐增自己写作七律时还会贯彻分解的意识,以前后二解的模式来结构诗篇吗?如果不是,他将如何处理七律的结构问题呢?这无疑是个很有趣的 问题。
正像王渔洋、赵执信写作古诗是否贯彻自己在《声调谱》里提出的规则,会成为吸引我们去验证的问题。凡是标举某种理论的作者,其创作实践是否贯彻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总是会惹人好奇的。从杜甫的“老”、黄山谷的“脱胎换骨”到王渔洋的古诗声调说,都曾引发前人讨论、验证的兴趣。说到底,像古诗声调论和律诗分解说这类主张,都无非是根据有限的例证提出的假说,并无有力的统计结果支撑。他们言之凿凿地论断,与其说是一个事实的发现,还不说是一个出自信念的主张。而验证这种主张的坚定性,即自信的彻底程度,最简便的方式莫过于看他们自身是否践行其学说。既然陈鉴《而庵说唐诗序》断言徐增“其所说即如其所作”[11],那么《九诰堂诗集》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让我们可以验证一个作者在实际创作中是否贯彻了自己坚持的诗歌观念。
三、徐增七律中分解式章法的遗留
徐增对分解说的理解和掌握既有如此大的变异,落实到创作上当然也会有相应的表现。徐增是一位热衷于写作七律的诗人,据我粗略统计,《九诰堂诗集》现存七律474首,比最擅此体的杜甫还多两倍,杜甫只不过一百六十几首而已。在徐增这些七律中,结构符合分解说的作品远非多数,正与作者对分解说的疏离相一致。经我甄别,除了诗集前两卷40首七律中有15首符合分解说,卷九34首、卷十八13首分别有10首、8首,比例略高外,其余22卷能确定适用于分解说的七律都很少,各卷总计95首,不到总数的1/4。这个比例已足以说明徐增的七律写作与分解说的普遍性、绝对性没有必然联系,更何况这有限的例子还同特定的题材和类型联系在一起。
从题材来看,合乎分解说的作品正像金圣叹说唐诗,几乎都集中于应制、联唱(初唐),庙堂、赓和(盛唐),饯送、酬赠(中唐)等几个类型。这些类型在体制、取材上均有严格的限制,以切题切事为紧要关目,容不得多少个性化的内容,因而结构也较为呆板,分为前后两解相对是比较清楚的。而像写景、即事或咏物一类,结构通常是连贯而下,符合分解说的作品就少见了。徐增七律在这一点上颇与金圣叹的选材相印证,类似《山行》《暮春石湖修禊》《遮山坐雨》《岩头晚眺有感》这样的写景、即事之作,的确很少看到两解分明的结构;而《新燕》《玄墓梅花》《月下梅花》《春草》之类的咏物诗,更是难得一见可分解之作。竭尽才智创作的百余首黄牡丹系列组诗,每沉湎于组织事类,体物传写,更兼偶俪对仗,穷力追新。只有像《黄牡丹诗又十首》其一,后半在用典之后继续发挥其意,才构成前后两段的章法,因此能够按上下两段分解的作品,实在寥寥可数。看来徐增的七律写作基本贯彻了他对七律结构更灵活的理解,没有受到分解说的束缚,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如果更具体地考察其七律中可予分解的作品,我们还能更进一步看出,分解说在徐增的意识中确实已很薄弱。
徐增集中符合分解说的七律以酬赠类最多,诗集前两卷所收的早年作品尤其明显。如《寄南昌徐巨源》、《黄石斋先生廷对放归道经吴门感而有作奉赠》二首、《奉寄张异度先生》、《牧翁师座上赠何士龙》、《投谢徐笏斋宫谕》,等等。最典型的是《投谢徐笏斋宫谕》一首:
末世谁怜士路穷,泌园身后赖明公。
才非王粲惭刘表,年过祢衡遇孔融。
疲马何能驰远道,破帆无力仗东风。
家中四壁苔生遍,抱膝偏宜对老桐。[2](130)
前四句庆幸自己身处士人道穷的时代,年未及壮即获得徐笏斋的垂青提携,后四句谦辞以无能力出仕,只宜丘园终老。两解一扬一抑,前解由自怜而结于自幸,后解由自伤而归于自解,各自分别起结,可以看作是符合金圣叹分解说的典型作品。《寄文端文寒山》一首,主题是思念友人,本来也可以轻松地写成二四二的三段式,结果却写成一个非常典型的前后分解式结构:
芝岭桃源路不赊,来寻只恐有云遮。
望中白马高僧地,梦里寒山处士家。
水浸莲房供洗砚,风吹松子助烹茶。
多君幽致人无及,日暮相思怅落霞。[2](145)
前四句说两地山高路远、不克造访,而只能日中遥望、夜里梦想,后四句悬想友人山中清况,由羡慕而至于惆怅。前半由实(望)入虚(梦),融情于景;后半由虚(想)归实(怅),由景生情。两段意脉各自起结,也是典型的分解式结构。
大体上,在我认为可以分解的95首七律中,多为前后两段意脉清楚、各自起结的作品。祝寿类如《陆岩公六十》:
雪藕冰瓜六月凉,南薰吹送寿筵香。
仙人载酒来芸帐,词客吟诗上草堂。
元晏春秋书里过,奉常日月画中长。
百年乐事应无尽,玉树添枝户有光。[2](204)
前解写寿筵盛况,后解以晚年乐事相祈颂。饯送类如《送岭南屈翁山游嘉禾》:
乾坤万里偶离家,五岭西方怅岁华。
那见遗民缝皂帽,但闻少妇弄琵琶。
阖闾山上号秋鬼,羞姆坟头落暮鸦。
临别约君重九会,恐君意不在看花。[2](298)
前解述屈大均西游得妇的韵事,后解写送别情景。自述类如《作诗论毕自题一首》:
风雅何年复中兴,宋元以后少师承。
拓开杜甫堂前月,看取王维家里灯。
景略向人扪白虱,仲翔知己叹青蝇。
秦余顶上千秋泪,除却陶孺却有增。[2](206)
前解自陈诗学志向,后解叙写见忌于时的境遇。评论类如《读申霖臣中翰宛陵诸作却寄》:
黄蘗道场留古院,敬亭爽气忆青莲。
孤云岂记登临处,双塔犹书建造年。
唐后何人看不厌,春初有客去忘旋。
示余五字真千古,宁教当时谢朓贤。[2](249)
前解略举申诗所咏宣城古迹,后解称赞申氏游历诸诗之佳。凡此之类,不待枚举。但即便如此,这些作品也应该是自然成文,而未必是作者有意构造。否则像《钱牧斋先生南还喜赋二首》这样,其一不分解而其二可分解,就不好解释了。
更进一步说,即使是被我判别为可分解的95首中,也有一部分是容有进退的。问题就出在金圣叹特别注意的颈联,因为“五六乃作诗之换笔时也”,当它截断上四句意脉而重起新意时,末联是否承接即金圣叹所谓“承认”,就形成两种章法,一是承接而收束于第二主题,一是不承接而呼应前解,回归第一主题。如《寄南昌徐巨源》一首云:
相引清流耕砚田,不知门外草齐肩。
琴声绕户僧来听,桐绿侵灯鹤对眠。
我党几人如旧雨,世情何处不秋烟?
那从识得匡庐面,更载西江水一船。[2](122)
此诗以自处孤独和想念徐世溥两层意思构成前后二解:第一联是闭户著书的传统表现,僧来听琴和对鹤而眠反衬出居处孤寂、独学无友的幽居清况。病痹废行的徐增比常人更多更经常地体验这种境况,因之对友情和交流的渴望也比常人更为急切。但故人或撄于势利,或迫于生计,有多少能常加存问或枉道相过呢?颈联不禁流露出难以克制的失望,非但用“旧雨”一词微寄讽意,更用秋烟暗喻人情的淡漠。这一笔宕开,使诗的意脉脱离自叙而推及世风之浇薄,彼此身世遭逢的不幸也同时得到传递和抚慰。结联以徐世溥匡庐之游后能枉顾相期盼,是收束于第二主题。如果不这么写,而是重申自甘孤寂之志,那就回到了第一主题,更符合徐增的开合说:前四句一解,是打开孤独的门;后四句一解,又关上了孤独的门。徐增的写法收结于第二主题,等于是新开了一扇门,没有去关前一扇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可的结构,缘于颈联在结构上的斡旋作用,它给结联提供了意脉走向的多种可能。金圣叹虽然意识到颈联的斡旋作用,但不是将它视为文本结构的一种功能,而是视为文本结构的一个形式,这就使他对颈联的认识趋于僵化,看不到颈联结构作用的多种形态。徐增虽然没有论及这一点,但写作中明显掌握了颈联的结构功能。这样,徐增的七律就更多地利用颈联的斡旋作用而造成结构的丰富变化。
四、徐增七律对分解式的脱逸
徐增七律中分解式结构的非主流化非中心化既得确认,那么其结构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也就不再是问题,甚至再举例都不需要了,常态化的现象本来就可以忽略。但如果我们从常态中看到一些特异的例子,以极端化的方式挑战常态的界限,那就可能出于某种矫枉过正的意向,意味着对前人固有模式的突破和反叛。徐增七律中的确有一些结构很特殊的章法,不仅抛弃两段式的分解法,而且也为起承转合的一般结构框架所难容,值得特别注意。
我们知道,某些作品因题旨简易,中间常会插入其他内容,使意脉区分为三层。比如赠答类的《颉仙将归云间后会无期怆然有作》:
交如明月意如琴,如此声光不易寻。
一卷汉书名世业,数行血泪古人心。
相期鹤驭春天远,每怅蓬壶海水深。
岁月玩余余径老,青苔黄叶在寒林。[2](143)
这首诗的结构是,首联表达自己对颉仙这段友谊的格外珍视,颔联称赞对方的学问和诗文,后两联感怆后会难期。颔联的插入将作品分为三层,两句只是充实了诗意,而并无文体功能,相对来说是较为孤立的部件。颈联没有承上而是直接启发后会无期之意,可以说是一般格式。但在日常写作中,并不都是刚好到第五句生发新意,有时也会有错综变异。比如徐增《钱宗伯来灵岩相会口占呈二首》其二:
已拚沟壑尚风烟,无力躬耕掷砚田。
大泽龙蛇何处问,空山雨雪有谁怜?
十年不踏江东地,一日来参济北禅。
贫病死生齐放下,且同佛子去随缘。[2](257)
前四句自陈孤苦无助的境况,第五句没有另起新意,而是概括前四所述,说明十年未出游历的寂寞生涯,第六句才续言来灵岩礼佛之事。与之类似的是《红荳花》:
有美嫣然洵足夸,芙蓉庄上老人家。
江南留得相思树,研北题为忠节花。
十七年来鹦鹉饿,五千里外子规嗟。
湖湘抱怨知何似?记曲频教玉指斜。[2](258)
据自注“芙蓉庄植十七年,无花,今始开”,可知第五句是总括前四句,第六句才起第二层意,与前首一样是五一三结构。这点错综在古典诗歌中算不了什么,但对强调前后四句对开的分解说而言,却是一股不可轻视的消解力量。无论徐增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的创作实践已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自己对分解说加以改造的必要性。
粗粗阅读《九诰堂诗集》一过,我已对徐增的才华留下深刻印象,若非其身残而不能出仕漫游,广交天下英髦,他或许能成为当世引人瞩目的文学家,尽管事实上他在文坛上也不是默默无闻。对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来说,力求摆脱陈规,不断求变出新,乃是最正常不过的念头。徐增不仅在说诗中摆脱了金圣叹分解说的束缚,提出更富于变化和灵活性的规则,在写作中也表现出章法的新变意识。仅就七律而言,他在章法上的创变意识也是不难体察的。比如《冬初沈硕庵申维久莘民过寓斋》一诗,原本是很容易写成上下四句的两段式结构的,但徐增营造了更为独特的章法:
自昔邺都称绣虎,只今碧海出鲸鱼。
诸君江表皆名下,一客墙东正隐居。
红叶西泠迷去雁,青藜高阁拥遗书。
相思岁晚无开菊,不道柴门有驻车。[2](145)
在这里第三句承首联称赞诸友的才华声望,第四句以自己的隐居无闻相对照,启下联两句拥书远世之意,直到结联才转出题中诸友过访之事,于是形成一个独特的三三二结构。这种结构当然不是徐增独创,冯振先生在《七言律髓》中就曾举出薛能《牡丹》一诗:
去年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何因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欲就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冯振先生揭示此诗的章法是:“前三去年之事,后五今日之事。”[13]“何因重有武陵期”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写今日重见牡丹的意外惊喜,开启重赏牡丹的后半之意,粗看也可视为前三后五的章法。但若作更细的分析,“欲就”两句乃是未来的打算,严格地说是更一层意,实质上也是三三二的结构。类似例子还有不少,需要细致搜讨。
经过这番寻绎,我们清楚地知道徐增在改造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扬弃其中的僵化成分后,他自己的写作也用更灵活的方式处理七律的章法结构,不仅大部分作品不用两段分解的结构,更有一些作品表现出脱逸常格、追求创变的趣向。这一结论,不只因为验证了徐增个人在理论认知和写作实践两方面的一致性而对认识、评价徐增的诗学有重要意义,从诗学史的角度说,它也证实了我在《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一文中提出的论断:在一个讲究“活法”,追求圆融浑成的表达方式,以“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为极致效果的诗学系统中,当然是无法容纳起承转合与分解说这类机械结构论观念的[12]。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增对金圣叹分解说的改造,是顺应了中国诗学的传统观念的,在美学原理上也是与有机结构观念和至法无法的技巧论相通的。这使他的《而庵说唐诗》没有成为金圣叹分解法的传播者,反而做了它的终结者。《而庵说唐诗》问世后,分解法不是更流行而正相反是日趋消歇。除了偶尔为通俗性的唐诗选本(如王尧衢《古唐诗合解》)所引述外,诗论和诗话里在贬斥之外就很少提起了。这未尝不是徐增改造分解说的结果。为此,徐增的诗论和诗作可以成为诗学史研究的一个经典个案。在宋元以降的诗学史上这样的个案还很多,类似个案的研究积累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加深我们对古典诗学的认识。
① 见湖北图书馆藏抄本《九诰堂全集》卷首陈宗之《梅鹤诗人传》。徐增生卒年,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定为1603—1673年,未知所据。樊维纲先生校注《说唐诗》据三槐堂刊本《而庵说唐诗》所附康熙七年(1668)征今诗启称年五十七及康熙十年(1671)所作《重修灵隐寺志序》称年六十,推其生年应为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今按《九诰堂全集》卷首方文题赞言“何幸同生壬子年”,可证樊考甚确。
② 徐增《感怀诗·陈玉立宗之》其二自注:“余与先生刻诗稿,互相为序。”《九诰堂全集》,第150页。
③ 前者见王尔纲《名家诗永·凡例》著录,后者邓之诚有藏本。
④ 有关《说唐诗》的研究,除樊维纲先生校注本前言外,还有郭宝元《而庵〈说唐诗〉研究》,东吴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吴宏一《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72页;江仰婉《明末清初吴中诗学研究——以“分解说”为中心》,中正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⑤ 见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牧童出版社1973年版,第164页。后在《清初诗学中的形式批评》一文中仍持此说,见《清代文学批评论集》,第59页。
[1] 蒋寅. 清代诗学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 徐增. 九诰堂诗集[M]//九诰堂全集. 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第41册: 193.
[3]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 卷三十二(徐子能集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4] 徐增. 留别去息和尚暨若如诸上人: 其二[M]// 九诰堂全集. 湖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220.
[5] 黄翼圣. 徐子能甲集序[M]//九诰堂全集. 湖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6] 徐增. 贻谷堂诗序[M]//九诰堂全集: 543.
[7] 孙琴安. 中国评点文学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196.
[8] 江仰婉. 明末清初吴中诗学研究——以“分解说”为中心[D]. (中国台湾)嘉义: 中正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146.
[9] 金圣叹. 金圣叹选批唐诗: 附录“圣叹尺牍”[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514.
[10] 徐增. 说唐诗: 卷十六[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367.
[11] 陈鉴. 而庵说唐诗序[M]//九诰堂全集, 湖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21.
[12] 蒋寅. 起承转合: 机械结构论的消长——兼论八股文法与诗学的关系[J]. 文学遗产, 1998(3): 65−75.
[13] 冯振.七言律髓[M]//中国诗学:第七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Patterning and dissolution of seven-syllabic verse structure: Centering on the decomposition and composition practice of Xu Zeng’s seven-syllabic verse
JIANG Y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Xu Zeng’s poetics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to be in the same line with that of Jin Shengtan's poetics. Statements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his regular poems are often regarded as mere acceptance of and inheritance from Jin’s theory of decomposing seven-syllabic verse with yet their wide disparities being ignored. But in fact, Xu greatly modified Jin’s theory by discarding the rigid and mechanical elements in Jin's theory, and put forward more flexibl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regular poetry. Such perception and recognition is embodied not only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Tang poetry but also in his own poetry composition practice. Probing into all of Xu’s extant seven-syllabic verses, we can clearly uncover his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of arranging seven-syllabic verse so that most of his poems have go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two-part structure of decomposition, and that some poems have even broken off the regular meter and rhyme with a tendency of innovation. Such a result verifies Xu’s continuity in theory cognit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Hence, Xu Zeng's poetic theory of decomposition and his composition practice can be a classic case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oetics.
Xu Zeng; Jin Shengtan; seven-syllabic verse; structure; theory of decomposition
蒋寅,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04.001
I207.22
A
1672-3104(2020)04−0001−07
[编辑: 谭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