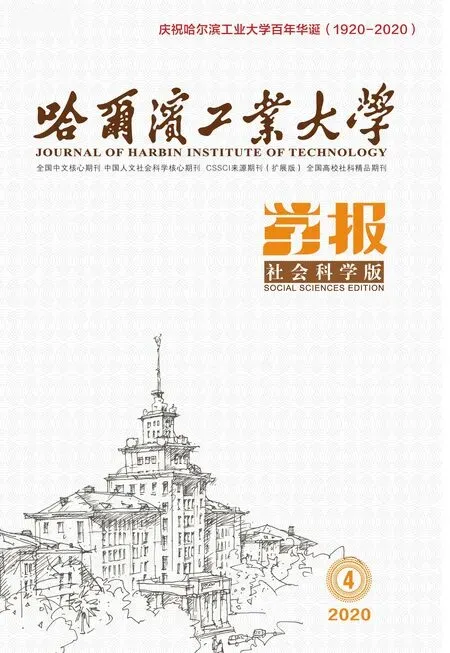民族文化认同与太清词的民俗文化书写
孙艳红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顾太清(1799—1877),满族镶蓝旗人,原姓西林觉罗氏,后改顾姓。名春,字子春,一字梅仙,道号太清,晚年又号云槎外史。顾太清才貌双绝,善诗词,工书画。太清学习填词较晚,约36岁才开始与丈夫唱酬,“在太素的指导下,她遍读唐宋名家词”[1],但她却用词笔道出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八旗论词有“满族词人,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2]之语,可见对其词评价之高。
学界研究顾太清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平考证、词风界定和总体评价上。太清生活在满汉文化高度融合的晚清时期,在她身上既存留了满族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又吸纳了汉族文化。太清作为满族贵族女子,要严格遵守皇室规范,外出活动受到限制。寺庙道观礼佛斋戒是贵族妇女生活常态,偶有郊游踏青则是对其最大的恩赐。她生活圈子狭小,所思所历无非是日常生活起居、亲朋闺友的交往和自然时令变幻等,因此在太清词中有大量满汉民俗风情的描写,这正是其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展示性书写,也是满汉文化涵化现象的一种揭示。这些民俗民情的书写,铸就了太清词自然清逸的淳雅词风和理性色彩。民俗文化传统是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现象的潜在力量,太清词的民俗文化书写便是重新解读太清词的神奇密码。
民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首先是对传统的沿袭,同时又在日常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更新演变。民俗风物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承载着民俗文化,既有渗透着人们精神理念的自然之物,也有积淀着人们生活认知的人造之物。钟敬文先生把民俗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方面[3]。笔者以民俗文化视角梳理审视太清词,发现其中关涉民俗文化的词有百余首,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数量之大,本文且择要析之。
一、太清词中的物质民俗书写
物质民俗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民俗、狩猎游牧渔业民俗、商贸民俗、饮食民俗和服饰民俗等。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农耕时序节令、占天象测农事、祭祀田神社神的书写等。太清虽为满族贵族,但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她有机会接近平民生活,非常关注社会农事和时序变迁。太清词中关于物质民俗的书写主要有骑射狩猎、捕鱼割麦、乡野采摘、市集卖花、节日美食、妇女衣饰等方面。
(一)骑射捕鱼活动的书写
太清作为满族女子,承继了满族人擅骑的生活习惯,经常骑马郊游。据《孽海花闲话》记载:“太清与太素,并马游西山,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漆。”①冒 广生《孽海花闲话》,载《古今》,1944年第41期,第5页。关于这段记述,后来文人又加一层形容,比如《清词玉屑》中说太清“于马上抱铁琵琶,宛然王嫱图画”;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中说太清“作内家装,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如玉,见者咸谓王嫱重生”。这不仅记录了太清与丈夫出游的场景,也表现了太清之才丰貌美,更是对太清骑艺之娴熟的由衷赞叹。太清的《浪淘沙》词是其擅骑的最好见证。
春日同夫子游石堂,回经慈溪,见鸳鸯无数,马上成小令。
花木自成蹊,春与人宜。清流荇藻荡参差。小鸟避人栖不定,飞上杨枝。归骑踏香泥,山影沉西。鸳鸯冲破碧烟飞。三十六双花样好,同浴清溪。②文中所选的太清词均见于卢兴基编著的《顾太清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5年1月第1版。此书是叶嘉莹主编的《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之一。
从词序中看,此词写的是夫妻二人骑马游春。春色宜人,花木成蹊,夕阳西下之时,一对对鸳鸯在水中自由嬉戏,此情此景令人心旷神怡。与丈夫联骑并游的顾太清,不禁诗兴大发,马上吟成这首小令。顾太清不同于裹足于深宅大院的一般闺秀,她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山水中陶冶性情,在美景中感悟生命,词人不经意间为我们自塑出一位诗情画意的满族女子形象。擅骑对汉族官宦之家的女子来说是不可能具备的技艺,但满族则不然。满族入关前以游牧生活为主,骑马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必需技能,也是满族的民族特征,满族女子擅骑毫不足怪。
满族是渔猎民族,狩猎捕鱼是其谋生的主要手段。太清词中多次写到满族的捕鱼情况,比如“好生涯、叉鱼活计”“称鱼市,儿童戏,也效叉鱼技”(《蓦山溪·慈溪看捕鱼作》),活现出满族劳动人民捕鱼卖鱼之乐。《柳枝词》其五则全面地展现了满族人的日常农事生活,描写了收割小麦、打鱼买鱼、卖酒饮酒等场景,俨然是一幅生动的旧京民俗图。
(二)采春踏青活动的书写
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除了捕鱼、狩猎,采春也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太清词中对采春风俗的描写,颇有生活情趣。像《柳枝词》其二总体展现了满族采春活动中的民俗风情,“苦荬茵陈挑满筐”一句突出了采春收获满满的喜悦。
荠菜是野菜中的骄子,有“三月灵丹”之美称。荠菜是春天到来的象征,采食荠菜是满族人的生活习俗。太清有同牌同韵的两首咏荠菜的词,即《鹧鸪天·荠菜》《鹧鸪天·元日咏荠菜》。女词人捕捉了踏春时采荠菜的场景,描写了野外荠菜的清雅飘香和盎然生长之势。词人极力赞美田野的自然生气,显示了太清返璞归真的生活志趣。
太清词中表现采摘乐趣的还有《迎春乐·乙未新正四日,看钊儿等采茵蔯》一词。词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勾勒了一幅风景画:风和日丽的初春时节,晴空下蜂飞莺舞。“采采茵陈芣苢,提个篮儿小”,提着小篮儿的孩子们正在采摘新生的鲜嫩野菜,画面色彩鲜明,生气盎然。不仅突出了采春活动,还体现了太清母性的温情和看着钊儿等采摘时怡然自得的心态。这或许就是张菊玲所说的“写平易情真的慈母心”[4]吧!
(三)满族饮食服饰的书写
满族人擅骑好饮,性格豪爽,饮食丰富多样。满族社会相对开放,贵族妇女也可以彻夜饮酒,并饮至极醉,这在前代妇女哪怕是李清照那里也不是常有的事。太清不仅会饮酒,而且擅饮。她涉及“酒”的诗词颇为丰富,以酒会友成了她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仅在其词集《东海渔歌》中,就有近40首词直接或间接提到饮酒。在《喝火令》一词中写了女词人悠闲自在地饮酒,在“拂面东风冷,漫天春雪飞”环境中尽享生活的美好,甚至于“醉归不怕闭城门”,恰如东坡之“老夫聊发少年狂”,更是具有一种非普通女子所能有的不怕挫折阻挠的豪气。在这豪气之下呈现的是她那种既富有细腻的情感,但在遭遇曲折时又具坚强个性的真性情,这使得她能更沉静、更执着地体悟美,一个开朗自信、有着自然活泼生活情趣的健康形象跃然于读者眼前。
太清写酒,有“宿洒新愁浑未醒”(《壶中天慢·和李清照〈漱玉词〉》)的借酒消愁,有“且斟美酒对清辉”(《浣溪沙·楼外秋寒知不知》)的及时行乐,有“邀明月,酌美酒,共山翁”(《水调歌头·急雨响岩壑》)的纵情痛饮,有“凝妆处,玉壶亲贮,词客醉芳茵”(《满庭芳·剪到秾香》)一起醉倒在花丛的豪迈洒脱,等等。太清把饮酒这种带有强烈男性气质的行为视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她旷达不羁的心目中,酒不再是男性的专利,而是女子颐养性情、引发逸兴壮怀的酵母,这与太清豪爽洒脱的满族民族个性是分不开的。
太清词中还写到过满族妇女的服装头饰,比如“双彩胜、金钗并悬”(《太常引·人日立春》)、“彩胜云翘”(《蟾宫曲·立春》)等,都表现了满族妇女立春日佩戴头饰盛装出行的景况。
太清不仅在词中展现民俗风情,在其诗中也多有对满族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如《采菱歌》《蚕妇吟》等;还有一些农事诗,如《五月廿五雨中,过天宁寺看新麦即席作》《清明芦沟道上书所见》等。可见,太清对风俗习惯、民俗风物的情有独钟,这也正是太清对自己本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
二、太清词中的社会民俗书写
社会民俗一般是指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令民俗、婚丧嫁娶民俗等,其中岁时节令民俗地域色彩非常浓厚,也是少数民族作家经常关注的写作素材。
(一)岁时节令民俗的书写
满族人非常重视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太清词中记录了满族人逢年过节的民风民俗,生活气息浓厚。
月对中国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但对太清来说,中秋佳节月圆人不圆,引发了词人无限怅恨。太清写中秋的词有五首,其中《浣溪沙·中秋作》写中秋赏菊,《步虚词·中秋》《柳枝词》其八都写中秋赏月。这三首词属于普泛性地记写中秋,而《水调歌头·中秋独酌》和《金风玉露相逢曲·丙寅中秋,是日秋分》则是悲秋伤怀之作。奕绘去世后,词人被赶出家门,生活凄苦,风雨飘零。前者写中秋节词人独自对月饮酒,后者“能几见,团圆佳节”写年迈词人慨叹人生还会有几个团圆佳节,读来悲感萦怀。从这些中秋词中看出词人作为女性的敏感细腻,也有满族女性的洒脱率真。词人能很好地发挥词体的优势,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表达出来,这对词体文学来说是一大丰富。
词人的这种悲感在记写重阳节、上巳节的词中也有所呈现。如“临歧莫唱折杨柳,风雨重阳最断魂”(《柳枝词》其九)写重阳节的民俗风情,哀感动人。“九日登高眼界宽”“茱萸插帽不成欢”(《鹧鸪天·九日》),写重阳节登高家人不能团聚而引起的愁绪。上巳节是指每年的三月三日,各地活动不同,北方以春游为主。重阳节、上巳节踏春一般都是家族倾室而出,一起登高避灾。“南郭同游上巳天”(《鹧鸪天·上巳同夫子游丰台》)写的就是太清全家上巳节同游的场景。
《风入松·春灯,次夫子韵》二首写元宵佳节,太清夫妇同游天桥灯会,将元宵节的街会描写得绘声绘色。满族的元宵节活动和汉族基本相同,但是庆祝中元节的活动略显不同。满族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传为目莲救母之日,俗称“鬼节”,有超度亡灵之意。中元节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念经,举行超度仪式。比如《望月婆罗门引·中元步月》一词,词人起笔紧扣“中元步月”词题,突出展现了月夜的静谧清幽。继之写中元风俗:中元祭扫时的“痛哭”,还有放河灯、赏河灯等民俗活动。词人将人事与鬼事、生与死、庆祝与祭奠交织在一起,不仅表达了词人的复杂心绪,也引发读者的思考,增加了词体内涵的厚重度。
除上述传统节日外,太清词中对七夕节的书写饶有兴味。由于奕绘早逝,词人怀念昔日的美好婚姻生活,故而对七夕节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与人文情怀。比如《鹊桥仙·云林嘱题〈闰七夕联吟图〉》:
新秋逢闰,鹊桥重驾,两度人间乞巧。栏干斜转玉绳低,问乞得、天机多少? 闺中女伴,天边佳会,多事纷纷祈祷。神仙之说本虚无,便是有、也应年老。
这是一首题画词,写闰年七夕。《闰七夕联吟图》是许云林(秋红吟社的成员之一,太清的闺中密友)画的一幅仕女图。词人选用《鹊桥仙》这个词牌,意在借牛郎织女的故事,表达对婚姻美满的期盼与祝福。闰年两度七夕,可以两度乞巧,两度乞福。但词的末句“神仙之说本虚无,便是有、也应年老”,是词人对神话故事中己成仙的牛郎织女的质疑。这种疑惑态度,表明了太清在潜意识里对人生幸福的思考。由此看出,词人不是简单地对节令时序的书写,而是引发出一个富有哲理的命题,丰富提升了词品。
太清写七夕节的词还有《伊州兰台·七夕夜雨》《鹊桥仙·牵牛》《柳枝词》其七、《浣溪沙》其三等,词人因为心念丈夫太素,对七夕节倾注了无尽相思和美好祝愿,借助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增添了词体的浪漫色彩。
此外,词人表现节令风俗的词还有《步蟾宫·至日》写冬至,《思佳客·腊九日》写腊日,《山亭晏·立秋》写立秋,《临江仙·清明前一日种海棠》写寒食节,《菩萨蛮·端午日咏盆中菊》写端午节赏菊,《太常引·人日立春》《蟾宫曲·立春》写立春,等等。太清对这些传统节日的记述也是其日常生活的再现。
(二)满族婚恋风俗的书写
清代妇女观开放,满族女性对爱情婚姻自主更是高度认同。太清的《南柯子·咏香串效唐人体》一词中女子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正是满族开放恋爱观的体现,是一种企图打破封建桎梏的反传统恋爱观。满族婚姻观亦是如此。太清的《金缕曲》组词中的《红绡》写女主人公红绡自主勇敢的婚姻选择。《红拂》则是以词的形式敷演了红拂私奔的故事,词人将历史史实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表现出对红拂私奔李靖的认同,从侧面反映了满族的婚恋观。满族对婚前两性交往持宽容态度,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而且女子常常有与男子“私奔”而去的。据《金史·世宗记》载:“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5]女随男同奔虽然是以两厢情愿为基础,但其实与后世的“私奔”别无二异。
从太清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满族男女婚姻的观念与程式:男女二人若相悦,必先私奔,然后具礼到女方家聘娶,确不似汉族女子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为准。
三、太清词中的精神民俗书写
精神民俗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指灵魂、神、图腾、祖先等;民间娱乐,指游戏、竞技、杂技等。民间艺术指音乐、舞蹈、戏曲、工艺美术等。
(一)民间信仰的书写
满族人信奉萨满,相信万物有灵,对长白山有近乎宗教式的敬畏。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宗教里。”[6]人们相信山间一切都有神灵主宰,是神灵掌管着他们的祸福命运,长白山就成为满族人灵魂的最终归宿。满族入关后仍然保留萨满信仰,有明显的泛神论特征。也就是说,满族人心目中没有唯一的排他性的神明,是一种多神信仰。“既敬奉祖先、氏族和部落英雄神,也信奉动植物神、自然神,祭神时大多数又是笼统祭请、许愿,所以外族的神灵,只要有帮助护佑人的功能,就可能被满族人纳入自己的神灵信仰谱系中,成为敬奉的对象。”[7]这一点在太清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太清词中写到过很多神仙,比如“信谷神不死”(《水龙吟·题张坤鹤老人小照》)写谷神;“问花神、飘香堕粉”(《乳燕飞》其一)写花神;“不是封姨情太薄”(《金缕曲·咏白海棠》)、“无赖封姨不见怜”(《沁园春·落花》)写风神。这些虽然是词人的迷信思想,但却是满族人信仰多元的呈现。
太清苦难的人生经历,使她倾心于佛道思想,词中多处提及与佛道相关的人事和物象。太清以女性词人特有的敏感,将论佛谈玄融入景物描写之中。她的《菩萨蛮·东观音洞》《菩萨蛮·西观音洞》两首词表面上看是记游词,其实是词人信奉佛道思想的见证。词以游览观音洞为线索展开,描绘了佛家净地的深邃与清幽,展现了词人安静详和的心灵状态和摆脱人间苦难、尘世烦恼的渴望。还有《踏莎行·梦,次屏山韵》《江神子·浴佛日喜雨》《凤凰台上忆吹箫·题〈帝女花传奇〉》等词都写到了佛家普度众生的思想,这不仅是女词人慈悲善良的女性情怀,更是佛家悲天悯人思想的体现。
佛禅净化了太清的心灵世界,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深深地浸染词人的身心。如《西江月》:
秋日游鲇鱼关,晚过栖云道院,四十年风景变迁,得不有感。
鹦鹉湾头秋水,鲇鱼关外西风,崇山峻岭几多重。归路斜阳相送。 宛转长城如带,崎岖樵径斜道。栖云道院扣仙宫。四十年来一梦。
从词前小序可知,太清作此词时已年逾古稀,四十年的风景变迁,重游栖云道院,恍如隔世一般,词人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漫长岁月赐予词人对人生的冷静思索与感悟,铸就词人对人生的感恩情怀和淡泊名利、超然脱俗的精神。“尘世纷纷,残棋一局,谁非谁是”(《醉蓬莱·和黄山谷》),词人看透世态炎凉和尘世纷扰,幻想从求仙访道中寻求解脱。
由于满族宗教信仰的多重性,太清词中有许多佛道意象并举的现象。如《鹧鸪天·冬夜听夫子论道》一词,写的是太清与丈夫晚上谈经论道。从词题“冬夜听夫子论道”可知“夜半读经”读的是道家经典,而词的下片“恒沙有数劫无数”又语出佛家经典《金刚经》中“恒河沙数”,“劫”也是佛教用语。即便是佛道之玄妙共通,但此词更能看出太清的宗教信仰观是兼容并包的。另外,从其自号太清和又号云槎外史,足以见出佛道思想对其人生乃至于词的创作影响很大。
(二)民间娱乐民俗的书写
“民间娱乐民俗,主要包括民间游戏、民间舞蹈、民间体育、民间文艺、民间戏剧等。”[8]满族有许许多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娱乐游戏形式,满族人的娱乐游戏并不是简单化地追求享乐或物质奢华,而是一种生活情趣。把游戏艺术化融入日常生活中,是满族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太清词中有很多关于民间游戏的描写,如木偶傀儡、解九连环、抖空中等。
词人对业余游戏生活关注度也很高,像秧歌是颇具东北地域特色的一种民间舞蹈,是北方人民庆祝丰收的一种风俗。重大节日时的秧歌表演,形式多样,规模宏大,热闹非凡。太清的《贺圣朝·秧歌》一词就描绘了农民喜获丰收后进行秧歌舞表演的盛况,词云:
满街锣鼓喧清昼,任狂歌狂走。乔妆艳服太妖淫,尽京都游手。 插秧种稻,何曾能够?古遗风不守。可怜浪费好时光,负良田千亩。
这首词主要写了秧歌表演的热闹疯狂,虽然太清本人对于这种缺乏艺术审美的粗俗表演有厌烦之情,但她还是肯定了这是“古遗风”。据史料记载:“满族接受了秧歌后,按照本民族的审美兴趣、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去改造秧歌、发展秧歌,并将本民族的某些舞蹈融会其中,使其成为关东满族最广泛、最普遍也最为满族群众喜爱的民间舞蹈。”[9]词人批判此种民俗,表现出上层妇女对民间艺术缺乏正确的认识。
傀儡戏又称木偶戏,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太清的《鹧鸪天·傀儡》一词对这种民间艺术有所记述。词人借傀儡戏讽刺批判官场黑暗,表达词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揭示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的生活道理。这种笔法在其他游艺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如《玉连环影·元日解九连环》:
连络,个个环相约。解得开时,本自无缠缚。系连环,解连环,一笑人间万事理皆然。
九连环是民间的一种智力玩具,解连环是满族日常游戏生活中的重头戏,深受京城满族妇女儿童的喜爱。史载:“九连环游戏开始是闺阁妇女、孩童中流行,以后逐步普及到民间。”[10]太清的这首词就记下了她元日解九连环的事,但词人不是简单地记述这一活动,而是借“系连环,解连环”言说了词人领悟出的道理:“一笑人间万事理皆然。”又如《惜分钗·看童子抖空中》一词,其中“空中”也称“空竹”,抖空竹是一种儿童喜欢的游戏。此词写“消闲坐看儿童戏”,表现出词人当时开怀高兴之状。但词笔一转,写到“人间事,观愚智,大都制民深意”,从而悟出“理无穷,事无终。实则能鸣,虚则能容”的道理。
太清词中还记述了民间的水上或冰上的游艺活动,比如《台城路·四月廿四城东泛舟》《定风波·城东泛舟》写城东泛舟,这是太清生活时代京师人保留的一项水上旅游活动。而《浪淘沙·冰灯》则描述了冰灯制作的宏丽奇巧,这是中国北方民间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正是满族人所擅长的一种游艺。
太清的这类词已不再简单地局限于游戏本身,而是寓意深长,揭示出词人对艺术真谛的理解和人生价值的取向。
太清细心体察生活,一些民间工艺美术品也写入词中。比如:“竹簏盛来,多少像生花卉”(《卖花声·像生花》)中的“像生花”是模仿各种人形制成的工艺品。“风丝日影暖相加,岁朝图上应填写”(《鹧鸪天·元日咏荠菜》)中的“岁朝图”是庆贺新年时张贴的年画。“暖入屠苏,宜春剪字”(《蟾宫曲·立春》)中“宜春”是指旧时立春及春节所剪或书写的字样,等等,日常生活气息极为浓郁。
四、太清词民俗文化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一)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太清生活在清朝晚期,满族全面接受汉族文化,汉字汉语基本取代了满文满语,满族在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文学创作等方面基本汉化。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是传承该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其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11]。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存在一种文化展示性书写,即作家在作品中对所属民族的文化进行详尽地记录与描绘,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其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书写。太清词记录了满族的节令风物、乡野采摘、业余游戏等民俗风情文化,书写细致入微,犹如一幅幅民族风俗画,保留了满族普通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太清词的民俗文化书写,不仅是满族人民的业余生活,也是满族人民的闲暇时光,更是有清一代满族人民的集体记忆和心灵映像,传之百代而历久弥新。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太清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为满族民族史和满族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清词的民俗文化书写具有文学人类学的价值,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二)日常化的写作特色
太清作为满族的贵族妇女,其创作较之男性文人更贴近于日常生活,使其词有自我化、生活化的写作倾向。太清以家庭生活和时序变化为主题的词作,其中所描摹的节令风物,基本都是生活中最平实、最普通的事物或现象。描写的是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咏叹的也都是春花秋月、辛酸苦辣等个人情感,和一般闺阁题材作品比较相似,主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呈现出日常化的写作特色。不过细细品之,这些词情真意切,俗中有雅,闲淡纯厚,自有味道。正如有学者所云:“女性词人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无非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琐细闲居生活,然而在太清笔下这一切都贯之以‘深情’、贯之以‘安闲’、贯之以‘雅趣’、贯之以‘灵性’,于是在她的词中最平常的生活细节就是最具有生机的诗意境界。”[12]太清词中的民俗文化书写,让我们感受到“世俗化的写作态度从某种意义上倒是人性的高扬”[13],这一点无疑是词史的一大进步。
(三)理性色彩的高扬
佛道的清心寡欲、忘忧颐养的人生哲学消解了太清作为女性词人特有的感性,使之通达智慧,其词充满理性色彩。词人直接表述自己身外无他累、不为人世无休止的竞争而烦恼的价值取向。这种看破红尘、清心寡欲的人生态度,正是当时一些满族贵族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词人参禅悟道,清静无为,尽管岁月难留,女词人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清醒:无论生前多么声名煊赫,“百年同作土馒头”(《浪淘沙·偶成》)。这正是对初唐诗僧王梵志的《城外土馒头》①王梵志的《城外土馒头》诗云:“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的千年回响。由于女性接触的生活面极为狭窄,所以女性作家往往都是以自我为创作中心对象,像太清这样超凡脱俗、冷静客观地审视人生百态,实在难得。词人全然不在意世间豪华富贵、功名利禄,心目中“惟有真知最高尚”(《冉冉云·雨中张坤鹤过访》),这是一种超然通达的人生态度,同时又是对世人的劝勉。
太清抒写人生感悟、阐述人生哲理的词,较之前代的以伤春悲秋为主调的女性词大大不同。词人采取了镇定与平静的口吻叙述,理性色彩更为鲜明。这正是由于满族复杂的宗教信仰,使词人接受道家思想,赞同道家的“虚无”之说,反映在词中就显得极为从容理智。
太清词“全以神行,绝不局局绳墨”[14]。其词朴实雅正、清新自然,婉约中不失理性与气格,少数豪放词还体现出满民族的自然纯朴、豪放洒脱的性格特征,非一般女性词人所能及。恰如卢兴基所言:“太清的词,能不失大家风范,表现了一种整体美,超越了一般闺秀词的‘小慧’和‘纤佻’。”[15]正是她心目中的“满族情结”铸就了其俊朗洒脱的个性,反映到词作中便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太清词是满汉文化交融碰撞之下的产物,她既注重汉文化的声律与章法,②关于太清词的艺术风尚,可参见拙文《论太清词本体特征的表现形式》(《词学》第三十七辑,2017年6月,174-192页),以及《清代第一女词人作品的特征与成因》(《光明日报》,2017年9月25日第13版)。又保留了少数民族自身的纯真自然,对满族民俗文化的书写正是其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