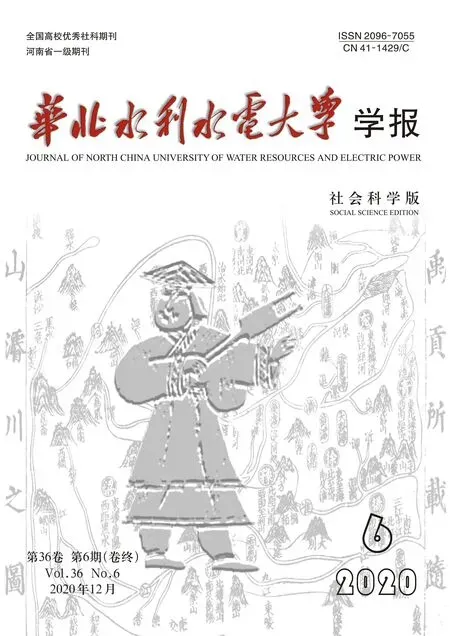马克思早期对哲学变革的最初探索
——以《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为中心
邵宇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下文简称《笔记》)通常被视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准备性材料,其内容主要由七册关于伊壁鸠鲁的摘要和笔记组成。在《笔记》中,马克思突破黑格尔的理解,发现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价值,即对精神自由的推崇和无神论的立场,进而引入“自我意识”概念来界定古希腊哲学。因此,《笔记》中蕴含着马克思早期对哲学思想变革的思考,以及对哲学问题、哲学方法的创新性理解。
马克思在《笔记》中指出:“只有当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整体的时候,世界的分裂才是完整的。所以,与本身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相对立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1]136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支离破碎和世界的支离破碎息息相关,哲学是一种能够影响世界的积极力量。但是,哪一种哲学才能影响世界?所影响的世界又应当是怎样的世界?这就涉及哲学实现和哲学使命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则要立足于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和研究。
一、马克思探讨哲学变革问题的背景
奥古斯特·科尔纽和尼·拉宾在介绍马克思的青年生活时,都着重强调了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思潮对马克思的影响,一致认为马克思最初的精神人格离不开他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深受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和维登巴赫等几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的影响。这种启蒙精神首先表现在《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中。他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出发指出人具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自主选择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这种自由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基于理性的慎重选择;同时,自由的选择也应当具备尊严和高尚,应当以“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为原则和目的[1]3-7。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仅有17岁的男孩所能着眼的高度和立下的宏伟目标!马克思旨在追求全人类的自由与幸福,虽然这一呐喊在当时看似不可思议,但是回顾马克思毕生所从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以说,这一理想与抱负正是他进行哲学改革、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指导理念。
面对深入生活(学习法律)还是研究抽象真理(学习哲学)的职业选择,马克思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学习法律。虽然刚开始马克思表现出了对法律学习的热情,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不满足于已有的法学理论,特别是到了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中心——柏林大学,他旁听了萨维尼和甘斯的讲座,对历史学派和发展了的黑格尔学派产生了兴趣。在《给父亲的信》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哲学是研究法学的前提。他参照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和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建构法学体系,尝试借助浪漫主义和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去探讨法的本质问题,并以此原则去重构法学体系。但问题也就出现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者说马克思的世界观危机就出现在这里。马克思一开始就延续康德的做法,将法的形而上学和法哲学两个部分分开,法的形而上学原则是立法的原则,一切实定法或具体法律都不能违背法的形而上学原则,法律必须立足于形而上学的自由原则之上,并由此写了一部分法的形而上学的原理。但是,马克思发现,他所写的这些形而上学的原理只是理想层面或基于理性的构建,脱离了经验的事实,也即超验的、形式的知识;而实际的法恰恰是与经验事实密切相关。本来寄托于从康德、费希特那里出发重构法的体系以探寻法的本质,马克思发现这样的做法加重了矛盾的严重性,他们二人的法学体系本身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分裂,因此他认为他所建构的体系都是费希特的翻版。不难想象,基于康德、费希特的结构,不加批判地构建,又如何能够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所以他说:“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的领悟,在地面上遇到日常事物。”[1]651-652可以说,经过这次哲学体系试验的马克思已经彻底认识到理想主义的虚幻性。他已经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更加关注现实,或者说从实有角度出发去研究对象。同时,马克思也对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表达了不满意,他把这种方法称为“数学独断论”。这不仅是对康德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的反对,而且揭示出康德先验哲学的矛盾所在,即形式与内容的脱节;同时指出真正科学知识的获取不能完全依赖于数学知识或哲学知识,即思辨理论层面的知识。马克思本来是希望借助康德的哲学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在康德哲学体系和法学体系中发现这个矛盾一直贯穿其中。面对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11这就是说,形式与内容必须统一在事物或对象本身之中,而理性也应当在事物本身之中进行思考,只有立足于事物本身,才能得到真正的与事物本身一致的内容。而这就走进了黑格尔的哲学之中。虽然之前马克思反感黑格尔哲学,指责它那种以阴暗晦涩的语言为掩饰的、虚假的高深,但是马克思在对理论问题的发现和对研究方法的寻找中还是再次走进黑格尔哲学,并借助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体系去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展开自己的哲学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研究方法主要受萨维尼的中介影响,而甘斯则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上起着中介的作用,甘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变革的肯定和对社会斗争的预言等唤起了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此,以往学界有这样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走向黑格尔哲学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原则,即从康德到费希特和谢林,必然会进展到黑格尔哲学。这就涉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动力问题。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最终才又回到黑格尔哲学。真正推动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不是这种外在逻辑形式上的力量,而是马克思从自身理论困境中不断探索,这是实践活动的推动,是在解决形式与内容的同一性和寻找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中不断前进。虽然这个过程也离不开甘斯的中介作用和萨维尼的影响,但是就总体而言,马克思基于自己独立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只不过刚好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展路线相吻合罢了。因此,文艺复兴以来的理论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起到的是理论支撑的作用,而推动马克思走向对哲学变革探索道路的核心主体因素则是马克思这种自身独立的实践活动。
总之,马克思之所以展开对哲学变革的探索,一是由于他追求全人类幸福和自由的崇高理念的支撑,二是他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意识到哲学研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哲学变革,回应现实的社会问题,才能解决形式与内容相分离的矛盾。
二、哲学变革的方向——自我意识哲学
马克思最初是以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家的形象参与德国哲学界并开始自己的哲学批判[2]。他坚定地认为自我意识哲学指明了哲学变革前进的方向。这与他参与博士俱乐部的讨论以及与布鲁诺·鲍威尔的来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在《给父亲的信》一文中得到印证,同时也与当时“实证哲学”和“自我意识哲学”的争论有关。后黑格尔哲学时代指的是黑格尔逝世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状况。黑格尔哲学体系从整体走向了分裂,并逐渐形成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和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总体哲学的崩溃首先表现在精神领域的分裂,各种思想的斗争层出不穷,并由此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割裂的现实状况。因此,对统一哲学的需求实际是哲学界的整体愿望。但是,黑格尔哲学内部争论不休,各个派别都认为自己的理论延续了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哲学史考察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希腊哲学史。在《笔记》第六、七篇和增补篇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历史哲学的研究,进而指出整个希腊哲学其实就是自我意识哲学。他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希腊哲学的发展,代表着希腊哲学的完成。这也体现出马克思一直是按照黑格尔哲学史观的看法来规定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即哲学的发展过程是螺旋上升的过程,后一哲学是对前一哲学的超越和发展。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一样,二者都是总体性哲学(世界哲学),涵盖了世界的各个方面。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崩塌之后,“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中”[1]136。这里的主观形式指的就是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强调其代表着哲学精神走出毁灭的出路和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换言之,自我意识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基于此种情形,那么在后黑格尔时代(总体性哲学的分裂坍塌,时代精神的整体性危机[3])中能够代表哲学生命和未来时代精神方向的也只有自我意识哲学,也就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只有自我意识哲学才能指明哲学变革的方向。马克思以“自我借镜”的方式对古希腊哲学和现在哲学中相似境域的考察,不仅有力论证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合法地位,也明确指出自我意识哲学能够解决目前的哲学困境,代表了哲学变革的方向。
黑格尔虽然认为自我意识哲学不仅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实质,同时也代表了哲学的生命,但是他又把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哲学视为仅仅高于感性、还没有达到理性认识水平的自我意识哲学。这就产生一个矛盾,即这里的自我意识哲学到底指的是哪一种属性的哲学,换言之,哲学变革的方向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涉及另外一层意思,即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在《博士论文》中对希腊哲学衰落问题的处理。如果从理论哲学的角度来讲,理论哲学发展到亚里士多德已经结束了,因为亚里士多德已经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从世界观意义上来讲,他已经到达了终点,因为后续的哲学体系都是对他的重复与搬移。如果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讲,亚里士多德哲学并不是终点,因为如果按照马克思把希腊哲学理解为自我意识哲学的看法,伊壁鸠鲁哲学才是终点。同理,黑格尔哲学并不是德国哲学的最高峰,因为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比拟为亚里士多德哲学,说明黑格尔这样庞大的哲学体系对整个哲学的环节来讲,它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且只是一个初始的环节,而它还要经过哲人把哲学世界化以后,在世界本身形成一个自我意识,这时候才算是一个哲学的完成。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实践化、世界化的哲学,也即实践哲学;同时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雄心壮志:黑格尔只是一个环节,虽然提供了好的基础,但还是需要超越,而超越的路就是走青年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条路。而马克思自身就是这一“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变革者,这足以彰显出马克思的担当与勇气。在《笔记》《博士论文》文本中,皆可以看到马克思正是以哲学变革者的身份深入到哲学和日常经验的研究之中。
三、哲学变革的主体——哲人统一体
马克思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批判考察中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哲人”这一现象。他在《笔记》第二篇中虽然是以“顺便可以提一提”的说辞来阐明哲人的规定,但就其后面的论述而言,这绝非随意一谈;并且马克思在黑格尔《逻辑学》的体系下建构了“实体-哲人”这个统一体,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了哲人规定辩证发展的三个阶段:哲人对现实世界的研究构成理论,而这个理论在反映物理世界的同时,也内含着哲人本身的自我规定;理论进一步上升为概念,即具有更高原则的哲学,如此一来便将哲人从物质意义上升到概念意义,从自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换言之,哲人是通过概念式的把握来实现哲学的变革。这种概念式的把握实则代表着哲学的最高目的即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是纯粹理念的表达和引导。
“希腊哲学从包括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在内的七贤开始,而以在概念中表达哲人形象的初次尝试结束。”[1]63即古希腊哲学家们的历史代表着古希腊哲学的历史。这里已经显现出哲人与哲学的关系。哲人的规定也可以称为哲人与哲学的辩证发展运动。马克思认为哲人作为优秀个体,能够认识到实体的内部生活;并且能够将这种实体的内部生活通过自身的生活和实践活动落实到现实世界;也正是在这样认识外在世界和从事实践活动中,哲人认识到其中的差别与不同,在实体内部生活的规定或指引下,他们又如同造物主一样尝试构建那种符合规定的、不同于外在世界的内在世界,也即思想世界;虽然这只是在思想世界上的尝试变革,但无疑哲人的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紧接着又从哲学史的角度考证了哲人的发展。他从整体上将古希腊哲人发展的整个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发展。最早的哲人只是对自然现象简单地转述,是对生活的直接表达和反映。到了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这里,他们的对象依旧是自然现象。毕达哥拉斯派用隐秘的生活方式和抽象的认知形式去表达他们对实体的内在生活的认识。埃利亚派依旧站在抽象的、超越的、神秘的角度将实体的内容看作是隐秘的东西,并不是基于自身的考虑。这个时期的哲人还只是以抽象的形式来体现概念判断层面的哲人。马克思指出,如果这种实体观念没有融合现实的人民生活,说明它依旧还只是处于观念形式之中,只能是抽象的存在,缺少现实性和人民性。其二,苏格拉底之后的哲人发展。在苏格拉底之前需要提到阿那克萨戈拉。马克思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1卷中说,阿那克萨戈拉象使用机器那样使用智慧,并且只在他不能作出自然的解释时才使用它。……智慧在没有自然规定性的地方是发生作用的,是被采用的。它本身就是自然东西的非存在,即观念性。”[1]64阿那克萨戈拉将观念性的智慧应用到自然规定之外,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活动之中,而这一举动则引领了以后哲人的变化。或者说就是从阿那克萨戈拉开始,哲人不再是隐秘的个体,实体的内在生活也不再仅仅以抽象的形式存在于其自身之内,而是通过哲人的活动走向主观性,特别是苏格拉底,他完成了哲学意识的内在性,同时他将哲人的规定或哲学意识实现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进而将善、目的等都贯穿于他的生活和学说中。实体在哲人的宣扬中逐渐转变为指导现实具体活动的意识、原则,实体的内在生活也逐渐外在化,换言之,哲人将实体主观化,进而使实体性的规定变为自身的规定,于是观念性本身相对于实体而言就不再是相对立的抽象物,实体和自己的观念性实现了统一,也就是说实现了实体与哲人在规定性上的统一。哲人的自我规定不仅是自己的智慧,同时也是实体的表现,哲人的现实性也就是实体自身的现实性。由此,马克思便初步建构出“实体-哲人”的统一体。
但是,“实体-哲人”的统一体是否就是最完美的?马克思认为并非如此,还需要以哲人的概念反思“实体-哲人”这个统一体概念,这才是概念运动的最高形式,也才是哲人规定的最高原则。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概念”需要结合其后面所谈的“概念的判断”:“这种揭示自己内部的观念性的主观精神的表现是概念的判断,对于这种判断来说,个别事物的标准是自身中被规定的东西,目的,善。”[1]67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概念的判断才能揭示主观精神,即寻求更高形式的统一。显然,马克思对“概念”“概念判断”的把握是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紧密结合的,需要放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才能得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把表象上升到概念的层面是哲学的主要工作,概念是对全体的把握,体现了普遍和全部规定性,因此,概念和整体具有一致性。而概念的产生也就意味着个体与实体已经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统一,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主词(个体)与谓词(实体)的初步统一;但是随着概念的运动,这种否定的运动还会一直发展,即概念要接受概念的判断,这是“应当”和“善”的问题[4]。
黑格尔指出,概念的判断代表的是事物的普遍性和全部规定性。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样的判断最终都还是应该归结为现实的应有层面,难道这“概念的判断”不是最高的形式?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冠以现实的名义?这就又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中。黑格尔认为“应当”作为与对象对应关系的范畴是可以具有合适、不合适的属性,具体则是要看实在的对应因素。这就指出“应当”的不确定性,它并不是作为根本的、普遍的原则而存在。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曾经将合乎理性的东西与现实对等,他认为首先就要对范畴进行准确的区别;他对偶然的事物和现实加以区分,指出偶然存在的无价值性,或者说偶然事物的存在不配列入现实的名单之中。这就说明,黑格尔所言的现实并不是指存在的一切,而是指与纯粹理念或理念相符合的事物,它们不是“应当”的存在,也不是“应当如此”,而是“真实如此”;因此,现实性的本质就在于纯粹理念。“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5]45。由此再去反观马克思所言的“现实的应有”,马克思很明显想要强调的是“真实如此”,是理念引导和实现的真正现实,是贯穿本质的现实,也就是说精神在现实中实现了自己的统一,这样的“现实”才是马克思想要达到的“世界”。由此看来,马克思对哲人的规定,实际就是对哲学变革的思考,是对哲学使命的探索。
总之,哲人的规定(“实体-哲人”)过程就已经显现出哲学具体的实现路径,即通过生活和实践活动,依据概念的判断或纯粹的世界概念对现存的世界进行批判,这是一种哲学批判;进而推动现存的世界走向“现实”,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哲学变革使命的理解基本还是遵循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通过概念或纯粹理念的方式进行把握。
四、哲学变革的终极使命——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
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史的批判考证,已经认识到要解决“后黑格尔哲学”的时代危机,就必须要实现哲学的变革,寻找哲学传承的实质载体,提出确切的哲学使命。
马克思认为在哲学史中总会出现重要的关节点,不同关节点之间则代表着哲学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整体而言,哲学总是从抽象的原则开始逐步上升到统一的高度,形成囊括世界各个方面、具备普遍性和全部规定性、完善的、完整的哲学体系,如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和黑格尔哲学体系。但是,这种世界哲学或总体性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自我分裂,即哲学具有历史性;并且都转向主观形式的自我意识哲学,如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伊壁鸠鲁哲学。马克思通过对哲学转向的分析指出哲学的变革会产生新的哲学形态,并且会结束当前哲学的分裂状态走向统一,所以马克思说不必担忧哲学变革所引起的风暴。但是,风暴之后的时代又是怎样的时代?哲学又该走向何方?
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已经认识到哲学与现实之间的相互斗争性,因为现象总是与本质相互矛盾,因此现象世界是历史的存在;而哲学则需要从本质世界出发建构符合本质理念的体系,马克思认为只有总体性哲学才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的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信仰体系,具有普遍性和全体规定性。而马克思认为这种新哲学也是以精神或意识的主体性为核心;同时哲学的研究对象也从自然层面转向自我意识或自由意志,从认识世界转向深入世界的创造,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哲学代表了哲学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他发出“为什么在黑格尔之后还能出现现代哲学家们的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尝试”[1]137的自问,他的隐语则是:后黑格尔时代还是存在一少部分有价值的尝试,即鲍威尔和马克思他们的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借“雅典的毁灭与重建”来说明哲学的变革过程,而自我意识哲学则像种子一样,既保留了以往哲学发展的全部真理,同时又要成为未来哲学产生的起点[6]170。这种作为自由精神的自我意识哲学就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言的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
总之,马克思在《笔记》中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史的批判考察,提出一条“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发展的路径。他借助对哲人的规定,在肯定哲学家中介作用的同时也以概念为基础,通过哲学批判的方式试图建构一个理性与现实统一、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世界哲学,也即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这也是马克思对哲学变革探索的目的所在。马克思并不仅仅停留在哲学重建的视域之中,他的重点一直是哲学实现。沿着这条思路考察马克思《笔记》之后的文本,就会清晰地发现这个重点或哲学使命一直贯穿于他一生的哲学研究之中,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在《笔记》中对哲学变革的最初探索过程是他哲学思想前进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