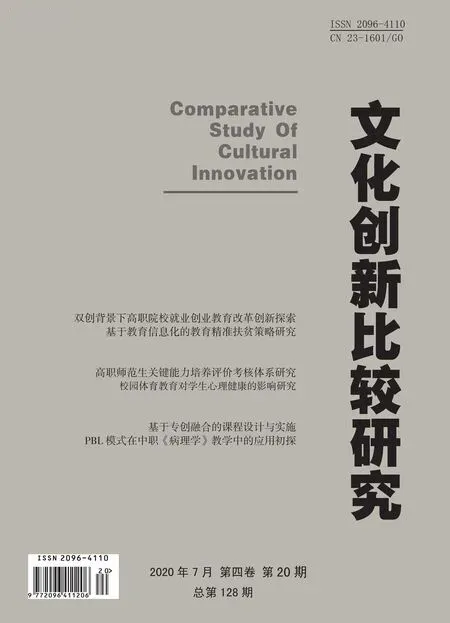从《边城》到《长河》看“人事”之变
——从《边城》题记中的伏笔说起
田海林,夏津蓉
(1.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2.巴东县人民法院,湖北恩施 444324)
1934年4月25日《边城》题记中开始打下伏笔,“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读者)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1]。“人事”就是指人际、社会关系的总和,写小说必然要写“人事”。从1934年4月23日完成《边城》写作,到1942年9月在《文学创作》创刊号发表《长河》的“大帮船拢码头”[2],沈从文从32 岁到40 岁经历了8年的风风雨雨,而湘西的“人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8年的等待和思考,才写下了《长河》,也冲破了“边城”时期的情愫,由他的思考而进入了小说,再呈现给读者。“人事”就是大社会,这样的变化是随着写作心境、情感角度和主要意象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也为比较《边城》和《长河》提供了依据,增加了趣味。
1 心境方面:由“虚”到“实”
《边城》题记中的伏笔“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这种对照是早有“预谋”的。写作时间轴相对现实心境时间轴是不对称的,呈现了“虚”与“实”的对照。《边城》与《长河》在写作时间上跨度很大,沈从文的心境在8年的时间轴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写作时间轴相对心境时间轴是延迟的,拉开了每个故事对应的实际“时差”。从《边城》题记中伏笔可推断,在创作《边城》就已经体会到农民由于遭受“内战”和“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穷困与懒惰”,但这些变化都留在了8年之后的《长河》写作中,只是当时写《边城》的选择性地轻松自由,而不愿写《长河》的紧张多变,也就是说写《边城》是“虚”的心境,而写《长河》是“实”的心境。
1.1 “虚”的心境与《边城》的由来
翠翠是沈从文《边城》中的女主人公,是作者倾注着“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透过主角可以看出写作心境。沈从文在《老伴》《水云》等文中说过,翠翠是由“绒线铺的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即夫人张兆和)”3个原型“合成”的。“这是沈从文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3]。罗义华说“沈从文虽创造过众多人物,唯独对翠翠念兹在兹;与之相对,翠翠这一形象也最能映照其生命情怀”[4],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个体的形态,它还有一种美学的形态在里面,正是沈从文发现了或者是塑造了这种美学形态。由此看出《边城》的实际写作时间轴比现实中“绒线铺的小女孩”和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等一系列女孩子出现的时间轴远远延迟了,那么《边城》中的故事也是远在1934年4月23日以前。虽然“边城”时期的沈从文认识到社会现实的沉痛,可他却写出了农人本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更是写出了翠翠的天真、活泼与无忧,这些共同营造了轻松自由的氛围。
1.2 “实”的心境与《长河》的由来
虽然在1942年9月才完成《长河》,但写的相关故事确实发生在1934年前后。《长河》题记中沈从文写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5]。沈从文多年后回到湘西,发现以前“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这些发现强烈冲击了沈从文的三观,沈从文写下了沉痛的《长河》。因为在8年前就感受到了“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加之8年的社会经历,对湘西农人的变化有更深刻的体会,是怀着无比沉痛的思绪写的,是真实心境的再现,所以《长河》中充满了紧张氛围。
2 情怀方面:由“爱”到“忧”
《边城》写出了对普世“农人与兵士”的“大爱”,也写出了沈从文自己追求爱情的“小爱”;《长河》写出了对湘西乃至整个民族经历战乱的担心的 “大忧”,也写出了对自己当前生活和经历的“小忧”。由“爱”到“忧”的情怀转化,正是从轻松自由到紧张多变的真实映照。
2.1 《边城》的“大爱”
《边城》题记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沈从文怀着一颗不可言说的爱心创造着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他要让爱的氛围笼罩全书……把整个故事谱成一曲牧歌”[6]。沈从文爱这些质朴的“农人与兵士”,在他的笔下,这些人至纯洁、至善良、至豪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和平和欢乐,正是有这样的人才有人间的大爱。他要把“对老船夫的爱,对边城所有平凡人物的爱,直至升华为对民族对人类的爱”,有大爱就有大胸怀,透过《边城》看到“人事”就是欢快的、轻松的、自由的。
2.2 《边城》的“小爱”
沈从文1934年4月23日写完《边城》时才32岁,这时的沈从文正值壮年,精力旺盛,思想活泼,距离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新婚才6个月零14天,正是激情四射、温润甜蜜的美好时光,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欢快。“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那是沈从文梦萦魂牵二三十年之久的“偶然”翠翠和渡船的外祖父都出场了。“他要把翠翠吟成一首诗,他要把自己受压抑的感情和欲望,醇化为对翠翠的爱”。此时的沈从文正处于艺术创作的高峰,不仅完成了《边城》,还创作了《湘行散记》,把固有的艺术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终而成就了具有永久魅力的独特风格。
2.3 《长河》的“大忧”
《长河》几经周折才得问世,其原因就在于内容方面。沈从文有意识的,不仅像《边城》那样,写出民族的“过去伟大处”,而且要写出《边城》未涉及的民族的“目前堕落处”,要写出“常”与“变”。所谓的“常”,即指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等素朴人性美,优良的民族品德;所谓“变”,即是经过20年来的内战所造成的人事上对立和相左,人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素朴关系的日渐消失,从而给首当其冲的农民从肉体到精神所带来的伤害。“清朝以来的湘西,一直是战火不断,兵戎相见是家常便饭。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一区域的男人无疑就会变成战争的一分子”[7]。沈从文在《长河》题记记载了“中日战事发生后,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机会回到湘西……耳目见闻复多,湘西在战争发展中的种种变迁,以及地方问题如何由混乱中除旧布新,渐上轨道,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我都有机会知道得清清楚楚”。沈从文回湘西后再次见证了“常”与“变”,对世事变化的“忧虑”和对未来人民的出路的“忧虑”,这是一种大情怀和大格局,由无比言说的爱到无比沉痛的忧,这个过程是一种文风的流变,也是思想痛苦挣扎的过程。
2.4 《长河》的“小忧”
孤独的和忧虑始终伴随着沈从文,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8],由于天生地孤独,才天生地忧虑。“小忧”的对象是自我,“长河”时期的沈从文自己也正处各种忧虑之中,从他的经历可发现端倪。其一,沈从文先生中日战争发生后的一九三七年又回到湘西,感觉“人事”都变了,自己有种“外人”的陌生感,自己已经与当地格格不入了,没有找到“家”的感觉,由此“忧虑”;其二,由于“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长河》几经周折才得问世,这是对作品本身与能否出版的“忧虑”;其三,1937年和1942年分别写信“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给云麓大哥”,表达了对家人的担忧。这些透露了沈从文真实的思绪,由对农人的“忧虑”内化为个人的“忧虑”。
3 意象方面:由“常”到“变”
沈从文的很多写作都与水有关系,水给他种种印象[8]。与水相关的作品中又产生了很多意象,比如,《边城》中小溪边的“渡船”和《长河》中腾长顺家的“桔子”,都是“水”的衍生物,然而“渡船”和“桔子”却不能只看表象,还要透过意象分析寻找真谛所在。
3.1 《边城》中小溪边的“渡船”
渡船贯穿始终,见证了“茶峒”城边人民的一切“人事”。渡船既是爷爷工作岗位又是偶尔休息的地方; 既是形形色色的人过渡的桥梁又是聊天沟通的“桥梁”;既是运送货物的工具又是礼尚往来的渠道。在《边城中》,爷爷和翠翠住在清幽的环境里,爷俩无疑是最快乐的,白天爷爷撑渡船,15 岁的翠翠或独自玩耍,或偶尔帮爷爷渡路人过河。遇到风和日丽的日子,无人过渡时,爷孙俩就坐在门前晒太阳,翠翠逗狗,爷爷吹笛;抑或爷爷讲故事,翠翠眯缝着眼睛看太阳。渡船是爷爷收入的主要来源,每月公家会派人送来三斗米,七百钱,偶尔有渡船人掷几个钱在船板上,倔强的爷爷必把钱塞回去,口气极严肃认真地嚷嚷着“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渡船”既见证了爷孙俩的快乐,又见证了“茶峒”城边人民的慷慨和互帮互助,但同时又将翠翠和天保、傩送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渡般代表的是撑船老人的孙女翠翠,傩送选择“渡船”,象征着选择爱情,这个结果代表傩送对生活态度的,对物质和爱情的抉择。
但在“渡船”所见证的一切人和事都是那么平和、善良、质朴。在文学创作中,沈从文有意识地追求唯美的文学创作原则,坚守古典的浪漫主义情怀[9]。他把“茶峒”城边的人和事写得美到了极致,展现了当地“人事”的轻松与自由。
3.2 《长河》中腾长顺家的“桔子”
“沈从文青少年时期,经过七年军营锻炼,对苗疆各地风情习俗,民间疾苦,观察入微,十分关切”[10]。正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才对战乱中的辰河中部小口岸吕家坪的“人事”有沉痛的审视。“桔子”既像一双审视的眼睛,又像沈从文的“笔”,充分发挥了“证明人”的作用,证明了“经过二十年来的内战所造成的人事上对立和相左,人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素朴关系的日渐消失,从而给首当其冲的农民从肉体到精神所带来的伤害”。
4 结语
从《边城》问世后,读者们等待了漫长的8年,等到《长河》发表后,故而又等到了比较“人事”之变的机会。就小说情节本身来看,《边城》中的场景是在自给自足的民国初期,社会人员结构比较单纯,农人和其他人相处和平且和谐,人与人之间是自由而轻松的;《长河》中描绘的场景是“经过二十年来的内战所造成的人事上对立和相左,人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素朴关系的日渐消失”。所谓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正值战乱年代,加之国民党的统治腐败,随意压榨商号、鱼肉百姓,造成了更多不稳定因素,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更加激化。
前后的“人事”之变,和沈从文的文风转变是高度一致的,刘保昌认为“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完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转变”。《边城》因为创造的是多年以前的故事,尽管社会动荡,也在遭受战争,但沈从文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以写“虚”的手法写出了轻松自由的故事。创造《长河》是因为经历了社会的蜕变,沈从文痛定思痛,以写“实”的手法将自己忧虑的心境写入了小说。由写作心境在时间轴上的“虚”与“实”,将作者的“爱”与“忧”进行了升华,将主要意象“常”与“边”进行了对照,让读者走进文本,更走进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