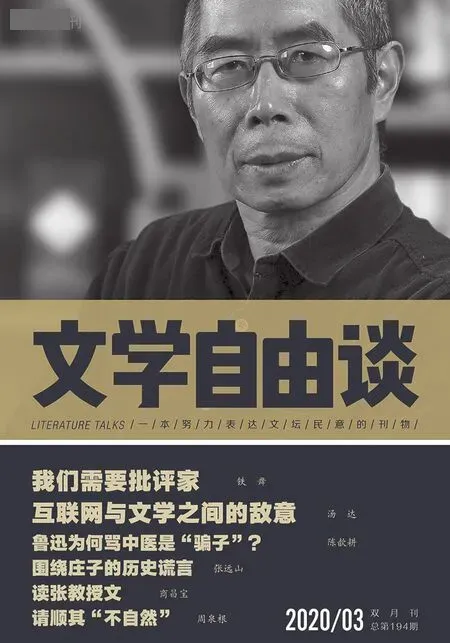读张教授文
□商昌宝
作为大学教授,不但要教书,还要进行学术研究,撰写学术文章,尤其是对那些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
张颐武先生就职于北京大学,在其专著和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中会注明: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既然学术光环如此耀眼,张颐武教授教学之余应该有大量学术文章问世。检索2019年CNKI“期刊”一项,果然发现其名下有十六篇文章,去除一稿两发的同名文章外,也还剩十五篇。
如果单看数量,按照一般大学的科研考核,一年十五篇的量肯定是优秀了,也可能因此获得年终绩效科研奖励。不过,若看一下文章发表的刊物,《中关村》九篇,《北京观察》两篇,《电影艺术》《当代电影》《新闻战线》《红旗文稿》《美术观察》各一篇,感觉就有些诧异了。首先必须声明,笔者绝不是那种机械的唯核心期刊、CSSCI论者;但作为文学同行,感觉这些刊物还是有些异样,有点不那么惹眼。尤其《中关村》这个也可能是很著名的杂志,确为笔者眼界狭窄有所不知,不过这次借机补课,得以见识。
当然,刊物作为文章的载体,很多时候是唬人的招牌,只有那些行政管理的低能儿为了方便才作为评价指标,真正的学术检验还要看文章的质量。有道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标题大体上可以看作文章的眼睛。咱们来看张颐武2019年发表的文章的标题:《从二月河逝去说起》《〈无名之辈〉:脆弱与感伤的力量》《2019:影视产业转变中的机会》《〈流浪地球〉:关于人类选择的想象》《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立方向》《“鸡汤”的优劣在于营养》《“五四”与当下——一个侧面的思考》《三十年后看海子》《人文素养不可缺少》《荷花的境界》《〈哪吒〉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动漫电影的未来》《〈哪吒〉的启示》《“冰墩墩”“雪容融”:既有京味儿,又有内涵》《从诺贝尔文学奖看全球“纯文学”的审美趣味》《“吉祥物”的文化意涵和美学追求》。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这些文章的“眼睛”,真的不敢相信堂堂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年中竟然就在忙乎着这些!为了安抚自己几乎惊掉的下巴,也是为了“最起码的求真之心”,笔者又检索了一下CNKI中的“报纸”一项,结果显示一共三十四篇,其中数量较多的是《环球时报》十六篇,《中国文化报》七篇、《人民政协报》三篇。认真浏览文章的题目后,确信与上述杂志所发文章的内容与格调大体趋同,也就不去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归类总结了。
为了有的放矢,也为了以理服人,笔者不惜耗费时间将十五篇文章全部浏览一遍。结论是:能够勉强作为学术文章或学术随笔的两篇,文学、电影评论(短评)六篇,准领导讲话稿两篇,其余可笼统归为通俗文化批评。
既然是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们就来看看那两篇学术文章的水准。
首先是学术分量略重的《“五四”与当下——一个侧面的思考》。这篇文章姑且不说关于五四的历史背景完全是闭门臆想和道听途说,基本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层次,也不说关于五四的基本认知剑走偏锋,表现形式就是一上来就议论、抒情,却几乎没有给出什么证据和论证。这些文章之道和观点阐释,毕竟属于学术之争,一言两语说不清楚,所以暂且不去评说,这里单就文章的内容和结构来说。
作为主体部分,文章先是引入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从中提炼出前人所忽视的“自觉”与“奋斗”这两个相生相伴的五四主题。不管这个学术发现是否重要,能够将“自觉”与“奋斗”补充到五四的“民主”“科学”“人权”等大主题中,又由五四发展到当下,引申出民族复兴之类的话题,都可以算作是学术贡献,符合一个教授的水平。
接着,文章引述了李长之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特别引证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之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究竟是胡适之的五四文艺复兴论更客观,还是李长之的五四启蒙论更切题,五四启蒙到底是不是“太清浅,太低级”等观点之争,这里都不去评说,能注意到二者的存在和区别,也算是教授水平的体现。
之后,文章重点谈了冯友兰的《新事论》。张颐武非常服膺这样的观点:“现代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延伸和展开,只是其社会又由‘生产的家庭化’的传统社会要转变为‘生产的社会化’的现代社会。这种转变是‘现代性’的历史询唤,也需要是传统的成功的转化,而不可能是传统的断裂的结果。中国社会和西方相比需要从根本上通过‘现代性’的追求,进入一个‘生产社会化’的新格局。”然后,他自己据此评论和阐发道:“这些论述所提供的超越把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模式,这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启发性。”
笔者学识有限,读不懂冯友兰的《新事论》,不过就张颐武教授这段语病突出的分析和总结来说,感觉冯友兰要表达的意思是:传统中国是“生产的家庭化”,在根本上通过“现代性”的延伸、展开、追求和转化而不是断裂,从而变成“生产社会化”的现代社会。张颐武教授就此观点,怎么忽然得出了“超越把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模式”和“重要的意义和启发性”的结论呢?现代性,尽管不能百分百地等同于西方,但是如果说等同于印度、阿拉伯、非洲、南美、拉丁美洲和中国,恐怕更说不过去。既然把冯友兰的“根本现代性”观点作为证据,就应该符合逻辑地说: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根本上不能超越西方的普遍模式(或者根本上要比西方更加现代性)。怎么忽然来个自我否定的回马枪结论呢?实在是让人想不通。
当然了,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冯友兰,在中日战争背景下所做的关于“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思考,究竟存在多少局限和自相矛盾,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此前写过专论《对“现代”的中国思考——重读冯友兰的〈新事论〉》的张颐武教授,应该好好理解和阐释、表达才是。
如果说张颐武教授一不小心做了错误的理解或阐释,尚可以原谅的话,文章到了最后的两小段,实在不能不令人出离惊奇了。因为正如前面所述,整篇文章,他一直在谈五四以及五四与中国的复兴之类的高大上问题,结果忽然“跳加官”似地扯起当下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还说什么“总体来看,五四与电影的关系,其实展开了如何面对电影的‘现代性’的关键性议题,人们对此的不同回应其实也是五四和电影关系的展开,也是电影文化探索的关键部分”。
笔者真是不揣冒昧地想问问张教授:您评上教授年头不少了吧?指导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也不少了吧?您是就这水平还是为了应付约稿随便对付了一下?您在指导学生时也是跨度这么大,让人跟不上节奏吗?您这样写和发表文章时,没考虑到北大中文系的声誉和您自身的教授头衔吗?您不能这样随性去写来对待相信您的天真的读者和粉丝呀!
另一篇比较学术的文章是《三十年后看海子》。客观地说,虽然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新观点,也不见得在海子研究中占有什么分量,但其中涉及到海子在大学时期发表的长诗处女作,也算是一个文坛史料。为了凸显张颐武教授的学术价值,这里引录其中一段,以飨读者:
八十年代初,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办了一个小期刊《启明星》,有了一点反响,作为法律系同学的查海生来到我的宿舍留下了他写在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当年的分部劳动时的感受的诗。那是一首恢弘的长诗。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怀那篇写在400字稿纸上的作品。作者写到尽兴的时候,干脆把稿子横过来,把一气呵成的长句子尽情地展开,那是一首山的颂歌。当时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同学都为他的不羁的诗才所震撼,我们的《启明星》发表了这首诗。这大概是海子的最初发表的诗作。
说完两篇勉强算作学术的文章之后,笔者本来不想再继续写下去,因为那六篇评论文章,若论文学和影视的见识与审美水准,与一个普通中文系的本科生差不了多少,实在不值得一说。
但如果以为这样的判断是笔者的偏见或激愤之语,那就不妨举《从二月河逝去说起》这个例文。
张颐武在文中以赞许和维护二月河的立场写道:“有些批判,诸如说他歌颂封建,思想落后,对帝王的现代批判缺乏等等,其实是从五四以来的流行观念,老生常谈去批评他,也其实抓不住二月河流行的核心。就是用一种老观念看新现象,缺少真正的对二月河的具体认知和判断。二月河其实是通过一种民间化的对历史的理解,把历史变成了一种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人的选择。这让他充满争议,但也受到当时的大众的欢迎。其实他的作品也让人感受到一种在复杂的变化和不确定中寻求某种确定感的状况,这似乎是人们接受二月河式的历史解释的一个方面。二月河的历史解释根本就没有从现代和传统对立的角度立论,而是从人们对历史的期望的现实感受出发的讲述。他有点像个说书人,带我们进入那个情境,但他和说书人不同的是他的想法又和过去说书的正统有距离。他可以说是敏感到当下需要的说书人。……因为二月河的小说作品都太成功了,特别是令社会大众能够最大限度内了解有关明清的历史。因此,当社会大众对于明清的历史了解达到一定的饱和时,他们也就不需要补充新的‘知识’了,这也正是短期内难以有人超越二月河地位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引述这样长的一段话,目的就是让读者充分了解一下张颐武这位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风采。为了让这个风采更直观、更鲜活,笔者不妨也来借机做一下文学评论:
首先,在这一段引文中,张教授大概急于为二月河辩护,所以词穷到连续使用四个“其实”,意思就是批评二月河的那些人,都是误读,“其实”只有张教授读懂了,然而一时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转折连词,无法传达那份迫切的劲头儿,就只好颠来倒去地“其实”来“其实”去。
其次,二月河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追求究竟如何,笔者这里暂不去评价,但对于维护二月河的张颐武教授来说,他自然是欣赏和赞誉有加。既如此,将那么成功的一个作家比作“说书人”,哪怕是“当下需要的说书人”,总是让人感觉这不像是表扬,反而是不怀好意的讽刺和揶揄。据笔者所知,二月河生前一直自以为是个不错的作家,从来没把自己定位在老北京的天桥,也从来没有像赵树理那样自诩为“地摊文学家”,他如果知道有人打着夸他的旗号而把他说成“说书人”,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王朔当年说鲁迅坐起来扇那些所谓鲁迅研究专家们耳光的结果。
最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虽然在市场上赢得了大众,也可以说是“太成功了”,但是否就最大限度地让人了解了明清历史?大众是否就因此达到了历史的“饱和”而不需要补充新的历史知识了?这话的意思好像在说:作为大众,了解了二月河笔下的历史,已经足够到不需要更多、更新的历史知识了。可是,张颐武教授不能自己跃升为知识精英后,就不让别人进步了,要知道大众中也有不愿一直做大众的人,他们怎么就不需要新历史知识了呢?你让大众安于二月河的帝王将相历史叙事,怎么能在影视产业转变中寻找机会呢?怎么能为文化艺术发展确立方向呢?尤其是作为当年的“后学”大家,提倡如此前现代的东西,将“前”“后”无原则、无差别地混淆,怎么去领导文化事业呢?
其实(笔者也是词穷了),深究张颐武教授的大作实在没多大意思,因为从那些天桥式的文章题目来看,就已经可以下个初步判断了,只是考虑到胡适曾建议做文章当从小处着手,学术本身又讲究严谨,于是才这样费时费力地做了功课,结果仍旧是无用功。至于那些高蹈的学术良知和学术羞耻,不适宜在这篇文章中深谈。
北京大学曾经令多少中国学子向往,北京大学中文系曾经是多少文科学子的梦想,其教授、博士生导师当然不都是这样。就是张颐武教授本人在2019年之前,也有很多探讨大问题、产生大影响的文章、著作、课题和学术贡献,甚至曾经一度引领学界之风气。但就2019年来说,他实在是丧失了学者的底线。斗胆说一句,或许这会影响到北大中文系和北大声誉了。
文章结尾之际,差点忘了说,《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立方向》这篇绝非秘书代笔的文章,立论之高远,内容之充分,条理之清晰,气势之磅礴,尤其是其间所体现出的张嘴就写、提笔就说、倚马可待的精气神,绝对是一流领导的一流讲话稿,这一点笔者很是折服。哪怕是基于这一篇文章,都可以公道地说,张颐武教授绝对称得上是有文化的领导。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