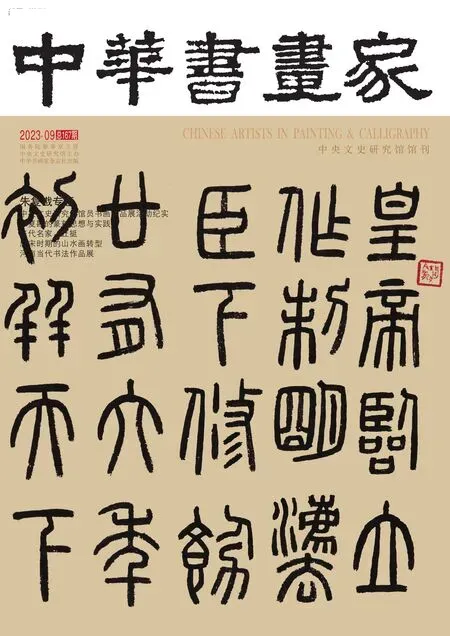朱复戡《致巢丈书》探研
□ 樊英民
《致巢丈书》是朱复戡现存书札中年代较早者。全文是:
十年前千里外得长者书,以旧拓阁帖见赠,幸何似焉!侄自得帖,晨夕浸淫,孜孜以还,未尝废离。其所以如此,欲以报长者情意之殷、相期之深也。比者所书,还乞诲正,不审尚得一二不?侄别来故我依然,䌹丈每以未达见痛。侄终以候权门、贿阍者、立厩下、献上寿、五六揖为不能,此所以迄无所成。然侄未尝以此戚戚也。比年忧患余生,临池自遣,每临纸笔,辄怀长者。盖侄于书,其转变实蒙其赐。今吾丈高龄远处,每一念及,辄为神驰。关山遥隔,时切梦系;北地多故,尚祈珍摄!临书拳拳,不尽阔怀,专肃敬上巢丈尊前。
侄百行拜顿首
解读此书,首先应解决的是巢丈是谁和此书信的写作时间问题。
在笔者所接触到的有限材料中,可以被朱复戡称为巢丈的有巢鹏云、沈卫(晚号兼巢老人)、李拔可(晚号墨巢)、陈去病(字巢南)、涂紫巢等多人。我曾经认为巢鹏云的可能性比较大;后来得到张戈先生的指正,他认为巢丈不是巢鹏云,而应是自号“苦巢”的张颐。
关于张颐,十几年前我整理张美翊的《菉绮阁课徒书牍》时曾接触过他的一些材料,但一直不知道他有“苦巢头陀”这个别号。后承王璨先生提供线索,使我对张颐有了较多了解。
张颐,浙江鄞县人,寄居天津。字张颐,号一香、亦湘,又号苦存、苦巢头陀。有《南归草》诗集、《张颐诗稿》等传世,从中可知与他所交往者有章一山、赵叔孺、方药雨,顾衡如等,多是当时在学术诗文、金石书画以及收藏鉴赏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家名士,而且基本都是宁波人。其《己卯草》题下自署“廿八年七三陈人张颐苦存甫”。以此推算,他当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诗稿最后一篇是《戊子元旦》,故应卒于1948年后。张颐比朱复戡年长36岁;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辈份看,朱复戡都应该称他为丈。张戈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现知张颐与朱复戡的翰墨因缘,可追溯到令张美翊视如拱璧的那方晋太康砖。砖是20年代初张颐从天津寄给他的。青年朱复戡琢之为砚,又刻上“太康砖,晋初肇,中砚材,发墨藻,子子孙孙其永宝。百行造”的铭文,令张美翊叹赏不已,乃作题跋记其事,又请冯君木题。一砖而关联多位名家,可称艺林佳话。
虽然张颐比复戡年长很多又长居天津,但从张美翊《菉绮阁课徒书牍》看,两人之间还是有一些直接交往的。如《致百行》第64书,“张颐今日来沪,已告贤寓处。”第49书后附“再”:“张颐在此已数月,睠睠念贤不置。”张颐在致张美翊信中也曾提到朱复戡,如第54书有:“张颐来函极称贤才品出众,又谓近写石鼓不落缶老一派……”。
朱复戡摹写的石鼓文,曾得到张美翊以及方药雨、俞语霜等诸多名家的赞赏和题跋。张颐也有题跋:
晚近书《猎碣》文字者首推吴老缶,老缶故老作家,然偶犷悍之气,欲以此炫流俗之目也。今观静堪此册,缩其结构,笔笔清劲不懈,而入于古。兰花空谷,无言自芳,其见识洵高人一等哉!壬戌八月四日,一香居士张颐时与静堪同客海上。
壬戌是1922年。《菉绮阁课徒书牍》是庚申(1920)到癸亥(1923)四年间所作书牍。以壬戌年计,当时张美翊66岁,张颐57岁,朱复戡21岁。他们是三代人。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间谈书论艺的情境,更不难想象两位长者对青年朱复戡的高度欣赏和期许。
但张颐和朱复戡在艺术趣味上有时并不一致。如上引题跋中张颐称老缶(吴昌硕)书法有“犷悍之气”,是“欲以此炫流俗之目”;还有张美翊致百行第44书的“张颐、叔孺皆以缶翁刻印有江湖气”,都反映了他对吴昌硕艺术的不满。而“静堪此册,缩其结构,笔笔清劲不懈,而入于古”之评,和他致张美翊函中说复戡“近写石鼓不落缶老一派”,正可互相发明,都是以正面肯定的方式鼓励青年复戡要跳脱出吴昌硕的窠臼,以形成自己面目。关于这一点,早在两年前就有方若的提醒:“定海方药老自普陀来访,谓贤临字皆像,然是人家字,非自己字。书字必须有我在。”(《菉绮阁课徒书牍》第9书)
《菉绮阁课徒书牍》第45书有:
此次篆额尤佳,仓派亦殊可爱,总较邓、徐(三庚)好看,料此派流传较邓、徐为久,张颐訾之太过,贤訾赵君亦太过。文人相轻,老朽最不谓然。我生平交友,崇拜多而訾议少,君所知也。
其中的“仓”,自然指吴昌硕;而“仓派”,是把朱复戡列入其中了。又第49书,说老朋友费冕卿“谓贤篆似仓”。按费冕卿并非书法圈子中人,他是实业家,时任四明商业银行经理,可以说代表了社会上多数人的看法,即当时朱复戡书法属于昌硕一派。张美翊说“张颐訾之太过,贤訾赵君亦太过”,张颐所訾是昌硕一派,朱复戡所訾之赵君疑指赵叔孺,赵书风恬静秀逸,当然与仓派有较大距离。“訾”是批评、是指责,甚至是诋毁,可以想见两人都有过比较激烈的言辞甚或辩论。三人间评论艺术,臧否人物,两个晚辈难免舌剑唇枪,说出出格的话来。张美翊居间调停,并不论谁是谁非--当然,艺术趣味本来就无是非可言。但我们不难想象,张颐对年轻的朱复戡一出手就学吴昌硕是不以为然的。
清末民初书坛,隐然有碑学和帖学两派。张颐似可归入重帖的一派。他比复戡年长很多,自认有引导后生的资格和义务。《菉绮阁课徒书牍》第49书有:“张颐总劝贤留意晋唐字。谓元明大家确有独到处。”张美翊当然也是赞成的,说“鄙意总愿贤于书牍写晋隋唐字,晋如《兰亭》《集王圣教》,隋如《开皇兰亭》《龙藏》寺,唐如虞之《汝南公主墓志》、褚之《枯树赋》、欧之行楷(见《三希堂》)……先从书牍入手,惟贤能为此也。昨得一老长函两纸,完全《十七帖》,此老豪杰,何可及耶!”(第53书)其对帖的推崇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张美翊和张颐都希望年轻的复戡加强帖学修养,不要在吴昌硕犷悍之气的影响下愈走愈远,而应向清劲内敛、含蓄蕴藉的方向发展。“兰花空谷,无言自芳”八字,可说是张颐对青年复戡未来书法面貌的愿景。我想这就是张颐不远千里从天津寄赠阁帖的原因。
阁帖,即《淳化阁帖》,在法帖中有崇高地位,被称后世诸帖之祖,旧拓本尤为珍贵。张颐赠旧拓阁帖之举有“红粉送美人,宝剑赠壮士”的意味,充分显示了他对青年朱复戡的器重。
而朱复戡也不负所望,他得帖后“晨夕浸淫,孜孜以还,未尝废离”。帖学在他一生的艺术历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他在多篇题跋对二王、对锺、张、怀素等书家都作出自己的评价,所据大多是阁帖。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复戡在书法尤其行草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和阁帖是分不开的。“侄于书,其转变实蒙其赐”,不可以理解为一般的客气和应酬,而是自我总结得出的结论。海纳百川、不主一家是他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故此书于了解朱复戡的艺术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致巢丈书》未署年月。考此书有“十年前千里外得长者书”,而从上引材料看,张颐在1922年的下半年与朱复戡常有聚首(题石鼓文署“壬戌八月……与静堪同客海上”),应是张颐返津后寄赠阁帖。如此推测不误,则赠帖应是1922年底或次年初的事。十年后作《致巢丈书》,当为1933年。
《致巢丈书》的又一意义,在于生动地显示了朱复戡刚强不屈的性格和极其看重风操气节的人生价值观。细读其文,典雅的文字后面,能使人感到某种震撼,尤其“侄终以候权门、贿阍者、立厩下、献上寿、五六揖为不能”一句。
这句话典出明代宗子相的《报刘一丈书》。文章的背景是奸相严嵩当权,小人们蝇营狗苟,毫无羞耻地奔走于权奸之门,令正人君子齿冷。作者用尖锐泼辣的文字,描写贪图仕进者干谒送礼的过程:
……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明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
这段描写细致生动,干谒者的奴颜婢膝,被接见后的洋洋自得、恬不知耻,都真实如在目前,活画出古代官场的丑恶不堪。而这就是要博取所谓“功名富贵”必须付出的代价。有骨气的士人对此当然深恶痛绝,所以作者说自己有时走过权相之门,要“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而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即使因此“不见悦于长吏”,也只好以“人生有命,吾唯守分而已”安慰自己。
《报刘一丈书》是被选入《古文观止》的名文。据《朱复戡年表》,朱复戡8岁起就读《古文观止》。此文引发过他强烈共鸣,所以记忆深刻,会很自然地在《致巢丈书》中引用。
朱复戡的人生志向就是艺术创作,做学问;他做人的原则始终是坚持独立人格,光明磊落,不事攀附。从这个意义上说,《致巢丈书》可看作是他的人生宣言,宣示的是他对操守的坚持。这种视功名利禄如敝屣,将道德人格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贯穿朱复戡一生。
《致巢丈书》可以说是深入理解朱复戡艺术和人生的钥匙,值得重视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