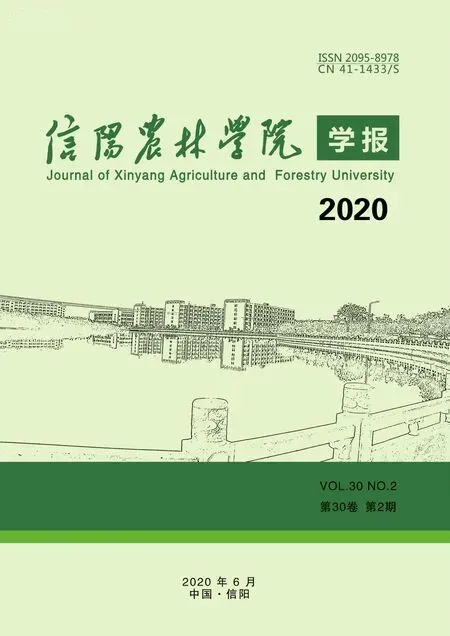司马迁生平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吴长城,刘得腾
(1.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陕西 渭南 714000)
1 《索隐》及《正义》之司马迁任官履历不足凭信
在司马迁生年问题上,有王国维、梁启超、张鹏一、郑鹤声、刘汝霖、泷川资言、水泽利忠、钱穆、朱东润、季镇淮、徐朔方、张大可、施丁等人的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说,有桑原骘藏、山下寅次、李长之、施之勉、郭沫若、王达津、陆永品、赵光贤、吴汝煜、袁传璋、李伯勋若等人的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说[1]。造成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聚讼的主因是两则史料。其一为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张华《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其二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条下作注“迁年四十二岁”。根据司马贞和张守节这两种不同的说法,结合古人按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分别可以推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或公元前145年,刚好相差十年。这造成双方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争论不休。前说认为《史记索隐》传播过程中“三讹为二”,司马迁应该在任职太史令时三十八岁。后说则从“卄卅卌”都为一笔之差来论证《正义》的“四十二岁”也可能是“三十二岁”。除从《索隐》和《正义》中找到的两条主要证据外,学者还纷纷从司马迁生平大事略和与人物交集角度寻找旁证。
然而,这两则作为二说判断司马迁生年的共同史料存在致命缺陷,次论如下:
一是现传司马迁履历资料为孤证。根据今本《索隐》和《正义》关于司马迁的任官履历均可倒推其生年,恰好就是十年的巧合,难免令人心生疑虑。按司马贞与张守节同属唐开元间人,但行年不详,据《正义》书中多有补充或纠正《索隐》的话,可见张氏撰写《正义》时是看过《索隐》的[2]。因此,王国维所说的“《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只是猜测之语,“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三十八……”等均是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论。相反,更大的可能性是张守节作《正义》时,与前后许多学者一样为司马迁生年所困扰,待读到《索隐》“元封三年,司马迁二(三)十八岁”,便稍加变通,采纳为“太初元年,司马迁四十(三十)二岁”。后来由于文献抄刻致讹,产生了十年的误差。因此,《索隐》《正义》两则史料只能看为一则史料,且当以《索隐》为早。在未发现古本《博物志》之前,从逻辑上来说,更倾向于《正义》史料转引自《索隐》而非直引《博物志》。
二是《索隐》司马迁履历资料来源存疑。退一步说,就算关于司马迁履历的这则史料见于《博物志》,亦不能确定它的真实性。太史公生年和涉及具体年龄及纪年的任官履历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本传,在《西京杂记》《汉武故事》之类好奇发幽的作品中也不见提及。司马迁辞世八百多年后,司马贞骤然在《索隐》中提出,却又指证《博物志》为史料提供者。今本《博物志》恰好也没有《索隐》提及的这则史料。按《索隐》计有5处,《正义》计有4处,合计达9处征引《博物志》,但仅得1处提及某人(即司马迁)任官时间及年龄。除此二家注外,在其它大量征引《博物志》的著作中竟也是一种孤立的现象。退一步来说,就算司马贞所见的古本《博物志》的确有这则史料,仍不足凭信。《晋书》华本传及《隋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十卷,新、旧《唐书》移入小说家,卷帙同,《宋史·艺文志》亦作十卷,但收入杂家类[3]。这说明用《博物志》补充正史显得荒诞。这种现象也并非没有引起司马贞、张守节二人的注意,反观二人书中,仅在地理沿革、名人字行、口头传闻等方面谨慎引用《博物志》,精确引用司马迁的任官时间和年龄的确是唯一的一次。
三是《索隐》司马迁履历资料不符合西汉京官任命文书的特点。为证明《索隐》使用司马迁履历的正确性,王国维从《敦煌汉简》中找了两个例子,“新望兴盛里,□杀之,年卌八”和“□□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郭沫若认为《索隐》司马迁履历中“官职、乡里、身份、姓名、年岁、事由带年月日,是一个完整的公文格式”,相形之下王国维的例证还不完备,遂从《居延汉简》补证了十条,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仅将他视为铁证七、八、九、十,共四个例子转引如下。“水门队长,张掖下都里,公乘江睖客,年卅,建昭二年(下缺)”;“(上缺)长平田辛里,公乘王弘,年廿八,五凤元年十一月丁酉除,就还”;“居延甲渠止害队长,居延收阝佳里,公乘孙勋,年卅,甘露四年十一月辛未除”;“ □□甲□第十三队长,□田万麻里,上造冯匡,年廿一,始建国天凤元年闰月除补,止北队长”。二位先生征引的简牍文献似可证明《索隐》所传司马迁履历不假,然而仔细琢磨,发现这些简牍都是基层吏卒的履历。据王玉璘研究,西汉官方文书涉及官吏任免分为上下两类,上层官员多用制书,牒书、除书、遣书则为地方人事任免的官文书主体[4]。蔡邕《独断》“制书……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表明西汉用于任免官员的制书只称官职及姓名,不涉及籍贯年龄等信息。任命之例见于《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于是制诏御史:其以胶东相(张)敞守京兆尹。”免职之例见于《汉书·萧望之传》:“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这种现象不能用史书记载简单来说明,原因有二。其一,《汉书》对诏书、策书、制书有全文征引的习惯,如各诸侯王的封策。其二,现传司马迁履历资料在古文献中独一无二,再无任何一个西汉官员有如此详细的任官信息,似指向于人为增益作伪的可能性。
上述可见,景帝中元五年说抑或武帝建元六年说均因主证史料的缺陷导致不成立。倘若利用司马迁生平大事略和与人物交集去探寻,在没有新的有力证据出现以前,亦只能求其大概。
2 “自请宫刑”当为“赎为宫刑”
有人认为,司马迁一开始就被判处宫刑。这种说法已经被另一种观点从《报任安书》等文献中找到一系列证据予以驳斥,在此不再赘述。韩兆琦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开始被判处死刑,后来在他本人的请求下改判宫刑,依据是汉景帝中元四年(前146):“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也就是说,死刑犯可以自请改为宫刑。按景帝元年(前175),诏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可见汉文帝在除肉刑时,宫刑作为其中之一,也予以废除。不过随着原有宦官年老等原因,景帝不得不在中元四年恢复宫刑。根据这两则资料来判断,似乎的确存在死刑犯自请宫刑替代死刑的可能性。韩兆琦所指的“自请宫刑”,还包括有偿赎免死刑为宫刑,但未对此进行深挖,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5]。下文试就此展开论述。
一是司马迁遭受宫刑时大小罪行都可以出钱赎免。死刑犯自请宫刑在武帝时代是有偿的,需要花钱赎买。据《史记》之《平准书》,《汉书》之《武帝纪》及《食货志》,元朔六年(前123),武帝行卖爵和赎罪之法,设武功爵十七级,总值三十余万钱,但不久废除。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上奏请求恢复“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的政策,任治粟都尉仅一年,“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武帝又于天汉四年(前97)、太始二年(前95年)两次颁布赎罪诏,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其针对的主体为死罪。韩树峰认为,从理论上说,死罪可赎,则其它罪亦可赎。因此,推断这两次诏令的目的,并非禁止赎其它罪,而是将原来赎死的资产数额提高,以增加财政收入。入五十万钱只是降一等服刑,并非成为庶人,似可证明此点[6]。也就是说,当时为了弥补征伐南粤、西南夷、匈奴,东游西巡,大兴工役等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赎刑主体扩及到一般民众,所有罪行都可以赎免,宫刑自然也在其列。
二是司马迁遭受的宫刑在当时是第二等刑罚。按汉文帝之前,刑罚从轻到重大致有完(剃除须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宫、弃市。文帝十三年(前167)除肉刑,改完为城旦舂(劳役),改黥为髡钳(剃发加镣铐),改劓为徒刑加笞三百,改斩左止为徒刑加笞五百,改斩右止为弃市,废除宫刑。景帝元年改笞三百为二百,改笞五百为三百;中元四年恢复宫刑;中元六年又改笞二百为一百,笞三百为二百。因此到武帝之世,刑罚轻重依次为城旦舂、髡钳、徒刑加笞一百、徒刑加笞二百、宫、弃市这六等(城旦舂下还有鬼薪白粲、隶臣妾,劳动强度依次降低,但到释放合计需要五年之久,因此这三等可合为一等,即五年有期徒刑)。宫刑为第二等重刑,与司马迁有过交集的孔安国就曾论述这一点。孔安国在《尚书孔传》中明确指出“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女人幽闭,次死之刑”。(按:《尚书孔传》清人以为系后人伪托之作,对宫刑的论述是否系安国原书内容已不可知,但宫刑是武帝时的次死之刑应该可以取得共识。)
三是司马迁的财力足以赎死刑,但不足以赎宫刑。司马迁遭宫刑的时间为天汉三年(前98),恰处于桑弘羊请“罪人赎罪”到武帝提高赎钱额度之间。如前文所述,这个金额大致在三十万钱至五十万钱,即三十金至五十金之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令”条的俸禄,司马迁是六百石的官员,而当时俸禄主要以货币的形式发放[7]。黄冕堂等人的意见,当时粮价在石谷百钱左右[8]。颜师古注《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再根据一石即为一斛的换算关系,即可计算出司马迁的年薪为70斛/月×12月×100钱/斛=8.4万钱。另一种算法可根据《汉书·贡禹传》:“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穅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按比例式“180斛:1.2万钱=70斛:司马迁的月薪”,可得出司马迁的月薪为4667钱,年薪为5.6万钱。两个结果极为接近,且不难看出造成误差的原因是不同时期粮价的波动。在这里姑且取其年薪的平均值7万钱,赎死之金也取中间值40万钱。据《自序》称,司马迁任职太史令“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也就是说七年期间,司马迁的货币收入为49万钱左右,但正如贡禹所说,除了货币工资外,还有“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等实物福利。此外,还要加上老太史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间”的收入。按最保守方式从建元最末的那年(前135)到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至少在武帝朝领到7万钱/年×26年=182万钱的工资,父子两代货币收入累积达231万之多,拿出仅为其总额的1/6,对于司马迁来说显然并非难事。因此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并不是说“无法赎免死罪,只好自行请求用宫刑来替代死刑”,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赎免余下的刑罚等次,只能接受宫刑的处罚。当然,遭受宫刑已令人万分羞辱,在出资赎买的情况下仍获得宫刑,更是辱上加辱,这就难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激愤难平。无独有偶,李广也曾两次下狱论死,第一次赎为庶人,第二次虽出现资金困难,但从平常积蓄拿出钱来减死一等应当不难做到,但李广选择自杀,应该就是不能接受宫刑的缘故。
3 “太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补证
王国维称司马迁“卒年绝不可考”,并考证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作《报任安书》为其卒年上限,又根据武帝后元二年(前87)郭穰为内谒者令(经王国维考证内谒者令即中书令),说明司马迁此时或因死去职,得出卒年下限。李伯勋则根据司马迁没有记录征和四年至后元二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将下限提至征和三年(前90)[9]。王李两先生之论能够成立,则司马迁卒年当在公元前93年至公元前90年之间。
自从郭沫若根据《汉书·司马迁传》“既陷极刑”“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判断“似乎司马迁之死有点不明不白……可能是不自然地骤死了”之后,李伯勋进一步阐发指出征和二年(前91)十一月司马迁作《报任安书》,再犯“诬上”的罪行,被武帝所杀。此外还有《史记》书成后,司马迁自杀雪耻的说法[10]。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者罔顾王国维对司马迁和武帝行迹的比对结果,称“若任安在太始四年论死,不可能在短短一至两年内就担任北军使者的亲信职位”。然而武帝用心非常人可以揣度。张汤以区区小吏,数年之内旋踵为廷尉、御史大夫,位极人臣;卫青为骑奴,亦数年内为大将军,操天下权柄;即使司马迁个人,在天汉三年(前98)遭遇宫刑,也于太始元年(前96)为中书令。以此来看,任安在太始四年下狱论死后不久出任北军使者完全可能。
司马迁死于非命各说(被诛、自杀)亦不成立。按《史记》《汉书》成书体例,凡寿终正寝者,官员在侯爵以上才著录卒年。官员非侯爵者被诛、被谋杀、自杀者则都能通过帝王本纪或本传大事记推测出卒年,如爰盎死于梁王派遣的刺客之手,张汤、李广自杀,朱买臣因诬告张汤被诛杀,皆能推算卒年。相对来说,正常死亡如司马相如、东方朔、冯唐、孔安国之卒年皆不可考,这可反证出司马迁和他们的情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