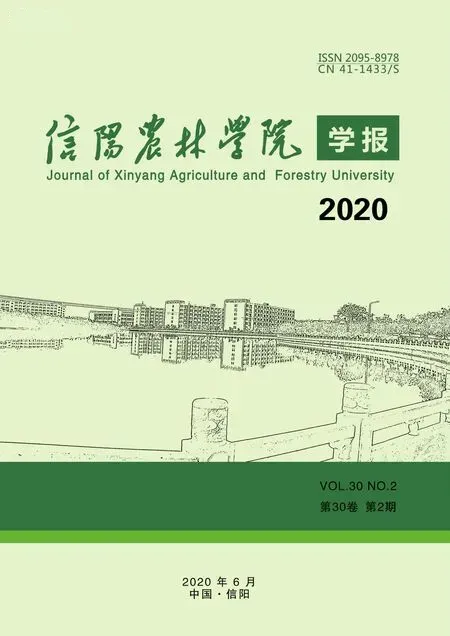零度写作下情感如何存在
——追问《故事新编》的特殊不及物性
王治涵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呐喊》与《彷徨》中,鲁迅毫不吝惜情节的设计精力,通过各种预设的意义片段来强调悲剧和沦落母题,进行中心化的意义凝聚,以文本不断的层级化去搏求启蒙原动力;但与同时代同门类的文本比较观之,《呐喊》《彷徨》留下的更多是没有答案的冗长回声,或曰一个个置身两难困境的悖谬者的心灵。
鲁迅先生曾坦然自白“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1]2,于是在前后十三年的创作中,出现了区别性的新体尝试《故事新编》——略微拾取古代传说、旧书根据,加上一点“信口开河”的技巧,便产出一部“油滑之作”来。但可贵的是,对于这本速写的集子,鲁迅自诩“并未将古人写得更死”,因此在文学史上还算有了“存在的余地”;而这独特的“余地”,不仅在二三十年代的近代文学国度中初露光芒,而且换了今日现代性的语境看来,在暗含的批判情感上有着独特的建构技巧,其中普适性的成分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
同时,自新时期以来,对《故事新编》作的新式解读层出不穷,学者们将主要目光置于文本上空漂浮的后现代色彩,切入点大多为区别于《呐喊》《彷徨》的新式反讽艺术,戏仿文体的表达力,情节的荒诞意味,诸如此类。笔者将试图借助西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从最主要的二元对立入手,而后沿着这种非理性的写作思维,从语言结构等行动角度具体追问小说本身的“不及物性”,以及《故事新编》中隐现的零度写作理念,从形式零度背后的主体介入情感真相,从鲁迅的文学布置手段中更好地理解现代反映机制的建立过程。
1 从“二元对立”退入生活——善恶对立的分离
“结构主义”滥觞于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之父”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批评方面的影响力以罗兰·巴特为前驱,本文将扎根于二人的论述展开结合性研究。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最主要的理论方法便是“二元对立”,翻看《故事新编》可以发现许多二元对立的痕迹,诸如神性与人性的对比,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生与死的矛盾,但最明显、蕴义最丰富的一处要数其中性格鲜明的善恶形象,完成了对形而上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而退入真正的生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既是一本汇集了历史故事的小册子,又是一部承载了审美时代下结构形态与生存命题的大书。
出于生命的传统崇拜,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在大众的阅读印象里,往往客观性更强;但在《故事新编》中,仔细观察鲁迅对于人物的建构,却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掺杂了更多的个人好恶色彩。他在为人物设计细节时,一面作着传统的英雄立意,另一面仍然毫不犹豫地将人性的极丑陋面展示给读者看,以此来说明志士们的“回天之力”在现实意义上值得怀疑的必要,产生结构主义的对立意义。正如“绝对的选择自由的观念,像世界由之而出的绝对的自我观念一样是虚幻的”[2],在作者看到个人的自由不过是一副虚像时,不仅他自己失去了对光明、对自我的信心,而且这时“生命力”本身也成了一种空洞的安慰,暴露出人性的贫乏和情感的衰竭,于是文本中的群体大多生活在纵欲之上,鄙陋之下——淋漓尽致的揭示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良知据点的缺乏,很有向隅而泣的意味在。
从《铸剑》来看,鲁迅细致刻画了多种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伟大坚强的母亲的引导下,眉间尺完成了从不稳定、不成熟的少年到勇敢果断的复仇者的转变。在这期间,他的性情从要不要救出老鼠的优柔寡断,进化成为明显的成熟果敢——为了完成复仇的使命,“暗中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颈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1]77,生死观念的转变展现了他坚定的复仇信念,迅速的成长对比也算某种程度上的“二元”;而文本隐含结构中死去的父亲,早在为国王铸剑时就预见了自己的死期,但他毫不畏惧,仍然坚守道义与本职,并且向死而生,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好好的将他抚养,一到成年之后,你便交给他这把雄剑,教他砍在大王的颈上,给我报仇”[1]71。从表述中可以看到一个正直且充满睿智的雄性强者形象,尽管他为了坚守本心而将更大的使命托于儿子的行为并非完全的正面,甚至存在关于他生存恐惧的一种过度解读;于是在此基础上,作者着力塑造了第四个正面的形象,亦即真正的时代勇士——“善于报仇”的义士宴之敖者,并且超出典籍的简单记载“客有为报者”(《孝子传》)“遇客欲为之报”(《列士传》),运用大量的现代语言手段将其拔高到了相当的地位,以文本中给予他的三次外貌描写为例:
“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
“那是一个黑瘦的,乞丐似的男子。穿一身青衣……”
“眉须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
棱角分明的脸庞代表了他深明大义的性格,这是鲁迅小说中传统的时代先驱者之模样,近似于黑屋子中难得的掌灯人一角。“宴之敖者”其实本为鲁迅的笔名之一[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此超人的形象中也含有一些不知蝴蝶庄周的自喻意味。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把小说中的对象分解为零散的结构成分之后,在这四人中间,我们看到了鲁迅想要表达的人性的真实存在;对比之下,其他人物的缺陷也就很容易凸显出来——无论是昏聩暴虐、只会说“奏来!”“玩来!”的皇帝,还是愚忠无能的大臣宦官,以及在皇帝生前献媚、死后便“装出哀戚颜色”的妃嫔、百姓,都是对丑恶的极端揭露,从而在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中将社会的复杂性向深度推进,无情的笔法愈发强烈,相对古典文本的忠实记载更具现代性特征,蕴含着一种告别式的人性反叛力量。
2 向死而生的环形迷宫——从叙事功能探考鲁迅的讲述之道
除了对人物的多样塑造,在形式与内容这对关系上,“结构主义批评家倾向于把一切内容都看成形式,或者至少认为内容是使最后完成作品得以存在的一种技术手段”[4]190。从这种略带有形式主义痕迹的观点入手,在结构主义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文学的传播手段,更充当了内容和主题的角色,文学在他们心中已经成为“语言的某些性能的扩展和应用”。对于语言形式之于文义表达的重要性,他们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巴特在他的集中性论著《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借助语言学的演绎法,指出“语言中某一孤立元素本身缺乏意义,只有在与其他元素及整个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对宏观的作品来说更是如此”[5]。虽然《故事新编》是在旧情节范围内的新发挥,尽管意识的震撼力在根本上是去势的,但作者的构思激情也因此得到了尽兴发挥,鲁迅看到了叙述技巧所带来的文本赏戏性价值。
以结构主义的理论来解释,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发掘的“新余地”可以用叙事所引发的“通畅的审美愉悦”来概括,即结构辅助主题的表达;实际上,内容与形式的配合程度,也正传达出一个作家的讲述功底和高明所在。在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其他小说集中,最常用的便是线性主干的叙事原则,如《铸剑》将事件发展整理成四个片子的连贯,每一片都有因果相接,不留痕迹地使读者陷入作者的设计之中,将作品的阅读接受变得更容易实现。但要论他的原创性最高之叙事法,笔者认为,最出彩的是一种具有特殊功效的环形结构。
从章法布局上观其小说,所见之处多有首尾的协调。作者追求的是一种严整缜密和环环相扣,令人物只能在既定修罗场中作跳梁小丑。可以看到,《故事新编》在神话、史实的既定情节范式下,对剩余的叙事空间进行了充满想象力的填充。以《奔月》为例,故事开始于羿与马匹进了家门,因没能寻到理想晚饭而疲惫丧气;而结尾处又回到羿为了晚饭奔波一整日后的故事,甚至待发觉嫦娥已飞升无法寻回后,他的反应仍旧是“我实在饿极了,还是赶快去做一盘辣子鸡,烙五斤饼来,给我吃了好睡觉”——首尾相接,“羿”这一形象在日日的温饱中无方向地反复奔突,已经不复传说中的神性色彩,给人的感觉是强烈的无能,强烈的麻木,甚至透过“即刻心花怒放”“慌忙拈弓搭箭”“惶恐地说”一类行为的描绘,暴露了其本性已经滑向庸俗的事实;而从主题情节来看,中间的主体部分则重点叙述了羿为了生计辗转反侧、终无法满足妻子的物质需要而走向既定的爱情悲剧,并且这一结局似乎从作品一开篇即表现出的消极氛围中就有了模糊的意义确认。以结构主义分析,这种终止、生长、展开又终止的过程,代表的是无限循环机制对于未来信义的否定,在首尾闪现中消解人物,得到一种无生命的叙述节奏。正如纳博科夫阐释自己的时间观时,曾提到,“未来的基本要素是彻底的虚无;未来只是一种修辞格,一个思想的幽灵”[6]。如果说《故事新编》的环形结构意义不够明显,那么在被视作文学革命实绩的《呐喊》《彷徨》中,有着堪称经典的时空交汇和环形叙事,并借此来辅助命运的悲剧性。
在鲁迅笔下一个个的曲笔圈子里,人物的行径全被局限在鲁镇这一封闭小圈子里,浓厚的封建氛围主导了一时一地之文化,阻挡了新的精神净化物进入,因而人物的思想变化,只能在固定的小小的活动空间中反复,正像阿Q画的不成形的圆圈,悲剧复悲剧,让阅读变成了一场场的反思——诸如《孤独者》中的“我”与魏连殳结识于一场葬礼,二人辗转辛苦,最后见的一面竟是在魏连殳自己的葬礼上;《风波》同样有着首尾重叠的场景,以土场吃饭开始,传言既生既落,平静生活中陡起波澜,终复归于土场吃饭的沉寂;而《祝福》一篇显然环形意味更深远一些,爆竹声起,爆竹声落,讲故事的“我”离家又归,归而远离,此间主人公祥林嫂也经历了山村——鲁家——山村——鲁家的循环,最后还是死于鲁镇,这中间许多圆形相套,仿佛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小蛇,总体上又嵌于大的圆环中,在近现代小说的叙述结构中可谓先锋性的典范创造。
在纳博科夫看来,圆环极具哲学深意,封闭、首尾相接、毫无出口,将文本中所有的生命个体囚禁在当下的时间之狱中。然而人物并无法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坚固困境,无论是横冲直撞,还是螺旋式的逃离,终究不能超越人性这一永久命题,突破既定的悲剧结局——因为无论是车辆、行人,甚至树木、房屋,在宏大的时代隐语下,似乎都受着一种隐藏力量的摆布,或曰一切偶然都有必然的前提,总之反抗之前剧情早已敲定。
除此之外,环形结构的表现手段还可以借助第三人物视角,例如在前文提及的《祝福》和《狂人日记》中,鲁迅借助讲述者“我”的回忆和空间的变换来还原事件,或曰一种“管中窥豹”的镜头方式,而不是靠模拟情节、渲染表演色彩。比起鲁迅亲自下场现身说法的唠唠叨叨,环形结构能更为内在地包含着作者对世界意义的理解,更为内在地充当其文化哲学的模式展示物。无论是羿,还是阿Q、祥林嫂、魏连殳,无不在环形迷宫中被抛掷于“别无选择”的空地中,困境的轮回指向生之苦难,更指向死之轮回。
华莱士·马丁曾经解释道:“我们感受到的、统一了开始与结尾的循环回归感来自自然——日夜、季节、年月,它们为人类的死亡与再生概念提供了一种模型。”[7]在鲁迅小说中,这种有意无意的环形结构将开头与结尾重新缝合,为小说叙事和美学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文本。正如外国文学神话中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形象——表面上被惩罚推巨石上山,在他心中其实是有意识的行为,“他知道他的悲惨的状况有多么深广,但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造成他痛苦洞察力的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他高于他的命运”[8]。以环形的迷宫来表达命定的结局,这是文学原创性的至高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作为写作者面向存在的勇气。
3 零度写作——一种陌生化的乌托邦
除了二元对立和结构分析之外,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大观点认为,“在直接可见的事物和直接可见本身之后的结构都是心智结构特性的产物”[4]305,因此从鲁迅小说形式的不及物特征和零度写作的色彩下,我们透过表面的冷漠其实可以发现隐含的情感取向。
鲁迅评价自己的《故事新编》时,承认了创作的无目的性的存在,“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依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不妨采用结构主义来解释:“零度写作”并不意味着零度情感,而是指写作者将澎湃的爱憎情感降到零点,拉紧野马的缰绳,以理性的笔触娓娓道来,将感情的生成源地转移到读者一面,从而表达得更加深沉、凝练,由此恰恰形成了“情感非零度”。所以对于《故事新编》来说,作品借着神话传说本身的虚构性,加之作者个人的想象发挥,由此呈现出的语言乌托邦使得内容和结构本身即被赋予力量,以一种看似目的纯洁的写作摆脱了纯粹社会承载物的枷锁,引发了读者客观冷静的思考。
作品的本质就在于对“国民性”的改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他的笔下最具典范言说意义的便是阿Q、祥林嫂、狂人一类被现实完全控制灵魂的角色,满含问罪他人、问罪社会的义愤,此外便似乎没有什么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整个的叙事氛围可以用“浑浑噩噩”来概括,作者从悲剧道路上的一个个死魂灵出发,将批评矛头对准赤裸裸的现实血色,幻想中国新文明逻各斯体系的出现,充满现实主义风格;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实际上关于对鲁迅创作的类型划分的讨论从未停止,笔者的意图也并非要作额外附会,而希望能借着结构主义的主调,单从零度写作和隐含的情感取向方面观看鲁迅的建构秩序,准确地说,希望对其写作特性的分类进行新的认识。
正如人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鲁迅不仅在思想上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小说手段的多样化尝试方面,他同样是一个非常的自由主义者。早在阿Q时代,鲁迅已经有了不安守于纯现实叙述的暗流,汪晖曾经提到:“一位翻译了《阿Q正传》的捷克汉学家曾对我说,她认为这种描写不是现实主义的方法,农民阿Q不可能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想头……他的现实主义里不仅有浪漫主义的成分,还常用象征手法。”[9]
这种细小的杂糅在鲁迅早期的小说文本中并不少见,例如所有文本中的乡村变化常常表现为门牌号更换、辫子的剪掉、朝代官员等政治符号的更替,但形而上的乡村精神结构却从来泥古不化。他本人也曾在晚年作过很有意味的回答:“所写的事迹,大概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原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10]
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于文本的陌生化效果并非刻意追求,但限于传统情节的框架,他没有走出更远,而是暂时地接受文字的娱乐消遣功能,减弱了文体所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正如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中言及的:“假如要使艺术隶属于人生的别的什么目的,则这一刹那间,即使不过一部分,而艺术的绝对自由的创造性也已经被否定,被损毁。”[11]而这恰恰与巴特“不及物写作”的概念有很大程度上的共通之处,正如写作“write”既是及物动词又是不及物动词一样,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多次强调了文学本身即有意义,有无限的解释维度,“写作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写作自身,引向对符号和语言人为性的揭示,引向意义生产和多义的网络”,因此对作家来说,语言并非传达思想的工具,甚至在《故事新编》中,常有抽空了情节和主题的自由语言,像《奔月》的前部文本中出现了大段的环境描写:“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暗的眨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可以看到,这里的语言已经不再是观念的、沉重的,呈现出工具性的美学色彩,这在典籍里极为少见,反而经常出现在当代的滥情小说中;甚至将这段华美流溢的文字去掉后,直接将女娲醒来的情节老实述来,语义也并未受到影响——这便是艺术的、自由的、理想的语言,对思想的表达无任何作用,带有无限的解读可能性,是一种典型的不及物写作,自律而非他律的创作原则也深含零度意义。
于是沿着零度写作强调的由语言独立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在莫邪铸剑、客人替子复仇的故事原本上,鲁迅沿内部线索向前推进,增加了眉间尺的介绍和对老鼠的长时间拨弄,极小的叙述中就出现了两次“慌乱”,“忽然”,一个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无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鲁迅顺此时序,借助这种犹豫不决、同情心之深连一只老鼠都不忍伤害的铺垫,连接了下文中母亲讲述的深仇往事,辐射出眉间尺因血杀的复仇而骤然攥紧的拳头和改换的性格,“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如此一来,在穿上青衣之后他的性情理所当然地发生大变,“虽心跳着,但很沉静地一锄一锄轻轻地掘下去”,从轻狂年少到沉着冷静,一夜成长,关键的人物性格转换环节由此结束,并无外界如革命起事一类的助力,而是完全靠着文本自身语言的设计。
除了语言的活用外,我们还可以从小说的人物、结构、叙事立场中理解零度写作的中性项思想,从逐渐白化的文体中探寻那些可能存在的无数关系如何被照亮。其一表现便是,《故事新编》没有采用十分明显的后设技巧,但带有现代性叙事色彩的形式强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于是,在本就超出一般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鲁迅的思维态势的开放性、多元化随着对日、欧先进作品的“拿来”而逐渐升级,而同时旧的文化形态不断瓦解着他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念,因此他做了一次退居古书的实验,以一种与现实十分遥远的距离垂手而立,保持了一种罗兰·巴特所说的“中性的或惰性的状态”,使文体不再为社会意识所绑架。正如他曾对许广平袒露的,“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12]因此在《故事新编》中他将自己两种文学愿望合而为一,初步将语言从思想内涵的窠臼中解放了出来。
我们还可以发现,鲁迅的人物选取手段也随之进了一步——从具有完整影像的祥林嫂一类,到《示众》中“秃头”、“胖孩子”、“学生模样的头”这种不很能看得清的“杂取”形象,及至《故事新编》,更是换成了文化神坛上已经出现了的固定人物,如此一来,小说整体呈现出人物的漫画倾向和场景的闹剧性,叙事的任意发挥有了更充分的理由,也消解了“报私仇”的误读顾虑,在这一概念上也算是合格的“零度书写”。故事抛弃了内与外、表层与深层、能指与所指的对立,神话传说下人物互动的可能性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既定图示下对语言的打磨,更增强了表述的现代色彩。
4 结语
且让我们回到总体的知识清单上来,本文尝试从二十世纪结构主义批评下的语境中考察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特殊不及物性质,发现其中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并非简单的并置,而是在善恶、历史现实等多对能指对立方面的强化中,将历史人物搬下神坛,并无法避免地加入了作者的情感立场;从结构分析的叙述层来看,《故事新编》及其他作品的环形结构又体现了无限循环机制对于未来的否定意义,可以看到作者敢于直面现实黑暗的勇气。而这一切又可以用零度写作来解释,作者把社会文化现象和表达形式转换为操作力更强的符号形式,在用新方式操作旧语言的力量中让人体验到他的真实性。不及物的形式本即高妙,而在表面的零度下我们仍可以时时听到作者的愤懑和启蒙之声,这正如上古的食物陶罐是今日的珍贵工艺品,《故事新编》中的许多结构技巧使作品更具可读性,却也更难深读,体现出作者的写作能力之高。这大约并非他刻意为之,但对于从事文学创作及再创作者来说,这种新旧文本的相互激活,在废墟上建立新文化的艺术,却是值得“拿来”细细钻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