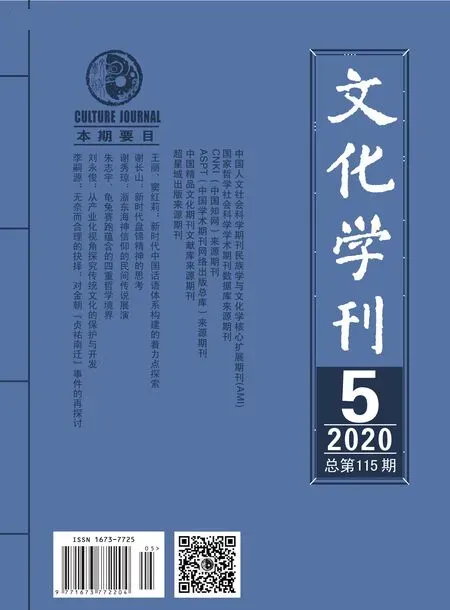《女勇士》的解构主义解读
付馨媛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是美国当代著名华裔女作家。1976年,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TheWomanWarrior)问世。小说一经发表便在美国文坛引起极大反响,荣获当年美国“国家图书批评界”非小说奖,汤亭亭也凭借这部小说成功立足美国文学界。小说以充满想象力的文笔讲述了几位女性的故事,再现了华裔小女孩的文化困惑与身份认同危机。在《女勇士》中,汤亭亭颠覆了男性高于女性、西方优于东方的等级秩序,消解了男性与女性、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本文试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这部小说加以解读。
一、解构性别二元对立
在“白虎山学道”(White Tigers)中,汤亭亭将花木兰由一个为完成孝顺的使命被动出征的女性改造为一个为了自我实现主动出征的女勇士,通过呈现女勇士“双性同体”(androgyny)的特质以及女勇士与丈夫、老汉与老太太相互依存的关系,实现了对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
女勇士七岁时在一只鸟的带领下进入深山,跟着两位老人修炼武功。十五年后,女勇士学成归来,准备代父出征,“父母像欢迎归来的儿子那样,杀了只鸡,整个地蒸了”[1]。在父母眼里,习得一身本领的女儿不再是弱小的女子,而是肩负复仇使命的英雄,因而女勇士能够享受男儿一般的家庭地位。出征前,女勇士的父亲在她背上刻下了仇恨。代父出征和父亲刺字分别基于中国文化中花木兰和岳飞两个人物原型,汤亭亭将这一男一女的形象融合在女勇士的身上,塑造了一个武力高强、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暗示着女勇士具有双性同体的特质。
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融合了西方女性和中国剑侠(剑仙)特点,因此“具有普通女性所没有的中性气质”[2]。她不仅在衣着上女扮男装,在军事技能方面也毫不逊色于男性。出征前,女勇士“穿上男装,披挂上甲胄,头发挽成男士”[3],俨然一副男性的形象。女勇士集结了自己的军队并担任首领,行军路上养军育军,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态势冲锋陷阵,与中国父权的最高象征——皇帝的军队作战,一路北上,直抵皇宫,斩杀皇帝。女勇士与皇权的对抗象征着汤亭亭对两性关系不平等的反抗和对父权制的消解。怀孕也丝毫未削弱女勇士的作战能力,她在履行女性生儿育女职责的同时像男人一样奋勇作战,穿上铠甲“看上去就像一个又粗又壮的汉子”[4],此时“其性别的混淆和复杂达到了巅峰”[5]。完成分娩后,女勇士便立刻恢复了作战能力,她把脐带系到旗杆上,“把孩子放进背兜,拴在胸前,罩上铠甲,催马杀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脐带和红旗一起随风飘舞,让人忍俊不禁”[6]。汤亭亭在赋予女勇士勇猛刚毅的男性气质的同时,也呈现了女勇士温柔贤良的女性气质。在完成由少女到母亲的身份转变后,女勇士在冲锋陷阵的同时,心中多了对孩子的挂念,其母性的特质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流露出来。“小宝宝贴着我取暖,他呼吸的节奏和我的相同,我们的心也好像在一起跳。”[7]为完成复仇大业,女勇士狠心与孩子分离,却无法抑制对孩子的思念,“在这段孤单的时间里,每当我听到一声啼哭,奶水就会流出来”[8]。完成复仇后,女勇士回到家里,拜见公婆,看望双亲,耕耘纺织,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履行作为女人的孝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女勇士自此退化为一个懦弱的女子,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在她进入丈夫的家庭生活的同时,她的另一个侧面使她不至于沦为一个男性中心家庭的无名附庸。”[9]她解决了父母乃至整个家族的温饱问题,她的伟绩在整个村子里流传,这为她赢得了立足之地,使她摆脱了男性的控制,在性别关系中不再处于弱势地位。这样,一个独立又贤良的女性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汤亭亭通过赋予女勇士刚柔并济、双性同体的特质,实现了对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
如果说女勇士身上呈现了刚柔并济的双性气质,那么女勇士与丈夫、老汉和老太太的相处模式则为读者呈现了双性同体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在描述女勇士与其丈夫的关系时,汤亭亭有意打破男尊女卑、两性对立的观念。作战途中,女勇士的丈夫不是作为她的权威,而是作为她的伴侣,是“作为‘同一体’丢失的那一部分”[10]出现在她的面前。中国传统意义上“夫为妻纲”的教条不复存在,夫妻两人平等相处、并肩作战,消解了性别二元对立。老汉和老太太的关系亦是如此。老夫妇虽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却总是呈现出和谐一体的局面。女勇士第一次到达深山中的小屋时,见到“门里走出一位老汉和一位老太太”[11],之后“两位老人带着我(女勇士)从拂晓一直练到日落”[12]。在送女勇士上白虎山时,“他们分别架着我(女勇士)的双肘”[13],尔后又一起消失。“老汉与老太太之间显然没有主次和尊卑之分,他们之间没有对立和冲突,而是处于永恒的互补、互变、互动之中。”[14]女勇士在白虎山学道期间,由于极度饥饿眼前出现了幻象:“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对金人儿,在那里跳着大地之舞。他俩旋舞得很美,简直就像地球旋转的轴心。他们是光;是熔化的金子在流变。”[15]在女勇士的幻象中,老汉和老太太变成了一对金人儿,他们在舞动中合而为一,完美结合,消解了性别二元对立,寄托了汤亭亭对于双性同体的向往。
女勇士凯旋后,为弟弟和村里的人报仇,斩杀了财主,解放了财主家受压迫的女人们。女勇士对财主的态度也是“我”对那些持有性别偏见的人的态度。正如女勇士憎恨“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的民谚,在美国华人社区长大的“我”也同样憎恨华人邻居口中“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养女等于白填”的说辞,对于母亲口中女孩长大了“不过当当别人的妻子或佣人”的观念不以为然。作为反抗,“我”满地打滚,大声叫嚷,坚决不做饭,在洗碗时故意打碎几个,立志成为地道的美国女性。汤亭亭借女勇士和“我”的故事展现了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表达了渴望男女平权、消解性别对立的思想。
二、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
汤亭亭在小说中不仅旨在消解性别二元对立,还致力于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汤亭亭出生于美国,成长在华人社区,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受到来自华人社区和父母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她的小说在美国人看来是“中国”书,而在中国人看来则是“美国”书。她美籍华人的身份赋予她审视东西方两种文化和质疑种族对立的独特视角。在小说中,汤亭亭通过呈现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共性、“我”对东方族裔“他者”身份的反抗以及代表西方文化的“我”与代表东方文化的母亲的和解,实现了对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解构。
“鬼”的形象几乎贯穿文本始终。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正是汤亭亭对文化对立的质疑[16]。在中国,“我”的姑姑活着的时候被家里人骂是“死鬼”,死后变成了“淹死鬼”,她的鬼魂也附在“我”身上;“我”的母亲曾遇到过“压身鬼”和“座凳鬼”。在美国,则有“的士鬼、公车鬼、警察鬼、开枪鬼、查电表鬼、剪树鬼、卖杂货鬼”[17]……“我”和母亲争吵后,被母亲称为“胡扯鬼”。汤亭亭本人在访谈中解释道,“鬼”在小说中指代很多不同的事情,如历史的幽灵、内心的鬼、鬼故事、白人等。考虑到demon(恶魔,魔鬼)与devil(魔鬼)两个词的贬义,汤亭亭在小说中选用了ghost(鬼,幽灵)一词来表示“鬼”以便传达出它更为丰富的含义[18]。“‘鬼’是消解西方二元对立基本思维方式、解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理论基础的策略之一。”[19]汤亭亭将“鬼”的存在同时置于东西方社会,拒绝给出“鬼”的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从不定义“鬼”的形象出发消解了东西方二元对立。除“鬼”以外,疯女人的形象也同时出现在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中。在中国,疯女人被人们用石块砸死;在美国,“我”居住的附近街区里有十多个疯女人,她们最终都被关进了疯人院。月兰来美国寻夫无果后也疯了,但在疯人院里,她和其他的疯女人们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她们“说同样的话,完全一样”[20]。在这里,东西方对立被消解了。汤亭亭通过描写中美两国社会里疯女人的遭遇和结局展现了中西方共有的对女性的压迫,在批判男权制对女性的残害同时消解了东西方二元对立。
在“羌笛野曲”(A Song for a Barbarian Reed Pipe)中,汤亭亭借小女孩之口表达了对“他者”身份的反抗以及打破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渴望。“我”在刚上学的前三年因为不得不讲英语沉默得最厉害,后来“我”意识到沉默是华人的通病,于是努力打破沉默,最终找回了声音。尽管在美国学校失语的华人孩子大多在中国学校里恢复了声音,但有一个女孩总是不讲话。“多年来,她能大声朗读,可就是不讲话”“她能低声读课文,可就是不讲话”[21]。同样作为华裔女孩的“我”无法忍受同伴的沉默和脆弱,因此既憎恨又恼火。为了强迫她说话“我”尝试了各种办法:拧她的脸,扯她的头发,摇她的肩膀……可她只是不断地流泪,不开口说一句话。“我”最终崩溃大哭,责怪她道:
你得为此付出代价。我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原因。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在帮助你吗?你就想这样下去吗?一辈子都哑着吗?(你知道哑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就不想当啦啦队长,不想做个善于交际的女人?……如果你不说话,就没有个性。你不会有个性,不会有头脑。[22]
“她有声音,却无声无语;有权利,但无能为力。”[23]“我”极力强迫同伴说话,希望帮助她摆脱边缘状态,获得权利,实则是“我”对东方族裔“他者”身份的反抗。哑意味着华裔在美国社会无法获得话语权,表达自己的诉求;无法改变“他者”的身份,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汤亭亭通过呈现“我”的反抗表达了消除种族对立的愿望。
小说中第二代移民的华裔小女孩“我”代表着西方文化,第一代移民的母亲则代表着东方文化。文化差异导致“我”与母亲难以顺畅沟通和相互理解。在小说中,汤亭亭有意建构了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我”以为母亲刊登征婚启事是想把“我”嫁出去,实际上母亲是在帮妹妹物色人选;“我”以为母亲割“我”的舌筋是不想让“我”讲话,实际上母亲是为了让“我”多说话、说好话;“我”以为母亲嫌弃“我”长得丑,实际上母亲是在说反话;“我”想当伐木工和记者,而母亲希望“我”像她一样做个医生;“我”想上大学,而母亲却不理解“我”为什么不上个打字学校。“我”与母亲的冲突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然而,汤亭亭建构这些对立的目的正是颠覆二元对立[24]。“我”与母亲的最终和解消解了东西方二元对立。在“乡村医生”(Shaman)中,汤亭亭讲述了中年的“我”与老年的母亲的相处时光。“我”学会了和母亲交流,当母亲感叹道再也无法回中国了,“我”对母亲说:“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25]在这里,汤亭亭没有将母女两人的归属地和身份认同划定为中国或美国,而是运用了更广泛的概念“整个地球”,从而消解了东西方二元对立,表达了对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的向往。薛玉凤认为:“写作本身就标志着母女之间的和解。”[26]汤亭亭在母亲讲述的原版故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想象加以改写,记录了她与母亲的关系从对立到和解的过程,这同时也是她消解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重塑自我的过程。
在小说结尾,汤亭亭以蔡琰的故事再次表达了消解种族和文化二元对立的愿望。蔡琰被匈奴的首领擒获后远离故土,生活在异乡的她无法言说汉语,她的孩子们也不会讲汉语,语言建构起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她无法融入匈奴民族,匈奴人也不理解她。然而,蔡琰和匈奴人却通过歌声实现了和解。
蔡琰唱的是中国和在中国的亲人。她的歌词似乎是汉语的,可野蛮人听得出里面的伤感和怨愤。有时他们觉得歌里有几句匈奴词句,唱的是他们永远漂泊不定的生活。她的孩子们没有笑,当她离开帐篷坐到围满蛮人的篝火旁的时候,她的孩子也随她唱了起来。[27]
汤亭亭以蔡琰与匈奴的和解作为小说的结尾,暗喻着她实现了对东西方文化的和解,完成了对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解构。
三、结语
在《女勇士》中,汤亭亭通过对花木兰代父从军故事的改写,塑造了一个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为一体的女勇士和两对蕴含双性同体特质的人物关系:女勇士与丈夫、老汉与老太太。在女勇士身上,不仅可以看到男性的勇猛尚武,也可以看到女性的温顺贤良。她在征战沙场的同时生儿育女,又在完成复仇使命后回归家庭。她向父权制发起挑战,打破两性对立,追求男女平权,体现出对性别二元对立的反抗。在两对人物的关系中,性别二元对立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男女两性合而为一、互补互动的和谐共处,表现出作者对男女平权的向往。此外,汤亭亭还致力于消解东西方二元对立。小说通过展现“鬼”和疯女人的形象跨时空、跨地域的存在,“我”通过努力找到声音、帮助华裔孩子打破沉默的故事以及代表西方文化的华裔小女孩和代表东方文化的母亲的和解,强调了东西方的共性,实现了对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解构,表达了作者对种族平等、多元文化共存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