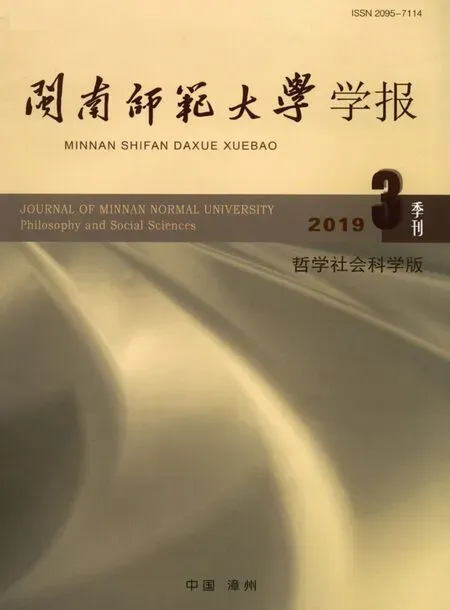吴敬梓的理想国及其建构
——兼论《儒林外史》的主旨及结构
吕贤平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即从康熙朝的后期,经过雍正一朝至乾隆朝的前期,是所谓的康乾盛世。 吴敬梓将眼光投入清代社会的广大空间,透过盛世的表面繁荣看到的是这个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危机。 吴敬梓尝试超越其深感失望的官方权力话语体系的桎棝,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改造,从而建构出他的理想国。
一、第一回所“敷陈”“隐括”的现实社会
《儒林外史》第一回开宗明义,“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直称是要借这第一回来说明小说主旨。 小说以凝练之笔描写了时代的社会秩序,并由此拉开了《儒林外史》叙写清代广阔社会风貌的序幕。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存在官制与民间的两种秩序与力量,它们分别以皇权和宗族为中心,连接上述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阶层,这个阶层是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这种“国家——宗族”或者“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是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典型范式[1]。 比照《儒林外史》之描述,具有相当的参照意义。
小说第一回,出身乡农的王冕母子和秦老构成传统社会的乡村基层;危素、时仁是士人中获取功名而为宦者,是官制秩序的象征;而胖子、胡子、瘦子,乃居乡之“士绅”,居于民间与官方之间。 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2](P63)。王母一个寡妇人家,生活不易,物价飞涨,“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得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贴补家用,非但不能供王冕上学,还要将他雇在间壁人家放牛,以得一口饭吃;而“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逃荒的百姓“一个个面黄饥瘦,衣裳褴褛……官府又不管”[3](P10-11);危素、时仁这些官府中人皆被功名富贵所俘,且相互勾结庇护,时仁“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是“拗不得的‘灭门的知县’”[3](P9,P7);三方巾是乡绅代表,或心羡富贵,或狐假虎威,表现出世俗的势利和小人物的卑琐,他们大都由科举出身,相互攀结,为谋固其位而置小民于不顾。本回还写到吴王拜访王冕,朱元璋向王冕请教平浙之策,王冕说要“以仁义服人”[3](P12),当洪武帝定下八股取士之法,王冕则直言“这个法却定的不好”[3](P13),因拒绝与时知县相与并不满朝廷,王冕逃往山东济南隐居。
第一回的叙写,作者深意寓焉。 民间社会的衰乱和崩溃往往与封建王朝统治的危机同步,预示着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已逐渐丧失。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吴敬梓的文学创作广泛触及这一主题,展现出叙事的广阔、思维的缜密与思想的深邃,《儒林外史》之宏大叙事也由此得以充分展现。
二、宗法社会式微之哀魂曲
1.宗法家族与民间社会的衰乱与崩溃
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特有的势力及其内在凝聚力在维护中国基层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成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然而,自明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人们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冲击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造成世风日下、伦常颓败的社会弊病。 《移家赋》中吴敬梓直言自己宗族的各种堕落:“于是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 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广平之风衰矣! ”怀有浓烈宗族情怀的吴敬梓不禁叹息:“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 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 ”[4](P10)对于家族没落所呈现的种种丑恶,《儒林外史》书写尤多,小说描绘出诸多兄弟群像,如严大位夺胞弟遗产而骨肉相残、五河县“非方不亲,非彭不友”[3](P541)、余虞两家绅衿巴结攀附盐商等。 失序的伦常关系不断冲击着这个“全在纲常上做工夫”[3](P69)的社会,风气之下宗族制度统摄的家族秩序摇摇欲坠,家族制度维系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社会功能正逐渐丧失,“伦理社会”已非现实便亦不言自明矣。
伴随宗法家族传统的没落,基于宗族维系的民间社会世风也日益堕落。 《移家赋》写全椒风气:“驵侩枝梧,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4](P10)吴敬梓的友人程廷祚在写给程晋芳的信中曰:“观宋明之季,忠义廉节盛于前古,其关系之故可知也。 近日置此事于不问,故贤否混淆,日流于顽钝无耻而不自知。 ”[5](卷八《与家鱼门》)《儒林外史》对衰风颓俗的描写用心尤多,“正如太史公作《货殖传》,嬉笑怒骂”[3](P572),第四十六回回目直接说“五河县势利熏心”,利之所在,“薄俗浇漓,色色可恶”,四十七回余大先生说:“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 ”[3](P581-583)全椒与五河只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缩微图画,盛世繁荣的表象下,社会衰象丛生,小说第三十五回皇上召见庄绍光曰天下“海宇升平”,而庄绍光征聘进京途中即遇强盗打劫,回家路上又遇贫病而死的老夫妻,第三十六回虞育德路遇无钱葬父而投河自尽的人,夏志清说《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坚持个人的生活观,作者充分利用其生活的阅历与认识,凭借他对社会各阶层的深刻的认识,已经完全跳脱出因果报应的说教而创作[6](P213)。 吴敬梓的笔触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写出整个民间社会的衰乱与崩溃。①如前所述,民间社会的衰乱和崩溃多与统治的危机同步,如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成为小说若隐若现的线索,还有贵州生苗闹事等。
2.缺少乡绅的世界
《儒林外史》直呼“乡绅”处不少,第四、第六回回目分别是“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乡绅发病闹船家”,至于正文中若张静斋、严贡生、胡三公子、彭乡绅辈皆以乡绅称之。 实际上,吴敬梓所称“乡绅”乃有真假、然否之分,这从各家的评点中便可看出。 娄家两公子对待侍候先辈的下人邹吉甫宛如家人父子,黄评便曰:“真乡绅反如此谦和,所以形假乡绅也”,当杜少卿拒见王知县,称“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 ”黄评则说少卿“是真乡绅,然与二娄迥异”,对于二余兄弟“守着祖宗的家训,闭户读书,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齐评则曰:“但知看重乡绅,不知别的。 此方犹有古风。 ”[3](P101,117,390,541)称“古风”者,乃今难见之故哉。
“乡绅”与“乡愿”相对,主要指未入仕而有功名的读书人,也指有官职但闲居或退居在家的人,有时还将出仕者也包含在内。②进士在中进士未做官之前还不是官员,举人、贡生可以进入仕途,但不做官的也不少,另外还有未获得功名的读书人,这些都可包括在乡绅阶层中。 有关“乡绅”的概念参照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的论述。他们是接受儒家基本价值观的社会贤达,维护公理是其重要职责。 《儒林外史》描写了大量假乡绅——乡愿辈,小说正文(第二回)即从汶上县薛家集切入,尝一脔而知鼎味。 申祥甫依新参的亲家夏总甲势做了“为头”人物,观音庵集会中七八个“薛家集之乡绅”皆仰其鼻息,请师酒宴上,新进学的梅玖之刻薄歹毒;其后小说又插进王惠,接之以周进,广泛描写了薛家集这个小社会,这里势利侵蚀到每个角落,已经看不到一个文人能够成为合格的乡绅并过上有意义的生活,第四回严贡生“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3](P64),第九回刘守备家仆人如狼似虎般行凶作恶,还有特旨太守王惠降顺宁王、万里假中书等无不显示他们趋炎附势而随波逐流。 特别是第四十八回王玉辉女儿殉夫入烈女祠,王三姑娘绝食而死,乡绅们立刻给她冠上“为伦纪生色”的美名,并在明伦堂大摆筵席庆贺,这散着血腥味的“人肉的筵席”,其座客是以乡绅为主体,他们懂得教化的来头,将被奉为上宾,并承担“宗庙之事”的司仪。
小说以大量笔墨写出乡绅阶层的蜕化、变质乃至堕落朽烂,而社会风气在他们搅动下,和尚吃官司、宦成敲诈主子、赵大做劫匪以及潘三吏之作奸犯科等,到处都是“要做些有想头的事”[3](P240)之人。 吴敬梓观照乡绅阶层,他的叙述已明白昭示整个民间社会的衰乱与崩溃。
三、泰伯祠大祭深意寓焉
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是在西周社会“礼坏乐崩”,“周公之道”价值体系日趋瓦解的背景下产生,而“六经”的整理研究既是对“周制”(即所谓“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体现出对“周公之道”价值的肯定与宣扬。 《儒林外史》泰伯祠大祭礼的书写亦当作如是观。
1.“三代之礼”的崇尚
中国传统士人在面对危机或是重大转折时,一再想象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回到上古三代,当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P1936)“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8](P507)自孔子礼赞泰伯三让天下,泰伯便受到儒家的高度推崇。 全椒吴敬梓家族与泰伯之渊源久远,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轫于东浙。 ”[4](P8)其所著《儒林外史》将南京先贤祠改写为独尊泰伯的专祠①南京只有先贤祠,真正的泰伯专祠在无锡梅里,带有地方性崇拜色彩。 《儒林外史》泰伯祠大祭提升了泰伯祠在国家权力及宗族村落中的作用与影响。,泰伯精神成为吴敬梓的思想滥觞,“礼”成为小说描写的核心要素,在小说内容与结构上发挥关键作用。 整篇小说在“礼”的架构下形成一个自足的系统,第三十七回泰伯祠祭祀是小说结构的顶点,故卧闲草堂本评曰:“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束。……以后则慢声变调而已。 ”[3](P465)
儒家的“礼”涉及了社会、政治和道德实践等诸多领域,一方面,礼的世界是一个规范秩序,其内部整体的和谐是基于个体尽好各自的本份,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同时,礼的世界又量下社会政治秩序的表现,它依照权力、权威及财富将个体归入各不相同的阶层,“君要臣死,父要子亡”便再明显不过。 理论上而言,儒家所提倡的礼若在现实社会中得以贯彻,尧舜、孔子所主张的等级有序而整体和谐的社会政治便能够实现,这是儒家所倡导社会秩序中本来具有的,也是吴敬梓所向往的理想部分。 然而,基于礼的两方面的特征,现实中礼与社会各种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等诸多方面之间分配、把制、交换、协商等,最终使我们看到礼在呈现道德律令等规范制度的神圣性的同时, 又不可避免地沦落为社会政治等操纵下交易的工具,其神圣难免遭受亵渎,这样礼便显示出明显的二重性特征[9](P87-98)。 明清的在位者通过八股举业迫使儒士在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一级级阶梯上攀爬挣扎。 假若规范性秩序和政治秩序能够以儒礼来同时维系的话,那么上述儒士的个体行为是基于于礼的规范,还是出自于个人的私心,便是一个问题,《儒林外史》总领小说主旨的第一回,王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3](P13)八股荣身之法使读书人看轻了文行出处。现实的社会秩序正如小说中所嘲讽的,“礼有经,也有权”[3](P53),人各不安其位而混乱不堪。那些出身举业而理应作为礼的践行典范的官员们,他们在“功名富贵”的漩涡中无止进地堕落,有鉴于此,吴敬梓把礼作为这部描述文人世界小说的中心,体现了他的世界观和小说完整的艺术构思。 基于上述方面,林顺夫指出礼是《儒林外史》的主题,也是建构整个小说情节的关键[10]。 另一方面,礼与“德”及政治的关系紧密,“儒者之说,其精者为道德,其粗者为礼乐刑政”[11],君子们注重个体的道德修养,也重视“礼”所发挥的政治功能。第三十三回中迟衡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故欲于南京与朋友们一道用古礼乐祭祀,使人学习礼乐,以成就人才而助政教[3](P244)。 在“最终放弃了进行官场角逐的全部奢望,他现在得以有时间以一种超拔的精神和自我消遣的态度来考察他周围的读书人”[6](P216),吴敬梓认真地相信古礼乐的教化作用,小说精心建构泰伯祠大祭典并弘扬泰伯精神,虞育德、庄绍光们都忠敬于泰伯,杜少卿鼎力相助。 参与盛典者,甚至卑污如臧荼之流在礼的熏陶下也能洗心革面,“《儒林外史》可以看成是吴敬梓对衰退了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广泛的完整的幻想”[10](P81),这种“幻想”并非守旧,守旧的人极可能是效忠当前认可的传统,吴敬梓则向着那更高更纯粹的三代,将批判的精神与文化的重建寄寓其中。 文木老人置身古人行列之间,庶几可解岑寂而愈见闻其道之不孤。
2.“孔夫子的周朝”
一般而言,大凡严肃的讽刺作家,大都表现出思想的保守方面,吴敬梓也不例外,他曾变卖祖业去修南京先贤祠(与小说中修复泰伯祠相类),这些都表明他虔诚地信奉夫子的主张。
在儒家的政治理性中,士人致用而能得君行道,儒家治平理想、“孔夫子的周朝”之治才能实现,儒学风貌也由此显现。 科举制度的推行正与此配合,并给了士人无限机会,《儒林外史》中编选八股选本的行家里手马二先生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 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3](P173)马二先生之言不无合理性,但仕宦之目的究竟如何? 八股制度使马二真诚地以为做官就是为了行夫子之道,实现“孔夫子的周朝”之治,这是马二心中“孔夫子的周朝”;杨执中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杜慎卿的意见恰好相反,“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 ”马二、杨执中、杜慎卿等皆有各自向往的“孔夫子的周朝”,实际上,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是“礼崩乐坏”了,马二所云是“八股举业”化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杜少卿说使读书人“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3](P424),书中高翰林、鲁编修、王惠、范进、匡超人等衮衮诸公莫不如是。 高翰林将“揣摩”二字视为举业的不二法门,“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 ”[3](P598)八股科举将道德政治化,造成了道德的妥协和解体,结果催生出一群人的信条:“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 ”高翰林批评杜少卿的父亲说:“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3](P422)做官与行道济世竟成水火,“此等说话,竟可大庭广众言之,时文取士之流弊,乃至于此! ”[3](P430)同王惠、范进一样,马二参加八股考试,“代圣人立言”,所立之言也皆朝廷所鼓吹的道德与政治,然而他却从未生出进一步的政治恶行与经济企图。 尽管马二先生的举业从来龃龉,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极好的法则”的八股。
八股举业导致实用主义儒家史之畅行,培养出一群从科场至仕途无不得意的狼奔豕突之士,书中范进、匡超人衮衮诸公莫不如是,他们一遇时机便放弃道德;庄征君的个案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一个正派的儒士要有所作为,可是他依旧难逃命运与环境的排斥。 小说终尾,吴敬梓借皇帝之上谕以喻朝政之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欤?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3](P677)世道变得如此糟糕,这是《儒林外史》文本所面对的,也正是吴敬梓苦心思考的。 可以这样说,正是在清代社会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吴敬梓表达出“吾从周”之理想。
四、士人精神之重建
1.八股举业下士人之异相
一般以为国家设科取士用时文,目的在于用科举之体制,达经学之本源,使人人讲明圣人之传不谬[12],从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它确实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 然而,八股文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要求代圣人立言,其核心所在是使朝廷成为道德与政治权威的来源。 统治者所尊信儒学,其实是他们最不信的东西,对于那些“操守虽清”却不能够言听计从的儒臣,雍正特别反感,进而将把他们污为“洁己沽誉”之巧宦,甚至说他们比贪官更坏[13](P690)。 余英时说乾隆帝一再反驳程颐,表明儒家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恰好是君主专制的一个主要的障碍[14](P14)。 实际上,僵硬、固化的八股制度培养的是能人,而不是贤人,国家通过科举制实现了表面上吏的儒化和实质上儒的吏化, 这种科举官僚制的发展更多可以理解为专制统治越益过度,从而确保更为集中的一元化控制,“从道不从君”的士绅则是他们的主要障碍,驯化士人便成为科举的一个重要目标。对臣下“君恩深重,涓埃难报”的献媚之语,雍正申斥说:“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15],乾隆为灌输愚忠本朝的观念,不惜贬斥开国有功的降清明臣为“贰臣”①吴敬梓曾祖吴国龙位列《贰臣传》中。。 极开放的选官制度与极顽固反动的思想共存于一体并固化,对于用知识和思想作标准来“分科举人”的选官科举制度而言,显然已经是一种异化,王亚南曾指出:“一个把专制君主顶在头上,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官僚社会,它如何能允许真正选贤任能的考试制度! ”[16](P109)实际上,科举制以前的地方贵族倒是乡绅产生的土壤,后来的乡绅成长则愈益枯竭,士绅之土崩瓦解,八股科举起了关键的作用。
八股制度下,大量举业成功者成为八股游士阶层,他们一再鼓吹八股的价值,鲁编修教导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3](P141)并假此以为学问之衡鉴,他们与真乡绅势若水火,高翰林攻击杜少卿曰:“他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3](P423)鲁编修同样以为“若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3](P130)此辈对八股的信仰实缘于自身的利益所在,王惠对同中进士的荀玫说:“你我都是天榜有名。 将来‘同寅协恭’,多少事业都要同做。 ”[3](P96)他们将儒学通权达变的方法和精神发挥淋漓,成为一群从科场至仕途无不得意的狼奔豕突之士。 一方面,他们将朝廷视为道德与政治权威的来源,参加八股考试,“代圣人立言”,从而获得王冕所说的“荣身之路”;另一方面,合法的“荣身”使其具有了道德的权威,由代圣人说话而变为对圣人的冒充,通过巴结、逢迎,结构种种利益关系,寻找靠山,为自己获得名望及本钱,从而兑现政治与经济的各种利益。 前后比照,不仅衰颓,更是异化。 夏志清认为《儒林外史》的创作是吴敬梓对伪文人和贪官污吏的强烈反对以及他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正直的儒者和孤高的隐士[6](P252)。 面对从八股举业中走出的大小官员们,他们治下的世界已一片灰暗,吴敬梓在小说中痛悼着士绅的式微。
2.经学是人生立命处
基于宗法结构基础上的家族形成及发展与儒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全椒吴氏历来有治经的传统并代有著述[17],吴敬梓《<尚书私学>序》曰:“敬梓自维学殖荒落,顷始有志三百篇。”[18](P37)其经学研究著述《文木山房诗说》则是对《诗经》的研究,从其“少治毛诗”[19]“涉猎群经诸史函”[20],成年后“抱义怀仁,被服名教”[21](P377)来看,经学的研究伴随着吴敬梓的一生,并与其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相互激发。 胡适说:
吴敬梓的时代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八股的气焰忽然又大盛
起来了。[22](P34-36)
庙堂之上的学术趣味及其文化政策的指向多左右学术发展的趋向, 清代学术重心的变化与此关联,从康熙后期经雍正至乾隆前期,程朱理学一尊地位渐趋确立,而后从尊宋转向崇汉,由辞章转向经学考据。 程晋芳云:“(吴敬梓)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也。 ’”[23]在吴敬梓友朋中,程廷祚、程晋芳、沈大成、江昱等都是当时活跃在江南学术圈的士绅,胡适将吴敬梓与程廷祚并举,说他们是“乾嘉经学的先锋”[22](P38),吴敬梓研究经学不盲从朱熹,甚至还有一些不满②参见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第五章第三节《吴敬梓的经学观》,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3](P424),在《尚书私学序》中,吴敬梓说:“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辩论,今文古文之真伪,聚讼无休,究何当于《书》之义理,……斯其卓识,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18](P37),清代统治者以八股、用“朱注”来统一天下士子思想的环境下,吴敬梓的表达别具思想精神。
科举本是官僚政体实现人才纵向流动,打破贵族垄断的有效手段,故近人常把科举制度视为乡绅产生的土壤。 然而,明清时期,由君权左右的八股科举在抑制世家发展的同时,也使君权日趋集中而高高在上,以“试”为选从诗赋至经义,再统于《四书》,最后变成八股制艺,其内容及思想都要求举子们不能自主地表达与思考,遂造成极开放的选官制度与极保守落后的思想共存之悖谬。 迟衡山认为学问与功名之间不必兼而得之,“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3](P599)即针对此。小说中以吴敬梓自身为原型的杜少卿即把经学作为“人生立命”,其“品行端醇,文章典雅”;庄绍光“名满一时”,与杜少卿在学问上惺惺相惜,“闲着无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诗说》,叫娘子坐在傍边,念与他听。 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彼此大笑”[3](P439)。 至于若金东崖辈虽也要“注些经书”,高翰林辈在举业平步青云后也来趋时治经,吴敬梓则充满鄙视,称此辈“于经生制举外,未尝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固其陋。 ”
小说写杜少卿离开家乡来到南京,以泰伯祠大祭为纽带所关联的文人群体,与《移家赋》“乃有青钱学士,白衣尚书,私拟七子,相推六儒”[4](P11-12)对应,他们认真地相信古礼乐的教化作用,是为助政教之“真儒”,小说最后皇帝“下诏旌贤”①实际上,这里与第一回朱元璋拜访王冕的描写,表达出作者对仁政以及统治者与士人之间良好和谐关系的向往。,这些人,吴敬梓寄予了大希望,他们是第一回出现的群星,“维持文运”是吴敬梓的用心处,也是士林中最大的问题所在。
《儒林外史》有经有史,八股取士将道德政治化的负面功能释放,造成道德的妥协和解体,吴敬梓自称“外史”,小说虽然通过世俗世界解构了正史的叙述,却从未放弃基于“经”的价值裁断,使史学所负有的伸张正义,维护道德和信仰的责任得以彰显。 `
3.三部大书的愿景
《儒林外史》描写王玉辉充满悲情与敬意。 王玉辉自称“是个迂拙的人”,徽州府三十年的老秀才,既不涉足仕途,又不教书设馆,依靠有限的廪膳收入艰难度日,却“终日手不停批”,呕心沥血,要纂三部书以嘉惠来学。
王玉辉道:“不瞒世叔说,我生平立的有个志向: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 ”……“礼书是将《三礼》分起类来,如事亲之礼、敬长之礼等类。将经文大书,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教子弟们自幼习学。”……“《字书》是七年识字法。”……“《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的意思。 ”[3](P585-586)
“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24],徽州古郡蕴藉是三部书着的底色,三部大书与泰伯祠大祭意旨相承。 《字书》与《礼书》相互辅助,二者作用相通,《乡约书》则植根于乡土伦理,直接回应宗法社会的现实。 乡约的理想始终吸引无数有志于整顿社会秩序的传统士人,朱熹、王阳明都提倡实行乡约②王阳明《南赣乡约》便是当时及后来人不断仿行的对象。 如果深入观察,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明代心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便是在地方及宗族中推行乡约之类的活动。,吕坤继承王阳明乡约的传统,撰成具有广泛影响的《乡甲约》,实际上,吕坤乡约在包括《儒林外史》等清代的不少小说中得到了响应③吕坤继承袁黄《功过格》的思想,并将其中“彰善纠过”思想作为医治病重社会的药方,(康熙)《全椒县志》卷十记载吴敬梓曾祖辈吴国器“做袁了凡‘功过格’,善否悉记,以自刻励。 ”《镜花缘》第二十四回《唐探花酒楼闻善政 徐公子茶肆叙衷情》描写君子国之理想国度即是乡约中的“彰善规过”思想部分。。
《儒林外史》中,有关王玉辉的《乡约书》并未详列,吴敬梓通过王玉辉,特别是其女儿王三姑娘殉夫入烈女祠故事加以说明,并且将这三部大书的价值思考蕴含其中。 吴敬梓并不回避宗法社会组织、士绅阶层以及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制度之间的错综以及整个群体在集体的喧嚣鼓噪与裹挟之下的异化。 在小说临近结束的五十五回,当王玉辉前往泰伯祠大祭地的南京,周围的朋友已四散而去。 “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 来到门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 两人走进去,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荠菜,大殿上槅子都没了”[3](P671),吴敬梓带着悲情,写出理想与现实的遥远距离,理想社会的变革之路并非通途④《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第671 页。 实际上,这里的泰伯祠、妇人、孩子的象征,鲁迅的《药》未尝不受其营养。,王三姑娘的死以及泰伯祠大祭“劝醒愚民”的作用尚有待时日,吴敬梓看到病症并希图疗救。
吴敬梓将历史的构想与真实相融合,主张以礼为中心,培养并巩固宗法社会中士绅(乡绅)阶层的中坚力量,实现如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建构他的理想国。 这一理想国呼应着宋明以来儒家乡村社会的理想蓝图,更吸引着无数有志于整顿与改革社会秩序的传统士人。
———无锡泰伯墓联